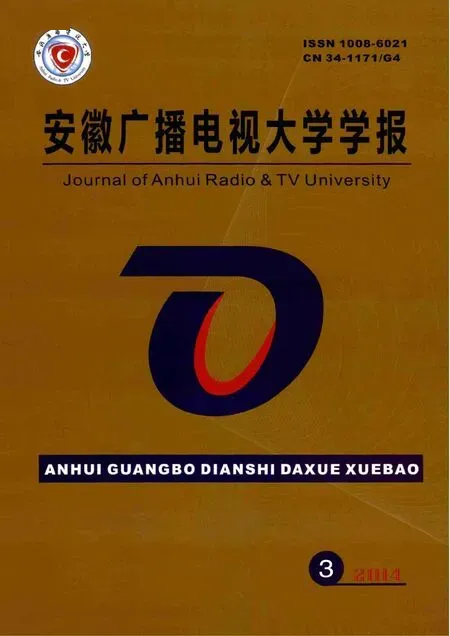《四库全书总目》正史类史学思想管窥
郭淑娴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历来对《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正史类提要的研究比较之多,或者注重研究某一文学体裁,如小说在正史类提要中的地位及评价;或者着眼于正史类目录学方面的研究;或者讨论正史类提要中的考据思想;或者专注于对正史类存目的研究;或者对正史类某一书目提要做辨证纠谬工作;还有一些学者讨论正史类某一部书目的版本流传等等,笔者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总目》史部正史类提要中所体现的史学观略作阐述。
《总目》史部收入正史类书目38部,3 739卷,存目7部,85卷。《总目》史部正史类提要中的史学批评并不像《史通》《文史通义》之类的史学批评之作那样自成体系,而是散见于对各书的具体评论之中,如果我们把这些具体的史学评论加以分析总结,就可以归纳出《总目》正史类提要所体现出的史学思想。
一、强调考证,反对空论
历代史书在流传过程中难免鲁鱼亥豕,史料记载真伪莫辨。倘若依据错误的史料修史,必然以讹传讹,贻误后学。《总目》史部总序云:“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1]乾嘉史家反对盲从前人之说,不加考证,提出了历史考证的史学批评论和方法论。四库馆臣强调记事得实,反对漫无考证。史料的真伪直接关系到史书价值的高低,修史者必须辨析史料,去伪存真,以真实正确的史料写出的史书才能是非分明,褒贬恰当,流传后世。如《总目》在《两汉刊误补遗》一书提要中称赏“仁杰是书,独引据赅洽,考证详晰,元元本本,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其淹通实胜于原书。”[1]403又在裴骃《史记集解》一书提要中评价该书“其所引证,多先儒旧说,张守节正义尝备述所引书目次。然如《国语》多引虞翻注,《孟子》多引刘熙注,《韩诗》多引薛君注,而守节未注于目。知当日援据浩博,守节不能遍数也。”[1]398对裴松之的援据浩博表示赞同。由此可见,《总目》把考证作为评价一部史书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总目》对宋明人著述好议论有着严肃的批评。史部总序里就指责唐宋以来儒生忽视前人对经书所做的解释,而自己随意发挥意义,“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1]397又在正史存目《班马异同评》一书提要中,对倪思妄发议论表示不满:
其点论古书,尤好为谶诡新颖之词。实数百年前预开明末竟陵之派。此书据文义以评得失,尚较为切实。然于显然共见者,往往赘论,而笔削微意,罕所发明。又倪思原书,本较其文之异同。辰翁所评,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底以意断制,无所考证。既非论文,又非论古,未免两无所取。[1]417
此外,《总目》对明人肆意删书也提出了严厉批评。在《史记索隐》提要中指出“漏略殊甚。”[1]399在《史记正义》一书的提要中,“至明代监本,采附集解、索隐之后,更多所删节,失其本旨。”[1]399指出明人监本与旧本相较,脱字多达65处。对于考证严密精细的史学著作则大加褒扬,如 《三国志补注》的提要中,夸赞其“皆参校异同,颇为精核。”[1]404
二、务求精详,重视体例
《总目》在《班马异同》一书的提要中,指出该书对于一些无关文义的字词也要一一列出,“似未免稍伤繁琐”[1]401,又说“既以异同名书,则只字单词,皆不容略。失之过密胜于失之过疏也。”[1]401可见,《总目》对于史学著作的评价,不仅注重考证之实,还强调内容之详细。《总目》对清代汪越所撰《读史记十表》评价很高,尤其对于汪越的著述态度大加赞赏,称“惟此书同时商榷而补之,故考校颇为精密。”[1]400古代许多史书的补正纠谬都是在作者成书之后,由其他学者来对其进行订讹补阙工作的。如先有司马迁作《史记》,后有裴骃《史记集解》、张守节《史记正义》和司马贞的《史记索隐》等书来补充。先有《后汉书》后有《补后汉书年表》十卷。而汪越作《读史记十表》,成书后遍求友人商榷,“仰惟细加推勘,示明纰缪,以便改订,”[1]400可见汪越著书,态度谨严,因而《总目》对其表示赞赏。但同时,提要也看到了过分追求精细考证的弊端,“越等排比旧文,勾稽微义。虽其间一笔一削,务以春秋书法求之,未免或失之凿,而订讹贬漏,所得为多。”[1]400对汪越过分勾稽微义有所微词,但仍然对其精细的考校态度表示赞扬,认为得大于失。
《总目》特别提倡史家博采史料,征引富赡。对于那些内容求全求备,俱不缺漏的著作都给予了正面评价,提倡一书的提要应做到丰富详瞻,认为内容的充实有助于考证之学。在薛居正所著的《旧五代史》提要中,认为薛史虽然文采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又何可使隐没不彰哉。”[1]411将其保留下来,并且对欧阳修《新五代史记》有所批评:“盖修所作,皆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记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1]411对欧阳修著史掺入己意和记载事件不够详备表示不满,认为薛居正所作史书虽然有文法烦冗,词语不工之弊,但是“遗闻琐事,反借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1]411由此可推知,在提要作者眼里,史家之著述,其核心在于征实详尽,以备后世考证之资,而对于史书的文采则并不做过多要求。四库馆臣强调史家能否广泛采摭史料的标准,认识到史料在史学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表现出注重史学求真的史学批评特征。
《总目》对史书进行评价时,也非常重视体例的严谨、合理与否,主张辨析体例,评骘书法,特别强调史家修史体例应当前后划一,史法周密谨严。对那些体例精当、有所创新的著作大加赞赏,如《班马异同》一书的提要:“特棐所列者,一人之异同,思所列者两人之异同,遂为创例耳。”[1]401欧阳棐编撰《集古录》跋尾时,使真迹与旧本并存,以便后来读者阅读之时能够对编者删改之意一目了然,倪思继承了欧阳棐的做法又有所创新。因此《总目》对倪思的做法表示赞美,而对一些体例不纯的著作则会有所批评。如指责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不纯,有碍史法,批评熊方《三国志》“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为例不纯。”[1]401在四库馆臣看来,如果史家不讲究史法,就会造成史书体例不纯结果记事混乱无定,影响史书质量。因此,史书体例必须纯粹,史家史法必须谨严,史著才有学术价值。
三、贬抑嗜奇,褒扬厚博
与《总目》强调考证务实相一致,四库馆臣对史书中的猎奇述远之作有所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学成就不容小觑,然而在《史记》提要中,只简单地交代了司马迁本人,考证了禇少孙的情况,对该书进行了辨伪和版本介绍,对于《史记》的价值却一字未提,而在后面清邵泰衢所著的《史记疑问》一书提要中对《史记》颇有指责:“史记采众说以成书,征引浩博,不免抵牾。班固尝议其宗旨之乖,刘知几颇摘其体例之谬。”[1]400考刘知几《史通·杂说第七》:
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如曹、干两氏《纪》,孙、檀二《阳秋》,则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若以古方今,当然则知史公亦同其失矣。[2]
由此可见,《总目》对司马迁的尚奇是持否定态度的。究其原因,编修《四库全书》的时代,朴学极为兴盛,而在汉武帝时代,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道家等思想仍然存留在读书人的血液里,淮南王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一书思想就颇为驳杂,司马迁本人思想也是博采众家,《史记》中收录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将儒家顺序排列在阴阳家之后,评价儒家思想为“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3]正如班固所批评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先黄老而后六经。”[4]这一点是不受清代官方思想所欢迎的。并且,司马迁所著《史记》有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而汉学讲求客观性,追求学问的广博,是排斥感情的。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总目》并未对《史记》大加赞扬的原因之一。在《汉书》提要中,批评李延寿所著《南史》把刘之遴所得《汉书》真本一事记载下来为“爱奇嗜博,茫无裁断矣。”[1]401在《晋书》提要中,批评其“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1]405即批评《晋书》忽视从正统典籍里取材料,而大量搜集街谈巷语不入流的小说,这里也可以看出《总目》的编纂者努力弘扬正统,贬斥任何与之相对抗的思想,因为小说大多来自底层民间,必然会有很多不符合上层思想之处,因此《总目》对《晋书》在这一点上持批评态度。在馆臣眼里,好奇会使史书内容芜杂混乱,缺乏史书应有的严谨性。因此,《总目》对那些有着猎奇倾向的史书持否定态度。
需要注意的是,正史类提要中也常推崇那些内容丰厚博大之作,这是否与嗜博爱奇相矛盾呢?其实不然。四库馆臣并不反对广博,在汪越《读史记十表》一书提要中,虽然对汪越过于精细的考究有所微词,但终究考据的广博可以忽略这一缺点,认为此书瑕不掩瑜。可见,馆臣并非反对广博本身,他反对的是爱好搜集那些有着奇异色彩的、不合儒家正统观念的,或者说,凡是不符合官方的思想的,不入当时所谓的大雅之堂的奇异材料,四库一律贬斥,即反对奇博。因此《晋书》里的街谈巷语,《史记》里充满神奇色彩的文学性想象必然会受到批评。
四、反对废表,推崇实录
《总目》认为表是一部优秀的史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汪越《读史记十表》一书提要中,提到“考史家之难,在于表志。而表文经纬相牵,或连或断,可以考证,而不可以诵读,学者往往不观。刘知几考证史例,至为详悉,而《史通》已有废表之论,则其他可知。”[1]403批评后世学者对表志的意义不够重视。考《史通》废表之论,出现于内篇《表历》第七:
观马迁《史记》则不然矣。夫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2]123
然而刘知几又赞扬司马迁的创表之功:
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宼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贤愚,激扬善恶为务尔。既非国家递袭,禄位相承,而以复界重行,狭书细字,比于他表,殆非其类欤!盖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吝而不去,则宜以志名篇。”[2]916
刘知几批评班固的《古今人表》,指出应该废人表,代以志。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刘知几本人对表的态度存在矛盾之处。他虽然扬言要废表,但对司马迁所创之表还是有所称赞的,他要求废除那些类似于班固所作之表,认为班氏的人表唯以品评贤愚、激扬善恶为务,是不可取的,他心目中表的功能是用来记载国家的第相世袭的,以方便读者熟悉史实,认为弘扬道德不属于表的职责范围。《总目》没有看到《史通》对表所持肯定态度的一面。
表在史书中的确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司马迁在创作《史记》之时,列十表八书,以排列诸侯国之间军政大事,班固后来所作《汉书》也继承了《史记》这一体例,列八表十志。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云:“朱鹤龄曰,太史公史记帝纪之后,即有十表、八书。表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书以纪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书为志,而年表视史记加详焉。”[5]又说“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5]1446表的功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补后汉书年表》一书的提要中,引《梁书·王僧虔传》称司马迁所创十表“旁行斜上,体仿周谱,盖三代之遗法也。”[1]402批评范晔的《后汉书》,“独阙斯制,遂使东京典故,散缀于纪传之内,不能丝联绳贯,开帜釐然。”[1]402称赞熊方所作是书“贯穿钩考,极为精详。纲目条章,亦俱灿然有法。”[1]402《总目》极力推崇表对史书的意义,可谓慧眼独具。
《总目》正史类提要还极为推崇史书的实录精神。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高度赞扬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评价其“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2738《总目》把实录作为评判史书优秀与否的标准之一,在对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提要中,评论道:“终以三皇本纪,自为之注,亦未合阙疑传信之意也。”[1]399这是对孔子《论语·为政》篇里“多闻阙疑”思想的继承。在后面的《南齐书》提要中说:“今裒合诸本,参核异同,正其灼然可知者。其或无考,则从阙疑之意焉。”[1]406认为史家著书应当实事求是,尊重事实,不能主观臆断。
《总目》评论历代正史类史书之得失,所表达出的以上史学思想,最终可以归结到一点,实事求是,务求考证。这是当时经世致用价值观的体现,正如白寿彝《中国史学史》里所评价的,“它奠定了无征不信的史学法门”,[6]“倡导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6]386《总目》所体现的经世观念,显然受到了明清时期澎湃的实学思潮影响。实学思潮对于明清史学的影响,就是使史学经世致用的重心,从宋代以来的“主于道”逐渐转向“主于事”,或者说从侧重内圣的经世路线转向侧重外王的经世路线。在这一思想观念的指引下,清代四库馆臣在正史类提要的编纂中,倡导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考据与经世相互统一的治史原则,这是清代乾嘉时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独特形式。它成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与清末龚自珍、魏源经世致用思想之间的重要环节,在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 〔清〕永瑢.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7:397.
[2] 〔唐〕刘知几.史通新校注[M].赵吕甫,校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0:899.
[3] 〔汉〕司马迁.史记[M].〔宋〕裴 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3289.
[4] 〔汉〕班 固.汉书[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2738.
[5] 〔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清〕黄汝成,集.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446.
[6]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5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