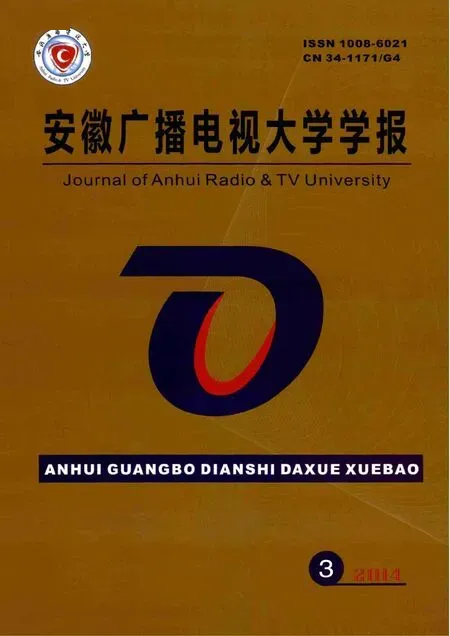“十七年电影”政治形态文艺学发轫与《武训传》再考
尹 兴
(西南科技大学 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众所周知,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分析理论中,既不乏“集体潜意识”的弗洛伊德原理,也蕴含着对“集体表象”做唯物主义诠释的马克思主义基因。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观点:社会化叙事及其神话表征并非由个人冲突构建,而是社会冲突创建的某种潜抑的“无意识”。一如布里恩·汉德森所强调:“神话所起的作用正是使人们从识别与解决实际问题上转移开来。最后,神话的作用——其出自实际冲突的建构与其对接受者的冲击力——始终联系着讲述神话的时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时代。”[1]对于“十七年电影”发轫之作《武训传》诞生的年头而言,1950年正是这样一个微妙暧昧的年头。不难理解,影片叙事修辞策略困境并非源自它所讲述的时代(昏聩腐朽的清末),而是作为某种特定意识形态实践的影片始终联系的时代语境(除旧布新的新中国)。
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实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观众无意识幻觉所投射的,无疑是以民族寓言形式为表征的高度政治介入。作为“十七年电影”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武训传》有助于我们理会“十七年电影”的政治修辞表述。其独特的叙事肌理和文本结构、所紧密联系的“十七年”特殊社会政治语境,都需要我们借助大历史的视野,去除误读、重启对话。
一、繁复与超载的历史语境
《武训传》缘起陶行知,筹拍于1944年春夏之交。武训是中国近代史上德高望重的平民教育家,自幼丧父,随母乞讨,因为目不识丁而饱受欺辱。1944年夏,在接到陶行知先生的《武训先生画传》后,孙瑜导演开始筹拍《武训传》。1948年3月,南京国防部“中国电影制片厂”正式在北京选择外景地,开拍《武训传》。当时的新闻舆论对电影十分关注,美国华人协会主办的《唐人博览报》就此评论道:“这是提倡识字运动,普及乡村教育的推动力。”但当影片开拍后不久,因经费拮据,加之险峻的政治局势,被迫停机。孙瑜导演为此曾感叹道:“1949年1月,上海昆仑公司买过来了《武训传》的摄制权和已摄成全片三分之一的胶片;可是不久后几位重要演员又南北分弛地走向北京和台湾!”[2]潜抑不住的忧郁中,分明预示着影片的多舛与颠沛。
作为一部于新旧时代交替间辗转生成的影片,《武训传》在1951年2月正式拍成之前,单是剧本就因为政治形势作了三次大改。①第一次修改在1949年7月第一届文代会期间,依据周恩来总理和一些电影名家的意见,“改‘正剧’为‘悲剧’”。第二次修改依据“上海电影事业管理处”的建议:“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但武训艰苦兴学,热忱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热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因此建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的场面,找一新的小学教师出来说话,以结合现实,又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第三次修改是迫于经济压力,昆仑公司发不出工资,要求孙瑜将影片拍成上下两集,添加一些丰富原剧本人物形象和深化主题的情节。[3]《武训传》的被述年代②依据周扬的说法:“清廷准给武训‘乐善好施’字样,作为旌奖,是在一八八八年,正是太平天国之后二十四年,辛亥革命之前二十三年,那是封建秩序遭受了农民大革命浪潮的冲击,正迅速地开始瓦解,而农民大革命正成了迎接历史新时代的先声。”[4]——满清末年本身就是一个颇为尴尬的年代。按照某类心照不宣的惯例,影片的叙事主题必须在一个高潮迭起,“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完胜中告结束。因此,原剧本开头“老布贩”在武训出殡之日告劝孙儿好好习文的故事,被顺理成章地改编为武家庄小学“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上,“人民女教师”黄宗英一番慷慨激昂的训诫。如果抛开现实主义艺术中所谓“历史真实”,将《武训传》单独作为完整的电影文本来看,影片的开头结尾显然暴露出政治形态文艺学的生硬、超载与繁复。而颇为吊诡的是,恰是这种繁复与超载成为众矢之的:“电影《武训传》是用艺术的手段巧妙地宣称了反动思想,捏造历史、掩盖真相、在艺术上极尽粉饰和欺骗之能事,它完全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从思想到手法饱含有美国电影很深的毒害……根据可靠的资料,我们知道孙瑜先生和昆仑公司是准备到恰当时机,便剪掉影片头尾空讲‘为人民服务’的部分,其他原封不动,就送到美国去发行上演的。”[5]影片的主要被叙人物武训——一个“庄稼人”“要饭的”,众多批评中所谓“对封建统治的幻想、哀求与等待种种没有骨气的行为代替了历史上真正为革命奋斗牺牲的英雄们的典型事迹,思想实质是投降主义。”[6]武训“乞讨兴学”的故事显然无法成功参阅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尽管影片已然极尽一切可能,运用多种修辞和叙事手段来遮蔽或者填充种种先天不足:私塾老师翘胡子瞪眼的夸张特写:“哼!你也配念书?滚出去!”小武训在众人的嘲笑声中被撵出私塾大门;张举人的爪牙来破庙拖走小桃,狂殴武训,此时天公震怒,狂风骤起,暴雨袭来,武训在凄风苦雨中艰难爬行,凄厉的惨叫回荡于旷野:报仇,我要报仇!……;稍显夸张的平行蒙太奇镜头组合中,衣衫褴褛的灾民嗷嗷待哺,张举人一众却在院中觥筹交错、赏花饮酒;武训拒绝下跪接受御赐黄马褂,发癫似的在地上狂笑乱滚,扰乱“庄严”的盛典;俯拍镜头中周大率领响马风驰电掣地飞奔过武训,阵阵黄尘汇成颇为壮观的革命表象:“将来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不难理解,如此明显的文本裂隙多少源于政治历史语境的必然驱力。《武训》的被述年代(昏聩腐朽的清末)无法为孙瑜导演提供充分的叙事闭锁;与此同时,“阶级斗争”的理念、无产阶级的凯旋胜利也未必为有着留美背景的导演所全然接纳。影片无法拼凑出一幅无产者领导下农民革命斗争彻底胜利的壮丽图景,只能呈现周大作为太平义军“残匪”的彷徨与无助。换而言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权威话语不仅无法充分表述,观众认可的精神力量与“真实感”反而来自武训的人格魅力与明理的士绅。参照20世纪50年代除旧布新的必然历史趋势,对旧时代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潜意识”范本,《武训》的受批似乎有着某种先在的必然。而对武训人格魅力的渲染,无形中又有对来自旧时代教育家陶行知“粉饰”之嫌。批判《武训传》无疑是一次对糊涂思想的“成功”肃清,重构唯一正确的文艺路线与文艺观——“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以及“无产阶级文艺观”。“无产阶级文艺观”权威话语的有效塑造,也因而成为“十七年电影”政治形态文艺学的重要政治历史文化语境。
二、缝合与混搭的叙事困境
“‘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规定与使命,决定了十七年的艺术必须在对社会现实的表述与触摸中完成其意识形态实践;同时,也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的铭文必须是中心构置,而不是中心偏移的。”[7]《武训传》出品的1951年,作为两个意识形态迥异时代的转折过渡点,反差巨大的政治需要不仅将《武训传》置于繁复超载的历史语境,更使影片中的武训形象脱离本身单纯的内涵所指,最终陷于缝合混搭的叙事泥沼。
作为新政权建立和巩固的关键年代,“从1951年秋到1952年夏季的反对腐化干部的‘三反’运动、针对那时为止受到尊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和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得极为激烈,并引起社会上的严重紧张和忧虑。”①该书认为,各种各样的措施对知识阶层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压力,不但形成一种不信任气氛,破坏了已建立的个人关系,而且导致约70万人自杀。[8]新政权的领导人意识到保持高度警戒的必要性,既是基于国民党势力重返内地的可能性,也同时为韩战中美国进攻的潜在威胁所激发。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由是观之,“主要的知识分子珍视独立思考,抵制强加给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约束”[8],统治阶级与知识精英的激烈矛盾无法遏制。
《武训传》所描画的清朝末年,是一个悲凉多于慷慨的乱世之秋。九死一生的武训立誓走上兴义学的苦行之途,为影片确立了一个“圣雄甘地”式、“中国特色”经典民间传奇的叙事格局。从当时影片所诞生的特殊社会历史语境(20世纪50年代初期)来看,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前史,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光辉远未及投射的混沌时代,武训的登场注定会是一个在妥协与反抗中辗转的尴尬角色。以下问题自然成为无法调和解决的悖论:武训的义学除了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能否解救穷人?武训带有落后愚昧封建局限性的“奇行苦操”,是否更似效忠皇权统治的奴才?他不同周大参加农民革命,是否可以当作反对农民暴动的“反动改良派”?对这部电影而言,“诋毁农民革命”“诋毁历史”“丑化中华民族”的反现实主义毒草这样的帽子,看似愈发名至实归。如何理解武训带有个人幻想式的自发抗争,成为理解整部影片,乃至其后“武训大批判”的重要途径。
毋庸讳言,《武训传》全篇的“低调叙事设置”显而易见。在“神话所讲述的年代”中,武训隐忍节制、对于苦难近乎极限的忍耐,无疑是导演所弘扬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与之相对,其同时所表征出来的对于仇恨的没齿不忘以及积极的复仇形态自然相形见绌(这正是当时批评的焦点所在)。殊不知,阶级斗争与阶级仇恨的电影语态即将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唯一绝对的核心话语,在繁复的历史语境中发挥意识形态功效。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希望以凝聚统一的思想文化捍卫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塑造增强共产党的权威感。早在1947年12月21日,毛泽东即明确提出“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之观点;[9]到1951年11月23日,毛泽东又要求文艺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学习、思想改造运动。[10]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于电影业特殊的关注,自然让留学美国、具有浓厚商业文化传统的导演孙瑜无所适从:“由于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文化观念,电影也可以十分准确地区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两种形态;同样,由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是倾向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电影还是倾向于以苏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电影,就成为衡量一个电影工作者甚至一个电影观众的立场正确与否的关键。而在这一点上,又可以将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划定为受好莱坞商业电影影响的‘落后电影’与受苏联电影及左翼电影人影响的‘进步’电影”。[11]
三、《武训传》与“十七年电影”政治形态文艺学发轫
源于1951年社会政治的历史需要,作为现象级电影的《武训传》在意识形态的表征中体现为传统文化意识形态、西方好莱坞商业文化传统、中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互倚重和彼此融合。不言而喻,这样的三重融合不仅无法和谐共生,反而只会呈现出巨大的潜在张力。影像的直观性和传播的迅捷与当局重现历史文化之像,藉希望以之完成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完美解决不无抵牾。“武训在凄风苦雨中艰难爬行,凄厉的惨叫回荡于旷野:报仇,我要报仇!让孩子们当上文官,与他们斗!”(文斗)话语层面上潜抑不住批评者所谓“封建意味”的梦想,而周大夜读《水浒》,率领众响马风驰电掣地袭击张举人,阵阵黄尘汇成颇为壮观的革命表象:“将来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武斗),又难免不被贴上丑化农民革命,革命思想狭隘局限的标签。探究电影文本《武训传》,梳理对其声势浩大的电影批评,无疑是反思“十七年电影”政治形态文艺学发轫的重要途径。其一,以《武训传》为肇始,“十七年电影”政治形态文艺学对儒学传统是否存在断裂?其二,滥觞于“延安道路”的文艺政治学,是否因当局对于电影的特别关注而强化乃至激化?其三,摒弃好莱坞商业文化传统,植入俄苏文艺情结的“十七年电影”政治形态文艺学,在范式上究竟归属何种新兴“工农兵文艺”?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撰文《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武训传》展开极其严厉的批评:“用革命的农民战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战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12]毛泽东悬置“神话所讲述的年代”,聚焦于“叙述神话的年代”,深挖影片所潜藏的深层“症候”,从作品中解读出有人对新生政权的不满和敌对,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不屑和抗拒。这种政治形态文艺学范式可以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七人影评”对于影片《国魂》的批判,都是认定“在表面的叙事下,隐藏着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射,影评的关键是要挖掘这种影射的深层含义,将其放置在现实环境中,给以政治定性,指出作者隐晦的政治动机,进行严厉批判,并归纳批判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13]对于《武训传》的批判,成为十七年“行政主导电影理论”的肇始。从1951年开始,全国电影主管部门除了制订电影政策、拟定电影出品计划、明确电影类型题材比例之外,还在电影的艺术风格、拍摄技巧等诸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统筹管理,最终形成“电影艺术理论与行政一体化”的学术体制。
1951年11月24日,周扬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做了《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的讲话。胡乔木以《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为题发表讲演,认为:“关于《武训传》的批评,并不是任何一个文学艺术团体发起的,而是中共中央发起的。要以工人阶级的文学艺术观去批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观。文学艺术界的出路在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与工农兵群众结合;充分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批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整顿文艺事业的领导、团体、文艺出版物;文艺工作者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模范。”[14]11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的正式决议。“十七年电影政治形态文艺学”以批判《武训传》发轫,直接影响着稍后“文革”时期的“政治修辞学”电影理论。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电影理念的探讨,实为考验人们政治立场的核心权威话语和试金石。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艺术理论与行政一体化”学术体制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语境。新中国成立后,史东山、陈波儿、袁牧之、夏衍、阳翰笙等“又红又专”的电影人身兼艺术权威与行政权威。“这有利于建立一种从战争体制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电影体制转化的制度,他们既拥有行政领导权力,又有关于电影知识的阐释权力,具备电影艺术家、理论批评家和电影事业家三种身份,有资格参与到稳固的权力结构中,协调艺术与政治、实践与理论、创作与行政管理诸多关系。”①1949年4月“中央电影局”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改属文化部领导,首任局长由著名导演袁牧之担任。1949年6月,华北临时影片审查委员会成立,负责审查华北地区旧影片的拷贝。1950年夏,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建立。[15]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等行政机构的成立,为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带来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电影指导委员会’这个由宣传、文艺、统战、工会、教育、新闻等各界高层领导与著名人士多达32人组成的庞大委员会,不但难以集中,活动不便,而且其中某些起实际作用的人(如江青,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16]
由此,新中国电影政治形态文艺学发轫,中国影坛由20世纪40年代多元共存的格局走向文艺“经国”的政治化过程。这上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国防文学”观念的提出(“左联”对唯文学倾向的批评),下延续至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在肯定“延安文艺座谈会”道路的正确性同时,明确“卡理斯玛”和“政治化”的时代诉求。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电影界种种所谓错误观念遭到肃清,“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社会主义文艺观”被奉为唯一合法的文艺观,并且理所当然地构成“十七年电影”政治形态文艺学“单一式”政治语境。作为特定电影意识形态实践的《武训传》批判,影响着“十七年电影”的叙事修辞策略,隐喻着一个全新时代的“风雨渐至”。
[1] 布里恩·汉德森.《搜索者》:一个美国的困境[J].戴锦华,译.当代电影,1990(3):68.
[2] 孙瑜.编导《武训传》[N].光明日报,1951-02-26.
[3] 祁晓萍.香花毒草: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7-9.
[4] 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的批判[N].人民日报,1951-08-08.
[5] 黄钢.从《武训传》讨论中看电影批评工作问题:加强电影批评的严肃性、战斗性和群众性[N].文艺报,1951-05-02.
[6] 陈波尔.从《武训传》谈到电影创作上的几个问题[J].新电影,1951(1):7.
[7] 戴锦华.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18例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97.
[8]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79.
[9] 毛泽东.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26-127.
[10] 毛泽东.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 [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38-139.
[11] 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5.
[12] 毛泽东.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N].人民日报,1951-05-20.
[13] 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89.
[14] 胡乔木.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N].文艺报,1951-05-04.
[15] 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92.
[16] 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