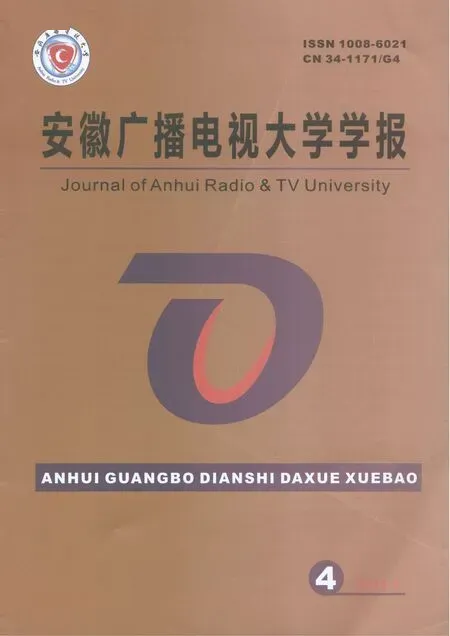“从心所欲,不逾矩”:论穆旦之诗歌翻译
李焕霞,刘卫东
(广西梧州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0)
穆旦一生与诗相伴,所有的作品都是与诗有关,包括自己创作的诗、译诗和谈(译)诗的杂感。因此,前人对穆旦的研究,多从文学角度探讨他的诗歌成就;也有探讨他翻译的成就,如王家新在《穆旦:翻译作为幸存》一文中赞颂了穆旦“以‘翻译的名义’侍奉于他所认同的语言与精神价值,并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宝贵的遗产”。[1]但是,穆旦独特的译诗实践及其相关译论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作为诗人的穆旦,内心遵循着“以诗译诗”之理想标准,实则归属“翻译艺术论”一派。纵观古今中外,翻译艺术论由来已久,正如黄振定教授指出,“西塞罗的翻译观注重对原作思想和风格的全面再现,强调艺术性的创造,与中国译论后起的‘神似’说无异,明显地是一种文艺美学观”。[2]随着语言学的蓬勃发展并开始介入翻译,翻译语言学得到空前发展。而建立独立的“科学化”的翻译学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翻译学的独立身份和地位日益得到承认。但是,与此同时,传统的翻译艺术论观被边缘化。因此,结合诗人穆旦的翻译实践探讨其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为特色的翻译艺术论,对审视当今西方 “科学化”的译论,重申传统翻译艺术论的价值意义深远。
一、“从心所欲”之译介选择
穆旦的译介选择可归结为“从心所欲”,但这个“心”有着特定的含义:一方面是一颗“爱国心”;另一方面是一颗“艺术心”。1953年初,穆旦抱着一颗报效祖国﹑投身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心”从美国学成归来,任教于南开大学外语系。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和文化生活环境里,他由一个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者转向文学译介,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幸存。对于译介素材的选择,首先,由于“爱国心”的驱动,他自觉地选择翻译苏联文学理论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别林斯基论文学》等[3]。通过翻译,穆旦努力让自己与新中国的主流文学观念保持一致,从而获得认同。究其深层原因,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在政治文化方面都采取“一边倒”政策,各方面深受苏联的影响,因此,也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政治上反动、思想上颓废、艺术上是形式主义,是反现实主义的反动文学,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也遭到否定和摈弃。因此,穆旦不可能随意进行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或随意选择对现代主义诗歌的翻译。他的翻译选择只能局限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所允许的领域。
另一方面,穆旦的译介选择也暗合其“艺术心”的倾向。穆旦对普希金、雪莱、拜伦、济慈、布莱克等人诗歌的选择,是当时意识形态所允许和鼓励的,因为他们属于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外国诗人。他的这种选择也是他“为获得出版权利,为赢得主流诗学、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所做的努力”[4]。更重要的是,此类浪漫主义诗人自身的人格魅力及其诗歌的精神价值对于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的穆旦来说,更令他觉得亲切,更暗合他内心深处的“艺术心”。以普希金为例,诗中的“那种流放的命运和对自由的渴望,那种诗人与权贵的对立,也都暗合了他内心中更深处的东西”[1]7。王家新在《穆旦:翻译作为幸存》一文中指出,穆旦所译《致大海》的首句“再见吧,自由的元素”(对此戈宝权的翻译:“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如“没有那种身处逆境而激发的对自由的渴望,没有对人类存在和悲剧性命运的深切体验,他怎么可能以一语道出大海的本质?”[1]7-8穆旦晚年的译诗选择,更突出了他个人“艺术心”的审美倾向。
事实上,即使在文革尚未结束的岁月,穆旦的译诗选择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当时的主流意识,而是体现着他作为学者的自觉、清醒和独立。正如他在和杜运燮的通信中所指出“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读者会看到:原来诗可以如此写。”[5]“我相信中国的新诗如不接受外国影响则弄不出有意思的结果。这种拜伦诗很有用途,可发挥相当影响,不只在形式,尤在内容,即诗思的深度上起作用。”[5]329在那个时代,译介选择既出自“爱国心”的驱动,又能契合其“艺术心”,实属难能可贵。
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翻译境界
“翻译艺术论”的核心便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此言概括了中华传统翻译思想的本质[6]。朱光潜先生把作文比喻成写字,过程可分为“疵境”“稳境”“醇境”“化境”,而“化境”是最高的境界。翻译作为艺术,同理。“从心所欲,不逾矩”,已至“化境”,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正如王秉钦指出“翻译的艺术是‘人为的’,‘创造的’,原作就是翻译所本。翻译只要‘不逾矩’,就可以‘从心所欲’,就可以使翻译达到‘成熟的境界’”[6]185。
穆旦先生遵循的译诗原则在他的《谈译诗问题——并答丁一英先生》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来:1.“字对字、句对句、结构对结构”的翻译原则“并不是他采纳的,也绝不是最好的办法”[5]270;2.“译诗有创造性,亦即在字面上有和原作脱节的自由”[5]275;3.译诗要结合内容和形式。
穆旦的翻译,以极富创造性与艺术匠心的“以诗译诗”著称。他的译诗语言准确、通畅、饱满、富有质感,饱含深情。下面以他翻译雪莱《长逝的时流》的译文为例:
长逝的时流
P.B.雪莱
有如一个死去好友的鬼魂,
呵,长逝的时流。
是一段永远沉寂的乐音,
一片希望,去了不再回首,
如此甜蜜的爱情,但不持久,
这是你,长逝的时流。
有过多少甜蜜的美梦,埋在
长逝的时流中;
不管那是忧愁还是欢快:
每天都向前投下一个幻影
使我们愿望它能够长存——
在长逝的时流中_。
有过悔恨,惋惜,甚至怨责,
怨责长逝的时流。
仿佛一个父亲凝视着
爱子的尸体,直到最后,
美,和记忆一样,漾在心头,
漾自长逝的时流_。
原文:
Time Long Past
by Percy Bysshe Shelley
Like the ghost of a dear friend dead
Is Time long past.
A tone which is now forever fled,
A hope which is now forever past,
A love so sweet it could not last,
Was Time long past.
There were sweet dreams in the night
Of Time long past:
And,was it sadness or delight,
Each day a shadow onward cast
Which made us wish it yet might last——
That Time long past.
There is regret,almost remorse,
For Time long past.
'Tis like a child's belovèd corse
A father watches,till at last
Beauty is like remembrance,cast
From Time long past.
此诗咏叹流逝的时光,是逝去的音符,希望,恋情,无论是欣喜还是悲伤,遗憾还是怨恨,时光每天都在一寸寸地前行,流逝,远去,只有美,铭刻在记忆里,在记忆中复活,回旋,永恒。译文语言娴熟优美,毫无“翻译腔”的生硬痕迹。原诗句"Was Time long past""That Time long past"和"From Time long past"分别被处理为“这是你,长逝的时流”,“在长逝的时流中”和“漾自长逝的时流”,遥相呼应;原句均“一字之别”("Was","That","From"),而译文不拘泥于追求与原文“一丝不走”,将第一句增字活译“这是你,”,可谓“大胆”而“忠实”地传达原作的诗质和精神。所谓“大胆”,是指译者充分发挥创造性,使得“译诗有创造性,亦即在字面上有和原作脱节的自由”,如原诗词句倒装"Tis like a child's belovèd corse/A father watches,till at last",译诗则照顾本国语言使用习惯,灵活调整词句语序为“仿佛一个父亲凝视着/爱子的尸体,直到最后”,使得全诗语气连贯,一气呵成。所谓“忠实”,是指译者能够准确把握原作的诗质和精神,特别是最后句增添一“漾”,可谓一字传神。深谙译事本质的穆旦以其深厚的学识素养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使译文得以精彩呈现。
由此可见,穆旦并没有“死扣字面”,而是灵活创造性地运用汉字去重现和谐而完整的文学作品。换言之,翻译家不是文字的搬运工,译文也不是陈列文字的标本馆。因此,穆旦的译诗,遵循着他自己的翻译理念,恰暗合朱光潜先生的观点“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必是完整的有机体,情感思想和语文风格必融为一体,声音与意义也必欣和无间。所以对原文忠实,不仅是对浮面的字义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同时忠实。”[7]穆旦提出“以诗译诗”的理念,更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艺术论的深化。他指出:
“字对字、句对句、结构对结构”的翻译原则,并不是我在译诗中所要采纳的……译一首诗,如果看不到它的主要实质,看不到整体,只斤斤计较于一字、一词、甚至从头到尾一串字句的“妥贴”,那结果也不见得就是正确的……考察一首译诗,首先要看它把原作的形象或实质是否鲜明地传达了出来;其次要看它被安排在什么形式中。这两部分,说起来是分立的,实则在实践中就是一件事,即怎样结合诗的形式而译出它的内容的问题……诗的内容必须通过它特定的形式传达出来。即使能用流畅的优美的散文把原诗翻译出来,那结果还是并没有传达出它的诗的内容,发挥不了它原有的感人的力量。[8]
可见,“以诗译诗”是翻译诗歌的较高境界。此时,若以简单的“字对字、句对句、结构(句法的)对结构”的所谓译诗原则来对其译文进行挑剔和责难,则可见批评者的狭隘和短见。朱光潜指出:
一个人到达了艺术较高的境界,关于艺术的原理法则无用说也无可说;有可说而且需要说的是在“疵境”与“稳境”。从前古文家有奉“义法”为金科玉律的,也有攻击“义法”论调的。在我个人看,拿“义法”来绳“化境”的文字,固近于痴人说梦;如果一味学文艺始终可以不讲“义法”就未免更误事。[7]107-108
就穆旦的翻译而言,他深厚的学识素养和语言文字驾驭能力已至成熟的艺术境界,似乎不合“义法”,实质已是韩愈所讲的“醇而后肆”的境界。换言之,若以“从心所欲,不逾矩”来解释,化境的译文是译家“从心所欲”地对语言的创造性驾驭,但前提“不逾矩”所依的“义法”是“原作的形象或实质”是否以恰当的“形式”安排,从而完满调和地结合起来,发挥感人的力量。
三、探因穆旦译文艺术境界
解读“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理念时,不能取半截子的话。尤其对于文学翻译,“从心所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译者自身的学识素养和翻译经验,并不是片面地说译者可以根据个人喜恶对原文任意粗暴地删减窜改,而是必须以“不逾矩”为前提条件。文字达到艺术成熟的境界,此乃穆旦译文艺术境界之原因之一。
其次,穆旦译文呈现出的岁月抚育过的成熟胸襟,此乃他译文艺术境界之原因之二。
穆旦的一生,可以用“痛苦出诗人”来概括。因此,要读懂穆旦,首先要理解他所经历的人生苦难。他年少壮志时,参加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战场,九死一生,而这逼近生命极限状态的生存体验,却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诗歌创作灵感。晚年的穆旦,在那个扭曲的时代,遭受了诸多冷遇和不公。一个出于热血壮志保家卫国参加中国远征军奔赴抗日战场,历尽生关死劫的青年,尽管随后生活困顿,但仍坚持写作和学习,并于赴美留学后抱着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学成归国,却在1958年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被剥夺了创作自由近二十年。于是,他只能转向诗歌翻译。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煞有介事地弄翻译,实则是以译诗而收心,否则心无处安放”[8]149。所幸的是,穆旦始终坚守学者的良心,在诗歌翻译领域,耕耘出同样绚丽的花朵。穆旦的译诗,也是他对人生与生命苦难体验的发掘与反思,是他诗才的另一种形式的绽放。这与语言具有体验性密切相关。语言的体验性决定了翻译的经验性。因此,译者的双语水平、学识素养、人生体验、治译态度等都影响着译者对原文的感受程度,最终也影响着译文的输出。其中,译者的个人生命体验影响尤甚。朱光潜先生指出“不但字的艺术成熟了,而且胸襟学间的修养也成熟了,成熟的艺术修养与学问的修养融成一片,于是字不但见出驯熟的手腕,还可以表现高超的人格;悲欢离合的情调,山川风云的姿态,哲学宗教的蕴藉,都可以在无形中流露于字里行间”[7]107-108。
《冬》可以说是晚年的穆旦步入人生的尽头时对人生的体验和思考。以第一节诗为例: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
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
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
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绕着温暖的炉火,
和两三昔日的好友闲谈,
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
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这诗虽以抑郁的“冬”的形象作底色,但是,“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生命的“跳动”,人生的“乐趣”,感情的“热流”,都是这严酷冬天的暖色。正如龙泉明教授指出,饱经苦难的穆旦“仍以一颗宽容的心情包涵世间的粗糙和伤痕,仍然对生活对生命充满热情和关怀”[9]。在翻译《唐璜》时,当拜伦感喟生死无常的时候,译者作出这样唯美的句子:
反正我坟头的青草将悠久地
对夜风叹息,而我的歌早已沉寂
其实,何尝不是译者自身诗魂的声音?一种看穿无常,看透生死后的从容,哲学宗教的蕴藉,已流露于字里行间。宋炳辉认为“晚年的穆旦,虽然历经劫难,但其创作不仅诗艺更趋精湛,而且诗思仍然保持一种精神的力度和厚度,保持了对现实和自我的那种怀疑和超越的穿透力……这是一种悲剧式的充实,一种宿命般的应验,它包含着一种无言的震惊和顽强的抗争,字里行间到底透露出一股逼人的凄凉来”[10]。
译例如下:
靠耕耘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
With the farming of a verse/Make a vineyard of the curse
其实,穆旦的译文语言正映照了他独特而坚韧的品格。呈现出其岁月抚育过的成熟胸襟。耕耘一片“诗田”,将诅咒变为“葡萄园”,以穆旦其身而言,他正是将扭曲而苦难的现实,耕耘为绚丽的译诗。在那个年代,穆旦以诗歌翻译的形式在沉默中挺立,这种强劲而执着的力量,正是他诗才与译才的和谐统一。
四、结 论
穆旦以其丰富的翻译实践阐释了翻译是一门语言艺术。尽管翻译语言有其不可忽视的规律性,翻译理论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对于具体的诗歌翻译,语言学中的“科学”论的指导意义却远不如“艺术”论具有启发性。译诗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指导,译出的诗才有诗味。穆旦翻译诗歌对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坚守,恰恰是最好的阐释。
[1] 王家新.穆旦:翻译作为幸存[J].江汉大学学报,2009(12):5-14.
[2] 黄振定.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47.
[3] 张曼.时代文学语境与穆旦译介择取的特点[J].中国比较文学,2001(4):50.
[4] 商瑞芹.诗魂的再生:查良铮英诗汉译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206.
[5] 李怡.穆旦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331.
[6] 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85.
[7] 朱光潜.谈文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7-108.
[8] 穆旦.穆旦诗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49.
[9] 龙泉明,汪云霞.论穆旦诗歌翻译对其后期创作的影响[J].中山大学学报,2003(4):20.
[10] 宋炳辉.曾经沧海后的超越:试论穆旦的晚年诗作[J].文学报,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