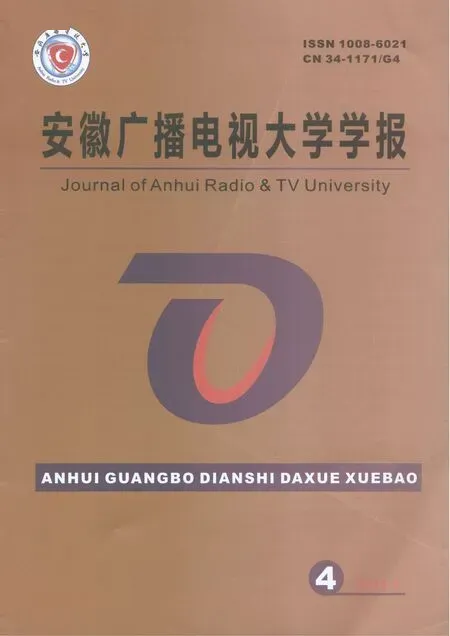《四库总目提要》方志思想述论
董海春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方志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地方性著作,内容丰富庞杂,包括地理,物产,风土,人情,政制,人口等内容。关于方志的发展,今人仓修良先生认为,方志起源于两汉时期的地记,发展于魏晋隋唐,完备于宋元,兴盛于明清。在提及方志的地位和作用时,仓先生又引述了宋人郑兴裔在《广陵志序》的一段话:“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1],可见,方志对于我们了解一地之风土沿革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清朝乾隆时期编纂完成的《四库全书》是对中国古代18世纪以前的基本典籍最大的一次整理。之后刊印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也是古代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对《四库总目提要》的学术价值论述道:“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评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2]因此,集古代文化之大成的《四库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在史部所辑录的都会郡县类中亦会“评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但同时,四库馆臣在品评过程中也体现出自己对于方志编修、体例的认识,这一点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笔者将对《提要》中所辑录的155部都会郡县著作归纳整理,试图总结出馆臣的方志编纂思想,进而窥探当时的学术界主流思想。
一、《四库总目提要》史部都会郡县类概述
我国古代方志的编修工作到了清朝,已经达到了全盛时期,无论是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完备、内容之广泛,都达到了前人未有的新局面。在书目繁多的情况下,如何考证辑录地志著作,四库馆臣在地理类总叙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今惟去泰去甚,择尤雅者录之。凡芜滥之编,皆斥而存目”。都会郡县类共收录155部等方志著作,其中正目共收录47部,2 752卷。存目108部,2 467卷。具体如表1。

表1 《四库总目提要》著录历代方志数量分析表
在47部正目书籍中,清代有22部,宋代有12部,元有6部,明有7部,而存目当中没有收录宋代书籍和元代书籍,但仅明代就收录91部,清代17部。此外,正目中,清代有15部是官方团体编修,有11部是宋代编修的。存目中,清代有15部书籍则是私人编修,明代的91部书籍全是私人编修。由于方志发展尚未成型以及年代久远,四库馆臣并未收集宋以前的方志著作,从正目中,除了清代,宋代的方志数量次之,这也说明了四库馆臣对于宋代方志的推崇,而存目中,明代方志数量之巨,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其方志编修为馆臣所轻视,其原因将在下文中赘述。
二、关于四库馆臣方志编纂思想的述论
从概述中所收录书籍数量的多少及所属目类,我们可以看到四库馆臣对宋代方志的推崇,以及对明代方志的贬斥。因此,我们主要可以通过对这两个朝代所收录相关书籍提要的研究,可以大致归纳出四库馆臣对于方志编纂、体例的几点认识。
(一)对方志叙述简括,征引典核的推崇
宋代统治者采用“重文抑武”的政策,多由文官担任要职。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宋代的学术空气活跃,讲学风气盛行,各地书院林立,各学派之间相互交流和竞争,促进了文学、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繁荣。从史学研究角度来看,宋代史学中整理和编纂当代历史的风气盛行,这与宋朝统治者重视此项工作是分不开的,当时政府不仅设置专门史官负责编修,而且也没有像前朝那样禁止私人修史。许多学者纷纷加入修史的行列中,例如范成大,陈耆卿,高似孙等文人,这样一批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加入,注重考证,讲究用语,因此势必会对当时史志乃至方志文体的用语、体例、文学性等产生影响。这样私人修史便从文与质上,得到空前繁荣,而这种私人性质的史志在一定程度上与官方正史互为佐证,为人们编修方志时提供了可供典核的基础。
与此同时,宋代的方志作者也已经注意到了这种作品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他们强调要有益于政事,有补于风教。宋人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就明确提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余奉简书,自庐移守兹土,表章先哲,利赖兆民,日求康治,而文献无征,心窍悼焉。”[3]在序言中,郑氏将方志视为国史,以“察民风,验土俗”,这样,宋代方志作者将方志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更加重视方志的真实性。因此,当时的作者在内容上除了沿革前代的地理山川书写外,又从史志中采用了更多真实可考的人文性内容。
在《提要》正目中,无论从提要的内容,还是从所收书目的数量来看,四库馆臣都特别推崇宋代方志的体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称《新安志》“叙述简括,引据亦极典核。”又称《延祐四明志》“志中考核精审,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而对征引繁富,冗杂的方志,则斥为存目。如称清书《杞纪》“既于《系年》录《春秋》经文之载杞事者,复为《年表》《世次》《系家》,不几于叠床架屋乎?且又全录《春秋》经传及《经传别解》为四卷,不更赘乎?于《遗书》录《夏小正》,于《人物》收姮娥,其泛滥抑又甚矣。”又将“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於总集”的书目,列为存目。
(二)对方志体例多样,编纂规范的推崇
方志的编修始于两汉时期,经过不断的发展到了宋朝时期,体例基本定型,而到了清代时期,达到了全盛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方志体例由最初的仅记录山水地理,发展为隋唐时以图经形式记录地理地貌,到了宋朝以记人述地并重,到了元朝,又增加记录国家地理的体裁“一统志”。明代则增加了凡例等说明性文字,到了清朝,承袭前代,种类、数量、内容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与四库馆臣同时代的学者章学诚在总结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对“志”的体例和内容做出了总结性概括,他认为,除了“志”外,志书还可具体分为“纪、传、书(考)、表图”等四种。“纪”是指按年编写的大事记。“方志撰纪,只是以为一书之经”这样做亦在于“存史法也”。因为“志者,史所取材,史以记事,非编年弗为纲也”,[4]“传”是指“邑志列传,全用史例”,它记录人物事迹,在方志中可以“纬本纪未尽之宜”。[4]805(《文史通义》中《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书(考)”则是“考之为体,乃仿书志而作,……综核典章,包函甚广”。[4]826(《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而“表图”作用则可使“文省事明”。
按照章氏的上述分类方法,我们可以更加有条理的将四库中的书籍做出类似分类,“纪类”有《历代帝王宅京记》《赤城会通记》《雍大记》《金陵世纪》《北地纪》《括苍汇纪》《杞纪》《台湾纪略》《澳门记略》等9部。“书(考)类”有《钦定日下旧闻考》《钦定满洲源流考》《金陵古今图考》《闽书》等4部,“表图”类有《吴郡图经续记》《岭海舆图》《三郡图说》《岳郡图说》《海盐县图经》《嘉兴府图记》等6部,“志”类有126部,其他体例有10部,如《剡录》《齐乘》《滇略》等。因此,四库馆臣如实地记录整理了前人的方志,并没有以己见以偏概全,体现了他们对于方志体例多样性的重视和公正客观的学术态度。
此外,馆臣在重视方志体例多样性的同时,亦在《提要》中为各种体例的撰写方式提供了相应参考。首先,他们明确提出门目要条分缕析,如称赞宋朝施宿《嘉泰会稽志》“所分门类,不用以纲统目之例,但各以细目标题”,从而“不漏不支,述次有法。”又称赞《延祐四明志》“条例简明,最有体要”,“志中考核精审,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而反对方志冗杂毫无体例,如存目中《万历信阳州志》“序次冗杂,殊乖体要”。其次,四库馆臣亦列举了方志编修上具有示范性的书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如,称赞《淳熙三山志》“然其《志》主于纪录掌故,而不在夸耀乡贤,侈陈名胜,固亦核实之道,自成志乘之一体,未可以常例绳也。其所纪十国之事,多有史籍所遗者,亦足资考证。视后来何乔远《闽书》之类,门目猥杂,徒溷耳目者,其相去远矣。”可见《三山志》为方志中掌故的写法提供了范本。又如,在方志中“纪人物”“纪山水”的创作方法上,馆臣又称赞高似孙的《剡录》“其先贤传,每事必注其所据之书,可为地志纪人物之法。其山水记,仿郦道元《水经注》例,脉络井然,而风景如睹,亦可为地志纪山水之法。统核全书,皆叙述有法,简洁古雅,迥在后来武功诸志之上”,不仅在单独一本书的编修上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在对原书的补修上,馆臣也找到了参考的样本。以原书《嘉泰会稽志》及其后来补充修撰的《宝庆续志》为例,称赞《宝庆续志》“复于前志内补其遗逸,广其疏略,正其讹误”,又“所分门类,不用以纲统目之例,但各以细目标题。前志为目一百十七,续志为目五十。不漏不支,叙次有法。如姓氏、送迎、古第宅、古器物、求遗书、藏书诸条,皆他志所弗详,宿独能蒐采辑比,使条理秩然。淏所续亦简核不苟,皆地志中之有体要者。”因此,四库馆臣特别推崇修志时重视考证,并提倡在后来的续志中能够继承前志好的做法,又能补其遗逸,正其讹误。
(三)对方志贯通古今,空发议论的批评
明代时,学者好空谈心性,不肯做切实的学问,专门空谈理论。虽然不读书,但是喜欢著书。在这种学术氛围下,明人在编修方志时,大多喜欢贯通古今,不切实际,导致对前人的著作既不考证,自己修的方志也没有多大价值。对于这种现象,清人阮元在《道光重修仪征志序》中就提出了批评:“明代事不师古,修志者多炫异居功,或蹈袭前人而攘善掠美,或弁髦载籍而轻改妄删,由是新志甫成,旧志遂废,而古法不复讲也”[5]明朝修志者为了“炫异居功”,对前人成果毫不尊重,对其任意删改剽窃,将东拼西凑的内容统统为己所用,而没有对乡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
而有清一代,由于政治文化上的禁锢和管制,清代学者一改前朝学术弊端,重视考据,讲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求证方法,力排无稽之谈。而拥有当时主流知识话语权的四库馆臣自然也会在《提要》的编辑过程中,大加鞭伐这种“芜滥之编”,无稽之谈。如正目,《吴兴备志》提要“(董斯张)虽意主博奥,不无以泛滥为嫌。然当时著书家影响附会之谈,剽窃挦撦之习,实能一举而空之。故所摘录,类皆典雅确核,足资考据。”四库馆臣在这里指出了当时作家著书中的攀谈附会,任意删改剽窃,挦章撦句的陋习,而提出了著书“典雅确核”的主张,而在存目中,四库馆臣对于这种空谈附会的批判更加激烈。如《嘉靖河间府志》提要“其体例颇谨严。而采掇古事,不免贪多;假借附会,均所不免。仍不出明人地志之积习也。”这里明确地指出了明代人编修方志的弊病:多採古事,事不师古,贪多附会,企图贯通古今。又如《万历江都县志》提要“而以史法变其体例。曰《纪》,曰《表》,曰《志》,曰《传》。《纪》之目一,《表》之目五,《志》之目七,《传》之目十。夫史之有纪,为帝王作也,称之一邑则僭矣。”四库馆臣对于这种用史志的写法编修方志的做法极力排斥,认为将用于记录帝王的“纪”而用在郡邑的创作上,这会造成了文体体裁的混乱。从上述所列提要,及存目中所收录的大量明代方志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库馆臣对于方志贯通古今,空发议论做法的批评,此外,我们亦可以看出馆臣对于明代修志者的批评,这也是从一个侧面窥探出明清两代学术之不同。
三考据学对四库馆臣方志思想的影响
《四库全书》修纂于乾嘉时期,而这个时期清代学术继承了汉代经师郑玄等人所倡导的朴实考据学风,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乾嘉学派。该学派重视考据,其研究侧重于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对、音韵训诂等,强调“实事求是、博瞻贯通、无征不信”,其治学方法为“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6]而四库馆臣中聚集了一大批乾嘉学派学者,于是在《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的编纂过程中,也能够体现出他们重视考据的学术思想,具体到对一本方志的评定上,是否有严密可靠的考据,成为评价一本书优劣的标准之一。例如,存目中《雍大记》提要“景明广事蒐采,意欲突过前人,而嗜博务多。如历代史赞之类,概为收入,未免氾滥。又文字多摹古而失真,……名目皆出臆创。几于鶠阁虬户,筿骖铣溪。七子末派,为世所诟厉,亦有由矣。”四库馆臣除了在提要中贬斥那些不重考据的志书之外,也在编写过程中通过方志对史书进行了考证,一则如《景定严州续志》提要“其户口门中载宁宗杨皇后为严人,而乡会门中亦载主集者为新安郡王、永宁郡王。新安者杨谷,永宁者杨石,皆后兄杨次山之子也。而《宋史》乃云后会稽人,当必有误。此可订史传之讹矣。”四库馆臣通过《景定严州续志》的记载判定了史书的错误。除了对史书的他校以外,又按照对内容详实的考证来判定书籍的所属门类,如《澉水志》提要中的案语:“澉水虽见《水经注》,然是书乃志地,非志水,不可入之山水中。以镇亦郡县之分区,故附缀於《都会郡县类》焉。”如果按书名来划分的话,《澉水志》应该归入史部河渠类,但经考证之后,将其归入都会郡县类,可以说是“归于至当”,这也体现了四库馆臣实事求是的考证态度。
四、结束语
《四库全书》是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向我们展示了丰富灿烂的中国文化。《四库总目提要》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浓缩,通过对他们的整理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古代文化、科学、艺术的发展过程。四库馆臣通过对史部地理类中都会郡县的整理,为我们展现了古代方志的变化,体例由简单到完备,内容由单独记载地理到记人述地。也为我们展现了各种体例的优秀范本。他们在整理裁夺的过程中,也体现了他们对于方志的认识,推崇语言简赅,考证有据,反对贯通古今,贪多赘述,空发议论。而这也体现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思想,重视考据,实事求是。但是,四库馆臣在重视考据的时候,其方志思想过于狭窄,过于好古,过于重视考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方志内容上的发展扩充,同时期的章学诚在其基础上,提倡将方志融入人文性的内容,这使方志的编修得以完善和定型。对四库馆臣的方志思想的研究,这有助于我们对于方志学科理论的认识和建设。
[1]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 [M].济南:齐鲁书社,1990:263.
[2]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45.
[3] 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 [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191.
[4]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5:901.
[5] 王检.道光重修仪征县志 [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
[6] 顾炎武.日知录校注 [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