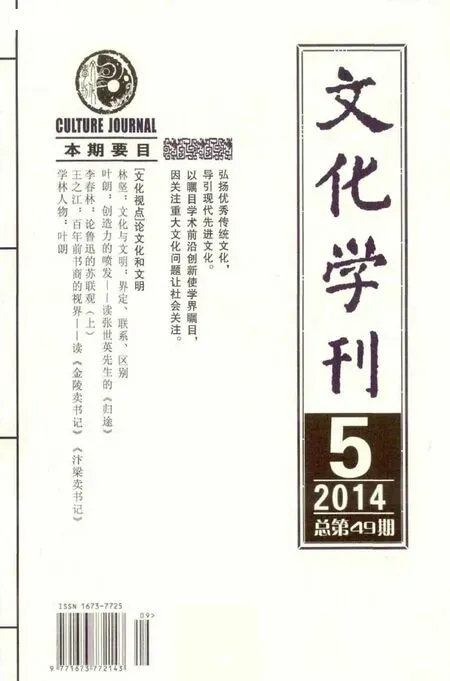创造力的喷发①
——读张世英先生的《归途》
叶 朗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张世英先生的《归途》是一本很有价值、很有意思的书,不仅写了他个人的学术经历,而且映照出整个时代的面貌。我读了后,感触极多。不能尽谈,只谈两点。
一、关于两个30年
张世英书中提到两个30年的对比,前一个30年张先生也十分努力,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介绍,张先生自己说是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做学问,他在书中都写了。我也有些了解。就拿张先生主编“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来说,在哲学界影响是很大的,在当时是哲学味比较浓的一块园地,我们作为学生都非常注意这个专刊,但是从总体上,这30年学术成果还是比较有限,因为那30年没有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到了后30年,张先生回归学术,创造力开始喷发。
对两个30年的对比,我深有体会。读张先生的书,这使我想起我自己经历的几个小故事。一是55年我刚进北大哲学系当学生时的经历。第一天进校门,一位老同学陪我办入学手续,路上向我介绍北大哲学系的情况。他对我说:“我们系的老先生完全值得信任,他们大部分已经可以上课了。”我听了大吃一惊。“完全可以信任”“大部分可以上课了”,这和我脑子里想的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张先生书中写的:“老教授大多数不得登上讲台讲课,主要是作思想检查或接受批判。”后来1958年“五四”北大校庆,陈伯达到北大讲话,题目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批判大旗,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共产主义大学”。他在讲话中就点冯友兰先生和贺麟先生的名字,说:“像冯友兰、贺麟这样的人,长期搞唯心主义,不进行深入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怎么行呢?”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进北大不久,当时请哲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来给我们做报告。潘梓年是一位革命老同志。他的报告,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谈矛盾同一性问题。他举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为例。他说毛主席当时和蒋介石谈得很投机。你说他们两个人怎么会有共同性呢?这是矛盾的同一性。再一点是他说,我们哲学工作者的最高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中央发布一个决议、文件,明天你马上写出一篇文章对这个决议、文件加以论证、宣传。这句话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当然,为中央决议、文件进行论证、宣传是哲学工作者的一项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十分有意义的,今天仍然如此,但把哲学工作者的最高任务归结为这一点,至少是很不全面的。哲学工作者、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还要研究基本理论,要研究宇宙、人生的一些根本问题,单就社会生活领域来说,也要研究前瞻性的问题,要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要起一个思想库的作用,不能限于对已有政策做论证。潘梓年的话说明当时理论工作的社会氛围。这种氛围不鼓励你去做原创性、前瞻性的研究,这和我们今天提倡思想解放的氛围大不一样。这样就可以理解那30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什么那么少了。这是一个故事。再一个是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时候。当时北大哲学系请了大兴黄村人民公社的一位主任来做报告。他主要是讲高级社面临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必然要求成立人民公社。我们听了都感到他讲得很生动、很精彩。这时有一位领导同志就说,现在真正的哲学家并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像这位公社主任这样的干部。我们听了觉得这个话非常对。冯友兰先生也认为这个话非常对。但是他补充了一句,他说,现在的哲学家当然是人民公社的干部,不过像哲学史、逻辑这样一个学问总还得有人去研究,像我们这些人可以做这种研究,当然我们不能叫做哲学家,我们可以叫做哲学工作者。当时就有人说,你看,冯友兰还是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故事也说明当时一种社会气氛。这种气氛不鼓励学者们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当然也不鼓励学者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
第二个30年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自己说是踏上了返回自己思想家园的归途。《归途》一书的书名就由此而来。张先生在这30年做出了许多为学术界关注的成果。这两个30年的变化,不仅张先生如此,其他学者 (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此。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确实值得纪念。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盛世的面貌,中国的学术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繁荣。所以我作为经历了这两个30年的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和大家一样,对改革开放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和喜悦之情。
二、关于学术原创性
我们北大发明汉字激光照排的王选院士曾经说,研究计算机的学者,30多岁是顶峰,过了40岁就走下坡路了,过了60岁就什么也干不了了。这是说一个学者的创造性与年龄有关系。王选说的这个高峰年龄,对于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对人文学科来说,并不合适。人文学科的学者的学术高峰多数要在中年之后。因为人文学科—要长期的学术积累,二要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所以年轻人成不了哲学家(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如王弼)。黑格尔说过,同一句格言,年轻人说出来和老年人说出来,内涵是不一样的。这是人生体验不同。所以很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年龄很大依然可以做出重要成果。冯友兰先生、朱光潜先生在文革中都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文革之后,他们都已是80和80多的高龄,但是他们依然做出一个又一个重大学术成果,显示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冯先生说他是“欲罢不能”,他说这就像一条蚕,既生而为蚕,便只有吐丝,它是“欲罢不能”。张先生也是欲罢不能。特别是近10多年,他连续出版了《天人之际》(1995)、《进入澄明之境》(1999)、《哲学导论》(2002)、《境界与文化》(2007)等著作,同冯先生、朱先生一样,显示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张先生这30年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五六倍于前30年的作品,而且形成了、结晶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哲学观点。张先生这些原创性观点是在会通中西哲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就是冯友兰先生说的“接着讲”。哲学史家是“照着讲”,哲学家是“接着讲”。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不一定“接着讲”,人文学科一定要“接着讲”。“接着讲”不是“照着讲”。“接着讲”是发展,是扬弃,是飞跃。对人文学科来说,“接着讲”才可能有原创性。当然,“接着讲”,还要思想解放,要敢于突破旧说,才能有原创性。思想解放我们天天说,但真正思想解放,敢于突破旧说,并不容易,这需要理论勇气。张先生著作的原创性,是融会中西哲学的成果,同时也是思想解放的成果。这一点,我想大家读张先生的书时一定会有感受。
我个人深受张先生这些著作的启发。近3年我在写一本美学基本原理的书,也是想把我这30年的美学研究做一个概括和总结,现在已经完稿。我想再做一番补充修改即可交出版社出版,我的书名是《美在意象》。我也是“接着讲”。从远一点说是从柏拉图、老子、孔子接着讲,从近一点说是从王夫之接着讲,再近一点就是从海德格尔接着讲,从朱光潜、宗白华接着讲。我的努力是想在北大老一辈学者朱光潜、宗白华等人的基础上把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往前推进一步。我在书中就大量吸收了张世英先生的研究成果。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谈。我只提两点。一是张先生对超越主客二分的“万物一体”的哲学的阐述,这对于我们突破美学研究的旧的思维模式,对审美活动 (美和美感)获得一个新的理解有重大的启发。再一个是对人生境界的论述。人生境界的学说是冯友兰先生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冯先生说,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就是人生境界的学说。张先生从冯友兰接着讲,把哲学定性为提高人生境界的学问。我非常赞同冯先生、张先生的说法。我研究的是美学,我认为审美活动可以从多方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但审美活动对人生的意义最终归结起来是提高人的人生境界。所以我那本书最后一章就是讲人生境界。这是受冯先生、张先生的启发。
张先生这30年的成果再一次证明,人文社会科学的原创性的高峰年龄一般并不在30岁,而是在中年之后,甚至是在黄昏时分。李商隐有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们北大有位杨辛教授把它改了两个字:“夕阳无限好,妙在近黄昏。”这两个字改得妙极。我曾写了一篇500字的文章阐释黄昏之妙。我讲了三点。其中一点就是说,人到了晚年,有可能获得一种生命 (时间)的自觉,因而在最后的生命段中,往往会进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时他每个瞬间的创造,从生命的高峰体验的角度说都具有永恒的价值。这是瞬间即永恒的境界。
张先生说,他虽然身体有些疲惫,但他胸中仍然波涛汹涌,万马奔腾。张先生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依然十分旺盛。张先生明年就是“米”寿。望之以“米”,期之以“茶”。我相信,在今后的第三个30年中,张先生一定会为中国的哲学、为中国的文化做出新的贡献,一定会给我们更大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