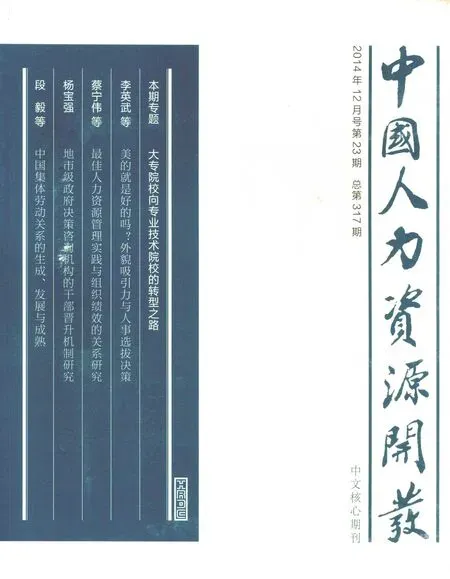结构性力量与新生代工人抗争的组织化趋向
● 刘爱玉 付伟 庄家炽
■责编/ 孟泉 E-mail: mengquan1982@gmail.com Tel: 010-88383907
一、新生代工人的组织化问题
30多年的改革正在将中国变成一座“世界工厂”,新生代工人是这个“世界工厂”催生并正在形成的世界上最庞大产业工人阶级的主体。从代群的意义上看,这一主体最大的特点是1980年后出生、几乎没有参与过农业生产、学校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其构成基本上为两大人群,一是户籍身份为农村居民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员,即学界一直广为关注和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据统计,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66亿人,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外出农民工的60%,加上就地转移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达到1.1亿人(国家统计局,2014)。二是户籍身份为城镇并从事非农生产的人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城镇30岁以下工作者占27.9%,约9677万人。对如此规模庞大的工人进行研究意义深远,其型构的劳动关系秩序不仅对于参与其中的工人、管理者、资方意义非凡,也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既往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农民工的平等就业、劳动保护、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障等方面权益缺损及其抗争行为,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忍耐、抱怨、退出、呼吁还是抗争。相关学者的研究认为,大多数农民工由于惧怕雇主辞退、失去工作而选择忍耐和抱怨,或选择逃离(蔡昉、王美艳,2005),或因内部的“分割”、“分化”而缺乏集体抗争的能力(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2004),但有时也会有一些集体性抗争(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汪建华、孟泉,2013)。总体来看,工人回避冲突与行动,较少发起和参与冲突,为自我保护而采取鸵鸟政策(许叶萍、石秀印,2006)。在特定的情况下农民工成为(造反倾向很强的)流民的可能性很小(孙立平,2003)。而形塑农民工行动选择的是生存理性(黄平,1997)和“生存文化”(陈佩华,2002)。(2)农民工抗争的代际差异。潘毅等认为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代际的更替和分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有更强烈的集体行动意愿( Pun & Lu,2010),以及更多的利益抗争行动(刘爱玉,2011),但刘林平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比老一代更向往城市,也并不具有更强的反抗意识和行为(刘林平、王茁,2013)。(3)农民工抗争的推动力。沈原的判断是:农民工是转型时期出现的“新工人”,与老工人(国企职工)比较,新工人的力量主要体现在“结构力量”上, 而老工人的力量主要体现在“结社力量”上(沈原,2006),刘爱玉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影响其利益抗争行动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权益受损及认知、人生及健康侵害经历和认知、结社力量(刘爱玉,2011)。汪建华和孟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体验,锻造了其抗争的独特模式:以同事—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增长型抗争、原子化的底线 / 增长型抗争和群体性骚乱(汪建华、孟泉,2013)。
过往研究对本文问题提出的价值或意义在于,第一,之前关于工人行动组织化和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讨论和结论多为基于个案研究或者文献分析的理论推断,那么在经验层面上,这种理论判断是否能够获得支持?第二,虽然一些学者如常凯敏锐地发现了工人行动组织化的趋向(常凯,2009),但对于这种组织化趋向到底由什么力量推动并无系统探讨;第三,既往研究侧重于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并倾向于将其视为与城镇户籍的新生代工人分隔的群体,但实际上这两者在劳动过程以及抗争行动实践中有着广泛且密切的联系。2010年是工人罢工频发的一年,5月的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工人罢工、南京新苏热电公司工人罢工、河南平顶山棉纺厂工人罢工、上海夏普公司工人罢工, 6月的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厂工人罢工、深圳美律电子厂工人罢工,等,阅读这些罢工事件的报道及相关研究,发现其并非单纯由新生代农民工发起,而是有大量城镇户籍新生代工人的组织动员和参与。我们认为,市场化改革极大地形塑了中国劳动关系的样貌,企业的用工行为和管理方式更多地是基于工人的人力资本特性而非户籍,工人之间会因人力资本特性而非单纯的户籍特性而发展出更多的劳动过程中结构位置的相似性。或许既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行动代际差异研究的矛盾性结论的部分原因可归结为此。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新生代工人的工作状况,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的不满与抗争行为,分析这种因不满而进行的抗争行动,相比于非新生代工人而言,是否有组织化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背后的原因。研究所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作者于2009年6月-11月在北京、上海、深圳、泉州、宁波、绍兴、余杭、新野8个城市的24个纺织、服装企业对1051个工人所进行的问卷调查,课题组首先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然后根据企业所有制、规模选择需要调查的企业,在每个企业调查40人左右,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010人,其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新生代工人共618人(男性241人,女性277人),占61.2%,年龄在30岁及以上的非新生代工人392人(男性169人,女性223人),占38.8%。研究所用的个案访谈资料,来自上述24个企业对105个工人所进行的访谈。
二、新生代工人的抗争
1、不满与纠纷
调查发现,新生代工人中,有37.5%的人因为权益受损而与目前所在企业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纠纷,按照纠纷事项及发生的比率,依次为:工资待遇(标准过低、拖欠)(占25.1%),劳动时间(占17.9%),职工福利(7.6%),劳动合同(占6.7%),劳动保护(占6.4%),社会保险(占4.9%),职务晋升(占3.4%),除社会保险一项之外,纠纷事项的发生均显著高于非新生代工人。
2、行动表达类型
新生代工人在劳动权益受损时的行动回应方式主要有退出、服从、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四种类型。
(1)“退出”作为一种选择
在所调查的24家服装、纺织企业中,“退出”行为普遍存在。在问及“如果您在企业里遇到不公正待遇时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时,26.3%的新生代工人表示会离开这个老板或雇主,这一回答与非新生代工人的回答相比并无显著差异( =0.041,Sig.=.839)。深圳服装厂工人小詹的说法很典型:对,你不能压迫式,强迫式的,压工资,我可以消极怠工的,怎么样,是吧?那哪个月我工资不高的时候,我吧唧一下就走人的。服装厂有多少啊 ,一大把,你这个老板不要,姓周的老板不要我,姓王的要我,现在服装生产的竞赛也很大(Zhan2008,男工,24岁)。选择退出的工人,更常见的行为是另寻“下家”而不是“闹事”,在他们看来,现在要找一份工作是“蛮容易的”,所以也就没有必要与工厂继续闹下去。
(2)“服从”:能忍则忍
服从可分为主动服从与消极服从两种类型。主动服从者认同企业目标,行为上表现为合作与投入,他们是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好战士”。消极服从者不认同企业目标,但在行为上不抱怨,不退出,并服从制度安排对他的要求。新生代工人中有39.9%的人表示在遭遇不公正待遇时会采取不表达(利益诉求)、不申诉(权益受损状况)的行动方式,其值略低于非新生代工人,但无显著差异( =0.422,Sig.=.516)。正如江苏一个企业的工人所说:工作中、生活中不如意的地方忍忍就过去了,再说我这个人也没什么不如意的地方。愤怒之后,只能忍受,找到人之后倾诉了之后又无力改变现实,那又有什么用呢(Jszc06,男,25岁,普工)。
(3)个体行动
个体行动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采用“怠工、旷工、消极参与”等“弱者的武器”来表达怨愤,在那些与企业有过劳动纠纷的人中,有13.3%曾经采取过“消极怠工,不好好干活”的行动,略高于非新生代工人(12.1%),但无显著差异( =0.086,sig.=.766)。二是采用个人倾诉的方式,常见的是发牢骚和工友之间的抱怨,以化解心里的不满和怨恨,如深圳服装厂员工Nhuang所说:跟自己玩的好的朋友说说嘛。一般,说说心里开放一点嘛,释放出来了也就好了(19岁,男工)。或者是向领导、上级反映自己的问题,跟上级发发脾气,以释放心里的怨气。深圳服装厂工人Xiao2008说:会去办公室里说一下,直接跟那个主管说一下,发点脾气就行了,有的时候也会找老板说。三是个体维权,主要通过政策、法律等制度安排来维护劳动权益。上海服装企业的陈女士说:如果老板拖欠你工资,或者碰到不公正,那肯定会不舒服的,如果有的话,那我就找管理人员要啊,说怎么还不发工资,天天烦他一下,提醒他一下,再不给,那肯定要到劳动局那里去告他,那不给钱嘛,当然是要告的,是吧。然后再离开(0901个案1,陈女士,30岁)。
(4)集体行动
在调查的纺织服装业新生代工人中,集体行动参与的比例为8.0%,其主要表现形式及参与比例为:一起上访过者7.9%,一起直接找老板/雇主者12.5%,一起直接找有关政府部门者8.6%,联合其他人通过司法途径谋求问题解决者8.8%,一起找新闻媒体帮助者5.6%,一起找工会帮助者6.6%,联合其他人罢工、讨说法者5.6%。在具体使用什么样的集体行动方式上,统计分析发现新生代工人与非新生代工人之间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3、个体化行动还是组织化行动?
从劳动纠纷与利益表达行动看,主要的行动方式是个体性行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工人诉诸于集体行动。新生代工人中,65.7%的人无劳动纠纷无行动,26.3%的人有劳动纠纷有个体行动,8.0%的人有劳动纠纷有集体行动。新生代工人的个体性行动与集体行动参与的比例远高于非新生代工人( =20.93,Sig.=.000)。如果进一步把新生代工人根据其出生年代分为80后新生代工人和90后新生代工人,则可以看到,90后新生代工人诉诸于集体行动的比例显著高于80后新生代工人( =25.460,sig.=.000),见表1。

表1 劳动纠纷与行动表达
三、结社力量、结构力量与行动表达
1.工人结社力量与结构力量基本状况
按照Wright的阐述,工人的行动受到“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 和“ 结 构 力 量 ”(structural power)的制约。“结社力量”是指“来自工人形成集体组织的各种权力形式”,即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组织、通过各种集体行动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结构力量”即“工人简单地由其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而形成的力量”。“结构力量”由两种“讨价还价能力”组成。一种叫作“市场讨价还价能力”(market bargaining power),包括:第一,工人拥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第二,较低的失业率,即所谓“紧凑的”劳动力市场(tight labor market);第三,工人具有脱离劳动力市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的能力。另一种叫作“工作现场的讨价还价能力”(workplace bargaining power)。这是一种“从卷入于严密整合的生产过程的工人那里所产生的能力。在那里,关节部位上的工作节点的中断,可以在比该节点本身更为广大的规模上,导致生产的解体”(Wright,2000)。

表2 结社力量与结构力量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制度背景,Wright所阐述的结社力量概念如要用于分析中国新生代工人的行动能力,需要进行重新界定。结社的“结”是一种行为,是组织、结合、创建,结社的“社”是一结果,是由公民结合后形成的一个小社会(团体),结社还包括社团成立后其他公民的加入。我们把“结社力量”视作工人通过酝酿计划、联络人员、筹备资金、寻找活动场所、起草章程等组建社团或者自主加入已经成立的社团而具有的集体性力量。工人组建或者加入的社团最为重要的有两类:一类是工会组织,另一类是社会上其他各类组织,如非政府组织或社会社团等。在操作层面上,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测量:一是目前所在企业是否建有工会且工人参与工会的状况。通过考察工人参与工会状况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可以检视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建设对于工人行动能力及其劳动关系的影响。二是工人参与NGO组织状况,工人参与劳工NGO组织的状况以及与集体行动参与的关系,可以检视自下而上的组织化对于工人行动能力的形塑。从工会参与看,新生代工人(21.4%)与非新生代工人(34.7%)之间有显著差异,非新生代工人参与工会的比例更高。从参与劳工NGO的情况看,虽然新生代工人的参与比例略高,但参与过劳工NGO的比例均较低(分别为10.1%和8.0%),且在统计上并无显著性差异。
结构力量反映的是工人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反映的是工人的议价能力。我们五个方面来进行测量。一是文化程度,它反映了工人拥有的人力资本的状况,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力;二是劳动过程中的结构性位置,是处于普通工作岗位上,还是从事有技术性的工作,或者处于管理职位上。三是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熟悉程度,蔡和等在分析影响农民工利益抗争行为时,主要将劳动合同法认知(是否了解)作为对剥夺状况的测量(蔡禾、李超海、冯建华,2009;西方一些学者也指出有权利意识的个人对法律、法规比较熟悉,并能够以之为工具,更趋向于诉诸集体行动(O’Brien & Li,2006;Zweig,2003)。但本文认为劳动合同法认知主要是提供了工人以法律为武器进行维权抗争的某种支持,是一种行动潜能的表现;四是寻找替代性工作的难易程度。越是容易寻找替代性工作机会,越是能够在结构上对于工人的集体行动以激励;五是居住状况。一些学者认为基于宿舍与小区的劳动组织推动了集体抗争,宿舍劳动体制既是一种新型的劳动管理方式,同时也为劳动团结、抗争以及新型劳动关系出现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Chan & Pun ,2009)。据此推断,居住在集体宿舍的工人,其利益抗争行为将高于居住其他类型场所的工人。
从结构力量的五个方面看,新生代工人与非新生代工人有差别的是文化程度、劳动过程中的结构性位置与居住状况。新生代工人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于非新生代工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34.8%),更多居住于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居住集体宿舍的占60.8%),绝大多数为普通工人(占77.3%)。新生代工人与非新生代工人相似的是劳动法及相关法律的熟悉程度、寻找替代性工作的难以程度。总体而言,四分之三的工人或多或少知道或熟悉劳动法以及相关法律知识,七成工人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替代性工作。
2.结社力量、结构性力量与集体行动参与
结社力量、结构性力量对于新生代工人行动参与影响的讨论,需要考虑控制一些可能会对其行动参与有影响的其他因素,比如性别、工人的不满、怨愤和认知,即对权益受损的认知。以往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权益受损认知对于工人的行动参与有显著影响(刘爱玉,2011)。本文将权益受损认知作为控制变量,并从三个方面进行测量:(1)工资权益受损及认知。以理想收入与实际收益的差距来测量被绝对剥夺的程度,以对目前工资水平合理程度的态度测量对工资权益受损的认知。新生代工人的理想月均收入为1913元,比实际月均收入高300元左右。非新生代工人期望月均收入为2141元,比实际月均工资收入高285元,两个群体给出的合理月收入存在显著性差异(t=5.49,Sig.= .000)。(2)人身及健康受损及认知,用劳动安全与生产条件状况 、人身及健康侵害经历及认知 、工作环境认知进行测量。(3)就业保障与保险权益及认知。就业保障与保险权益区分为两种情况:至少参加一种保险,没有参加任何保险。
本文分别以全部样本、新生代工人样本和非新生代工人样本为分析对象,分别对结社力量与结构力量对于工人行动的影响进行分析。
对表3的分析发现:
1、以全部样本为分析对象,发现新生代工人在劳动权益受损的情况下,参加利益抗争行动的比例要显著高于非新生代工人,其参与个体行动的可能性是非新生代工人的1.751倍,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是非新生代工人的2.408倍。
2、结社力量中的工会参与状况,无论是对工人个体行动的参与还是集体行动的参与,均没有显著影响,但参与劳工NGO组织状况对于工人个体行动有显著正面影响,参加了劳工NGO组织的工人,在面对工资、工作时间等方面的侵害与不满时,进行个体行动的可能性为没有参加者的3.49倍。
3、结构力量各要素对于工人的个体行动参与均没有显著影响,对非新生代工人的集体行动参与也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于新生代工人的集体行动参与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是文化程度、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结构性位置以及居住集体宿舍对于其集体行动的参与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越高者,对工资和工作状况等的不满,更少采用集体行动的方式,技术人员与低层管理人员相比于普通工人更多采用集体行动的方式解决问题,技术人员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是普通工人的5.998倍,低层管理人员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是普通工人的2.863倍。居住集体宿舍者的集体行动参与可能性是其他居住方式者的2.18倍。
四、结论与讨论
1.结论
利益受损的新生代工人不是被动的忍受者,而是能动的行动者。34.3%的人曾经以个体行动或集体行动的方式进行过利益抗争。新生代工人的行动在当下以个体性行动为主,但组织化行动的趋势明显,即越是年轻代的工人,越是表现出更多诉诸于集体性行动以消解不满与怨愤的特征。这种趋向也为近年来的劳动实践以及一些学者利用更新经验资料所进行的系统、全面分析所证实。如常凯指出,中国的劳动关系正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调整转型,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集体劳动争议和劳工集体行动,特别是2010年夏季发生的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代表的外企工人的“停工潮”,成为中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常凯,2013)。
新生代工人行动的组织化趋向,却不是由结社力量推动,而是由结构力量(如文化资本、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结构性位置、居住状况)推动的。本文考察的以工会与劳工NGO为表征的结社力量对于新生代工人的集体行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

表3 个体性行动还是组织化行动:结社力量与结构力量的影响(全部样本)
2.讨论
我们的疑惑或者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对于工人集体行动参与有显著作用的结社力量,在中国却未能对工人集体行动的参与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讨论工会对于工人组织化利益代表的集体行动的影响问题。从经验层面看,工会在利益抗争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影响的程度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有工会的企业,本身是属于劳动条件、工资及保障方面做得相对较好的企业,所以工人的利益抗争就少,我们对劳动权益的三个方面的变量在有工会与没有工会的企业之间进行了比较,证实了这一论点(刘爱玉等,2014)。二是由党政主导自上而下通过行政化手段组建的工会,导致“地方工会行政化”和“企业工会老板化”现象突出,工会与劳动者脱离问题严重,不能有效地代表和维护工人的权益。
摘录两段关于工会认知的对话,可以对工会在工人利益表达上的作用有更好的认识。
个案一(刘爱玉2010年对某私企公司老总张某的访谈)
张:中国的工会啊,说起来,他是共产党领导的传统的工会,这工会和外国的工会不是一回事。
刘:怎么个不一回事?
张:这个工会组织,它应该是个独立的……,中国的工会呢,到最关键的时候呢,它是替老板说话,(笑)。我这个就不要面子,想什么说什么了。到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工会是站在老板旁边的,为什么呢?因为老板可以不让他干了。到了国外,工人和老板纠纷的时候,工会必须站在工人的身边,跟工人是一起的,在中间起到调停人的作用。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个案二(刘爱玉2010年对一个年轻前纺女工的访谈。该女工1990年出生,中专文化。)
问:您所在企业有没有工会?
答:有
问:是哪种工会?
答:就是公司开会、车间开会,开工作会。
因此,新生代工人的怨愤表达依然面临着组织和话语资源的匮乏问题(潘毅、陈敬慈,2008;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黄岩,2010),即使诉诸于集体行动也往往呈现出自发的、分散的和野猫似的特征(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黄岩,2010)。自上而下组建的工会未能在工人的集体行动上表现出促进、推动作用,但工人行动的实践,无论是个体行动还是集体行动,必将推进工人的组织化,在经济诉求基础上提出了组织工会(改组工会)和集体谈判等诉求,促进工会的去行政化和自主性的增长。如南海本田罢工促使广东省工会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改组工会”的诉求,并在事件发生之后对南海本田企业工会进行了重新选举。得到工人支持的新的工会委员会在2011年进行了第二次集体谈判,并获得增加工资611元的结果,超出上年停工谈判的涨幅(黄应来,2011), 又如,2012年3月,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工人举行罢工,在工人提出的12条诉求中,有一条是重新选举工会委员会。2014年5月,广州番禺旧水坑胜美达电子厂的数十名工人在向厂方追讨社会保险金的过程中,提出了组建工会的要求。工人的集体行动直接促成了集体劳动关系中工人的组织化与工会的群众化的结合,催动了集体劳动关系的生成与成长。
NGO参与只是在个体层面上对于新生代工人的行动参与有影响,这种状况与劳工NGO本身在中国的生长历程以及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劳工NGO是自上个世纪中期之后,带有非政府组织性质的维权组织,这些组织大部分活跃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它们为新生代工人特别是农民工提供了在异地就业时所需的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撑与行动上的支持,也在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提供了及时的法律援助。作为植根于工人的非政府组织,它们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在于满足工人的需求。但是劳工NGO在现有中国政治条件下,其服务宗旨主要是对个体工人提供援助,其服务模式主要是工伤探访、工资追讨、劳动争议调解、紧急救助等等。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NGO参与未能对新生代工人的集体行动参与有显著影响了,所以有学者认为NGO是反团结的机器,其生长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与结构性限制,一方面是来自政治结构上的政治吸纳(political cooptation),一方面是来自商业化的压力(Lee & Shen,2011)。
结社力量的现况或许会让人们对于工人组织化行动以及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前景表示担忧,但是我们认为,结构力量对于工人集体行动的影响,以及这种结构力量促动的集体行动对于结社力量的倒逼,对于中国劳动关系的有序发展,终将产生积极影响,工人自发性的集体行动、利益诉求和劳动争议,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制度建设、劳动立法和行业自治,推进了各地集体劳动合同和集体协商机制的制度建设和实践。
我们在文末引用两个方面的数据,以考察新生代工人结构力量的前景。一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型及由此引起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改变。人口学家郭志刚指出:“我国生育率过低问题严重,以往那种靠吸引外来劳动力支撑的人口城镇化模式正面临城乡人口双双出现少子化和老龄化同时推进的挑战,今后十几年全国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数将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平均每年将递减4%,农村不再是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源泉,全国劳动力将全面进入短缺状况,以往的民工潮正在转变为民工荒(郭志刚,2014)。实际上,从2004 年初开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随后在长三角地区及在安徽、河南、陕西等中西部地区纷纷出现“民工荒”、“涨薪潮”,这些现象显示出我国劳动力供给形势出现变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 2012 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减少345万人,比2011 年下降0. 6%,而这种减少将因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而持续。二是义务教育普及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引致的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相比于第五次人口普查,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根据全国妇联妇女地位调查,30岁以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2010年为11.5年,1990年时为7.7年,十年期间30岁以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了3.8年。
上述两个方面的趋势告示:新生代工人的结构力量在进一步增强,未来劳动关系秩序的建构,有赖于我们对推动行动组织化趋向的结构力量的正确认识,以及在政策层面上应采取的积极行动。
1.蔡昉、王美艳:《“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珠江三角洲调查研究》,载《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5-10页。
2.蔡禾、李超海、冯建华:《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9-161页。
3.常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特点和趋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版。
4.常凯:“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91-108页。
5.陈佩华:《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的生活》,载《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年卷。
6.郭志刚、 王丰、蔡泳著:《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7.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8.黄平主编:《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9.黄岩:《脆弱的团结:对台兴厂连锁骚乱事件的分析》,载《社会》2010年第2期,第101-115页。
10.黄应来:《南海本田劳资谈判,今年工资再涨611元》,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3月2日,第A17版。
11.黄岩:《农民工赋权与跨国网络的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组织调查》,载《调研世界》,2008年第5期,第22-25页。
12.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3.刘爱玉 、傅春晖、阿拉坦:《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农民工的权益?》,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4.刘爱玉:《劳动权益受损与行动选择研究:两代农民工的比较》,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66-73页。
15.刘林平、王茁:《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80 后农民工与80 前农民工之比较》, 载《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36-151页。
16.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
17.潘毅、卢晖临、张慧鹏:《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
18.孙立平:《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几点基本看法》,载《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http://www.ccrs.org.cn。
19.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0.汪建华、孟泉:《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21.许叶萍、石秀印:《工人阶级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转换》,载《中国社会学网》,2006年,http://www.ccrs.org.cn。
22.Chan C.K.C. , Pun N.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2009,198(June):287–303.
23.O’Brien K., Li Lianjiang. Rightful resistance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4.Lee C.K.,Shen Y. The anti-solidarity machine?lab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in Sarosh Kuruvilla , LeeC.K.,Mary E. Gallagher ed.From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Markets,Workers,and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China,ILR Press,2011.
25.Pun Ngai, Lu Huilin.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Modern China, 2010, 36( 5).
26.Wright,E.O. Working-class power,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 ,and class compromis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0,105(4): 1687-1717.
27.Zweig D.To the courts or to the barricades: can ne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nage rural con fl ict?” in Elizabeth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Change, Con fl ict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