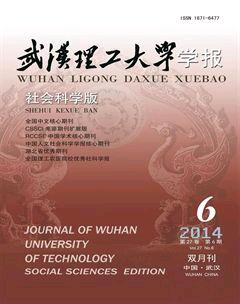职业与近代女工家庭地位的变动
*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LSZ003);江苏大学高级人才引进启动基金项目
摘要:中国近代女性的职业参与,是女性人格化社会化的起点.它改变了传统社会女性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并引致女性的家庭地位发生结构性变动.女工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提高了她们在两性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在代际结构中也改变了对女性的传统偏见,且对个体在家庭中自主性的提高具有关键意义,三重维度显示了女性家庭地位变迁的具体路径.但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受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女工家庭地位的变迁与社会化的进程并不完全同步,这其中既有规律可循,又反映出一定的历史非平衡性.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6.015
收稿日期:2014-06-03
作者简介:马方方(1979-),女,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性别史研究.
妇女的家庭地位是指妇女在家庭中享有威望和拥有与控制家庭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权力. ①有关妇女家庭地位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诸多影响妇女家庭地位的因素中,经济收入的相关度最高 [1].在传统社会的性别制度下,男性控制着家庭和社会的主要资源,被赋予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妇女的地位可以用“妇者,伏于人者也”来概述 [2].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兴起,女性从过去依附于家庭到参与社会劳动,进行劳动力谋生.“经济独立为女子解放的原动力”. [3]当女性通过劳动获得报酬,并贡献于家庭经济时,以传统性别分工为基础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制度也开始在家庭内部发生动摇.就业是女性从传统到近代形态过渡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并深刻影响到两性关系的变动,也成为其家庭地位变化的关键.
职业成为女性从“分利者”到“生利者”的转捩,并以此改变了女工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本文从三个维度分析近代女工家庭地位的变化:由姻缘设定的婚姻维度,由血缘设定的代际维度,以及个体维度 ②.以此探讨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职业对女性家庭地位变迁的意义,并为性别与近代社会的变迁提供参酌和借镜 ③.
一、婚姻维度:夫妻权力关系的变化
夫妻关系为家庭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夫妻关系方面.民国以后,家庭规模发生很大改变,以独立夫妻与子女为主体构成的小家庭制度逐渐成为家庭演变的趋势 [4].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家庭功能也在随之发生改变, ④即家庭逐渐变成了以生活为主要功能的处所,其经济来源主要是家庭成员从事各种职业的劳动所得,并通过社会交换来满足生活需要.随着家庭关系的简化,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庭生计的状况日益增多.台湾学者朱岑楼1977年对我国研究家庭问题的152位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收到的答卷,整理出«近六十余年我国家庭的重大变迁»表,其中有两项结论为:“职业妇女增多,妻之经济依赖减轻,家计趋向于共同负担”;“男女趋向于平等”. [5]
近代女性外出做工既是工业化推动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经济贫困的现实需求.1917年圣约翰大学学生在上海曹家渡调查时发现,“工人支持五口之家月须15元”,而该地区“常见男工谋10元、8元,女子做丝厂每月所入亦如此”,也就是说,在这一收入档次的工人家庭“非有一人以上在外谋生不可,仅靠男工赚钱的家庭,在曹家渡甚罕见.” [6]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物价开始上涨,“依工商部统计假定工人的生活标线为二十七元二角(此数包括饮食、衣着、房租、燃料、杂项五项),维持其家庭夫妇二人及子女三人共五人生存费用.依这标准来视察我国……一般工人的工资多半还在十元至十五元之间.在二十九个重要城市中,男女工资十元至十五元之间者,占二十四个.” [7]工人工资的低廉迫使许多女性外出做工以维持最起码的生存.陈达发现,已嫁的女工“完全受经济压迫,不能不做工,或因丈夫所入不丰,或因子女连累,出来帮同赚钱,以增家庭入款.” [8]烟台的劳工妇女也要外出做工负担家计,“她们日间到发网厂里做工,晚上到平民学校去念书,她们除了缝纫洒扫,抚育子女之外,还要自食其力”,“不但要维持自己的生活,有时还要用来养育子女,甚至要来养活丈夫.” [9]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兴社会调查之风,社会局和一些社会学者对城市工人家庭进行了深入调查,证实了这一论断.1928年上海社会局对上海305户工人家庭的生活程度进行了详细调查,显示的工人家庭结构及就业情况是,平均每户4.62人(其中夫妻子女的小家庭占81.42%),平均每户就业2.06人.在家庭收入中丈夫占53.3%,妻子12.6%,子6.9%,女7%. ⑤显然,在普通工人家庭,丈夫的收入仅为家庭支出的一半,妻子和子女就业,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社会学家陶孟和1927年对北京48户工人家庭共220人进行了调查,在47户家庭中男性外出做工的有45人,41家的妻子也在外做工 [10].
女性就业冲破了男外女内的公私畛域,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使夫妻原有的尊卑关系逐步发生改变.1935年,一位社会学家曾对上海和无锡的女工进行抽样调查,在受访的60名女工中,有23人在家中的权力丈夫为大,8人的权力和丈夫一样大,12人凡事均和丈夫商量,只有16人仍和旧式妻子一样地顺从丈夫 [11]520.费孝通先生30年代在江村考察时曾描述了工作对女子地位提高的意义:“现在挣工资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优惠,因为它对家庭预算有直接的贡献”,“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起了变化.例如,一个在村中工厂工作的女工因为下雨时丈夫忘记给她送雨伞,竟会公开责骂她的丈夫,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件小事指出了夫妻之间关系的变化,根据传统的观念,丈夫是不侍候妻子的,至少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不能这样做.” [12]198在厦门,“贫家妇女因为都能出去做苦工,扶助她的丈夫,所以夫妇间的地位,也许持着平衡.” [13]
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模式造成男女家庭权力结构的差异.如列宁所说,“妇女忙于家务,她们的地位总不免受到限制,要彻底解放妇女,使她们与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平等地位.” [14]女子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则婚姻的结合,以爱而不以利,男子自然承认女子的价值,真正改变态度,抛弃特权.” [15]女性的自食其力打破了男性对家庭经济的垄断,为夫妻平等对话提供了现实基础,也为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提供了契机.
二、代际维度:性别认同观念的再建构
“重男轻女”的观念与父权制社会的宗法制度相适应,是社会分配制度性别区分的结果.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使女性可以到工厂工作,赚取工资,既动摇了男外女内的分工模式,也动摇了男女不平等的观念 [16]516.女性做工有助于家庭经济的增长,使她们在代际关系中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父母在家庭中对女孩不再一味鄙斥,性别观念上渐显男女平等之势.
就近代女工的来源来看,她们多来自于城市周围的贫苦农民或是城市中的贫困家庭.家庭经济极度贫困的现实需要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甚至稍为年长的子女也要入厂工作,这对家庭的生存有着重要的影响.1935年«妇女生活»曾经对上海纺织业的女工进行了座谈,可知许多女工的收入都对家庭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名袜工因父亲年迈和家贫,不得不到工厂做工,所挣的钱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都要寄回家,如果每天有工做,一个月可补贴家里两三元钱.还有一位纺织女工也要负养家的责任,“我也是从乡下出来的,因为天干没有吃的,家里有一个老娘和两个弟妹,我必须尽力养活她们.” [17]邓裕志对上海277名女工的调查发现,有150名女工把所有的工资都交给了父母,而由家里供给衣食.如女工余蓉所说,“我一得到工资,就交给我的母亲,然后她将为全家人花这笔钱 [18]160.有些工人家庭因家长失业或体弱多病而过早丧失劳动能力,养家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未成年儿女肩上,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沪东工厂区,有靠3个女儿在纱厂做工维持生活的工人家庭;甚至有一家七八口全靠一个13岁的女孩进纱厂做工活命 [19].
女工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动摇了人们对女性的传统偏见.传统的封建观念中,女子通常被视为“赔钱货”,但是“自海禁大开,机器工业逐渐侵入,女子有做工的可能与机会,‘赔钱货’居然可以变成了工资劳动者,不但父兄们乐于把女儿送去做工,妇女们自己也欢喜到工厂去.” [20]正是女子入厂工作,“在经济方面,女孩不再为家庭的负担,所以劳工阶级的家庭也不讨厌生育女孩了.” [21]10上海杨树浦附近一个女工的母亲说:“今天的男孩儿和女孩儿确实是一样的.女孩也能帮她们的父母.对我而言,女孩儿比男孩儿更好,我的大儿子现在17岁了.由于他小学毕业……他只呆在家里吃闲饭.” [18]158还有一个已婚的青年女子没有孩子,她便抚养一个6岁的女孩,人家问她为何不立男孩为嗣,她说:“我愿意抚养女孩,因为现在男女都是一样的”. [22]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上海丝厂林立的大集市附近,看到稍微像样一点的工人家庭的女儿通常都是纺织工人,她这时才开始理解,“当工业主义似乎在其他地方引起灾难的时候,它对这里的女工所具有的意义.整个中国只有在这个地方,女孩子的出生才被认为是一件幸事,因为女孩子在这里是家庭的主要支柱.” [23]16
有学者论述了“挣工资”与“受重视”之间的关系:“女孩可以进工厂去做工,拿她的工资来帮助家用,在最初几个月之后,她的工资往往要比她生活费用多,家庭从此不但解除了负担,而且还可以得到一点额外进款的帮助.若是女儿被招工人招到远处的城市里去了,家里又可以得到三四十元的安家费,而且从此以后,她也能够自食其力了.住在家里的工厂女工,大约都晓得她们的工资很引起家里的敬重,假如一个午餐里有了猪肉,那一定是特为做工的女儿烧的.她在家庭的圈子里,已经变成一个被重视的人了.” [21]10拉姆森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一位女工的母亲在做晚饭时烧了一些肉,但自己却不舍得吃,她说:“我自己不吃肉,因为它太贵,两天就要花30个铜板,这是给我女儿的,她在工厂工作挣钱,所以我必须好好待她.” [18]158女工因能赚钱养家,甚至可以作为父母为其择夫的筹码.“做父母的对于她们的婚姻看得非常重要,非所谓‘老亲至戚’,嫁妆和聘礼是要求得非常苛刻的.”对于男方来说,娶一个女工,“不但得了一个媳妇或妻,而且每天能从她的身上增加些许收入,真是所谓‘双喜临门’了.” [24]
“家庭之维持,全在经济”,“女子为谋生活起见,另谋出路,自求职业,因此女子亦有经济权,而旧时家庭,其势必趋于崩溃.” [25]家庭经济权的再分工既是对传统家庭制度的冲击,也逐步改变了人们的性别偏见.为改善家庭的境遇,她们走出家之私域,参与社会劳动,自负养家之责任,这种担当意识让人不仅生出“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慨叹.在代际关系中,职业使女性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价值,且使性别认同观念得以再造和重塑.
三、个体维度:自主性增强
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是一个复杂和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是某一种因素或某几种因素简单组合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交叉、重叠、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学者强调了女性在家庭诸项事宜中的自主权利对其家庭地位变迁的意义 ⑥.其中,女性对婚姻的自主权,以及对经济收入的消费自主权是家庭地位评价的重要指标.
(一)婚姻自主权
近代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开始由传统的“功能性”家庭(以牺牲婚姻质量来维持家庭的稳定)向现代“情感性”家庭转变 [26].青年人争取婚姻的自主是转变的关键.五四启蒙思想家倡言女子经济独立的意义,将其视为争取婚姻自主的前提,“妇女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终逃不掉受父母兄长的支配,受不肖男子的诱惑.妇女如果有了相当的职业,就能和社会相接触,相交际,从而达到社交公开的目的,而且不但结婚可以自己作主,而且能够摆脱不良的婚姻,因此职业是“婚姻自由的第一个条件” [27].经济独立为女性争取婚姻自由提供了现实基础.
近代工厂多是男女同厂做工,传统乡土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以此发生改变.一位上海女工描述她入厂后社交和婚姻观念的变化,她说现在“世界变得太快了”,男女在一起谈天说笑话已是常事,“‘我主张在这个潮流之下……男女社交应该公开,父母作主的婚姻,应予废除才是,因为那是不自由的’,‘自由恋爱是正当的’.” [16]456-457报刊上经常刊登女子外出做工后婚姻行为的变化. 1928年,在上海棉厂做工的21岁女工孙小妹,与王书义发生恋爱,并出走以抗拒父母代定的陈某婚事.她父母状告王书义诱拐其女,孙小妹反而出面起诉“乃父顽固,不合潮流所趋,请求维持其自由恋爱之婚姻” [28].近代工厂各,青年女工已渐有勇气为争取恋爱自由,不惜与父母决裂,并诉诸法律以求解决.一位上海女工拒绝母亲为她订婚,母亲表示尊重女儿的选择,“假如她喜欢这样做,我是没有干涉她的权力,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 [29]
职业使女性在离婚上也掌握了一定的自主权.在传统社会,“出妻”是丈夫的特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除了法律和封建观念对女子离异的种种约束,因妇女无独立生存能力,故即使遇着不良丈夫,一般也只能慨叹认命,别无反抗解脱之道.近代以来,随着女性走向职场,她们在离婚方面逐渐掌握一定的主动权.“妇女担任职业,自属本分,同时获得经济权的独立,不要依赖男子来生活,更可脱离男子的不正当支配.” [30]一些从乡村进入城市做工的妇女,在城里生活两三年后,被城市生活潜移默化,常会出现这种事,“在城里工作的姑娘不愿和农村小伙子结婚,已婚妇女进城后,也开始嫌弃仍是农民的丈夫.” [11]548因为能够自营生计,有的女工甚至选择终身不嫁.在广州,自梳女(把头发像已婚妇一样自行盘起,以示终生不嫁)是一个独特存在的群体,是广州妇女中不同寻常的一群,她们结拜成姐妹,组成丝厂劳动力的重要部分 [31].20年代末,顺德的女工仍许多有着“不落家”的习惯,因为有生活费,她们可以自立,因而自愿选择独身的生活 [32].一位岭南大学的教授向史沫特莱描述了工厂女工的独身现象:“她们拒绝结婚.如果她们的家庭强迫她们结婚了,她们就用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去贿赂自己的丈夫,并唆使自己的丈夫娶姨太太.这样的姑娘结婚以后,最多只是为丈夫生一个儿子.然后她便重新跑回工厂去,拒绝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政府刚刚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妇女通过贿赂等手段逃婚.但是妇女们对此漠然视之”.“她们太有钱了——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23]14-15
女性自主性的程度与个体在社会和家庭结构中的位置有关.经济上的独立和公共社会交往的参与为女性提供了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机会和权利,她们在婚姻关系中不再完全处于被选择的被动角色,而是可以自主地择其所爱,弃之所不爱.这实质上也是“妇女家庭角色自主意识的增强”的表现 [33].
(二)消费自主权
在传统社会,男性掌握社会经济命脉,女性表现出“代理消费”的基本特征,即通过家务劳动提供消费服务,消费的目的是为丈夫和家庭展示荣耀和财富 ⑦.这种特征决定了女性在消费关系中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家庭地位的弱势状态.当女性外出做工,成为挣工资的人,这种情况随即发生了根本变化.
经济独立的年轻女性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消费自主意识.许多女孩在开始做工时把所有工资都交给父母,随着年龄增长她们开始留有部分积蓄.1937年,邓裕志发现在她研究的368名女工的预算中,289人住在父母的家中,其中有127人(44%)仅把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她的父母.“在和女孩儿们说到这一点时,她们告诉笔者,她们留下部分工资,就有更大的自由买她们想要的衣服,也不用征得家中老人的同意.在少数情况下,女孩儿们说为了不把她们挣的全部工资交给家里,她们不告诉长辈实际挣多少钱.”拉姆森也发现,在杨树浦工厂工作的很多女工,都购买诸如绸手帕、手表、金耳环、脂粉或擦脸膏、时髦的衣服等,购买这些物件的女工的人数使拉姆森颇为震惊 [18]159.朱邦兴等人对上海棉纺织厂女工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有的女工“和家长反抗,结果每月可在工资中取得一元或两元钱,作为私人用费.” [34]97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揭示了挣工资的女性在家庭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变化情况:“一个女孩的传统经济地位是依附于她的父亲或丈夫的.她没有机会拥有大宗的钱财.家的财权在一家之长的手里.这与传统的集体生产相互关联. ……但挣工资基本上是个人的事.挣钱的人能感觉到她的工资收入是她自己劳动的结果.这是收入者本人和家长,都会感觉到的.此外,工资由工厂直接付给她本人.至少在这个时候,她可以将她的一部分工资按她自己的愿望去花费.因此,家中的经济关系就逐步地得到改变.比如,女孩子在合理范围内,为了正当的目的,如买一些衣服,那是可以允许而不受干涉的……一个已婚的妇女则将她收入的一部分留作她自己的积蓄.这种情况说明了单个家庭不断从家的复合群体中分化出来.” [12]199女性通过自身劳动,为自己被纳入社会新的分配体系开辟了道路.
时代推动了女性社会化和人格化的空前发展,它推崇自我控制的原则.职业活动增强了女性自强自立的能力,使她们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家庭和社会,这为始终禁锢于家庭和礼教的女性提供了解放自己的机会,也为个人自主性的成长提供了可自由选择的空间.
四、结 语
人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位置,归根到底取决于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 [35].女性的职业活动,对于改变自身的经济与家庭地位,获得自由与独立具有极大意义.著名教育家陆费逵认为,女子的“实力”与“地位”有着正比例的关系:“有一分质地,用一分劳力,就可增加一分实力.” [36]正是实力大大促进了地位的提高.对于第一次从经济的依附者变为自主者的女性来说,经济地位的提高就表现为“经济独立” [37].在广东顺德,“女子富于独立精神,不依赖家庭,从小便有自谋生活之志,不为家之累,故其家庭地位,与男子同,不遭歧视……父母不敢专制,兄弟不敢欺凌,亲友不敢蔑视,夫家不敢虐待.” [38]通过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收入,女性不仅能够支配自己的生命活动,还可以赡养家庭,以此获得认可并赢得尊重.突破旧观念的自主意识,也正孕育其中.
但是,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父权制社会性别制度其实“只有一层皮表的刷新”, [39]对许多女性来说,“职业”与“家庭地位的提高”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比如上海纺织工人的婚姻制度,从最进步的“自主婚姻”一直到最落后的“买卖婚姻”都是有的. [34]99而且女性并不因从业而减少家务劳动,工作和家事是女性必须承担的双重责任.一个叫王富英的女工说她在婚后还愿意和父母住,因为和自己父母住在一起时,只是在工厂工作,从不做家务,而在夫家必须两样都做.杨树浦一个女工说:“我必须把我的工资给我丈夫,如果我不给,他就打我,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我打不过他.他经常拿我每月挣的八块钱赌博.” [18]180在上海,还有很多女工是生活在有父母兄弟姊妹的大家庭中,她们的工钱,大多得交给家长.因为生活困难,她们很难从家长那里取得零用钱和正当的费用 [34]105.在河南许昌蛋厂的女工中,“礼教的观念在她们脑筋里是很深的,年轻的女工,很少在街上行走,无论放工早晚,她们都忙着回家.她们的自由,无论已未出嫁,都操在她们的父兄及丈夫手里.” [40]两性角色规范在理想层面与现实层面常常是脱节和分离的.
总之,职业使女性迈出了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关键一步,对于一直主中闺的女性来说,走向社会不止于对婚姻家庭的权力结构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且对于自身有着主体意识逐步形成的关键意义.毫无疑问,女子就业在提高其家庭地位的正面意义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为女子解放的要义.但是,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应该是由其所代表的总和资源所决定的,资源的认定既取决于性别文化的规制,同时又有因家庭而异的复杂关系.正因为这样,家庭经济的性别再分工无法在短时促成男女旧有权力关系的根本改变.革故鼎新本是个漫长的过程,它表现为“原本的”和“新生的”新旧相兼的真实状态.女性家庭地位真正意义上的提高,将主要依赖于社会整体的进步及个人的努力与环境的配合,也是一个充满着复杂与曲折的趋新过程.
注释:
① 社会学者对女性家庭地位问题的解释常从女性对家庭的资源贡献、文化背景等角度展开.资源贡献包括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威望等;文化背景包括区域文化、性别规范、宗教信仰等.参见沙吉才的«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王金玲将家庭权力设定为三个维度:由姻缘设定的婚姻维度(包括了婚姻关系和拟婚姻关系,如同居),由血缘设定的代际维度(包括了所有血缘性的代际关系和拟血缘性的代际关系,如收养、过继)以及个体维度(包括了所有基于姻缘和血缘关系而成为家人的个体).参见王金玲的«家庭权力的性别格局:不平等还是多维度网状分布?»一文,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这种理论设定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③ 学界对职业与女性家庭地位变迁问题已有一定的研究:如谢忠强、刘转玲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的就业与家庭地位论略»,见«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池子华的«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婚姻家庭的嬗变»,见«福建论坛» 2010年第2期;李帝的«近代中国女工的产生及婚姻家庭生活概况»,见«昌吉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等.这些成果多从职业对女性婚姻自主的意义这一角度展开论述.
④ 传统家庭承担了生产、生育传承、教化、政治、宗教和娱乐等多项功能,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囿于家庭,家庭为重要的社会组织.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家庭所具有的综合社会功能逐渐分解,家庭不再是城市社会的中心,也不再与社会严密整合一体,城市中生成出许多新的具有单一功能的社会组织,逐渐取代了家庭的各项社会功能.
⑤ 此处按原文的统计显示数据.实际计算有一定出入,原表为妻女总计占家庭收入的53.3%,但从各项收入统计来看,实为53.1%.参见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一书,1934年版.转引自李文海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ű城市(劳工)生活卷(上册)»一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52 -357页.
⑥ 沙吉才主要从妇女婚姻自主权、生育决策权、经济收入的管理支配权与消费决定权、自我发展抉择权与对子女发展的发言权等多方面、多层次地论述了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权利和地位(参见沙吉才的«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版).单艺斌强调了婚姻家庭中自我发展的自主能力,对家庭事务的参与和决策能力,对家庭财产与资源的占有和支配能力等(参见单艺斌的«女性社会地位评价方法研究»一书,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陶春芳、蒋永萍、徐安琪、刘启明等学者分别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解释框架和评价体系.
⑦ 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提出“代理消费”的概念,他认为自从有闲阶级出现后,随着财富的累积,需要仆役阶级进行对财物的代理性消费;更广泛的代理消费方式是由家庭主妇完成的(参见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一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6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