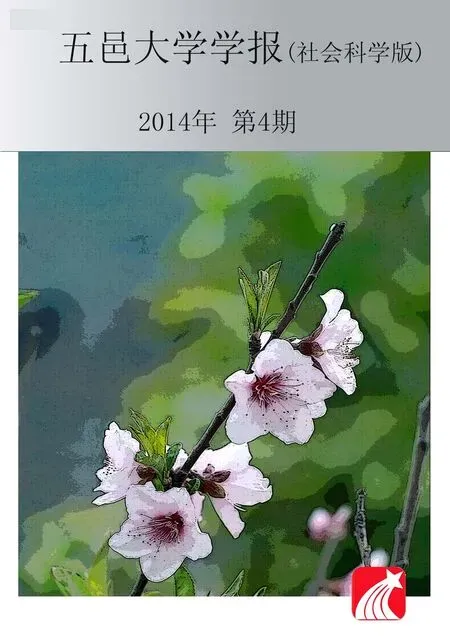论伍可娉小说的“原生态叙事”
——以《要嫁就嫁金山伯》为例
成慧芳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四年前,在美籍华人学者、旅美华人文艺家协会会长刘荒田先生引荐下,台山籍旅美作家伍可娉小说研讨会在五邑大学隆重召开,并一度引发了五邑侨乡社会各界对其“金山故事”系列小说的热切关注。不过,就学术而言,这种关注仍流于就事论事式的“感言”和“点评”,伍可娉“金山题材”创作的深层价值,即用文学“粗加工”的方式保留了该类题材的文学养分(故事、细节、情感等),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挖掘。笔者以为,如果将伍可娉的创作放在海外华人“民间写作”的大背景中考量,将其创作放大为某种“现象”,或许会得到更多有价值的认识。
刘荒田先生在评价伍可娉小说时用了四个字——“原汁原味”[1]封底。这种看似非“学术性”话语的点评,却是对伍可娉小说创作最客观和中肯的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海外华人“民间写作”的鲜明特质和价值。海外华人的“民间写作”相对于“文人写作”而存在,自然有其个性和特征(“海外华人民间写作”另行撰文阐述),这种个性特征被刘荒田先生用“原汁原味”点化出来,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学术课题:海外华人“民间写作”何以存在?“原汁原味”如何转换为学术表述?不同文体又如何体现“原汁原味”之特征?笔者此番关于“海外华人民间写作”的追问皆缘起于美籍华人伍可娉女士长篇小说《金山伯的女人》一书的出版和研讨,以伍可娉女士的“民间写作”身份以及小说的实际影响力,其创作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而刘荒田先生“原汁原味”的评价则成为笔者对伍可娉小说“原生态叙事”学术探讨的经验支撑和认知起点。
“原生态叙事”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无权威定义,笔者此处所用概念更接近于“前叙事”之说,即所谓“萌芽状态的叙事”[2],或意味着“不需要理论原理,不需要写作手法,不理会宗教精神、社会伦理,只关心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自己的关切,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来阐述故事”[3]。这是一种笼统的理念表述,对于“海外华人民间写作”而言,所谓“原生态叙事”显然应该有其特殊的内容。解析伍可娉的小说或许正可获得对于这些内容的认识。
一、“反叙述”的叙事格调
说到“反叙述”,还想借用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论述:“悲剧不可能模仿许多正在发生的事,而只能模仿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事;史诗则因为采用叙述体,能描绘许多正发生的事,这些事只要联系得上,就可以增加诗的分量。”[4]史诗与戏剧同为叙事艺术,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叙述与反叙述。而所谓“反叙述”,本质是突出事件、弱化旁白(叙述)。伍可娉的小说叙事更接近西方古典戏剧的“反叙述”路数:故事中心,场景完整,冲突集中,片段化等等。总之,伍可娉的小说是一种“以故事取胜”的小说,故事素材的占有,故事的原发性质,故事的戏剧化程度,故事的密集化,叙述功能的弱化等,构成了其小说的总体格调。
说《要嫁就嫁金山伯》是一部以故事取胜的“反叙述”作品,有两个突出的理由:
其一,故事密度大。这是指故事性强、戏剧性强的事件众多,冲突密集。本来,故事性强、冲突激烈是自小说产生以来相当长时期内作者和读者的普遍追求,也是小说应有的品质。只是小说发展到今天,其故事性逐渐被淡化,而让位于哲学、玄学以及各式各样的艺术技巧,以至于流行一种说法:“过去的人看小说是看故事,现在的人看小说是看模式”(欣赏作者如何说故事,即说故事的技巧)。笔者一直对没有故事的小说敬而远之,甚至认为,当今读者越来越远离了小说的主要原因正是故事的缺乏。其实,缺乏故事性的何止是小说,包括电影电视在内的叙事艺术似乎也都患了故事缺乏症。具体表现为:一个不大的事件往往要被创作者充分发挥和利用,拉长成一个很大的作品,添油加醋、大量兑水。这样的作品开头往往也很吸引人,但越到后来越拖泥带水,东拼西凑,最后则是草草收场。故事缺乏症的另一表现可从当前影视艺术的改编风潮中略见一斑。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的被多次改编以及其他一些小说经典的反复翻拍,给人的强烈印象就是:故事已被说完了。由此看来,拥有故事确实可算作当今小说家们的一大幸事。而伍女士对故事原型的占有也实在可令众多作家嫉妒不已。《要嫁就嫁金山伯》在故事性上可谓是占尽优势:“伍平安杀妻”的故事;“王俏蓉变身九天玄女”的故事;“梅奇珍冒死偷渡”的故事;“雪红与养子通奸生子”的故事;“爱美嫁亲哥以复仇”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明显带有特殊群体的特殊生活之印记,新奇而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使读者在震惊中又倍感真实。读者很容易因此产生一种认识:书中故事不大像是人为编造出来的,而是真真实实发生过。也许,世上没有比这种“真实的怪事”更吸引人的了,于是,读者便由于事件的离奇与真实而越发感到惊讶并在惊讶中充分享受源源不断的审美刺激。实际上,笔者也正是被这些令人称奇的故事所吸引从而进入到一个轻松而紧张的阅读胜境。除了主要人物如伍平安、王俏蓉、梅奇珍、刘日昌以及雪白、俏桃等均有各自奇特的经历之外,一些笔墨着色不多的人物如“芳姐”、“猪肉佬”、“三叔公”甚至“三叔公的媳妇”等也都有其不俗的生活背景,只不过作者要叙述的事件太多,一时顾不上他们罢了。伍可娉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动力是“海外华人先辈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故事,不说出来,恐被后人忘记,就太可惜了”(作者在研讨会上的自述)。既然故事原型如此充裕丰盈,作者自然无须做太多的人为加工,而这些未经勾兑的“原汁原味”的故事,对于在散文化小说艺术中浸润已久的读者而言具有怎样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
其二,细节的丰富和真实。说到细节描写,这是作者最得心应手的地方,无论是侨乡台山的生活还是海外金山的场景,每每下笔之处,无不生动传神,可谓落笔生花。以至刘荒田先生赞叹不已:“铺陈奇情易,达致地道难……读它,一似夏日安坐于台山乡村的榕树头,听手摇葵扇的沧桑老人讲古;亦似周末在旧金山唐人街的花园角公园,听一堆台山女人吱吱喳喳的乡音。至为朴素的原生态,呈现人生和人性的本真。在假的潮流之外,这一虚构文本以成色十足的真为品牌,教人爱不释手。”[1]封底细节的充盈真切,使得小说叙事十分轻松自如,毫无殚精竭虑之态,这里的“反叙述”,实在是一种无意识的水到渠成,作者对海内外生活素材得天独厚的占有,大大减弱了“编故事”的工作强度。显而易见,一切就发生在作者身边,只需信手拈来,随性粘贴罢了。民俗方面如“解关”、“柚叶水洁身”等;神话歌谣如“九天玄女的传说”、“卖花女歌谣”等;生活场景如唐人埠的洗衣馆、王俏蓉咖啡店、梅奇珍金银楼的生活、刘日昌的理发馆、购买“出世纸”等等。有一个生活场景最为生动有趣而令读者记忆深刻,这就是华人在警察厅接受检查的一幕:警察问麦福佑及其弟弟的名字,主人公用方言回答“福佑”“福添”,其发音则让警察误解为英文“Fuck you”、“Fuck him”而大为光火。以上种种细节和场景如此真实可感、独特鲜活,实非“作家”们闭门造车而能为也。以熟悉的生活细节支撑起来的故事不仅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还在还原生活情态中体现了叙事的质朴:看看王俏蓉开咖啡店时的那身打扮:高跟鞋配大红袍,洋不洋土不土,活脱脱“唐人埠一景”。再看刘日昌的理发店:
一张方凳,上面坐着一个已理了半边头的中年男人,那围在颈上的白布盖住了他的上身,他对面的木板墙上挂着一面约四个巴掌大的镜子,镜子两旁贴着两个漂亮西人男子的画报,那画大概是从杂志剪下的。镜子下方有个小木架,上面放着两件理发工具。侧面木墙上挂着两块白毛巾,下方一个水龙头一个洗手盆,背面木墙贴着一中一西两个美女海报。[1]34
寥寥几笔,海外华人的生活境况跃然纸上。凡此种种,一声“老番婆”的咒骂,让我们听到了台山人独特的音调;一个“两人同吃一碟斋粉”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了海外华人生活的艰辛;那“每月650美元工酬”的惊喜,把生活细化到“十位数”;那“肿得像熟番薯裂了皮”的“手”的描述,将画面清晰到高倍放大镜的程度。毫无疑问,小说中对细节的呈现,是最能体现“原汁原味”的地方,也是小说最有价值的部分。
二、“话本式”叙事方式
如果说《要嫁就嫁金山伯》可读性强只是由于作者对原材料的占有,无疑是不公道的。伍可娉女士不仅以广东人对“原汁原味”的偏爱为我们极力保持了侨乡侨民生活特有的风貌和色彩,还以其对生活和艺术的“直觉”,“艺术地”保留了故事素材潜在的感染力。
小说在叙事方面并非没有构思,反而是颇具匠心的。小说的开头结尾相互呼应,第二十二章所有的重要人物在王俏蓉的临终病床前聚集,尤其是爱美的身份与动机的揭秘,安排得非常奇巧,令人称叹。既然作者在叙事上确实也曾用心“经营”,那么,小说又是靠什么保证故事的“原汁原味”,即小说审美形态自然朴拙的呢?
第一,总体上保持讲故事的“话本小说”的叙事方式,且在人物事件上力求完整清晰,以凸显叙事风格的原始质朴。从叙事角度上看,小说采用的是全知视角,即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叙事。这是一种传统的叙事角度,最大程度保证了事件的完整清晰。从时空建构上看,小说尽管并非直线叙述,而是运用了插叙、倒叙等手段,但仍十分留心事件发生的轨迹,甚至是十分用心地不断地设置阅读“路标”。为了方便读者把握故事情节,作者还有意吸收“说书”的结构模式,在每章开头设置标题以点明故事内容,在结尾处亦不忘“收官”以留下深刻记忆。作为一种讲故事为主的小说,作者在事件和人物命运的交待方面是绝不含糊的,涉及主要人物的事件自不必说,即便是次要人物,作者也力图将其来龙去脉说清楚。比如雪红所收的养子“启光”,本不算什么重要人物,既无形象描写也无性格刻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无关重要的人物,作者也牵挂不忘,让其在雪红出国与刘日昌团聚之前“凭借家有金山路”,而娶了一个“容貌一般的黄花闺女”,从而获得了一个完整结局。总之,小说在叙事上处处体现了作者对事件的重视,也因此奠定了作品在叙事风格上的基调。
第二,心理活动书写的表层化和半叙事化,以实现“轻松阅读”。心理活动展示的层次是区别现代小说和传统叙事的一个重要标尺。《要嫁就嫁金山伯》在心理活动描写上并不追求深层发掘,而重在展示人物行动的动机和事件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说,心理活动的展示通常处于理性的层面并具有叙事的功能。小说在人物心理活动前常用“想”、“思量”、“自言自语”之类的词来提示,这与现代小说的意识流书写形成极大反差,而且在用“引号”特意标示出来的心理活动中,有许多是直接说给读者听的。比如关于“俏桃”的一段心理活动,作者这样写道:
看着整齐的家和屋外清静整洁的马路,她的心情如浪涌起,不觉自言自语:“本来,来到金山有丈夫照应,有屋住是最幸福了,但我的心却不快乐,主要原因是丈夫对我很生疏,而且忽冷忽热,有时三更半夜也不回家。他究竟上哪里去了,他有别的女人?”[1]235
相比较现代小说所谓“深度描写”,这种心理活动的描写似乎太清晰太完整太生硬也太幼稚,但如若放在“讲故事”这样的叙事背景下来看,这种不追求心理深度的书写笔调恰恰与整个叙事风格相吻合,充分体现了“原生态叙事”的叙事特质。
三、“华侨体”叙事语言
伍可娉小说的语言形态较为复杂。有时候直白稚嫩,有时候老到成熟。小说中有许多关于“男女激情场面”的描写,其语言均十分精准细腻,如下面这段写青年梅奇珍美丽身姿的文字:
她快步走着,晚风吹着她浅蓝色的褶裙,每走一步都卷起一个蓝色的波浪,那波浪一下下滚动着从第三宿舍直至第八课室。[1]138
这段文字自然贴切,流畅诗意。还有一些极富生活气息的特色比喻,比如形容俏蓉剥虾壳时肿胀的双手“像两条淡红的熟番薯裂了皮”,写梅奇珍拥抱丈夫的动作“像饿水蛭吸人血般”紧箍着丈夫的脖颈,等等。这些句子和段落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者不俗的语言功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伍可娉小说的语言基调仍然有着明显的“华侨体”特征——半文半白、古今杂糅。如下面这段对王俏蓉和麦福佑家庭生活的叙述:
她(俏蓉)看着红肿的双手哭了。麦福佑骂:“不做也罢,哭什么?”王俏蓉负气地真的辞了工,由麦福佑一人在肉店当杂工维持家计,他每天天未亮便上班,下班后总说累,总是叹气。王俏蓉知道他并非累成那样,而是爱美的官司使他没面见人,便说:“叹气也没用,你若太辛苦,便让我找份住家工做吧。”麦福佑大发脾气:“我们出的丑还不够吗?你去虾厂做不成,车衣你又不会,还能做什么?去做女佣,我的面子往哪里放?”[1]124
这段文字,有人物对话,有事件交待,语言表达上均简单直接,基本不作描述和分析,只求意思清楚明白。然而,就是这种不提炼、不加工、不润色、不追求语言张力的“大白话”却不时夹杂些“罢”、“若”、“便”等文言文字眼,透着些“之乎者也”的“夫子”气息。其实,这半文半白的表达,并非作者弄巧成拙,实则是一种通行于海外华人“民间书写”的独特文体语态。之所以限定为“民间书写”,自然是基于其文体形态的生涩幼稚和使用者的文化草根性,并不是指所有的海外华人的写作。客观说来,笔者所指称的“华侨体”并非一种成熟的语体,相反,它凸显出的是使用者多元文化身份而形成的对母语的生疏和隔离。
此外,小说中每章的标题和结语,文字皆浅显粗放,不事修饰,文白杂糅,生涩朴拙,此类表达应视为伍氏语言的正宗语态。也是海外华人民间写作的标志性特征。
总之,小说在叙事语言上呈现出了一种陌生而熟悉的味道,这种中式传统被异域化了的奇特韵味,其意义如同“泡菜”,本为保持“原味”(传统),却不经意地创造了“另一种原味”(异域化、港台腔、“华侨体”)。
四、“原型化”人物形象
说到小说中的人物,笔者更愿意称他们为“原型”而非“典型”。“典型”是加工创造出来的,而“原型”则以自然常态为特征。这样说并非指作者没有笔力创造出典型,而是强调一种创作态度。在创作风格、创作理念五彩斑斓的今天,“典型”其实早已不是一种标准了。
“典型”的基本要素,一是“个性突出”,二是“概括性强”,更精练一点的说法就是“寓共性于个性之中”。总之,无论是“个性”还是“共性”,都要求作者有一种对“原型”进行“概括”、“提炼”的自觉。经过“概括”、“提炼”出来的人物,往往有鲜明突出的性格,有合乎逻辑的行动,有复杂完整的心理,当然还有一定的人性深度。
伍可娉《要嫁就嫁金山伯》中的人物个性鲜明、生动鲜活:俏丽而世俗的王俏蓉、文雅又变态的梅奇珍、温和而简单的李雪红、浮躁自私的麦福佑、老实厚道的刘日昌以及儒雅软弱的伍国新等等;他们那些奇异的经历、非常的境遇、被残酷的现实撕碎的情感、在虚华与穷困遮蔽下的人性,那些深沉的妥协、质朴的浅薄……一切的一切,清晰而深刻。其中,尤以梅奇珍的形象令人难忘,那绝望中的声嘶力竭,那沦落后的斯文扫地,曾一度令笔者深陷人物所处的境遇和情绪之中而感慨唏嘘。不过,笔者却并不打算给这些人物贴上“典型”的标签而宁愿称其为“原型”。这是因为:
第一,小说细节的非典型化,冲淡了人物性格。如前文所言,典型形象通常意味着性格的鲜明突出,完整统一。典型是塑造出来的,这种塑造当然包括细节的筛选和提炼。而该小说在铺陈人物生活细节时,似乎并不在意将细节统一到性格中来并且为典型性格服务,而是依从事件发展和人物境遇的真实状况自然地陈述。有些细节不仅不能衬托、强化人物性格,反而还起到冲淡、消解性格特征的作用。比如小说关于梅奇珍在金银楼生活的描写,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一个是梅奇珍听说自己的工薪是每月650美金时的反应:“六百五十美金?”作者只用了这一句话,便将梅奇珍的惊喜展露无余,而其一贯所有的自尊矜持、知性文雅以及刚刚遭遇感情背叛所激发起来的愤怒,则伴随着这份惊喜而烟消云散。另一细节是她发现自己收来准备带回家的食物有短缺时的叫喊:“是谁吃了我的叉烧包?明明是两个,现在只剩一个?”从这句话中,我们听到的是说话人的精明与泼辣,这无论如何也不能与那个清纯羞涩的梅医生联系在一起。性格的复杂与变化本来也可归于典型,问题是作者似乎并不太在意给这种变化以必要的心理铺垫和性格发展空间,而只由着事件的推进真实地描述人物当下的行动。更有意思的是,主人公的这两句话语,出奇地平庸,只是两句很平常的询问,没有任何带有感情色彩或有“意味”的字眼。显然,作者并没有按照塑造“典型”所需要的那样对人物的言行进行必要的加工,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一种塑造人物的“自觉”,因此,这些细节实际上是非典型化的,所以还是用“原生态”来表述更为恰当。
第二,拒绝制造心理高潮,淡化“典型心理”特征。人物性格和形象的塑造往往要通过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充分展示来完成。一般而言,现实主义作家在展示人物心理时,倾向于推理并营造人物的心理高潮以突出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特征,如《复活》中马丝洛娃堕落前的悲剧心理。不过,在《要嫁就嫁金山伯》中,笔者看到了完全相反的书写。小说中几位主要女性的悲剧心理是很值得书写的,也是很容易制造出激荡人心的悲剧心理高潮的。但实际情况是,每当她们的悲剧心理即将上升到高潮时,却总是被一个现实的念头轻易化解。例如,李雪红因与养子私通的事遭到丈夫刘日昌的嫌弃,用尽心思讨好丈夫却换来一次次的辱骂和冷暴力,雪红由愧疚到期待,由期待到失望,由失望到愤怒,她甚至做好了离开金山回大陆的准备,并且向别人表达了内心的这份自尊。然而,就在这时,丈夫用强暴的方式“亲近”了她,于是,几近达到悲剧心理高潮的她只用了一句“两公婆,床头打架床尾和”就顿时化解了心中积聚已久的悲凉。应该说,小说中最震撼人的悲剧心理还要数梅奇珍遭遇命运的大起大落之后的愤怒与绝望。她的悲愤,本应该在吃安眠药自杀未遂后达到高潮。然而,作者却同样让一个“世俗”的念头将其化解了:
她重新拿起桌上的信和钱,正想一手把它撕掉,又刹地住了手。死而复生的她心情似乎平伏多了。“事到如今,何必还要与钱过不去呢?”她翻着那几张百元美钞在想。[1]200
这一心理活动,乍看起来很不符合梅奇珍知识女性的个性,然而,它却十分符合生活的实际。试想,人间有多少不幸和愤懑不是靠了这种妥协而化解的呢?梅奇珍在现实面前的妥协屈服,这种不失时机的变通,不仅反映出女性在生存困境面前的无奈与智慧,甚至蕴含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和智慧。因此说,小说中的这种心理描写是更具真实性的,是超越“典型”的另一种真实,因而也更具有人性的深度和文学表现的力度。
对《要嫁就嫁金山伯》及伍可娉小说的分析解读有多个角度,但以“海外华人民间写作”的角度观照,是笔者的特别用心。“海外华人民间写作”的原生态,是一种在自然状态下摹写生活的艺术状态,是一种饱含“情感冲动”却不计较“章法”的“文学粗加工”。其价值让人想到马克思对希腊神话的评价:一方面以情感、细节等原型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武库,同时自身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据笔者所知,海外华人民间写作队伍庞大,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至今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果把伍可娉的小说创作当作一种“现象”来看待,把其“原生态叙事”放在“海外华人民间写作”的大课题中来探讨,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刘荒田. 要嫁就嫁金山伯[M].纽约:纽约商务出版社,2010.
[2]傅修延. 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J]. 江西社会科学,2009(8):46.
[3]佚名. 原生态文学[EB/OL].[2014-05-18]. http://www.docin.com/p-814533932.html.
[4]亚里士多德. 诗学[M]. 罗念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