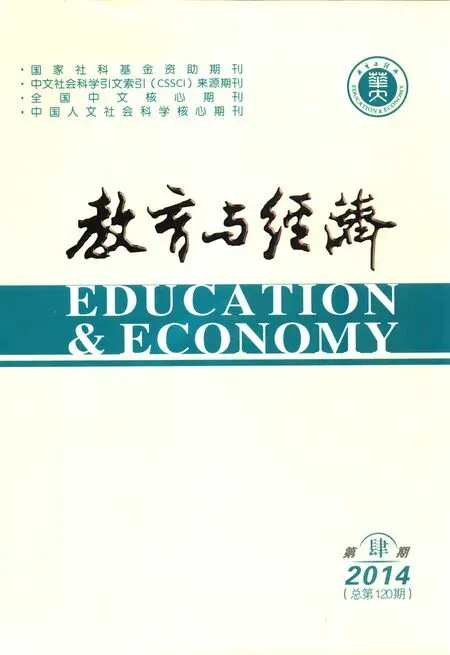试论职业教育的制度环境
许竞
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
试论职业教育的制度环境
许竞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北京 100029)
本文以系统论为理论基础,主要从教育的社会性、学校教育制度以及社会劳动分工和用工制度等角度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文章认为,教育体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它能够在个人身上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力;教育类型的分化是以社会职业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为前提;将教育类型狭隘地二分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是导致职业教育受鄙薄的观念性根源,以这种观念上的偏见为支撑的教育分流制度造成了教育系统内部的不平等;学校职业教育不可弥补的缺陷在于,它无法模拟或复制真实的工作氛围与工作关系,因此有效的职业学习必须依赖于现实工作世界的教育性资源,然而工作场所职业学习资源的可得性则得益于趋向扁平化的用工制度。
职业教育;制度;职业;分工;用工
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的社会活动,它首先是一种“教育”,其次是一种与“职业”有关的教育。我国职业教育受众已占据半壁江山,职业教育质量日益影响到我国人力资源整体价值的提升。职业教育发展目标与社会职业变迁以及用人规格的变化之间存在内在联系,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有赖于“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而这种跨界的合作与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综合治理的结果。制度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必然成为职业教育改革者诉诸的对象。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职业教育所处的制度环境进行考察,从而明确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本文从系统论和社会学视角考察职业教育所置身的宏观社会制度环境,主要分析了职业教育系统与学校教育系统、社会劳动分工以及用工系统之间的关系。
一、系统论的基本观点
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是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他在《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1968年)中将“系统”界定为“相互作用着的诸成分的综合体”。[1]这表明要构成一个系统,首先必须具备至少两个或更多组成部分,其次这些成分之间必须以某种直接或者间接方式发生着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指,若干要素(p)处于若干关系(R)中,以致一个要素p 在R中的行为不同于它在另一个关系R’中的行为。如果该要素的行为在R和R’中并无差异,那么就不存在相互作用。[2]因此,要理解一个事物,不仅要知道其组成部分,而且还要知道这些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提出的另一个概念“等级次序”(hierarchical order)是指构成某系统的任一个别成分与其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的次一级系统之间的交迭关系。由此,他提出的观点是,我们不能从各个孤立部分概括出整体的行为,为了理解各个部分的行为,必须要考虑各种从属系统与其上一级系统之间的关系。[3]前苏联哲学界较早研究系统理论的学者萨多夫斯基(1984年)提出,某系统的属性是由组成该系统的诸成分之间存在的那种联系和关系的特点
所决定。系统诸成分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及其所派生的系统的综合属性和整体属性,使系统能够相对独立地单独存在而且发挥功能或者(在某种情况下)得以发展。对于每个系统而言,除了它所具有的多种内部的关系和联系之外,还有许多外部的关系和联系。[4]
根据上述系统论观点,社会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社会制度则体现在多个不同方面,其中包括学校教育制度、社会劳动分工制度和用工制度等。这些社会制度之间的影响作用不仅表现在各子系统内部,而且也发生在各子系统之间的交互面上(如图1)。以下分别从这些方面来考察职业教育所处的制度环境。

图1 职业教育内嵌的制度环境
二、教育本身是一种社会制度
教育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一个社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其教育的功能和用途是不同的。不同的社会在同样一个历史时期,其教育的表现形式和结果也不同。我国教育学家顾明远先生曾经总结说,世界上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教育学家都未曾对教育做出完整的定义,教育通常被人们笼统地解释为“是一种社会活动或者社会现象,其本质在于培养人”。[5]既然教育是发生在特定社会里的活动或者现象,那么它必然是社会学家关注的对象。作为西方社会学奠基者之一,涂尔干就曾经指出,教育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发生无穷无尽的变化。如果把教育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中抽离出去,而去询问理想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这就无异于默认了教育体系本身并无实在性。[6]因此,教育在涂尔干眼里也是被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来看待。
既然被作为社会事实,那么教育必然具备社会事实的基本特征。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是一类具有特殊性质的事实,其特殊性表现在:其一,它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却对个人具有强制力,其二,这类事实不是一种有形之物,而是一种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或者感觉方式。这种事实不同于有机体现象,因为有机体现象由表象和动作构成;也不能把它们与仅仅存在于个人意识当中并依靠个人意识而存在的心理现象混为一谈。这种事实只能用“社会的”(societal)一词来修饰,因此称之为“社会事实”。涂尔干曾明确提出,可以把一切由集体所确定的信仰和行为方式称为“制度”(institutions),因此社会学可以被界定为关于制度及其产生与功能的科学。[7]如果我们考虑到每个社会既定的发展阶段,那么每个社会都有一种教育体系,这种体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它能够在个人身上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力。任何一种教育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宗教和政治组织、科学的发展程度以及产业状况等,如果撇开所有这些方面的历史因素去考察教育体系,教育体系则变得无法理解。[8]因此,教育本身具有社会性质。
虽然任何一种社会环境下的教育具有其特有的社会性质,但是教育之所以成为教育,必然有其共同的特征。从中抽取这些共同的特征,便构成了对教育的定义。涂尔干得出的教育定义是:“教育是年长的一代对尚未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儿童身上唤起和培养一定数量的身体、智识和道德状态,以便适应整个政治社会的要求,以及他将来注定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教育影响的范围不仅限于人的肢体方面,而且还涉及到人的心智和道德层面。这三方面的教育影响是面向人人,目的是为了让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下的所有人适应整个政治社会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社会环境下的教育都具有单一性。然而,涂尔干又指出,任何社会下的教育体系都呈现出双重面貌,即它既是单一的,又是多重的。[9]上述涂尔干所述教育目的后一句则说明了教育影响的多重性。显然,出生于同一社会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特定环境必然是不同的,这种特定环境是因种族、阶级、阶层、家庭、职业等方面差异而自然生成。以职业为例,每一种职业本身则构成了一种自成一类的环境,它不仅需要特殊技能,也需要专门知识。在这些技能和知识当中,某些特定的观念、实践以及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居于主导地位。[10]因此,教
育的目的也是为了使人适应他未来所处的这种特定的职业环境。
那么,既然职业是各异的,而且职业本身在性质上也是不平等的,[11]从某一个点开始,教育的分化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偏重于强调职业本身的不平等性,那么我们必须承认现代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一种完全同质而且绝对平等的教育。但是,如果从社会劳动分工的角度看,这时出现的教育分化是以社会职业本身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发展为前提。况且,倘若缺少了这种因分化而出现的差别,社会成员之间的协作则不可能产生。这种分化和差别是产生社会分工的前提,有了分工,每个社会成员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从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社会也才得以存在。[12]
教育的分化意味着教育也有许多不同种类,就像既定社会拥有不同环境一样。当儿童长到某个年龄时,开始为适应其未来身处的职业环境而接受某种教育。这种教育在类型上的差异表现在各个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特定观念、实践以及看待事物方式的不同。可以说,既定社会里有多少种职业分类,这个社会就会有多少种教育类型。假如既定社会里不同职业之间在工资和社会地位上是平等的,而且教育影响的效果达到了同样的标准,那么就不会出现教育类型的不平等。
但是,在现实中,某些特定社会里的教育不平等常常是源于人们在认识观念上的偏差或者偏见。比如,归纳起来,人们对现代职业教育的认识观大致有两种:一种观点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方面来看待,亦即教育具有多方面功能和作用,而向受教育者传递与职业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只不过是教育本身所具备的众多功能和作用之一。美国民主主义教育哲学家杜威便是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他主张,现代学校教育本身必然包含着职业教育的成分。[13]即使我们不对各种教育从内容和性质上进行分类,人所受到的教育总是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其未来所从事的职业活动发生关联。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即从类型和性质上将教育狭隘地二分为“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或普通教育、通识教育)。这种教育类型说不同于上面涂尔干所说的以职业为分界的教育类型。将“职业的”与“学术的”相对立,无异于向人们的意念中传递这样一种信号——从某个点开始,有些人需要为职业做准备,而另一些人则不需要。原本是一种人人都要面对和经历的事实,却扭曲成了一种个人竞争性选择的结果。这种教育类型二分法不可避免地导致受教育群体内部出现等级差异,甚至分化现象。当美国政府在1917年颁布《史密斯·休斯法案》之际,杜威就对这项立法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该项立法会导致分轨制的产生,移民和低层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少年会陷入被孤立的困境。[14]所以,尽管杜威的教育思想其实并不有悖于职业教育本身的存在价值,但他却反对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单列出来。
上述两种不同的职业教育认识观导致了职业教育在学校教育制度中的两种不同位置。一种是实施综合学校制度,即学校之间不存在种类之别,学生按年龄有序接受单一性质学校的晋级。尽管学校不在类别上加以区别,但是通过课程多元化,以满足不同能力和兴趣学生的各类教育需求。这类学校的毕业生在资格证书上不会产生类型差异,可能存在的差异只是在于学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另一种学校教育是实施分轨制度,即在普通教育之外另辟分支,并赋名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除了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差别在于两类受教育群体在进入就业市场时间上的早晚之差。通常情况是,受职业教育的年轻人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就业。受普通教育者则会继续接受更高水平学校教育,并由此推迟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时间。由此,预备劳动力在从学校向工作世界过渡时便实现了一种有序流动,即一部分已经掌握一些基本职业技能的年轻人进入经济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为接受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而做通用知识和技能上的预备。
总之,这种分轨制学校教育在客观上规定了个人最初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教育制度对个人与工作之间的匹配产生了长远影响。德国有位学者曾用“标准化”和“分层化”两个概念解释教育制度的性质对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后果所产生的影响。她指出,人若是在实行“标准化”的教育制度中接受教育,那么他在劳动力市场上变换工作的频率就相对较低;若是在实行“分层化”的教育制度中受教育,他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身份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因此,从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所获得的就业机会及其所经受的限制看,受教育年限和受教育程度这二者的真正意义,完全取决于这种教育制度本身的特性。[15]这意味着个人在学校教育当中所获得的教育量及其所经历的职业生涯,依赖于他曾经所身处的教育环境。
三、学校教育中的制度干预
学校教育制度影响着个体受教育的方式和结果。
学校教育中有哪些制度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发展呢?在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就是规则,在社会学家看来,制度就是社会事实。[16]两种看法并不矛盾,经济学家对制度的理解是从影响方式来说,而社会学家的关注点则是这种影响所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由于在治理和调节社会活动时采用了不同规则,因此造成了不同社会事实。那么,按照这种推理,我们可以通过当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事实,来识别现行制度。须注意,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制约对象和应用范围。从我国教育实际出发,大致有三方面制度对职业教育产生直接影响。
其一是义务教育制度。从名称上可以看出,“义务”代表的是一种强制性要求。我国学校教育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且最低入学年龄规定为6岁。这意味着年满6岁的儿童都会被其家长或者监护人送进学校上学,否则就是违法。对于不足6岁的儿童,学校则不予接收。因此,义务教育其实是既规范了学校,也规范了学生家长。从性质上看,这种义务教育属于通识教育,这意味着职业教育是发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之后。
其二是学制。学制是对教育过程的一种分段,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然裁断的性质。[17]110年前,我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学制(“癸卯学制”)。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我国学校教育开始实行6-3-3学制。该制度主要用以规范办学机构。目前,在我国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学校,几乎一律实行小学6年制、初中3年制、高中3年制。在这种学制下,年轻人在整个受教育阶段要经历三个门槛:首先是从小学升初中,其次是从初中升高中,最后是从高中升大学。这三个门槛设有三次重要考试,即小升初(12岁)、中考(15岁)和高考(18岁)。考试目的一般有两个,一是对一个阶段的学习经历(即学历)和学习能力(即学力)做出官方证明,二是按学习能力对学生进行筛选,然后因材施教。完成义务教育的年轻人通常会相继获得小学毕业证书和初中毕业证书。由于我国实行最低就业年龄是16岁的制度,因此,初中毕业一年后就可以在劳动力市场找工作。对他们而言,初中毕业证书是他们唯一可以向雇主证明其学历和学力的证明材料。
其三是分流制度。与前面两种制度相比,分流制度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尤为突出。近期国内有学者通过实证数据表明,我国教育分流以及重点学校制度对教育公平问题乃至社会不平等产生了负面影响。[18]分流制度亦称分轨制,其外在表现形式是单独设立职业学校。我国学校教育实行分轨制由来已久。《癸卯学制》颁布之时,当时就有“实业学堂”是单另设置,区别于其他学堂。民国最初十年,当时的“实业学校”也是单设于普通教育之外,而且还有层次上的划分(即甲种、乙种)。《壬戌学制》颁布后,虽然实业学校被“职业学校”取而代之,但依然是单设。分流制度是在学制基础上,在每一个门槛处按某种标准对学生进行筛选。最常见的筛选标准就是以考试的形式考察学生学习能力。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处理被筛选出的结果。当追求效率一旦成为学校教育发展目标时,学校会对学生按其学力程度进行分流,考试成绩靠前的学生被分流至“重点”学校,成绩靠后者则被分流至“普通”学校。这意味着与学生学习能力相对应的是一系列在教育质量和实力上存在程度差异的学校。目前,小升初考试便是这种性质的分流制度。虽然所有初中(重点的和普通的)都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教学大纲和指定教科书对学生提供初中教育,但是由于校际师资力量和教育资源等方面差异,必然导致普通学校学生难以享受重点学校优质教育资源。也就是说,由于这种分流制度的存在,一部分青少年在接受初中教育过程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其不公平性表现在,这种制度安排是仅仅建立在一次性考试成绩的基础之上。
与这种导向“重点”和“普通”学校的分流制度相比,更为重要的分流起于中考这个门槛。假如初中学校都实行通识教育,那么初中校际差异可能更多是与教学质量有关。但是,高中阶段(即后义务教育阶段)校际差异就不仅仅在于教学质量,更重要的与教育类型和教学内容有关。这个阶段学生所面临的分流是一种更为严格而残酷的分轨制度,即通向不同的目的地。按照中考成绩,成绩靠前的学生被分流到普通高中进一步接受通识教育,为进入大学做准备;成绩落后的学生或者被分流到职业学校接受与职业有关的教育,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准备,或者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打零工的机会。[19]这说明,一部分完成义务教育的年轻人是被这种官方的制度手段归入职业教育路径。
设想假如不存在这种分轨制度,这部分年轻人仍可继续接受通识教育,那么他们在高中毕业时至少可以与那些中考成绩靠前的年轻人一样获得“普通高中毕业证书”。他们高中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就可以向雇主出示同样性质的学历资格证明,即接受过高中教育程度的通识教育。但事实上,由于有一部分年轻人被分流至职业教育路径,他们在从职业学校毕业时将不可能取得“普通高中毕业证书”,而是取得职业学校毕业证书。那么,持有后一类学历证书的年轻人在劳动力
市场上就会受到雇主的不同待遇,这取决于雇主对“普通高中毕业证书”和职业学校毕业证书的认可度,也就是两种证书所传达的标准化和市场价值信息。在第3个门槛(即从高中到大学)的分流是根据学生高考成绩,这次分流对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专业类别(如文、理、工、农、医)、教育层次(本科、专科)以及学校声望(即重点高校与一般高校之分)。专业类别与劳动力市场的职业类别相对应,不同专业将导向不同的职业生涯。
然而,任何职业都是有结构的,它包含一系列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对从业者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要求,这就是职业本身的分层化特征。在面对这种职业本身的分层化特征时,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实施一种以培养多面手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即接受这种职业教育的学生被要求掌握该职业所包含的所有一系列工作岗位的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要求。这样,他在完成这种职业教育时所获得的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向雇主证明他可以胜任该职业范围内的任何工作岗位,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所体现出的标准化程度既便于雇主使用这种劳动力,也拓宽了求职者在这一职业中的就业机会,因为他可以从这一系列的工作岗位中做出选择。另一种处理方式是人为地将某一职业所包括的一系列工作岗位划分成若干等级,然后由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分别来承担专门针对较低和较高级别工作岗位的职业教育活动。这种人为划分其实就是一种制度干预。
四、职业是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果
职业是对于社会劳动的分类。劳动是一种人为的活动,它具有目的性和方向性。作为个体的人必然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随着工业在各种社会环境下不同程度地发展起来,人们在这些社会中所从事的职业要远比农业社会中的职业分类复杂得多。职业类别的不断分化和更替象征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也体现了社会劳动的专业化程度的增强。由于专业本身的不可替代性,导致其他人被排斥于这些专业之外,而去从事一般性的职业活动。由于职业是属于社会,而工作才是属于个人,[20]所以,职业分类的变迁和进化决定着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分配和流动。
然而,职业具有特有的社会属性,这种属性体现为人们在理解职业这一概念时所持有的偏好或者偏见。语言是社会属性之一,我们可以从职业一词对应的英语和德语来比较在英语和德语社会里人们对职业的理解有何不同。比如,电工和律师在德国都被称为“Beruf”。[21]据一位熟悉德语的英译者说,英语里没有与德语“Beruf”涵义完全对等的词汇,Beruf这个词可以被译成“occupation”、“profession”或者“career”,但是德国人所说的Beruf还涉及到人所受到的“训练”(training),以及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status)。德语Bildung也同样,在英语中没有一个对等的词汇可以表达其涵义,因为它同时包含有“训练”、“教育”以及“文化”方面的涵义。[22]由此看出,在德国社会和英国社会,人们不论是对“职业”还是对于“教育”的理解,都存有差异,相比之下,这两个概念在德国社会的寓意似乎更为丰富。正如有德国人曾精辟地说:大多数德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要寻找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想要得到一份职业——一份他将终其一生的职业,一份他将为之热爱的职业。若你在德国拥有一份职业,你则是一名了不起的人;若你只是有一份工作而已,你则什么都算不上。[23]
对于“劳动”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影响着人们对于“职业”的认识。有一位美国社会学教授在研究社会文化对人的工作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时发现,英国人所说的“劳动”(labor)比较含糊,而德国人在描述就业交换关系时惯用的词却是“劳动能力”(Arbeitskraft)。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1723-1790)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他们的经济理论都是将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视为等同于从一个有形商品中获得其所包含的劳动。而直到卡尔·马克思(1818-1883)才揭示了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能力”(Arbeitskraft,其英文表述是labor power或者labor capacity),而不是“劳动”(labor)。同样是将“劳动”作为一种商品,英国人在做工的时候可以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德国人则是既然受雇于他人,“自当倾其全力以为之”,即指德国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就业关系已经包含了购买工人在劳动中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能力倾向。[24]
上述例证说明,职业的现实涵义及意义实际上是被特定社会制度(包括文化)塑造而成。对于个人而言,职业是其社会生活的主要载体之一,如果说教育是帮助未成年一代为其今后生活做好准备,那么与职业有关的内容则是教育所不可回避的方面。杜威也曾说过,昔日教育其实更是与职业有关,只不过以前教育在名义上并不被称作职业教育而已。在“职业教育”这个名称出现之前,普通老百姓受到的教育确实具有明显的实用性,皆为满足其日常生活和劳作所需。假如将“享乐”和“治人”也视为一种社会职业,那么贵族和有闲阶级成员所受教育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职业教育。[25]当然,
实际上几乎在任何社会,人们并不把这些上层阶级所受的教育视为“职业教育”,而是称为liberaleducation(“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杜威对职业的意义进行哲学思考时指出,对于个人而言,有了职业,其人生则有了前进的方向。那么,职业的反义词是什么?他提出,从哲学逻辑上推断,没有职业的人,意味着其人生缺失了活动的指向,在个人身上表现为活动中的“漫无目的”、“反复无常”、“不积累经验”;它所造成的社会表现则是“人之慵懒无所事事或寄生于他人”。然而,人们在世俗观念上却将“职业”与“闲暇”和“文化修养”对立起来。[26]这说明,在任何社会环境下,人们所讨论的“职业教育”实际上是被特定社会观念化了的偏狭的职业教育,而不是一种理性的哲学概念。
五、分工和用工制度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工作世界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显而易见。当我们作为“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找工作”时,这里的“工作”是可数名词,即“一份工作”。而当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内部的员工,开展日常工作时,“工作”却更多是一个不可数名词,它可以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有时需要借助肢体动作完成,有时需要用头脑来思考,更多时候是头脑和肢体并用。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开篇指出,所有人类活动都包含着一定的脑力与体力活动因素,哪怕最愚笨的工人每天机械地从梯子上爬上爬下,他也运用了自己的一部分智力。[27]无论不同职业间存在何种差异,人们都很难将其所做的事情归结为单方面依靠手工技能,或者是脑力、心智技能。
职业学校的实训场所,或者集中建设的实训基地,并非现实工作世界的一部分,它并不能产生真实的工作关系或组织结构,以及真实的生产过程带给工作者的那种责任感、压力和动机。[28]但是,这种责任感、压力和动机却是影响个体在工作场所进行主动、有效学习的关键动因,这也正是学校职业教育所存在的一个无法弥补的缺陷。那么,这意味着有效的职业学习必需依赖于现实工作世界的教育性资源。于是,近年来工作场所学习深受西方职业教育研究者的重视。[29]工作场所学习的最大优点在于,置身工作场所的学习者能够直接感受到真实工作带给他的一种压力,并接触到真实工作环境下各种人际或人事互动关系。这种无形感受与有形接触皆有利于有效职业学习过程的形成。工作场所教育性资源的内容和性质取决于现场工作所隶属的职业种类。
任何社会都是依据其特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把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划分成职业,并对各种职业类别从社会地位上进行高低排序。由此导致社会成员通过选择职业来追逐社会地位和身份。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三六九等”在多数情况下是社会治理的产物。相同职业在不同社会中享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则可以被认为是因制度差异而导致的分歧。因此,职业教育在社会中的目标定位与该社会条件下的劳动分工制度存在密切关联。
如果将职业教育与社会上的低端职业联系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消极影响呢?在决策者看来,根据“人尽其才”、“因材施教”的原则,“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或者对学习高深知识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应该去从事低端职业,那么高端职业只能归那些学习成绩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占有”——这种观念其实就是一种在很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贤能主义”识人和用人原则。那么,从事低端职业的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自然也被视为“低能儿”、“下层人”,从事于高端职业的人则是“精英”、“佼佼者”、“上层人”。这种现象就是因职业和用工偏见而产生的对职业教育的排斥和鄙薄。决策者以仲裁者身份对职业教育进行设计规划时,尽管高度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但却罕见他们将子女送去接受职业教育。他们有关职业教育的说辞只是针对“别人的孩子”,其行为的责任感和公正性只能仰仗其自身的道德与良知尺度。
社会低端职业中大多数工作属于制造业。制造类企业的劳动关系主要表现在雇主与雇员之间,而现代企业制度中雇员内部却存在等级分化,即经理人、工头、普通一线工人。这意味着位于同一工作场所的雇员是按照不同结构组织起来的实践共同体。这种实践共同体内部的组织结构要么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要么是一种相对扁平的关系。这种组织结构差异影响着雇员在工作中享有自治权的程度,在上下级组织关系中,下级员工听从于上级指挥,他们在工作中的判断力和自决权受到限制。这种上下级组织关系的极端例子就是福特制流水线生产。另一种趋向扁平化的组织关系则以日本大型企业所采纳的“精益生产方式”为代表。[30]处于同一工作场所的员工属于一个团队,各个队员彼此间有相互监督对方作用的权力,每个人都有随时发言的权力,甚至暂停整个生产过程。在这种精益生产方式下,员工之间的组织关系是相对平等,任何员工均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力对整个团队的工作对象及其进展状况提出改进意见。
在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场所,作为新进安置
进来的职业学习者而言,他嵌入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教育资源环境。在实行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工作现场,这位学习者看到的只是流水线上处于运作当中的设备为他展现的作业工序,来自现场一线工人的教育性资源则几乎不存在,因为工人的举动仅是重复性地回应机械设备预定的要求。而在精益生产方式的工作现场,学习者接触到的是生动的人际交往,包括员工对工作任务的即时应变行为、解决突发事件的办法、员工之间沟通方式等。这些动态教育活动几乎不可复制和模拟。这些例子说明,企业的组织结构对工作场所学习的效果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以上分别从社会制度、学校教育制度以及社会劳动分工、用工制度方面分析了职业教育内嵌的制度环境。那么,如何才能改善职业教育所处的制度环境,使其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呢?系统理论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思路。美国系统论学者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1985年)曾指出,多个系统之间互相构成对方的环境,一个(或一些)系统的变化就改变了另外一个(或一些)系统的环境输入,后一个(或一些)系统就在原有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调节,以适应或抵消环境输入的改变。当这种调节达到极限仍无法适应或抵消环境输入的改变时,后一个(或一些)系统就被迫改变内部的结构,自我创造出新的构型。概括言之,变革和发展皆是受环境所迫,这就是系统发展(进化)的机制。[31]这一观点对我们的启示是,要改变职业教育制度环境,就必须进行综合性的社会治理,从改变学校教育系统、社会劳动分工和用工等相关系统的内部结构入手,只有各相关系统之间都朝着有利于发展职业教育的方向调整自身内部结构,才有望为各系统之间的协调提供便利条件,从而促成整个社会制度环境朝着有利于发展职业教育的方向发展和进化。
[1][2][3][美]L·冯·贝塔朗菲.林康义译.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35,51,69,63.
[4][苏]瓦·尼·萨多夫斯基.贾泽林等译.一般系统论的原理:逻辑-方法论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9-90,91.
[5]顾明远.对教育定义的思考[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 5-6.
[6][8][9][10][法]爱弥儿?涂尔干.陈光金等译.道德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1,210,232,258,233,234-245.
[7][16][法]迪尔凯姆.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5,19.
[11][英]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92-98.
[12][法]爱弥儿·涂尔干.渠东译.社会分工伦[M].北京:三联书店.2009.24-25.
[13]Dewey,J.Democracy and Educa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M].Bristol,England:Thoemmes Press. 2002.358.
[14][美]托马斯·贝利等.许竞,项贤明等译.工作实践出真知:业本学习与教育改革[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
[15]Allmendinger,J.Educational Systems and Labour Market Outcomes [J].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9.Vol.5(3). 233,247,248.
[17]Pring,R.Labour government policy 14-19[J].Oxford Review ofEducation.2005.Vol.31(1):71.
[18]吴愈晓.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J].社会学研究. 2013.4.179,186.
[19]目前,我国每年有多少比例的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于打零工活动,这一数据值得去发现。这部分年轻人为什么选择放弃学业,以及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处的状态和后续发展,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性的因素调查很有意义.
[20][21]Streeck,W.(1996).Lean production in the German automobile industry:a test case for convergence theory,in Berger,S.& Dore,R.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A].Ithaca and London: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6.145.
[22][23]Greinert,W.-D.The German philosoph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in Clarke,L.& Winch,C.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developments and systems[A].Oxfordshire, England:Routledge.2007.59(英译者注释1-2),49.
[24]Biernacki,R.The Fabrication of Labor:Germany and Britain, 1640-1914[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41-43、211.
[27][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金镝,金熠译.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3,19.
[28]Steedmand,H.The economics of youth training in Germany [J].TheEconomicJournal.1993.Vol.103(420),1248.
[29]西方有关工作场所学习的早期研究成果比如Winch,C. Education,Work and Social Capital[M].London:Routledge.2000;K. Evans,P.Hodkinson&L.Unwin.Working to Learning:Transforming Workplace Learning [A].London:Routledge.2002;H.Rainbird,A. Fuller,&A.Munro.Workplace Learning in Context[A].London, Routledge.2004.
[30]Womack,J.P.,Jones,D.T.&Roos,D.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M].New York: Harper.1991.
[31][美]E·拉兹洛.闵家胤译.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科学新发展的自然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1.
责任编辑 范先佐

Abstract:Past researches on premium schools around the world focus on teachers and teaching quality,paying little attention to reasonable allo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within schools.The author conducts a 3-year longitudinal study in six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located in five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the paper,attempting to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intra-school resources for developing premium schools.
Key words:intra-school educational resources;reasonable allocation;development of premium schools
责任编辑 范先佐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XU Jing

Based on the system theory,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institutions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ree approaches,viz,the societal foundations for education system,the rol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in the education system,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job market.Education itself functioning as a social institution,has a strong influence on individuals,education a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diversified and professionalized nature of occupations.Vocational education is not valued originates from the dual track stratifying teenager students into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general education,leading to inequality and inequity within the education system.The defect of vocational schooling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fails to create a real working environment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s the reality in the workplace,which makes an effective skills-learning dependent on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a real world of work where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resources relies on a more flexible employment of labour force.
vocational education;institutions;occupation;division of labour;employment
F08;G40-054
A
1003-4870(2014)04-0044-08
2014-04-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西方职业技能形成理论与实践体系研究——基于跨学科的视角”(项目编号:CJA120158)。
许竞,女,中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