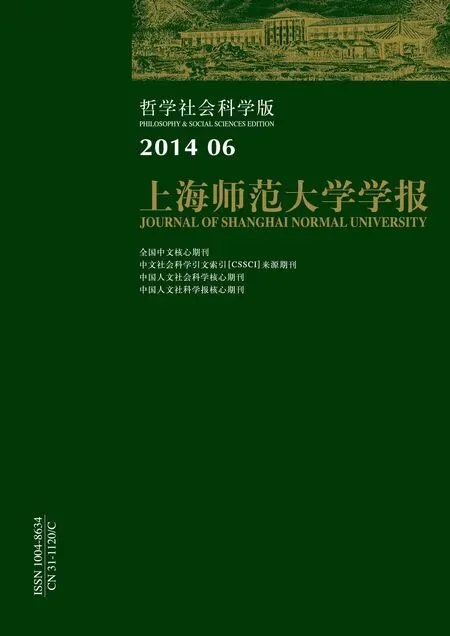隋唐精怪小说与佛教流播
夏广兴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精怪传说起源于原始的“万物有灵”思想,这是世界各民族原始文化的共有特点。万物有灵思想是神话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世界各国研究人类早期原始思维和文化的人类学家普遍认为它是早期人类原始思维表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最早提出并解释这个理论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他认为原始族群在形成宗教之前先产生“万物有灵”观念。原始先民往往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对于神、人、动植物的观念没有分别,认为神、动植物也和人类一样;并把一切具有生长或活动现象的东西,除动植物外的河流、日月以至山川等自然界的一切现象,皆当作具有灵魂(或生命)的东西。这就成为他们观察、理解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基本概念。基于这种观念的推导,由此产生了那些充满荒诞怪异内容的神话、寓言故事和传说。
本文所指的精怪故事是以精怪及其活动为描述对象的民间幻想故事,它是在民间原始宗教信仰基础上产生的。“精”者,《说文解字》释为“择米也”,即指优选的纯净米,又引申为生成万物的灵气。《庄子·在宥》云:“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①东汉王充《论衡·奇怪》有言:“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见奇怪,谓德不异,故因以为姓。”②“怪”者,据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七云:“凡奇异非常皆曰怪。”③据此可知,一切反常的事物或出现的未曾见过、不可思议的现象都属于“怪”的范围,它所涉及的要比“精”庞杂得多。所谓“精怪”,就是古代传说中的“物精”、“物怪”;或简称“物”,也就是人类自身以外世界上的自然物(包括有生命的动物、植物和山石、雨雪、日月、星辰等无生命物体)及人类制造和使用的器物,因自身获得了灵性或神性,或被精灵、神灵所依凭,而变为颇为神通的精怪。它既能化形为人(或具有人的某些特征),又能复现原形;既通人性,又具物性,并介入人间,作祟作怪,祸福于人。描写这种精怪及其活动的故事便是精怪故事。另有一途,即动植物幻化为人的意象还起源于原始社会动植物图腾崇拜意识。这种意识亦曾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原始氏族中,是先民渔猎经济时代的产物。费尔巴哈说:“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人的存在便依靠动物;而人的存在和生命所依靠的那个东西,对于人说,就是上帝。”④可见,对于动植物而言,原始的先民产生心理和情感上的关联乃至崇拜思想是不足为怪的。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具有悠久传统的民间信仰,在中华大地形成了各种瑰丽多彩的动植物故事和传说。在志怪小说中,宇宙万物无不具有灵性,而且往往产生出象征该物的精灵,像人类一样地活动,或造福,或行恶,具有人类一样的七情六欲。在泛神论观念的驱驶下,幻想了大量的自然界的动植物精怪故事,原始神话传说中就有许多类似的精怪传说。原始神话中的怪物异人,或者表现古民对某些自然现象原因的推测,或者表现他们对征服自然能力的渴望,均以精怪形式出现。还有,早期巫师出于自神其术的目的,也描述了一些怪物。此种由早期巫术产生出的怪物,或者与巫术的征兆、医药功能有关,或者是对遥远未知世界的臆测。这些原始神话传说、动植物图腾崇拜,或随巫术产生的怪物,就成为中国精怪小说发展的基础。
自汉魏六朝始创“志怪小说”一门,直至有清一代,延绵千余年,历代文人雅士,将流传于街巷市井的传说记录并加工,创作了大量动植物精怪小说。在中国,收录精怪小说最全的当属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编纂的《太平广记》,其中即专设“精怪”一门,大致能反映精怪小说演变、发展的轨迹。精怪小说,六朝始盛,但故事情节单一,叙事平铺直叙,缺乏变化。另外,由于当时世风确信鬼神之实有,小说创作亦为“发明神道之不诬”,故所叙多为实录的故事,缺少情趣。进入唐代,始“有意为小说”,此时之精怪故事不但叙事委婉,情节曲折,而且充满人文精神,张扬人性,显示大唐气象。明清之世,精怪小说日臻成熟。佛教传入后,精怪故事的思想、内容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一方面是建立在传统信仰演进的基础上,承接汉前精怪故事之余续;另一方面,接受了佛教文化的影响,增加了变化的活力,已大大超出中土士人的想象余地,此乃梵汉交融互汇的结果。鲁迅亦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现象,指出:“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的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⑤“志怪小说”一门是在佛教广泛流播的形势下兴起、发展的,其内容必然也在影响之列;作为志怪小说中的一大类的精怪小说,理所当然地亦在影响之内。近年来,从文学或是文化角度对精怪小说进行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为数不少,且新说迭出,但深入地探讨精怪小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特别是佛教传入所带来的影响,成果略显不足。本文拟对隋唐时期的动植物精怪小说的文化内涵进行解读,以探讨动植物精怪题材作品的内涵嬗变的成因及轨迹。
一
两汉之际,随着佛教的传入,原来只是民间的、自发的一般信仰也就在借鉴佛教理论组织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佛教的刺激下,对精怪故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思想了。许多佛教观,在僧俗两界的合力弘布下,浸透了精怪故事的骨髓,它们与精怪故事融为一体,难解难分,如果不细心分析甚至难以察觉。例如业报轮回观念,就是精怪故事与佛教文化中都具有的一种基本观念。自从人类脱离了混沌的蒙昧时代,善恶观就一直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调节着人们的处世行为,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的观念深入人心。精怪故事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自然会将人民的善恶观反映在其中。然而把善恶与报应结合在一起,却是佛教观念影响的结果。
佛教传入中土,在人们心中产生深远影响。其业报轮回的观念,在“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年代,被小说家广泛利用,给小说增添了表现的活力。但当时小说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不过是“丛残小语”,故其影响力还不够大。佛教文化向民间灌输自己的善恶报应观念,向来不遗余力。六朝时,佛教界的“唱导”艺术即是重要一途。梁朝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云:“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⑥与此同时,“释氏辅教之书”亦层出不穷,则是佛教信徒以小说形式弘扬佛家思想的结果。到了唐代,俗讲兴起,同时,大量的宗教劝善书流行,对当时的精怪小说产生很大影响。小说作家开始“有意为小说”,并充分利用佛教的思想观念,使所述之精怪故事内容更加丰富,情节更加曲折,叙述亦更加委婉。如对“业报轮回”观念的利用,佛教认为,在生死流转中的有情众生,常有升、沉、苦、乐之变,不停地在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之中轮回,生灭相继,因业受报;为善业升善道,为恶业升恶道,罪福报应,如影随形,谁也无法逃避这一自然法则的制约。精怪小说中有大量作品即是以此观念谋篇布局,设置结构,表现主题和思想。《续玄怪录》“张高”条记张氏家有一驴,张亡,妻命子骑驴营饭僧之具。出门,驴不行,击之,乃人言,曰:“吾今告汝,人道兽道之倚伏,若车轮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负汝父力,故为驴酬之。……汝父常骑我,我固不辞。吾不负汝,汝不当骑我。汝强骑我,我亦骑汝。”⑦《法苑珠林》“耿伏生”条记耿氏母将绢与女,数岁,母亡,变作猪身。……取绢与女,坐此罪,变猪。⑧其“王甲”条又载某母避其子送米与女被罚为驴。《宣室志》“李徵”条记李氏被疾发狂出走,月余不归。袁傪以监察使奉诏使岭南,遇虎匿身草中,人声而言,音似李徵。袁昔与李同登进士第,分极深,乃问之。虎呻吟数声,曰:“我李徵也。”虎曰:“吾前身客吴楚,忽婴疾发狂走山谷中……岂念我化为异类。”⑨《河东记》“卢从事”条记常有一人送黑驹经卢氏。后黑驹忽人语,告知其是丈人亲表甥通儿也。通儿少年无行,将丈人钱挥霍一空,后亡。冥间丈人征债急。平等王告知,若复作人身,待长大则不及,当须暂作畜生身,十年,方可偿。通儿遂被驱出畜生道,不觉在群马中,即阿马今身是也。⑩人因恶业而变成畜身,正是佛教业报轮回的直接表现。
根据佛教教义中所谓“众生平等”、“轮回报应”的说法,是动物亦或是人,其差别只是在外部形态上,而这外部形态还可以视其在上世所为而做一些改变(即报应)——前一世为人不善或欠了别人债不还的,这一世就很可能做驴或做牛做马。按佛教的观点,有情众生根据自己在前世所做的业,在“六道”中轮回,如失译人《佛说师子月佛本生经》云:“(比丘莲花藏)从地狱出堕饿鬼中,吞饮融铜,啖热铁丸,经八万四千岁从饿鬼出,五百身中恒为牛身,又五百身生骆驼中,又五百身生于猪中,又五百身生于狗中,又五百身生猕猴中。”可见,有情众生在“六道”的轮转中是以几世为代价的。“生死罪祸,皆有念作。刹那之间,即分天堂地狱,岂有前生后世也耶。”中土小说家在接受佛教思想时还有些发挥,即将佛教中人变动物或动物变人都是隔世才会出现的变化改为在此生此世也能出现,即所谓“现世报”。如《报应记》“岳州人”条云:“唐咸通中,岳州有村人涸湖池取鱼,获龟犹倍多。”“后归家,忽遍身生疮……举体投水中,渐作龟形。”报应如影随形,现世现报。又如《广异记》“牧牛儿”条载:“晋复阳县里民家儿常牧牛。牛忽舐此儿,舐处肉悉白。儿饿而死,其家葬此儿,杀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作虎。”《录异记》“蔺庭雍”条记“涪州裨将蔺庭雍妹因过寺中,盗取常住物,遂即迷路,数日之内,身变为虎。其前足之上,银经金钏,宛然犹存。每见乡人,隔树与语云:我盗寺中之物,变身如此”。业报神速,给人以警示。这是隋唐五代小说家把佛教的业报轮回的观念用于小说创作中,并有所增饰,以达劝惩之目的。
二
佛经中有大量记述佛、菩萨、帝释天等“随机现身”说法的故事,其中有许多变形情节——化为异类,广为说法,本生故事多是。释迦牟尼佛、菩萨、帝释天等均会变作任何禽畜类,如《佛说菩萨本行经》卷上记一菩萨施身于冢间,帝释天即化为众狗、飞鸟、走兽,欲来食之。唐义净译《妙色王因缘经》记帝释见妙色王为法忧恼,欲试之虚实,“遂即化作大药叉,身手足异常,面目可畏,来至众中”。另外,像护法神天龙八部、佛弟子或比丘等都有变形之异能。如箫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卷二云:“尔时山中有一树神,欲令王得见大德摩哂陀。树神化作一鹿。”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十五云:“昔此贵邦有一侨士适南天竺,同伴一人与彼奢婆罗咒术家女人交通。其人发意欲还归家,辄化为驴不能得归。”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一云:“于彼池中有龙王……每于月八日十四日,从宫而出,变作人形。”此种变形化现的描写在佛经中可谓信手拈来,比比皆是。如此神异、奇妙的变现,在佛教传入前的中土叙事文学中鲜见。这种变形的意识加入隋唐五代小说家的创作中,往往糅合了中国本土物久成精的迷信观念,成为一些精怪故事。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动植物能化形为人。如《集异记》“僧晏通”条记有沙门修头陀法,栖于道边积骸之左。忽有妖狐至,取髑髅安于其首。须臾,化作妇人,绰约而去。《广异记》“大安和尚”条记有女人自称圣菩萨,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后大安和尚至,与之论辩,女词屈,变作牝狐而走。同上“李元恭”条记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孙女崔氏,容色殊丽,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动物变人、人变动物故事的大量流行源于佛教的影响,即是在佛教文化的刺激和影响下出现的新东西。中土传统的物变人说法乃是物老成精,与前者有本质的不同。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云:“夫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象人之形。”葛洪《抱朴子·登涉》云:“山中有大树,有能语者,非树能语也,其精名云阳,呼之则吉。”“山中夜见胡人者,铜铁之精,见秦者,百岁木之精,并不能为害。”原始宗教的思想核心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原始先民由于认知水平较低,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生成、发展都匪夷所思,一定是由深不可测的神灵所主宰,故形成了所谓山神、水神、雨神等,这种观念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并行不悖地发展、流传。晋代郭璞《玄中记》中说:“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百岁之鼠化为蝙蝠。”“千岁之龟能与人语。”“千岁之鼋能与人语。”张荐《灵怪集》“姚康成”条记某入一廊内,听数人饮乐。及晓,并无此色人,唯见有铁铫子、破笛、扫帚。这种万物皆可成“精”,当然都是万物有灵的直接表现,是动植物精怪信仰的直接来源。
上述有关精怪变化的解释多出于原始宗教信仰或民间的信仰,说明精怪故事的产生是信仰文化的产物。
从动物成精变人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传统的“物老成精”的观念,有的是借助于某种方术,如《广异记》“王太”条夜中闻草中虎行,不久虎至庙庭,跳跃变成男子,衣冠甚丽。老虎变人,采用脱掉虎皮的方法,即是此种类型。但更多的动物变人、人变动物则被归结为宿命,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业力所致。如《酉阳杂俎》“王用”条记王用曰:“妻觉状貌有异,呼其弟视之,忽脱衣嗥跃,变为虎焉。”(王用)后曰:“我往年杀黑鱼,冥谪为虎。”《稽神录》“吴宗嗣”条记某人向吴氏借钱不还,召而数之曰:“我前世负汝钱,我今还矣,汝负我,当作驴马还我。”逾年,其人白衣而至,言来还钱,径自入厩中。俄而,有人报马生白驹。这种人变动物、动物变人,说明人与兽的分别甚微,不属于“动物成精”之列;那些出神入化的变形能力,实在是佛教刺激的产物,也即是佛教业报轮回教义影响下形成的另一种民间信仰,作家们缘此创作了大量精怪故事。
三
有些精怪故事乃是佛道之争的产物,即利用精怪故事反佛。在唐代有些人往往以小说形式为手段,攻击异己,如《补江总白猿传》《周秦行记》《牛羊日记》等乃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在小说进入“有意为小说”的时代,使小说又增加了一个功能。如《周秦行记》是“牛李党争”的产物,《补江总白猿传》则是影射欧阳询的,等等,不一而足。在宗教界亦存在此现象,因佛道之争,双方为了维护本教的地位,也会利用小说形式来攻讦对方。精怪小说正是他们所利用的一种形式。
精怪以佛教人物形象出现,以佛教信仰的形式来欺诳世人,作奸犯科,常被用来来揭露佛教的虚伪。如《广异记》“代州民”条记载:“母与女独居,忽见菩萨乘云而至,请母曰:汝家甚至善,吾欲居之,寻当来也。村人竞往,处置适毕。菩萨驾五云来下其室,村人供养甚众。”“菩萨与女私通有孕。”“窃视菩萨,是一老狐。”此处老狐化作菩萨淫人之女。同上“长孙甲”条记长孙甲,其家笃信佛道,举家见文殊菩萨,乘五色云从日边下,举家前后供养数十日,唯其子疑之,入京求道士为设禁,遂击杀狐。后复有菩萨乘云来至,家人敬礼如故,其子复请道士,禁咒如前。菩萨问道士:“法术如何?”答曰:“已尽。”菩萨云:“当决一顿。”并告知,自得仙已三万岁。因杖道士一百。《纪闻》“叶法善”条记某狐变僧作怪,乃执之鞭之见血,缚之往叶师处,道遇洛阳令,僧大叫称冤。入院,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师曰:“速还汝形。”魅乃弃袈裟于地,即老狐也。《潇湘录》“王屋薪者”记王屋山有老僧,独居一茅庵。忽一日,有道士来求宿,老僧不允。道士曰:“佛与道不相疏,混沌已来,方知有佛,师今佛弟子,我今道弟子,何不相容一宵,陪清论耳。”老僧曰:“我佛弟子也,故不知有道之可比佛也。”双方唇齿相讥,争佛道高下。有一负薪者过,知老僧与道士争佛道优劣,乃痛斥双方,并逐出山,两者化为物,乃知其皆精怪也。通过精怪故事来反映佛道之争,并从薪者之口,这又表明了儒者的态度。钱钟书于此亦已抉出。
精怪小说的创作又充分利用了佛经故事的某些类型。如报恩类型在佛经故事中多见,并有《报恩经》。报恩乃是佛经故事中的常见题材,亦是佛家所张扬之思想。失译人《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七云:“集如来躬,往病比丘所,即放顶光照病比丘,比丘遇光苦痛即除。如来即以右手,从天帝释受取宝瓶,灌病比丘顶,左手摩拭病比丘身,身诸疮病随如来手寻得平复。”“尔时如来告病比丘,如来今者念汝重恩,如来今者欲报汝恩。即说前世因缘。”《六度集经》卷三之“理家本生”、卷五之“难王本生”,皆叙某人救得一鸟、一蛇、一人,动物报恩,人则恩将仇报。佛经中赋予了这些被救的动物以人性,知恩图报。隋唐五代小说中亦充分利用了这一类型,在精怪小说中亦有,可见此等类型故事对唐小说的影响。《宣室志》“李甲”条载李氏其世以不好杀,家未尝畜狸,堂毁时因得鼠报恩之助而人无伤亡。又《闻奇录》“李昭嘏”条载李昭嘏举进士不第,后受鼠报进士及第。主司问其故,乃三世不养猫,皆云鼠报。《潇湘录》“周义”条记周义救一少年,其人乃虎也。临行化为一虎走去,后至周家,抛一金枕,告周义:“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将此枕,答君之惠。”言讫,复化虎去。这里所载多是因守不杀戒而获得动物报恩,显然是佛教的影响所致。
佛教文化对民间故事内容的影响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这从世界通行的民间故事分类法——AT分类法中的类型设置上可以得到很明显的反映。可见,佛教经典中用来说法的寓言故事,以及为在下层传教而进行的通俗宣传,诸如唐中期盛极一时的俗讲所演述的故事,甚至是佛教的某些观念,都对动物精怪故事的演变产生巨大影响。狐精的巨大神通也打上了清晰的佛教印记。如《纪闻》“靳守贞”条记靳氏见女子忽尔乘空过河,遂缘岭蹑虚,至其所,击之亡,乃狐也。佛教神通在佛经中的表现比比皆是,如后汉康孟祥《修行本起经》卷下云:“得变化法,所欲如意,不复用思,身能飞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亿万无数,复合为一能入地,石壁皆过,从一方现,俯没仰出。譬如水波,能身中出水火,能履水行虚,身不陷坠。坐卧空中,如飞鸟翔。立能及天,手扪日月。”可见狐精来去无碍,飞行虚空,实乃佛教神通之表现。
另外,佛门信徒均严守不杀生之戒,在民间流传开来就形成了一种尊重动物生存权的观念,如不畜狸猫食鼠,经常放生等。久而久之,佛教信条深入人心后就变成了一种信仰,人们不但遵守不杀生之戒,而且将动物看成本质上是与人相同的生命体。这是在佛教影响下所形成的民间信仰与传统的物老成精的信仰合流而完成的。
四
动物精怪故事的衍变,一方面是建立在传统信仰进化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是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平添了精怪化现的活力。由于民间一直存在着精怪信仰,所以表现这种信仰观念的精怪故事不断产生和流传。随着佛教文化传播的不断深入,这些精怪故事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已渐渐淡化了动物性而趋于人性。故事中的精怪形象,不仅有人的形貌,也具人性、人情,有人的意志、思想、感情和善恶美丑。虽然有些精怪还未摆脱形体和行为的动物性,但已明显超出信仰范围,进入有意识的艺术创作阶段。六朝志怪中的一些动物,到隋唐五代常转化为人格化的动物——精怪。如牛僧儒《玄怪录》中的郭振元故事中,乡人以乌将军为镇神,岁配以女。乌将军“言笑极欢”,还有道从之吏,颇似渔色的豪吏。其实所谓的乌将军,只不过是个猪精,但已完全人格化。当然,六朝小说中已有此类人格化的精怪故事,如《搜神后记》中的田螺精故事,但为数有限;只是到了隋唐五代才集中出现,并形成一种特色。这类故事中有许多人类主人公明知对方是异物却还深深地爱着对方,完全将对方视为平等的、有情感的、同人类没有多少区别的生命实体。如《任氏传》记贫士郑六某日与狐精幻化的美妇任氏相遇相爱,缱绻一夜。天明问邻始知为狐狸精所化,但郑恋其艳冶,仍与往来。小说所塑造的狐精形象远超其他神仙鬼怪,注意从“人”的角度刻画其形象。小说中所描写的任氏生动、活泼,展示出女性所特有的魅力,表现了她温柔、大方、机智的个性特征;与六朝小说同类故事所表现的简单粗陋的狐女故事相比,突出了任氏身上所具有的浓郁的人情味,减少了其身上的神秘性,充分肯定了其人身价值,这是狐女形象在小说中艺术表现的质的飞跃。可见,随着时代和人们心理结构的变化,狐精的情感、意志和欲望也不断丰满,人间生活表现更加真实、自然。《任氏传》在诸多狐精故事中独具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种清新、亮丽的面貌。有唐一代,有关狐的传说尤多,小说中涉狐题材亦特别繁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人对狐仙的崇信非常广泛。“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祈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又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在这样的氛围中,有关狐的传说必然也大昌于民间。另外,像《原化记》“天宝送人”(《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七)和《集异记》“崔韬”(《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三)两条中所记男主角明知对方是由虎化现的异类女子,但仍不离不弃,毅然与之结为夫妻,演绎出超越人类的大爱。又如《宣室志》“计真”(《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四)条载计真妻为狐。妻亡,计真“特感悼之,为之敛葬之制,皆如人礼讫”,不以妻为异类而葬礼有别。再如《柳毅传》所叙柳毅与龙女的婚配幸福美满,为人间饮食男女所艳羡不已,作者充分肯定了动物精怪的人性。《广异记》“郑氏子”(《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二)条载:“……妇人忽谓郑氏子曰:‘曩来欲与君毕欢,恨以尼故,使某属厌。今辞君去矣,我只是阁头狸二娘耳。’言讫不见,遂绝。”《潇湘录》“焦封”条载焦封为求官别妻赴京洛,而其由猩猩所化妻也愤而归山,临行她说:“君亦不顾我而东去。我今幸相伴相召归山。愿自保爱。”(《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六)其夫妻绝别,情真意切。这些应该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出现的新东西。佛经故事中大量的人格化的寓言故事,大量的佛本生、本缘故事,在唐代兴盛的“俗讲”及各种艺术形式的弘传下渐渐深入人心,文人、市民亦乐此不疲。有唐一代,动物精怪故事演变中这一新的东西,在文人的创造性改编下,使中国古代文化之林中结出了一朵奇葩——完全人性化的精怪文学。由此可见佛教文化对精怪故事的影响之深远。
动植物的成精变怪还只是精怪故事的初期阶
段,只有在佛教文化的刺激下,才使得这类精怪故事情节曲折,人物的思想内涵也变得深邃繁富,并逐步向成精变人的高级形态演变。
概而言之,因原始宗教信仰而形成的中国传统的动植物精怪信仰,随着异域佛教文化的传入,交融互汇,使得此类动植物成精的路径、动植物人格化的模式、动植物艺术表现诸方面都有深化,以及使这种传统的异类故事,经文人的艺术加工而演变成为中国古代所独有的精怪文学,异彩纷呈,乃至对中国精怪文化诸方面都产生毋庸否认的巨大影响。
注释:
①孙通海译注:《庄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7页。
②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4页。
③《大正藏》第54册,448b。
④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
⑤《鲁迅全集》卷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页。
⑥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21页。
⑦《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六,第3548页。
⑧《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九,第3577页。
⑨《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七,第3477页。
⑩《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六,第3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