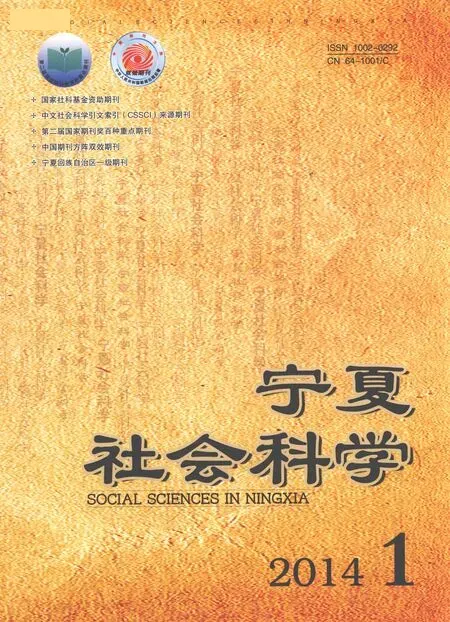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汉事会最人物志》抄本考述
王慧玉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91)
《汉事会最人物志》是清代著名学者惠栋(1697~1758年)辑录的对两汉重要人物的史实进行搜集汇总的一部书,内容采自《太平御览》《史记》《后汉书》等涉及有关人物传记的注文,意在为其《后汉书补注》做前期的资料准备工作。此书为后世了解和研究两汉人物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汉事会最人物志》一书,常见的有《丛书集成初编》(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中所收的《汉事会最人物志》3卷(中华书局于1985年重印,以下引用《汉事会最人物志》内容均出自此本,简称《丛书集成》本),这个本子的底本是江标(1860~1899年)所辑《灵鹣阁丛书》本。笔者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见到《汉事会最人物志》的一个旧抄本,又考察了上海图书馆所藏2卷本与5卷本写本的《汉事会最人物志》,发现哈佛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藏本又与《丛书集成初编》所收《汉事会最人物志》大有不同,兹将几个本子详加比较,以期厘清几个本子间的关系。
《丛书集成初编》本《汉事会最人物志》,分为上、中、下三卷,目录页写明“此据灵鹣阁丛书本排印”。查《灵鹣阁丛书》所收《汉事会最人物志三卷》,首页背面记有“光绪乙未借仁和汪氏振绮堂写本刊”字样。《灵鹣阁丛书》为江苏元和江标所刻,世称精本。江标称《灵鹣阁丛书》中《汉事会最人物志》的底本为光绪年间所借仁和汪氏振绮堂写本,然查《振绮堂丛书》不见收录此书,清汪宪所编《振绮堂书目四卷》亦不见录。《书目》序言介绍了振绮堂“代有藏书”,“插架甚富”,但“至咸丰庚申辛酉,杭城两遭兵燹,散佚殆尽”。[1]振绮堂藏书因兵燹而“插架之书百不存一”,书目之编写与传承亦久历波折,故《汉事会最人物志》未见著录,不等于说汪氏振绮堂没有收藏过此书。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汉事会最人物志》为旧抄本,一册,半页12行,行26字。从现存内容提供的线索来看,此抄本原来应有2册,10卷。因为抄本中有几页书眉处分别标有“七卷”“八卷”“卷九”“卷十”字样,此本内容始自樊重条,写有“汉事会最人物志”“元和惠栋定宇”字样,虽未写卷数,亦可知其所对应当为第六卷之内容。由此可知原抄本应有10卷,而抄本又恰在董卓条页(即页上空白处标注7卷页)内夹有纸条,写有“抄本汉事会萃人物志二本”(应为装订前粘贴于页内)。故哈佛藏本当为两册中的一册,所含内容为六卷到十卷的内容,所失为1卷至5卷的内容。与《丛书集成》本比对,旧抄本内容对应的是《丛书集成》本之下卷,所遗部分则为《丛书集成》本之上、中卷。细睇哈佛藏本,可断定此本为《汉事会最人物志》的一个早期抄本。抄本中所有“玄”字均作“元”,并外加框,此避康熙帝讳。抄本首页有印三方,分别为“朱锡庚印”,“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燕京大学图书馆”。朱锡庚之父朱筠学识渊博,为乾隆间著名学者,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藏书数万卷,所居名椒花吟舫,至朱锡庚时仍藏书不辍。朱锡庚诞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距惠栋去世仅几年,故此抄本定为《汉事会最人物志》的一个早期抄本。哈佛藏旧抄本自“邴原”等人以下,有小字“以下照先生所开编录”,此部分内容为《丛书集成》本所无,此为哈佛藏旧抄本之重要价值所在,待下文详述。
上海图书馆所藏写本《汉事会最人物志》有两卷本与五卷本两种。两卷本为稿本,1册。封面写有“红豆村人遗稿”字样,内中有印多方,分别为:精本、王氏书库、王氏秘箧、栩栩盫、上海图书馆藏书、红豆书屋、元和王同愈、栩栩盦长物、栩缘所藏、栩缘印信等。“红豆村人”、“红豆书屋”,所指为惠栋,表明此本源出于惠栋。其他印章则提供了另一位收藏人的信息:王同愈(1856~1941年),有号栩缘,江苏元和人,晚清民国年间著名学者、藏书家、书画家、文博鉴赏家。编著有《栩缘藏书目》、《栩缘随笔》等。所以“王氏书库”、“王氏秘箧”、“栩栩盦”、“栩缘”等所指均为元和王同愈。两卷本人物始自高帝,终于李弘①,辑有高帝、元帝、吕后等共63人,相当于《丛书集成》本上卷。
上海图书馆所藏五卷写本《汉事会最人物志》为一册②,封面亦写有“红豆村人遗稿”字样,首页有印三方:“马鼎父是正文字之印”、“上海图书馆藏”,另有一方辨析不清。将此本与两卷本详加比对,可以发现五卷本前两卷内容与两卷本内容几乎完全一致;而且二者卷前均有小序,内容相同:“两汉人物志三册,皆撰集前后汉逸事,经营缀辑颇寓苦心,他日脱稿后当与同志者共欣赏也。松崖。”惠栋号“松崖”,此序表明了惠栋辑录此书之心迹。因此五卷本前两卷内容,应是依据2卷稿本抄出。③五卷本后3卷共录68人,相当于《丛书集成》本中卷内容,但多出卫兹、王柔、王泽、郗虑、国渊、张逸、赵商等七人。
那么哈佛藏本与上海图书馆藏本间是否有关系呢?笔者对此详加勘查辨析后认为:上图藏五卷本《汉事会最人物志》与哈佛藏《汉事会最人物志》为一套旧抄本的上下册,上海图书馆藏五卷本对应《丛书集成》本《汉事会最人物志》的上卷与中卷,哈佛图书馆所藏旧抄本对应《丛书集成》本之下卷。从以下几点可以见出:一、两个本子的版式均为黑格黑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均为半页12行,行26字;二、这两个本子笔迹极为相似,应出自一人之手;三、从辑录内容来看,哈佛藏本相对于《丛书集成》本下卷少了郗虑等7人,而上海图书馆藏五卷本中于第三卷内恰好比其所对应的《丛书集成》本中卷多出这7人,因而上海图书馆五卷本与哈佛藏本正好构成完整的辑录内容;再从避讳形式而言,哈佛藏本与上图藏五卷本均将“玄”字写作“元”,并外加方框以避康熙帝之讳。还可以从辑录方法、所录人物在条目中列出的方式等几个方面来看。《汉事会最人物志》所有辑录内容,《丛书集成》本均指明出于何人传注,哈佛抄本与上图五卷本均注明出于某书某卷;对于所辑录的人物,哈佛抄本与上图五卷本于此人物条目下往往附列人物较多,有时这两个本子还会将部分附列人物单独开列,而《丛书集成》本则只列其要者;哈佛藏抄本与上图五卷本对部分辑录人物在其开列名目下略有身份说明,也异于《丛书集成》本。
此外,上图两卷本与五卷本中,惠栋序曰此书3册,但目前哈佛藏本与上海图书馆藏五卷本合为2册。应该是原稿本为3册,前2卷即为第一册,而依据稿本钞出的旧抄本将稿本第一册与三至五卷合为一册,则此书共合为2册,因而哈佛藏本中会夹有纸条注明此本共两册。
由上述可见,哈佛藏本与上图五卷本在很多形式的细节方面表现出有别于《丛书集成》本的高度一致性;在内容上也呈现出完整的系统性,较为清楚地显现出它们应为一个本子的上下册关系。
这套旧抄本究竟为何人抄录?从“以下照先生所开编录”一语中抄录者对惠栋的称谓看,其身份当为惠栋的学生或者普通抄工,遵惠栋之旨,依惠栋所嘱,将余下内容加以抄录。而两个抄本中又多有介绍、说明、注释性文字,此类文字既有抄录者以小字抄录于正文之下,亦有另一种笔体书写于书眉之上或正文之侧,这些传抄过程中的部分细节表明抄本在抄录前后均有校对审阅者。如哈佛藏抄本中所录陈寔条:“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邱,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彊者绥之……’”在“老”字之下抄录注文曰:“本作先,惠君改之。段氏曰,先犹昔也。”所谓“惠君”,当为惠栋,既称惠栋为“惠君”,此人当非普通抄工或惠栋弟子及后学。上图五卷本中所录繆斐条也很值得注意,“公卿举斐任侍中”的“卿”字与“举”字之间较《丛书集成》本多出“博举名儒时”若干字正文,但此五字被置于括弧内,并于其旁以另一种笔体小字注出“惠本删此五字”。此处注文指出《汉事会最人物志》较《三国魏书刘劭传注》中缺此五字的原因。从以上两处可以推测校订审阅者的大致身份,或称“惠君改之”,或曰“惠本删此五字”,从其称谓直称“惠君”或“惠本”来看,加此评语的应是惠栋同时代的一个学者,很可能即为五卷本前印章“马鼎父是正文字之印”中的“马鼎父”,而此人究竟为谁,笔者无从查出,只能由此推知此本中其余评点补充注解等文字亦可能出自其手。
通过以上对几个本子的介绍、比较与推论,并进一步参酌《汉事会最人物志》辑录的原始材料对其内容进行比对,可以看出旧抄本系统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哈佛藏抄本中很多内容为《丛书集成》本所无,此为两个系统的《汉事会最人物志》最大的不同,也是哈佛藏抄本的重要价值所在。哈佛藏抄本“邴原”条下“以下照先生所开编录”所录人物计18人,这些人物均不见于《丛书集成》本,此外还有部分“外域”内容亦为《丛书集成》本所无。据笔者统计,抄本较《丛书集成》本多出约8 500多字的内容。
从整部书的完整性以及抄本所提供的线索来看,抄本中多出的部分被纳入《汉事会最人物志》中应更加符合惠栋本意。首先,《汉事会最人物志》下卷内容多出自《三国志·魏书》,抄本较《丛书集成》本多出的自“邴原”以下至“外域”部分,正承接《三国志·魏书》卷十一“王修传”注文中关于“脂习”的内容。④经笔者将《汉事会最人物志》与《三国志》作详细对比发现,《汉事会最人物志》下卷内容所出自的《三国志》的卷数,虽不是严格按照从开卷至卷尾逐卷选择,但大体上还是依顺序来辑录的。而抄本中多出部分绝大多数都是《三国志·魏书》中后几卷的内容,因而从选择内容的完整性及辑录规律而言,这部分内容被纳入其中可谓顺理成章。其次,抄本中多出的近二十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外域”部分内容的分量与《汉事会最人物志》中其他内容相一致。第三,抄本较《丛书集成》本中多出的内容,无论从抄录笔迹、抄录格式还是从标注方法及书写习惯等各个角度而言,都与前部分没有任何差异,体现出抄录的连贯性、一致性和完整性,足可见出是出自一人之手,并有明确的抄录思路和目的。最为重要的,就是前已提及,在此部分之前有抄录者说明:“以下照先生所开编录”,更是交代了多出部分的明确原因。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推断,抄写者依惠栋之旨,将更多的内容纳入到《汉事会最人物志》中来,为我们展示了此书应有的面目,对进一步了解惠栋的辑录意图与思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
第二,抄本系统对《丛书集成》本具有重要的勘误作用。
先以上图藏五卷本为例,在《丛书集成》本中,董仲舒条有如下部分文字:“风俗通云,武帝时迷恋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数以为言,武帝欲验其道,令巫诅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诵咏经论,不能伤害,而巫忽死。”但是上图两卷本与五卷本都与此不同。两卷本于此部分内容后注明:“当有在后页。”此后,新起一页关于东方朔的内容,又另起一页关于董仲舒的内容如下:“潜夫论赞学篇曰: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景君明终年不出户庭⑤,得锐精其学。……董仲舒勤学三年不窥园,乘马不知牝牡。艺文类聚九十三御览八百四十。”上图五卷本董仲舒条下内容同于两卷本,但中间并不被东方朔条隔开,亦无“当有在后页”诸文字。董仲舒条情况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验证了五卷本由两卷本抄出的事实。可以推知,两卷本因为装订出现差错,董仲舒条被东方朔条隔开,而五卷本抄录两卷稿本时发现这一情况,于是加以调整,将这部分内容抄录到应在的位置;第二,因为两卷本与五卷本均注明出处,而《丛书集成》本没有出处,并缺少了部分内容,这说明《丛书集成》本丢失了包括出处在内的少于两卷本与五卷本的部分内容。因此,可以依据上图五卷本董仲舒条对《丛书集成》本丢失的内容加以补出还原。
再以哈佛藏抄本为例。如周不疑条,《丛书集成》本作:“零陵先贤传曰:刘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幼有异才,聪明敏达……”而哈佛藏旧抄本中则于“周不疑,字元直”与“幼有异才”之间多出“零陵人《先贤传》称不疑”若干字。查之《三国志》,承接上文而来,并无开头“零陵先贤传曰,刘”若干字,其余《三国志》与旧抄本同。[2]哈佛藏旧抄本更贴近于原貌。且此条应可以作为旧抄本较之《丛书集成》本底本为早的证据。因为开头若干字“零陵先贤传曰”是为注明本段引文出处,而哈佛藏旧抄本加上出处后就将《三国志》中此段内容全部抄录下来,《丛书集成》本所据底本认识到这样直接的抄写造成文义的重复,于是将正文中的“零陵人先贤传称不疑”若干字省去。
通过对几个本子的比较,也可以发现抄本系统存在的不足之处。如《丛书集成》本中何苗条:“又疑其与宦官同谋,……,遂引兵与卓弟旻,共攻杀苗于朱爵阙下。”此条“宦官”二字在哈佛藏抄本中作“宦者”;“朱爵阙下”抄本中作“朱雀阙下”,查《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文,与《丛书集成》本同。亦为“宦官”、“朱爵阙下”。⑥又如张邈条、袁绍条等,抄本系统亦有不精确之处。
以上是对《丛书集成》本、上图藏本及哈佛藏抄本所作的比较。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还藏有《汉事会最人物志》两套抄本,其中一套抄本之母本即为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汉事会最人物志》旧抄本,所含内容与哈佛藏本完全一致,每页版心下角有“哈佛大学图书馆钞”字样,除首页有印“北京大学馆藏”外无其他印章。
另一抄本为清吴清如抄本,吴氏抄本共分3卷,抄本末有吴起潜跋文:“惠定宇先生原本,旧藏黄大荛翁家,兹不知何所归。此本系吴清如中翰就原本录出,寿云持以赠予,不啻百朋之赐。壬寅立冬后六日重为装订之云吴起潜志。”从其跋文可见,原稿本藏于黄丕烈之所。而上海图书馆所藏两卷本与五卷本均不见黄氏藏书印迹,故所指当非上图所藏之稿本。此抄本有印三方:“庆嘉馆印”、“北京大学藏”、和“木犀轩珍藏印”三种,“木犀轩”表明此本出于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所藏。吴氏抄本所收人物及基本内容同于《丛书集成》本,但与《丛书集成》本亦多有不同处。比如书中人物辑录的顺序,《丛书集成》本中依次辑录人物张羡、刘修、刘琮、傅巽、刘先,而吴抄本同于哈佛抄本,将张羡置于刘琮之后;在具体收录内容细节方面,也有部分与哈佛抄本同而异于《丛书集成》本。
通过对上述几个版本的考察、比较和分析,我们对《汉事会最人物志》的版本情况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抄本与上图五卷本所构成的抄本系统,内容丰富,也比较精准和完善,对目前通行的《丛书集成》本能够起到重要的补充及勘误作用。通过这一抄本系统我们能够更准确、全面地了解《汉事会最人物志》,对此书有更明晰的认识,因而其相应价值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注释:
①目录中未录此人,但内容中实有。
②上海图书馆图书信息注明此本为稿本。
③上海图书馆图书信息亦持此意见,认为五卷本由两卷本抄出。
④《丛书集成》本“脂习”之后只有一个“徐英”,见于《三国志·魏书》卷十五“张既传”注文,这是此本中辑录的最后一个人物。
⑤于“景君明”与“终年”间有双行稍小字夹注曰:“景疑当作京”。
⑥《三国志》,第173页。此“爵”是“雀”的通假字,《后汉书》作“雀”。
[1][清]汪宪,编.振绮堂书目四卷·序言[M].民国十六年(1927)活字本,一册,一函。
[2][晋]陈寿.三国志[M].[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