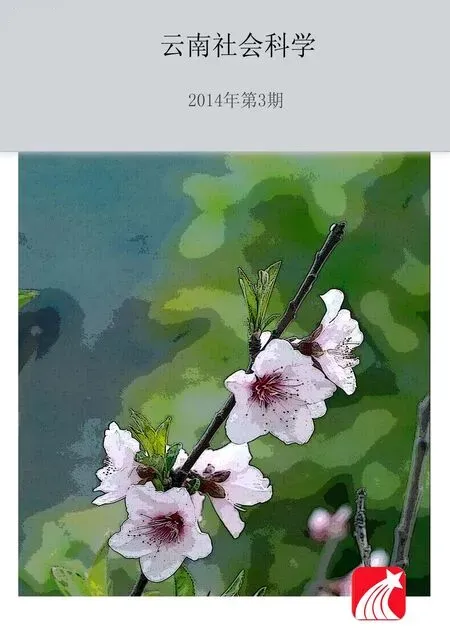唐宋人眼中的西南沿边民族地区研究
张 勇
沿边地区,古代又称缘边地区,是一个政权靠近其边界的地带。*古人对于“边”、“边界”有多种认识,参见周振鹤:《构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3页;[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第9页;杜芝明、黎小龙:《“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本文指的是中原政权与周边民族政权间的边界。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沿边地区多是民族地区。例如,唐宋时期,唐宋王朝西南部的沿边地区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学术界对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民族做过大量研究,但专门将西南沿边地区及其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却很少,更极少关注唐宋人对这一民族地区的认识。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唐宋时期的史料记载出发,探讨唐宋人眼中西南沿边民族地区的范围、民族、作用等问题。
一、范围与民族
唐宋时期,西南地区有吐蕃、南诏(大理)等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鼎立、对峙,西南沿边地区就是唐宋王朝毗邻吐蕃、南诏(大理)边界的地带。这一地区居住着众多的民族,中原王朝在此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州县。因此,本文根据所设置的边州情况,简要勾勒唐、宋两朝时人眼中西南沿边地区的区域范围与民族构成。
唐朝在与吐蕃、南诏毗邻的地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州,统属于沿边各都督府。从西到南,分别为剑南道的松州、茂州、雅州、黎州、嶲州、戎州、泸州都督府和江南道的黔州都督府。*唐前期在西南地区还设有姚州都督府,天宝后没于南诏。下面根据新、旧《唐书》等史籍的记载,简单叙述唐朝西南地区各沿边都督府所领的羁縻州及其民族构成状况。
松州都督府,旧领104州,“其二十五州有额户口,但多羁縻逃散,余七十九州皆生羌部落,或臣或否,无州县户口,但羁縻统之”[1](卷41,P1699)。松州都督府所领羁縻州的民族多为生羌或降羌。
茂州都督府,旧领9个羁縻州,其中生獠与生羌杂居。永徽以后,生羌部落万余户内附,又析置30余州。
雅州都督府,领57个羁縻羌州,分为“天宝前置”和“天宝后置”两部分。《新唐书·南蛮传》载:“雅州西有通吐蕃道三:曰夏阳、曰夔松、曰始阳,皆诸蛮错居。凡部落四十六……皆羁縻州也。以首领袭刺史。”[2](卷222下,P6323)可见,雅州“诸蛮错居”,在时人眼中是蛮族聚居之地。
黎州都督府,《旧唐书·地理志》云“统制五十四州,皆徼外生獠”[1](卷41,P1685)。又《新唐书·南蛮传》载:“领羁縻奉上等州二十六。开元十七年,又领羁縻夏梁、卜贵等州三十一。南路有廓清道部落主三人,婆盐鬼主十人。又有阿逼蛮分十四部落”,“黎、邛二州之东,又有凌蛮。西有三王蛮,盖莋都夷白马氏之遗种”[2](卷222下,P6323)。在时人眼中,此地獠、蛮众多。
嶲州都督府,下领16个羁縻州。同时,在嶲州周边还有不少蛮夷部落。《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巂州新安城傍有六姓蛮:一曰蒙蛮、二曰夷蛮、三曰讹蛮、四曰狼蛮,馀勿邓及白蛮也。”[2](卷222下,P6324)嶲州有勿邓、两林、丰琶等部落,合称东蛮;还有以磨些蛮为主的西蛮。
戎州都督府,《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年间“羁縻三十六州,一百三十七县。并荒梗,无户口”[1](卷41,P1693)。《新唐书·地理志》记戎州都督府领65个蛮州。《新唐书·南蛮传》载云:“戎州管内有驯、骋、浪三州大鬼主董嘉庆,累世内附,以忠谨称,封归义郡王……又有鲁望等部落,徙居戎州马鞍山,皋以其远边徼,户给米二斛、盐五斤。北又有浪稽蛮、罗哥谷蛮。东有婆秋蛮、乌皮蛮。南有离东蛮、锅锉蛮。西有磨些蛮,与南诏、越析相姻娅。自浪稽以下,古滇王、哀牢杂种,其地与吐蕃接。亦有姐羌,古白马氐之裔。”[2](卷222下,P6324)时人认识到戎州有着许多蛮夷部族。
泸州都督府,《旧唐书·地理志》云“都督十州,皆招抚夷獠置,无户口、道里”[1](卷41,P1686)。《新唐书·地理志》则记州下领14个羁縻州。这些羁縻州所领部族大多为獠族或山洞蛮民。
江南道有51个羁縻州,均隶属于黔州都督府,后分江南道黔中采访使为黔中道。黔中地区分布有众多的部族,包括牂牁蛮、南谢蛮、东谢蛮、西赵蛮、昆明蛮等,皆“羁縻,寄治于山谷[1](卷40,P1620)。
由上可知,唐朝西南沿边地区的范围,从西到南,包括剑南道的松州、茂州、雅州、黎州、嶲州、戎州、泸州都督府和江南道的黔州都督府所统属的各羁縻州县。时人认识到,这些地区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包括了“羌”、“蛮”、“獠”等民族类别,而每一类民族下又有许多部族,如蛮族在黎州有阿逼蛮、凌蛮、三王蛮等部族,在戎州有浪稽蛮、罗哥谷蛮、婆秋蛮、乌皮蛮、离东蛮、锅锉蛮、磨些蛮等部族,极其繁多。由于沿边地区的民族种类复杂,数量极多,所以尽管部分地区也有汉人与夷人杂居,但人们更多地将这些地区看作是蛮夷聚居之地。
进入宋代,西南地区的政权局势发生了变化,西部吐蕃分裂为诸部,南部大理替代南诏。虽然宋朝西南沿边民族地区的范围有一定的盈缩,但并无很大的改变。正如《宋史》所称:“自黔、恭以西,至涪、泸、嘉、叙,自阶又折而东,南至威、茂、黎、雅,被边十余郡,绵亘数千里,刚夷恶獠,殆千万计。自治平之末讫于靖康,大抵皆通互市,奉职贡,虽时有剽掠,如鼠窃狗偷,不能为深患。”[3](卷496,P14244)宋代西南沿边地区的范围,从西到南,包括茂州、威州、永康军、雅州、黎州、嘉州、叙州、泸州、长宁军、黔州、涪州、珍州、思州、南平军等州军及其羁縻州。这些地区居住有茂州蛮、保霸蛮、东蛮、西山野川路蛮、叙州三路蛮、淯水夷、西南蕃等众多的蛮夷民族。
与唐朝有所不同的是,宋朝西南沿边地区由于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这些地区多呈汉夷杂居的格局,时人对此有清晰的记载和认识。例如,宋人记威州“皇朝管汉税户五十四,蕃户税户九百,蕃客户五千六百九十四”[4](卷78,P1578);黎州有蕃人与汉人,“汉、蕃博易不用钱”[5](卷56,P999);叙州“系通放夷蛮互市之地,汉蕃杂揉”[6](第6册,P129),“夷夏杂居,风俗各异”[4](卷79,P1590);泸州“皇朝管汉户主二千四十七,獠户二千四百一十五”[4](卷88,P1739)。宋人还看到,沿边地区在汉夷杂居,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蛮夷”民族受汉文化影响越来越大。如宋人称茂州“渐渍声教,耕作者多”[7](卷149,P4446);叙州“诗书礼义之泽,渐渍至今”[7](卷163,P4935);泸州“虽鸟言夷面,久被于文明”[5](卷56,P993);南平军本“南獠之故地”,“自唐宾服,开拓为郡。今衣冠宫室,一皆中国”,“四民迭居,冠婚相袭,耕桑被野,化为中华”[7](卷80,P5230~5231)。这些都体现了宋人对沿边地区“夷夏杂居”并逐渐汉化的深刻认识,可见时人更多将沿边地区视为汉夷杂居之地。
二、作 用
西南沿边民族地区位于吐蕃、南诏(大理)等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汉族区之间,唐宋人除了对其区域范围、民族构成有所认识外,还对该地区的作用较为重视。
由于唐代西南地区吐蕃、南诏等强大的民族政权长期与唐朝鼎立对峙,因此唐人认识到,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在地理阻隔、军事力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作用。首先,这些地区大多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地势险要,被唐人看作是能阻拦吐蕃、南诏进攻的天然地理屏障。如陈子昂在《谏雅州讨生羌书》中说:“吐蕃羯虏,爱蜀之珍富,欲盗之久有日矣,然其势不能举者,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顿饿狼之喙,而不得窃食也。”[8](卷212,P948)他认为西羌地区“山川阻绝,障隘不通”,是防止吐蕃入侵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屏障。后人对这些地区的阻隔作用也多有认识,如胡元质称“唐之季年,吐蕃入寇,必入黎、文;南诏入寇,必入沈黎;吐蕃、南诏合入寇,必出灌口。其文、黎两州去成都尚千里,关隘险阻,足以限隔。惟灌口一路,去成都止百里,又皆平陆,朝发夕至”,提出威、茂两州可为“灌口之蔽障”[5](卷55,P981~982)。其原因就在于威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5](卷56,P993),茂州“岷山巉绝崛立,实捍阻戎,以全蜀倚为巨屏”[5](卷55,P981)。其次,在军事力量方面,时人认识到这些沿边地区的民族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一是这些民族可直接参与到唐对吐蕃或南诏的战争中来。唐朝多次联合一些沿边民族的兵力,攻打吐蕃或南诏。如韦皋镇守西川时,对边境群蛮广为招抚,贞元五年(789)“遣将王有道等与东蛮两林苴那时、勿邓梦冲等帅兵于故巂州台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猎城二节度”[1](卷196下,P5256)。后来镇守西南的李德裕也提出“欲遣生羌三千,烧十三桥,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没身恨不能致者也”[9](卷244,P7878)。二是由于沿边民族比较熟悉当地情况,可使其为向导。三是唐朝可招募沿边民族为军队,以助其守边。如杜甫在《东西两川说》中说“兼羌堪战子弟,向二万人,实足以备边守险”,建议“仍使兵羌各系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阅”[8](卷360,P1617)。
正是由于沿边民族具有这些重要作用,唐人意识到这些地区的稳定尤为关键。陈子昂称“雅州边羌,自国初已来未尝一日为盗;今一旦无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惧诛,必蜂骇西山;西山盗起,则蜀之边邑不得连兵备守;兵久不解,则蜀之祸构矣”[8](卷212,P948),他认为西羌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蜀的安危。再如,嶲州地区的东蛮位于唐、吐蕃、南诏三者之间,人们看到“东蛮地二千里,胜兵常数万,南倚阁罗凤,西结吐蕃,狙势强弱为患,皋能绥服之,故战有功”[2](卷158,P4934),其政治倾向与唐朝边地之安危的关系尤为密切。
然而,沿边地区的民族处于唐朝、吐蕃、南诏几大势力之间,迫于形势,一些部族不得不常怀两端,依违于其间。唐宋人对沿边民族左右摇摆的两面性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史籍中多有记载和议论。如剑南西山生羌,其部落代袭刺史等官,但仍然潜通吐蕃,唐人谓之“两面羌”[1](卷197,P5279)。剑南西部另外的一些蛮夷部落,“春秋受赏于巂州,然挟吐蕃为轻重”[2](卷222下,P6324)。黎、邛二州以西有三王蛮,常怀两端,“岁禀节度府帛三千匹,以诇南诏,而南诏亦密赂之,觇成都虚实”[2](卷222下,P6323)。唐人对位于嶲州地区的勿邓、两林、丰琶等东蛮部落的两面性也有论述,称这些部落“内受恩赏于国,外私于吐蕃”[10](卷1,P52)。可见,唐人在看到沿边民族地区重要性的同时,对其“常怀两端”的两面性也有清醒的认识。
到了宋代,两宋王朝积贫积弱,较之于唐朝国力大为衰退,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宋朝对沿边民族地区的作用更为重视,常视其为“藩篱”,倚之为屏障。曾巩在代宋神宗起草的诏书中云:“西南之地,延袤万余里,外临殊俗,内杂溪谷,诸蛮列州成县,以保安吾民”[11](卷25),就是主张西南地区以诸蛮夷羁縻州为“藩篱”,保境安民。对于四川西北部的氐羌,郭允蹈称:“武都氐羌,至杨氏而始,大其后遂为阶成、兴凤等州,为蜀之藩篱”[12](卷9,P439)。四川西南边境的邛部川等东蛮部族,唐宋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藩篱”作用。但嘉定九年(1216),“邛部川逼于云南,遂伏属之”,人们因此感慨“其族素效顺,捍御边陲,即折归云南,失西南之一藩篱”[3](卷496,P14235)。甚至有的沿边民族也自称为宋“藩篱”,如曾经叛乱的青羌部落在宋招降后,自云“我三族为汉障蔽,诸蕃动悉必以告”[12](已集卷19,P854)。
宋人视西南沿边民族地区为“藩篱”,与宋人对这些地区在战略位置、兵源补充、市马贸易等方面作用的认识有关。
第一,沿边地区大多地势险要,又处宋朝与民族政权之间,因而人们认识到这些地区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如宋人称四川西部的雅州“抵接沈黎,控带夷落,在蜀最为保障。当蛮出入之咽喉”,“当西南夷孔道”,为“南诏之咽喉”[7](卷147,P4390~4391);黎州“内捍右蜀,外捍蛮夷”,“南邻六诏”,“为蜀西门”[5](卷56,P999~1000);川南的叙州“号为重地,盖控扼石门、马湖诸蛮”[7](卷163,P4936);泸州为“西南要地,控制一路”,“地控云南之六诏,疆连井络之三边。维泸川之大郡,控巴蜀之群蛮”,其“控西南诸夷,远逮爨蛮,最为边隅重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5](卷62,P1089);长宁军“外邻蕃蛮,内接泸、戎。以盐官置监,深介夷腹”,“控扼蛮、蜒,捍蔽泸、叙”,“实西南之控扼也”[7](卷166,P5021)。通过宋人对这些地区地理位置、形胜险要、战略地位的描述,可以看出人们认为这些地区是宋朝四川之“屏蔽”,可以“外控蛮夷”、“内捍巴蜀”,在军事地理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二,宋王朝为了镇抚西南沿边各族和防备大理政权、吐蕃诸部,在沿边地区除了部署数量可观的官军外,还将边地的熟夷、降羌和汉民组织起来,组建了各种形式的乡兵组织,成为辅助宋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统治的重要力量,是其“以蛮夷治蛮夷”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具体体现。[14](P602)四川西部组建有威、茂、黎、雅、嘉定土丁,南部有泸南夷义军、胜兵,东南部有夔州路义军。宋朝以这些沿边地区的民族为镇抚蛮夷、守备边疆的重要兵源,时人说“自大中祥符以来,每有边事,则屯集名夷义军为用,屡获功赏”[5](卷65,P1139),对这些乡兵的作用有较高的评价。
第三,宋人还认识到沿边地区在市马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历代中原王朝的战马多来自北方,两宋时期北方先后为辽、金所占,西北又为西夏所踞,因而其战马主要依赖从西部沿边民族地区买进。北宋时,西北地区战马主要来自秦凤路沿边吐蕃等部族,西南则来自四川沿边民族地区。“宋初,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川峡则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军。”[3](卷198,P4932)据统计,北宋在四川设置的市马场有益、雅、嘉、黎、维、永康、茂、文、龙、戎、泸、夔、黔等13处,南宋又增设南平、珍州、长宁等3处。[15]这些市马场都是位于宋朝四川的沿边地区,主要以黎、雅、泸、叙为中心。宋朝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的马匹交易还带动了其他物品的交易。“先是,以铜钱给诸蕃马直。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3](卷198,P4933)宋朝与沿边民族进行互市贸易,除了满足朝廷对马匹的需求外,更主要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买马、互市的方式羁縻沿边民族,从经济利益上安抚这些民族,以保持边境的安宁与稳定。正如南宋兵部侍郎陈弥作所说:“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初不借马之为用,故弩骀下乘,一切许之入中。”[16](第183册,P7161)泸州知州何悫在谈到叙州设场市马时也说:“西南夷每岁之秋,夷人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厚以金、缯,盖饵之以利,庸示羁縻之术,意宏远矣。”[16](第183册,P7156)显然,对于在西南地区与周边民族进行买马等互市贸易的意义,宋人已有深刻的认识。
南宋时,北方的政治、军事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影响到了宋人对西南沿边民族地区作用的认识。宋室南渡后,西部大散关以北为金人所占据,金在四川北面对宋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此时,宋朝虽仍对西南地区的大理政权态度冷淡,但由于大理对宋的威胁性较小,故宋对其的敌视心理远逊于金。宋朝将金视为最主要的敌手,在与金抗衡的时候,考虑到了四川沿边民族的力量。例如,绍兴五年(1135),眉州人喻汝砺在《论蜀事四可忧并陈经画之策疏》中说:
缘自总领司行盐酒之策,失羌夷之和,于是叙州诸羌攻陷诸寨,官吏歼夷,百姓奔遁,若使金人博其胸掎其背,四川老孺何所遗?死耶!况黎、雅、石泉所在诸羌,山谷联绵,径道秦陇,倘使金人乘诸羌怀怨之隙,啖以金帛,约以攻我,不知何以御之?此其可忧四也。[6](第4册,P332)
他认为如果金人联合四川黎州、雅州、石泉军、叙州等地的少数民族一起攻宋,则四川危险。这说明南宋人认识到,在与金对抗时沿边民族地区有着重要的作用。
南宋后期,北方蒙古势力迅速发展,攻占了宋大片领土。基于此种形势,南宋人认为西南沿边民族地区是宋朝与蒙古对峙时需重视的地带。蜀人吴昌裔听闻大小云南为蒙古所破,上《请湖北蜀西具备疏》曰,分析了西南地区的民族格局及军事形势:
南方诸蛮之大者莫如大云南,其次小云南,次乌蒙,次罗氏鬼主国,其它小国或千百家为一聚,或二三百家为一族,不相臣属,皆不足数。而其它皆蜀之徼外诸蛮。接黎州大渡河之于有所谓邛部川,邛部川之后即小云南也,邛部川之下即两林庐、虚恨蛮,虚恨之下即马湖大江蛮之部族夷都蛮也。……其它皆与蜀之诸郡接。由邛部川可通黎州大渡河,由虚恨可通峨眉县中正寨,由夷都可通犍为县沐川寨,由大江蛮可通宣化县崖门及叙之开边寨,由吕告可通长宁,由阿永河可通泸水之江门寨,此皆通行往来之路。今小云南已困,小云已亡,若乌蒙次第皆破,则驱诸蛮行熟路,嘉定、泸、叙、长宁皆可至矣。……万一计出于此,不但蜀边腹背受敌,而湖右之腹心先溃可不畏哉。[6](第7册,P51~54)
他看到,西南地区有卭部川、两林蛮、虚恨蛮、马湖大江蛮、小江蛮(乌蒙)、吕告蛮、阿永蛮等部族分别与四川的黎州、泸州、叙州、长宁军等边州相接,认为如果蒙古驱使这些沿边民族攻打四川边地,则会使“蜀边腹背受敌,而湖右之腹心先溃”,形势极其危急。可见,宋人认识到了西南沿边地区及其民族在宋朝与蒙古对抗中的重要性。
三、余 论
综上所述,唐宋人眼中的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其范围包括唐宋王朝在西南部毗邻吐蕃、南诏(大理)边界的这些羁縻州县。这一地带有“羌”、“蛮”、“獠”等众多民族。唐人将西南沿边地区主要看作蛮夷聚居之地,而宋人则认识到沿边地区“夷夏杂居”并逐渐汉化,更多将其视为汉夷杂居之地。唐人看到沿边地区在地理阻隔、军事力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对其民族“常怀两端”的两面性也有清醒的认识。宋人对沿边地区的“藩篱”作用认识进一步增强,南宋时更意识到了该地区在与金、蒙对抗中的重要性。
实际上,早在汉晋之前西南地区就居住有许多“蛮夷”民族,时人统称为“西南夷”,后来汉代开疆拓土,在这些民族地区设置郡县,遂成为中原王朝统属之地。不过汉晋时期西南地区并没出现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相抗衡,所以沿边民族地区尚未引起时人的足够重视。直至唐宋时期,由于崛起了吐蕃、南诏(大理)等与之相对峙的民族政权,沿边民族地区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才凸显出来,认识也更为丰富和深入。到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结束了割据对峙的局面,王朝边界向外扩展,此时沿边地区的范围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
此外,唐宋时期其他地区也存在为时人所关注的沿边民族地区。如西北地区,突厥、吐蕃、回鹘、西夏等民族政权长期与唐、宋王朝相对峙,在这些民族政权与唐宋王朝之间,分布着一些非汉民族聚居区或者蕃汉杂居区。唐王朝和北宋王朝在这些地区设置有许多羁縻州,时人对这一沿边民族地区也有深刻的认识。例如,北宋人曾公亮曰:“今之夷人内附者,吐蕃、党项之族居西北边,种落不相统一,欵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17](前集卷18上)夏竦也认为:“缘边熟户号为藩篱……国家非不知其若此,所宜速见良画深破贼计,及早羁束以固藩篱,此西陲之急务也。”[18](卷14)他们认识到这一沿边民族地区的作用,提出以沿边熟户为“藩篱”,以巩固其西北边疆。
可见,沿边民族地区也存在于其他时期、其他地区。不过,本文限于篇幅,主要对唐宋人眼中的西南沿边民族地区进行探讨,而对于人们眼中其他时期、其他地区的沿边民族地区,仍有待学界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