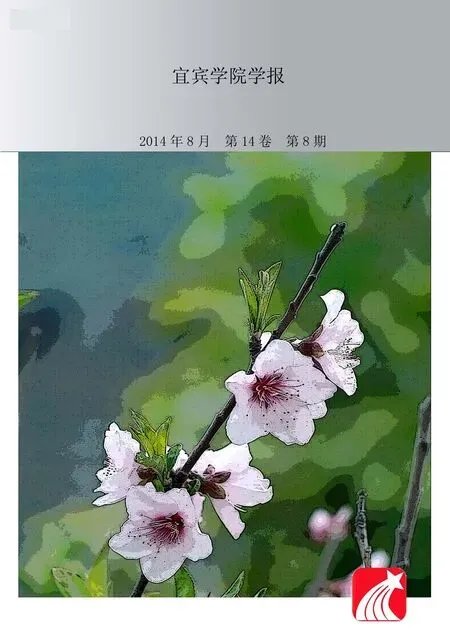从儒家思想的影响看寒食节从汉到唐宋的兴衰
罗恒宇
(西南交通大学 艺术与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儒学至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正统地位,儒家思想遂成中国两千年的正统思想,是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代节日作为俗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自我完善,逐渐成为我国文化的另一重要传统。两种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表现在儒家学说中的礼乐思想和仁义孝悌的主张,通过改变民众的思维和文化态度,为传统节日提供了发育的土壤。传统节日弘扬的精神,受到民众的推崇,又促进其自身及儒学的发展;民间传统节日的发展,既受文化发展规律的支配,又存在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统治阶级的态度。一方面,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传统节日逐渐向儒家思想靠近,从而形成了雅俗文化相结合的节日;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节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儒学化的倾向。寒食节是我国古代重要节日之一,它的发展经历了汉代兴起、魏晋南北时期衰落、唐宋复兴而后更加繁荣的跌宕历史。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自身的儒学化进程导致了其发展的兴衰变化。
一 兴于秦汉
追溯寒食节的源头,可以从介子推说起。《庄子·道跖》中记载了介子推的故事。“介子堆①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堆怒而去,抱木而燔死”。[1]而介子推与寒食发生关系要推移到汉代桓谭在《新论》中指出:“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堆故也。”[2]另东汉蔡邕《琴操》中记载:“介子绥割其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3]根据文献,在春秋时期文公便下令五月五日不得发火,而桓谭记载在汉代时,仍有人民为了纪念介子推而不举火。所以我们可以说,至少在汉代时,民间便有了寒食纪念介子推的习俗。那么,为什么寒食节兴起在汉代呢?这与汉代官方的主张不无关系。
西汉自汉武帝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所推崇的学说,在全国范围内宣扬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的忠义仁孝观点逐渐深入人心,成为汉代民众所追求的人生修养和行为准则。介子推为尽忠割肉啖文公,而文公复位后为报答其放火烧山亦不出,这体现了他施恩不图报、功成身退的义。介子推的故事无疑受到了百姓的推崇,而儒家经典对介子推故事的刻画,更是促进了他在百姓中的地位。《左传·僖公廿四年》载“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4]《左传》对介子推的记载已没有了他被火烧死一说,从而打消了人们对他恃才傲物的猜疑。同时,还添加了介子堆母亲这一角色,设计了母子一起归隐的结局,突出了慈母孝子与隐世高义。于是儒家学说将介子推塑造成为一个忠义仁孝而不求功利的隐士形象,这无疑将他推上神坛,成为民众修身律己的精神堡垒。
所以,寒食节兴起于汉朝,与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两汉时期的寒食节,存在着地域小、影响小的缺点,儒家思想虽然是官方思想,却只是在心态上影响了群众,促成寒食节兴起。官方没有对其有足够重视,预示了寒食节在汉代以后经历了一段衰落时期。
二 衰于魏晋
在两汉时期,因为介子推受到的推崇而促进了寒食节的兴起。但是介子推却在寒食节后来的发展中起到了阻碍的作用。首先,两汉兴起的寒食习俗是为了纪念介子推的忠义,反映了人们对高洁之士的崇拜,所以寒食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祭祀功能的活动。而在这一活动发展壮大之后,官方便不能再把它当作一种简单的民间活动,需要将其正统化。但是,由祭奠介子推演变来的祭祀活动,在源头上并不能与由儒家经典《礼记》《周礼》《仪礼》等记载的祭礼活动相联系,这就让寒食与儒家礼法对立起来。没有儒家学说作为理论渊源,也就失去了官方的支持,所以,寒食节便经历了几度存废的灾难。魏晋时期,官方便多次明令禁止民间的寒食活动。曹操《明罚令》:“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一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堆。夫子堆晋之下士,无高世之德,子胥以直亮沉水,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子堆,独为寒食,岂不偏乎?云有废者,乃致雹雪之灾,不复顾不寒食乡亦有之也。汉武时京师雹如马头,宁当坐不寒食乎?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小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书到,民一不得寒食。若有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俸一月。”[5]从这段文献中可以发现,在曹魏时期,民间寒食之风已盛,并且将寒食作为祭祀的活动,甚至“云有废者,乃致雹雪之灾”。但是,曹操因为其源头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而禁止民间寒食,实际上也是在说明寒食活动不具有儒家礼法的正统渊源,不应当被广泛推行。另具《晋书》记载,石勒时,发生了冰雹灾害,群臣建言曰为禁寒食之害。于是“勒下书曰:‘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尚书其促检旧典,定议以闻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更为植嘉树,立祠堂给户奉祀。”[6]这段文献同样也可以发现,寒食节在当时的某些地区已经形成了惯例,并且认为祭祀活动能够祈求风调雨顺,所以在石勒当政时发生的冰雹灾害被归咎于前年禁寒食,以致群臣要求解禁。石勒权衡之后,下令“尚书促检旧典,定议以闻有司”。所谓旧典即是指儒家经典,石勒为了解禁寒食,命令群臣在旧典中寻找与寒食有关的渊源。显然,石勒是不可能在儒家经典中找到渊源的,所以他只是稍稍放宽了寒食的禁令。
另外,还有很多文献记载了如北魏孝文帝禁寒食等官方的禁令,这些文献甚至可以追溯到《后汉书》。可以知道,在汉代兴起以后,根基于介子推传说的寒食活动逐渐发展壮大。寒食节在受到官方关注之后,却因为其没有经学渊源而成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祭礼活动,随即被官方所禁止。所以,介子推反而成为了阻碍寒食节发展的最大因素。面对被官方禁止而在民间却禁而不止的祭礼活动,摆脱介子推的影响成为了寒食节想要发展需要做到的首要目标。
汉代以后长期分裂的局面,也让人们无暇顾及寒食节的问题。
三 复兴于唐
历史发展到了隋唐,统一的局面促进了寒食活动在民间的扩大,而由寒食所延伸出来的祭祀活动,也逐渐摆脱了传说因素而更加注重现实公用。这种民众心态上的转变也影响了学者们的思维,跳出介子推的束缚。重新溯源寒食,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隋朝杜公瞻《荆楚岁时记》中载“《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注曰:‘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也。”[7]文献将禁火的时限往前推移到了周代,渊源则是周代对天文的崇拜,随即衍生出禁火的礼制。杜公瞻在提到禁火时,并未提到介子推,这一点对寒食来说意义重大。杜公瞻的观点得到了唐人李贤的认可,其在为《后汉书·周举传》做注时,曰“龙、星,木之位也,春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俗传云子推以次日被焚而禁火”[8]。李贤不但肯定了杜公瞻关于寒食承袭于《周礼》的说法,而且进一步提出关于介子推而寒食的说法乃俗传,以此来分辨寒食的渊源。作为俗传的介子推之说,当然不是正式的,其背后的《周礼》的礼制规定才是其存在的根本理由。再追究到李贤的人物性质,其观点基本可以代表当时的官方主张。
溯源《周礼》的主张,启发了唐人对寒食的进一步探究,“检旧典”彻底抛弃介子堆的俗传,成为了寒食节正统化活动的核心思想。唐代后期的李涪《刊误》曰:“《论语》曰:‘钻燧改火。’春榆夏枣秋作冬槐,则是四时皆改其火。自秦以降,渐至简易,唯以春是一岁之首,止一钻燧。而适当改火之时,是为寒食节之后。既曰就新,即去其旧。今人持新火曰‘勿与旧火相见’,即其事也。又《礼记·郊特牲》云‘季春出火,为禁火。’此则禁火之义昭然可征。俗传禁火之因皆以介推为据,是不知古。故以钻燧证之。”[9]文献明确指出将介子推作为寒食的依据,是不知古的表现,而溯源寒食,可以从《论语》《周礼》等儒家经典中找到禁火与钻燧改火的礼制。
从众多文献中可以发现,隋唐时期在论及寒食时,学者们摒弃了前代介子推理论,转而在儒家经典中找寻根据,并且有所收获。这样一来,寒食便与儒家经典产生了联系,也就消除了介子推所造成的阻碍,并且逐步将寒食祭礼纳入到儒家传统的礼法活动之中,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消除了阻碍的寒食节,由此走上了兴盛的道路。这一点可以体现在唐宋诗文对寒食的大量创作上。就唐代来说,寒食诗数量就有近192首。从数量上来说,寒食诗是唐以前不可比拟的。从内容上来说,其中涉及介子推的数量特别少,仅5首左右,而更多的是对唐代寒食具体情况的描绘,其中不乏名篇。如韩翃的《寒食》篇:“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10]便是记录当时长安城寒食节的场景。
四 延续于宋
宋代寒食节的风气不减反盛。据《岁时杂记》记载:“元丰初官镇阳。镇阳距太原数百里,寒食火禁甚严。有辄犯者,闾里记其姓名。忽遇风雹伤稼,则造其家,众口交偏谪之,殆不能自容,以是相率不敢犯”。[11]文献反映了官方不但不禁寒食,还下令必须寒食禁火,用法令的力量来维护寒食的礼制。寒食作为广泛的民间习俗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同时官方也顺应儒家经典中关于“改火”的礼制,大力发展了赐新火礼。
寒食节赐火在唐代时已经成为了一项节日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官方仪式。唐代《翰苑群书》便有记载指出,在当时依据官方的规矩,当政者会在寒食节的时候给新进入翰林院的学士行赐新火礼,以此来表达当政者对官员们的关心。这种礼法仪式极具象征意义,不仅是儒家传统的承袭,而且成为了当政者表达其对臣子恩惠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臣子们为了表达这种皇恩浩荡的授予,多有人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来表达对当政者的感激之心。由此所体现出来的儒家君臣忠爱之礼也是寒食节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重要表现。但是,唐代赐火的范围还比较小,到了宋代,顺应宋代“火德”,赐火礼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如下表现。
首先,官方赐火范围的扩大。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中记载:“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赏赐”。[12]从中可以看出,赐火的范围,从当政者亲信之臣,已扩大到了各种品级的官员,赐火的人员选择并非由当政者选择,而是依据官员的品级来决定。也就是说,赐火的对象从特定的人扩大到了特定的身份。这就使赐火礼成为了一种固定的礼制,而不是当政者的一时兴起。奉行火德的宋朝当政者,借由赐火,在颂扬火德时,传达着一种当政者作为天子代替上天行国运的象征性意义,同时也体现了当政者对民众的关爱,让民众在这个特殊的节日中满怀感激之心。
其次,赐火礼跳出官方中央的局限,成为一种在各地普遍施行的一种礼法活动。通过史料记载,宋朝寒食节时,各地官员按照中央设定的礼制,像当政者赐火于臣子一样,赐火给管辖地方的民众。苏轼有诗曰:“临皋亭中一危坐,三见清明改新火。沟中枯木应笑人,钻斫不然谁似我。黄州使君怜久病,分我五更红一朵。従来破釜跃江鱼,只有清诗嘲饭颗。起携蜡烛绕空屋,欲事烹煎无一可。为公分作无尽灯,照破十方昏暗锁”。[13]诗歌体现了苏轼在黄州时,徐使君分新火给他的感激之情。而与苏轼相反,祖无择有诗曰:“禁烟故事存遗俗,改火平时有旧章。纵道齐民皆按堵,堪惊烜氏昧修方。晨炊已绝供宾馔,春酒何来独酌觞。不似前年为客日,富邻犹许借余光”[14]。从诗名《庚辰清明州衙不送新火》便可以明白大意。曾任开封府知府的祖无择被贬寿州,当地官员因为其被贬身份低微,尽然在清明节时不给他送新火,祖无择一气之下写了此诗。从苏轼和祖无择的诗歌可以发现,赐火礼在宋朝时,已经从中央扩展到了地方,成为固定的节日礼制,而民众也普遍认可了官方的这一行为,将其看做是寒食期间一个和节日本身息息相关的仪式,并且有着无可取代的象征性意味。
最后,官方通过赐新火来唤起民众对当政者的感恩,寒食节的功用再一次扩大。赐新火不仅表示民众可以在寒食禁火之后生火做热饭了,更可以表示一种万象更新的意味,预示着接下来日子的丰衣足食。这种具有先秦儒家礼法特征的活动,实际上是儒学思想对寒食节改造的重要成果。唐宋以后的寒食节,逐渐摒弃了前代介子堆说的束缚,从根本上找到了寒食传统的礼法渊源,使之与儒家经典相结合,最终得到官方认可。在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助推下,寒食节在唐宋发展成为和冬至、元宵节并重的重要节日。而在其中的许多习俗,已然延续到了今天。
结语
综上可知,寒食节的兴起,因为其介子推的传说故事而受到儒学思想主导的汉代社会的推崇,介子推身上所具有的儒家传统思想所褒扬的品行以及儒家经典对其人物的塑造,使他成为民众寒食纪念的对象。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介子推的身份使得寒食祭礼成为不经之礼,从而受到官方的阻碍。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屡屡下令禁止民间寒食活动,使寒食节的发展陷入窘境。到了唐宋时期,寒食节在民间的广泛兴起促使学者开拓思维,彻底摒弃介子推俗传,转而从儒家经典寻找寒食渊源,确立寒食与儒学的契合,最终得到官方的支持。唐宋两代的大量寒食诗作以及宋代官方对寒食赐火礼的大力发展,都是寒食节与儒学结合的重要成果。最终,寒食节走出低迷重新兴盛,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沿袭至今。
注释:
①在部分文献中,介子推、介子堆和介子绥相互换用,据考证,实为介子推一人。本文采用介子推的名字,但在文献中的其他使用情况不予修改。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1] 孙通海译注.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汉)桓谭著.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 (唐)欧阳询, 等著.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
[4]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147.
[5] (隋)杜台卿著.玉烛宝典[M].北京:中华书局,2010.
[6] (唐)房玄龄,等著.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 (南朝)宗懍著.杜公瞻注.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97.
[8] (南朝)范晔著.李贤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 (宋)欧阳修,宋祁著.新唐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彭定求,等编.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宋)陈元靓编.岁时广记[M]//续修四库全书:8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2](宋)江少虞著.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410.
[13](宋)王宗稷著.东坡先生年谱[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07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4]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