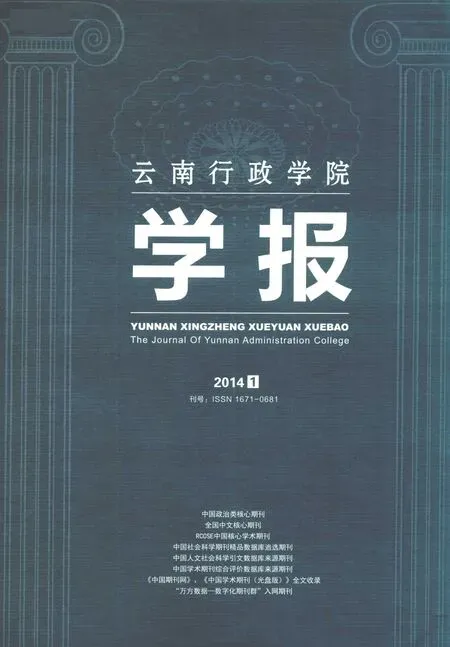金里卡论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国际化的可能性
张慧卿
(1.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镇江,212013)
金里卡论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国际化的可能性
张慧卿
(1.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镇江,212013)
金里卡针对当前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族群关系的问题上,国际社会致力于把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输出到“后共产主义”和“后殖民国家”的趋势,提出证明这种趋势合理性的四个假设。他对其中的一些假设进行了批驳,从而对西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但从长远来看,他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的全球普及充满信心。像西方很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金里卡的思想具有很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对其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我们应当批判地借鉴吸收,而不应当盲目套用。
少数族群权利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后共产主义国家后殖民国家
金里卡认为,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①模式要想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②取得胜利,依赖于以下四个假设:第一,西方国家在处理国家—少数族群关系时,有普遍的模式,即: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第二,这一模式在西方运作良好;第三,“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具备适合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生长的条件;第四,国际社会在促进或施行这一模式时应起到合法性的作用。”[1](P1)
一、西方国家是否具有处理族群关系的普遍模式?
金里卡通过分析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处理族群关系的变化趋势,阐述了西方国家处理少数族群与国家关系问题上的模式。
金里卡通过分析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苏格兰和威尔士、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比利时的佛兰德、意大利南蒂罗尔讲德语地区,美国的波多黎各等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认为西方国家对待这些少数民族的方式,呈现出如从武力镇压到融通(accommodation)的变化趋势,融通是通过地区自治和赋予少数民族官方语言权利而实现的。
他通过分析包括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澳大利亚土著人、新西兰毛利人、斯堪的纳维亚的萨摩斯人、格陵兰岛上的因纽特人、美国的印第安部落等,认为:在如何对待土著人的问题上,西方国家至少在原则上接受这样的思想,土著社会将会在不确定的未来作为独特的社会而存在于更大的社会之中,他们应当有土地要求,文化要求(包括对习惯法的承认)以及保证其作为独特社会的自治权。
另外,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在对待移民、客工、难民、非洲裔美国人等群体的问题上大多采用同化措施,是排外主义的。而在今天,大多采取承认和容纳多样性的“多元文化”的措施,是兼容并蓄的。
金里卡认为,以下五方面,是自由的多元主义模式赖以存在的原因:“不断增长的权利意识,人口统计的变化(即少数族群的人口在增加)、安全政治动员的多重途径(建立在民主政治发展基础上),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少数族群对多元文化主义越来越自信;种族问题的去安全化以及在人权问题上的共识,则降低了掌握国家权力的民族在接受少数族群在权利诉求方面所面临的风险。”[2](P122)而当这五方面的因素都具备时,一个国家不管存在不存在拥有特殊魅力的领袖、特定的政党、特定的选举制度,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趋势都不可避免。
二、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在西方是否成功运行?
金里卡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评价,体现在很多方面,我们集中在对多民族联邦制的评价上,因为它与“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最为相关也最有争议。
他认为,不能轻言多民族联邦制成功。比如,西班牙和比利时是最近几年才实行这样的制度的。不能靠一种制度仅仅运作几年的经验来评价该制度的好坏。多民族联邦制在一些方面是成功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是失败的。多民族联邦制在以下方面是成功的:促进和平和个人安全、推动民主、保护个人权利、促进经济繁荣、增进群体间的平等等。
但在以下方面,是不太成功的,第一方面,多民族联邦制不能很有效地促进族群间的交流。从乐观的方面看,很多多数族群的公民忽视或漠视国内少数族群的生活。反之亦然。更糟糕的情况是,不同族群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愤恨和不满。许多人避免族群间的接触。即使接触,也简化为讨价还价和谈判的原始形式,而不是深层次的文化共享和普遍共识。国家越来越公正、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和调节能力,而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却依然有分歧和紧张。第二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多民族联邦制并没有把分离主义从政治议程上取消。即使多民族联邦制降低了分离的可能性,但并没有把分离主义彻底从政治议程上取消。分离主义者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和选举政治中。分离主义政党在选举中经常受到强有力的支持。“即使在成功包容了少数民族的联邦制度中,它们的成功也仅仅是使分离主义的情感合法化,同时又减弱了这种情感。”[3](P96)
金里卡认为,尽管人们对多民族联邦制的感情是复杂的,但对于自由民主国家而言,这恐怕是最好的、或者是唯一的解决民族主义问题的方式。
三、“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是否具备推行
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的条件?
金里卡认为,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推动的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在大多数“后殖民国家”和“后共产主义国家”失败了。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之所以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遭到反对,是因为这些国家缺乏该模式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具体表现为:
其一,缺乏人权保证。
金里卡指出,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人权几乎没有保证。接受自治的少数民族不会在人权的框架内践行他们的权力。他们也许会利用他们的权力创立地方专制的孤岛,建立原教旨主义以及宗教不宽容的权威王国。在有效的人权框架和政治文化缺席的情况下,外来者也许会被剥夺财产、剥夺工作权利,剥夺居住权利,甚至被驱逐或被杀害。简言之,自治的运行威胁到人的生命权。对于内部成员来说,自治权力的下放可能意味着族群内部人权的滥用,比如对性别平等的践踏。这与金里卡支持“外部保护”,反对“内部限制”的立场是相对的。
其二,出于地区安全化的考虑。
金里卡认为,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种族政治不像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那样,是去安全化的。“在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国家—民族关系被认为是高度安全化的。”[2](P256)少数民族被视为潜在的第五纵队或相邻的外国势力的勾结者,这些少数民族的自治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他们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甚至进行武装起义。“后共产主义国家”许多少数民族成员是领土收复主义者。这同西方国家的情况非常不同。西方国家中不存在与其少数民族有种族和宗教亲缘关系的邻国。与之不同,“后共产主义国家”则有宗教与种族上有亲缘关系的邻国,甚至在边界重新划分之前,这些少数民族是其母国(kin-state)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不仅仅在于少数民族要加入或重新加入邻国,而且可能存在其母国要通过政治甚至武力干涉来保护“它们的”少数民族的利益。一个这种“三元”关系的典型例子是匈牙利民族、在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以及他们各自所在的国家。同样的可能遭受少数民族母国干预的担忧存在于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民族,马其顿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克里米亚、波罗的海和哈萨克的俄罗斯民族,乌克兰的罗马尼亚民族。[4](P201)
“后殖民国家”存在类似的情况,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阿富汗的乌兹别克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印度少数民族、泰国的马来西亚人、越南的华人、伊朗和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民族、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人,这些民族被认为可能回到他们的“母国”。中东的库尔德人,分散在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叙利亚,期望成立独立的国家;俾路支人,被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分开,期望成立独立国家,非洲这样的民族更多,如埃维人(居住于加纳、多哥境内和达荷美边境的黑人种族)、柏柏尔人,被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分割。有些少数族群被认为与国际上的穆斯林组织联结在一起。如,印度的穆斯林少数族群(克什米尔)、菲律宾的棉兰岛人,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人。在谈到东亚和东南亚拒绝其非公民定居者享有公民权的原因时,金里卡认为很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在文莱的华人仍然被拒绝享有公民身份。在柬埔寨的越南人的公民身份也仍然存在争议。这些情况被证明较难解决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安全恐惧的存在,也就是说,非公民定居者被视为邻国潜在的第五纵队。还有一些非公民定居者,尤其是华人,也许是由于殖民时代的特权地位,拥有不应该获得的财富。因此对其政治权利的否定被看作是对其极端的经济力量的平衡。”[5](P53)
由此可见,多民族联邦制不适用于“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在所有的这些情形下,少数民族因其与外界相勾结,而被视为国家的威胁力量,这些情况在国家弱小,或地区安全组织不存在,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存在。
其三,对国际社会的不信任。
毫无疑问,“后共产主义国家”很憎恨家长制作风,也反感西方社会把保护少数族群权利的状况作为其重返欧洲组织的前提。但事实上,“后共产主义国家”寻求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承认,认为这可以保证他们的稳定和安全。
但是在“后殖民国家”,人们并不相信国际社会会保护西方国家以外的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相反,广泛流传的看法是,人们认为少数族群权利的国际化仅仅是为了特定国家的稳定,金里卡举例说明了这一点,“例如,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关于少数族群权利的国际讨论,实质上是CIA的阴谋,西方社会试图鼓动其两个最重要的少数民族的分裂运动,包括西南的西藏和西北的维吾尔,从而分裂中国。另外一个阴谋理论也非常流行,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他们认为关于少数族群的国际讨论是为了削弱伊拉克、伊朗、埃及、叙利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在他们不同的群体中煽动分裂和叛乱。”[2](P258)少数族群权利国际化被特定国家认为是阴谋和双重标准。金里卡认为这是这些国家对国际社会的不信任的体现。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是对西方社会掩盖在人权外表下的真实面孔的揭露。
换言之,“后殖民国家”不仅害怕相邻的敌人把少数族群权利作为制造不稳定的工具,而且害怕西方社会会利用这些标准。“后共产主义国家”有第一重担忧,但是他们本身希望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所以并没有第二方面的担忧。
考虑到少数族群权利的现状,试图说服非西方国家接受自由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便是徒劳的。这三个因素解释了“后殖民国家”和“后共产主义国家”中的精英和统治集团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抵制的原因。一些推动少数族群权利在西方合法化的因素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并不存在。
第四,殖民的种族等级制遗迹。
历史上,殖民者因为害怕多数民族的反抗会在殖民地培育少数民族,比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他们曾被英国殖民者授予凌驾于僧伽罗多数人的特权。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殖民结束后,多数民族觉得他们是历史的受害者,而不是少数民族。因此,同西方不同,他们认为应当削弱,而不是加强少数族群的特权。所以,斯里兰卡独立后,要求减少泰米尔人的权利,结果引起了国内战争。在这些国家,多数族群成为遭受不公正待遇者。
第五,多数民族的缺乏。
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来看,在许多后殖民国家,没有多数民族,比如许多非洲国家,没有一个种族群体超过人口的20-30%。金里卡指出,“如果没有一个群体可以掌握国家权力,并把其作为普及特定语言、文化、认同的工具。那么,少数族群并不需要特别的保护来抵御这样的危险。”[2](P263)
第六,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认识的影响。
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对少数族群以自由民主的标准来实行地区自治是持悲观态度的,但是对民族主义终将消失则持乐观态度。相反,西方公共意见则对少数民族自治持乐观态度。而对随着现代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将会消失则持悲观态度。按照金里卡的理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对分离运动的容忍,是因为他们认为少数民族即使分离,也将会成为国家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他们将会以与人权和自由民主相一致的方式进行统治。而“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的看法正好性反。金里卡的这一论断具有主观臆测的色彩。
四、国际社会是否起到了合法化作用?
要想使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少数族群权利模式输出到“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外力。而现在,国际社会确实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少数族群权利的保护当中,但毋庸质疑的是,国际社会在处理少数族群问题时存在诸多矛盾。
金里卡认为,国际社会在普及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少数民族、土著概念的含混性及二者权利国际保护程度的差异
联合国在2007年通过了《土著民族权利宣言》,这一宣言对土著并没有作出很明确的界定,其权利的主体包括土著群体和个体。③
金里卡指出,国际社会划分少数民族和土著的标准通常是根据其在国家创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脆弱程度、现在的生产和居住方式以及权利诉求来划分的。金里卡并不赞同这样的界定,他坚决维护西方民主国家的做法,即赋予少数民族和土著同样的权利,他批评了当前国际社会对土著和少数民族的划分方式以及与相应的对待方式。认为这两个群体拥有同样的权利诉求,他们的权利诉求具有同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脆弱程度看,有的少数民族比土著受到的伤害更大、更加脆弱。金里卡提到,有一些少数族群,例如库尔德、泰米尔、巴勒斯坦、车臣、西藏等等,他们的境况比土著的境况更差,不应该遭到国际社会的忽视。金里卡把西藏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相提并论,反映了他和其他西方学者一样在西藏问题上存在偏见。西藏问题和库尔德、巴勒斯坦和车臣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土著主要是针对新大陆的族群(博茨瓦那除外),亚洲和欧洲没有土著人。然而,在殖民统治时代,针对殖民者而言,所有的故土少数民族都可被称为“原住民”或“土著民族”,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所有“后殖民国家”的族群(包括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都可以被称为“土著民族”。事实上,很多亚洲和非洲的民族(包括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都声称自己是土著。“如果少数民族把他们自己重新界定为土著的活动继续下去,将会使土著权利国际保护体系崩溃。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国际组织反复地重复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把自治权赋予那些强大的少数民族。他们不允许他们获得自治权,仅仅因为他们把自己视为土著人。”[2](P287)
金里卡指出:“试图在土著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进行严格区分以及把少数民族和新少数群体视为同一个种类,容易产生一系列困难问题:(a)道德上的矛盾;(b)概念上的混乱以及;(c)政治动力(politicaldynamics)的不稳定。”[6](P159)
在《超越土著/少数民族二分法?》④一文中,金里卡认为很多国家支持《联合国土著民族权利宣言》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宣言的通过,意味着土著民族有更高程度的自治权,而这可能成为赋予亚国家少数民族更大程度上的自治权的一个开端。很多评论者也是这样认为的。而金里卡则认为,这一估计事实上过于乐观。他通过很多事实说明,给予土著的支持,可能意味着对少数民族更大程度上的敌视。
正如金里卡在《少数群体权利的国际化》一文中所分析的:“在处理土著问题时,国际法通常采取‘融通’(accommodation)政策;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时,则采取‘整合’(integration)政策。”但这里的“土著”(indigenous)和少数民族(minorities)的含义有很多歧异,无法反映现实世界中少数族群的真实存在状况。西方土著和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国际化程度并不相同。土著居民的土地要求、习惯法和自治要求都被编入国际法文件中,例如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草案中的体现。国际法反映了西方民主国家在容纳土著方面的最新实践成果。然而,在体现少数民族的最新实践方面,国际法却明显滞后。譬如,他们只承认少数民族母语的初级教育权,而没有国际文件承认少数民族的地区自治和母语的官方语言地位。
2、国际准则和实践的矛盾
国际社会在处理少数族群问题时,并不完全遵循国际准则,很多时候,国际社会对少数族群问题的处理,特别是处理本土少数民族(homelandm inority)问题时,对于诉诸武力和顽强抵抗的族群,通常支持其自治行动;而对于力量薄弱,不具有斗争力的族群,则往往不支持其自治行动。国际社会在处理少数族群问题时,具有任意性,从而降低了自身在处理该类问题上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例如,欧洲组织在解决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本土少数族群问题时,远远超出了《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框架公约》(FCNM)的规定,因为他们认识到,FCNM在解决种族冲突时,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事实上,出于地区安全的考虑,欧洲组织在豁免一些国家,使其不受FCNM要求的约束。比如,在保加利亚,现存的制度是违背FCNM的规定的,因为他们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并且禁止种族性政党。但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民族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倔强性,在巴尔干地区,保加利亚常常被认为是积极的力量,因为其种族冲突较小。欧洲组织,决定听之任之,并不强迫保加利亚遵守FCNM标准。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无视少数族群权利的基础上存活和繁荣了很多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支持一些国家的自治,包括乌克兰(克里米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Ngormo-Karabakh)、塞尔维亚(科索沃)。欧安组织认为他们是例外的和非典型的。他们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民族是通过非法律化和非制度化的途径来获得权利的。相反,对有些少数民族在法律范围内,通过和平和民主方式寻求地区自治,欧安组织却是反对的,因为它会引起紧张状态。这事实上导致道德上的悖论,金里卡分析了这一悖论,“安全化路径鼓励了国家的强硬态度和少数民族的好斗性。”[2](P236)“它同样刺激少数民族使用暴力威胁或攫取权力,因为只有这样,它的痛苦才能得到国际安全组织的注意。”[2](P236)
事实上,国际层面的组织,比如联合国大会,在个案干预中,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联合国预设了这样的准则,少数民族只寻求整合(而且仅仅有获得整合的资格),少数民族被归属于新少数族群一类。然而在解决实际的个案冲突时,联合国却抛开这种预设,承认融通(accommodation)代替整合(integration)的必要性,并促进融通模式及其最好实践的普及。”[7](P19-20)国际组织在个案干预中,凸显了这样的问题,金里卡对揭示了这一问题,“为什么联合国支持印度尼西亚少数民族的自治而不是巴基斯坦少数民族的自治?为什么联合国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而不支持伊朗库尔德人的自治?从最好的方面而言,这些建议是专断的,而且从最糟糕的方面而言,它们是对好战的奖赏。对联合国支持一些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支持另外一些少数民族自治的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前者拿起武器并进行武力斗争。”[7](P19)
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金里卡承认西方民主国家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族群关系时有普遍的模式,即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西方运作是否良好,仍值得商榷;“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并没有适合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生长的条件;国际社会在促进或施行这一模式时并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金里卡认为在当前,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并不具备全球普及的现实性。但从长远来看金里卡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的国际化持乐观态度。“我确信,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创建正义的和富有包容性的社会仍然是最好的选择。没有国际组织的努力,就不可能做到多元文化主义的普及。因此,保证国际社会在过去十五年间做出的努力继续进行仍然是很重要的。”[2](P25)“我确信精心设计前后一贯的国际化少数族群权利体系的可靠基础还是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观念”。[2](P297)
注释:
[1]Will Kymlicka.Multiculturalism and Minority Rights:West and East,Journal of Ethnopolitics and Minority Issues in Europe(JEMIE)[J].issue#4(2002).
[2]Will Kym licka.Multicultural Odysseys:Navigat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D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3]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M].邓红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Will Kymlicka.Nation-Building and Minority Rights:Comparing East and West,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J],Vol.26,No.2(2000).
[5]Will Kym licka and Baogang He eds.Multiculturalism in Asia[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6][加]威尔·金里卡:《少数群体权利的国际化》,张慧卿、高景柱译,《政治思想史》[J],2010(2).
[7]Will Kym licka.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inority Righ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J],Vol.6,No.1(2008).
(责任编辑 :刘强)
D602
A
1671-0681(2014)01-0029-04
张慧卿(1977-),女,山西繁峙人,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13-07-24
基金:江苏大学高级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潮追踪研究”(项目编号:1281210018),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辩护及其局限—金里卡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3SJB810002)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