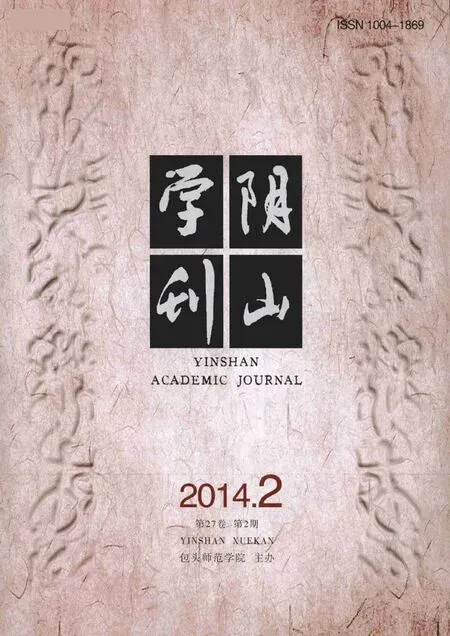“小山重叠金明灭”新解
赵 建 军
(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一
董仲舒所谓“诗无达诂”(《春秋繁露·精华》),谢榛所谓“诗有不可解,不必解”(《四溟诗话》卷一),当指诗歌的启示义而言,而非就宣示义而言。宣示义与启示义之别为袁行霈先生所提出,其言曰:“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我在这里提出两个新的概念:宣示义和启示义。宣示义是诗歌借助语言明确传达给读者的意义;启示义是诗歌以它的语言和意象启示给读者的意义。”[1](P6)不揣愚陋,稍作引申:宣示义与启示义同在一个诗歌文本之中,前者是诗歌浅显直接的部分,后者是诗歌深微含蓄的部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媒介,后者蕴含在前者之中。两者关系恰如人的躯壳与神明,躯壳的黑白胖瘦当一目了然,而神明之贤愚智不肖则需假以时日,认真考察。故而对于宣示义的解释,因其明确,是则是,非则非,不容含糊;而对于启示义的揭示,因其深藏不露,总需下一番抽丝剥茧的功夫,而结果可能“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亦不必强求一律。
然而,因为名物训诂的分歧,因为句法结构的灵活,有些古典诗词语句的宣示义竟也模棱两可,使人如坠五里雾中。如“花间鼻祖”温庭筠的代表作《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的首句“小山重叠金明灭”,就是著名的一例。
二
历来解读“小山重叠金明灭”一句的歧义主要集中在“小山”释义的不同,因“小山”释义的不同,又有“金明灭”之说解各异。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一)以“小山”为“屏山”。俞平伯先生的《读词偶得·温飞卿〈菩萨蛮〉五首》云:“小山,屏山也。其另一首‘枕上屏山掩’,可证。‘金明灭’三字状初日生辉与画屏相映。”[2](P13)屏山即屏风。又唐圭璋先生的《唐宋词简释·温庭筠〈菩萨蛮〉》云:“首句,写绣屏掩映,可见环境之富丽。”[3](P3)此处虽未“注明词中字句之音义”,(见该书《后记》),但在逐句窜讲之中,以“绣屏”对应原文的“小山”,显然是把“小山”释为“绣屏”的。“绣屏”为屏风的美称,所以此说与“屏山”说实同。(二)以“小山”为“枕屏上所画之景”。刘永济先生的《唐五代两宋词简析·温庭筠〈菩萨蛮〉》云:“小山,枕屏上所画之景。金明灭,屏上之金碧山水,因日久剥落,故或明或灭。”[4](P1)(三)以“小山”为“小山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欣赏·温庭筠的〈菩萨蛮〉》云:“‘小山’是指眉毛,(唐明皇造出十种女子画眉的式样,有远山眉、三峰眉等等。小山眉是十种眉样之一)。‘小山重叠’即指眉晕褪色。‘金’是指额黄(在额上涂黄色叫‘额黄’,这是六朝以来妇女的习尚)。‘金明灭’是说褪了色的额黄有明有暗。”[5](P31)(四)以“小山”为插在妇女发髻上的小梳子。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宫乐图》云:“当时于发髻间使用小梳有用至八件以上的,……这种小小梳子是用金、银、犀、玉、牙等不同材料作成的,陕洛唐墓常有实物出土。温庭筠词‘小山重叠金明灭’所形容的,也正是当时妇女头上金银牙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情形。”[6](P351)(五)以“小山”为“高髻”。王子今先生的《温庭筠词〈小山重叠金明灭〉图解》云:“‘小山’形容‘高髻’。重叠,形容‘玲珑云髻花样生’的形式。而所谓‘金明灭’,则形象地描述了‘玉梳钿朵’、‘宝梳金钿筐’一类髻饰在‘在头发间重叠闪烁情形’。”[7](P76)(五)以“小山”为“山枕”。此可见诸浦江清先生的《词的讲解》:“二谓枕,其另一首‘山枕隐浓妆,绿檀金凤凰’可证。‘金明灭’指枕上金漆。”[8](P146)
以上诸说,不加深究,都让人觉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细加辨析,却又都让人觉得前后扞格,窒碍难通。职是之故,才会有各执一词的聚诉纷纭。今试一一稍加辩说,以驳其非:(一)“屏山”说。所谓“‘金明灭’三字状初日生辉与画屏相映”,“金”为何等事物,“明灭”为何等情状,皆语焉不详,未免简略浮泛。况且如本文将要指出的,屏风若静止不动,虽有朝日的光辉映射,也不会有“明灭”的视觉效果。(二)“枕屏上所画之景”说。“日久剥落”云云,如此残破邋遢,实非“花间”生活情调。又“或明或灭”并非“明灭”的准确含义。(三)“小山眉”说。以为“‘小山重叠’即指眉晕褪色”,把“重叠”当“褪色”解,牵强附会之处何其明显。(四)“小梳子”之说。此说据考古以立论,诚为新颖,然而满头小梳且重叠闪烁,显然是起床之后,严妆已毕,此与下文“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之慵懒无状,及“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之方始化妆相矛盾。(五)“高髻”说。一则“小山”从来无此义项,完全是作者把自己的臆测强加给古人;再则“‘玉梳钿朵’、‘宝梳金钿筐’一类髻饰”如何“明灭”起来也不得而知。(六)“山枕”说。山枕既不能“重叠”,也难以“金明灭”。
三
一词多义是极为常见的语言现象,但经“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文心雕龙·章句》)之后,每一个词语在前后文语境的牵制限定之下,只能有一个义项被采用,而不能或此或彼,两者皆可——当然,刻意使用双关修辞者另当别论。何况温庭筠这首《菩萨蛮》所写的内容,是歌妓生活的再现,自首至尾,都是生活场景及细节的呈现,而内心的情绪隐约其中。既然是生活的再现,那么词中语句与生活场景及细节应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即凡词中所写皆以生活为蓝本,反之,生活的本相都可以由词句看出。既然如此,对于“小山重叠金明灭”的理解,便是对当时该歌妓生活的还原,只有符合该歌妓生活原貌的理解才算是正解。此外任何言之成理,皆属一厢情愿,甚或“言伪而辩”。笔者遵循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则,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为“小山重叠金明灭”另辟一说。
“小山”一词,当以“屏山”说为是。在《花间集》中,这种屏风或谓之“屏山”,如“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温庭筠《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鸳枕映屏山,明月三五夜,对芳颜”(温庭筠《南歌子》(扑蕊添黄子)),“寂寞对屏山,相思醉梦间”(毛熙震《菩萨蛮》(天含残碧融春色))。或谓之“小屏”,如“日映纱窗,金鸭小屏山碧”(温庭筠《酒泉子》(日映纱窗)),“小屏屈曲掩青山,翠帷香粉玉炉寒,两蛾攒”(顾夐《虞美人》(碧梧桐映纱窗晚))。或谓之“小山屏”,如“枕欹小山屏,金铺向晚扃”(顾夐《醉公子》(漠漠秋云淡))。其他因材质或装饰的不同,又有“画屏”、“银屏”、“锦屏”“翠屏”,“绣屏”、“云屏”、“粉屏”等名称,不一而足。种种屏风频繁出现,又精致华美,是“花间”生活的重要元素。所谓“小山”,应是“小山屏”之省,而意同“屏山”、“小屏”。
只不过“屏山”之说太过笼统,仍需深入考索,方能惬人心意。屏风是我国古代极为常见的家具,到唐宋时期,名为“屏风”者,实则种类已多。大体而论,以位置之不同,有落地式,有床置式;以形制之不同,有单扇式,有多扇式。加以变通组合,又有落地而单扇式、落地而多扇式,床置而单扇式、床置而多扇式,更加花样翻新,可以因空间、用途之不同,灵活使用。“小山重叠金明灭”一句所涉及的,只是床置式的屏风。床置而单扇式的屏风,只放置在床头,即枕头的外侧,古人谓之“枕障”或“枕屏”。如唐顾况《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有句云:“杜生知我恋沧洲,画作一障张床头。”所谓“画作一障张床头”,正是在床头安设带有绘画的枕障。床置而多扇式的屏风,在当时以六扇联屏式的屏风最为时兴。如五代花蕊夫人《宫词》:“床上翠屏开六扇,折枝花绽牡丹红”,顾夐《玉楼春》(拂水双飞来去燕):“拂水双飞来去燕,曲槛小屏山六扇”,孙光宪《菩萨蛮》(小庭花落无人扫):“晓堂屏六扇,眉共湘山远”,都提到六扇联屏式的屏风。这种绕床而设的多扇联屏式的屏风,每扇之间,以金属的“屈曲”相连缀。韦庄《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云:“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金屈曲”即用以连缀屏风的扇面、可使来回折叠的金属搭扣。而床的外侧——即供人上下的地方的屏扇,并不连为一体,而是有如两扇对开的门一样可以开合。夜晚上床就寝后,这两扇屏扇要关上,于是在床上形成一个封闭而隐秘的空间。温庭筠《酒泉子》(花映柳条):“近来音信两疏索,洞房空寂寞。掩银屏,垂翠箔,度春宵”,写女主人公独守空房,其“度春宵”前,要“掩银屏,垂翠箔”,即合上屏风,放下床帏。若是已登床而未入睡,屏风还可以是半开半掩的。李珣《望远行》(露滴幽庭落叶时):“屏半掩,枕斜欹,蜡泪无言对垂”,写女主人公困于相思,伤心流泪,尚未入睡,当此际,屏风“半掩”。情势之所必然,次日一早起床,定要打开昨晚关合的屏风。如张泌《浣溪沙》(翡翠屏开绣幄红)云:“翡翠屏开绣幄红,谢娥无力晓妆慵,锦帷鸳被宿香浓”,只有打开屏风出了床帏,女主人公才能去临镜化妆。至此当明白,所谓“小山”者,多扇可折叠的床上屏风也。
人们的注意力总是太多地被陌生的事物所吸引,而对熟悉的事物则每每习焉不察,熟视无睹。对于“小山重叠金明灭”一句,历来“小山”及“金”成为关注的焦点,而“重叠”与“明灭”两个词语,则因读者“习焉”而“不察”,故“熟视”而“无睹”,无人问津,不加辩诘。其实,如何解读这两个词语,关乎“小山重叠金明灭”一句能否前后贯通。许多学者,就因为忽略了这两个词语,虽把“小山”考证得细致入微,却与正解失之交臂。
根据上文的论述,多扇可折叠的床上屏风的形制与使用想必已经清楚。既然此屏风在睡前关合,醒时打开,则次日起床后,是要把屏风重新折叠回睡前的原样的。是的,“重叠”应为“重新折叠”之意。古汉语中单音节词语占有大多数,以单音节词“重”与“叠”相组合,既可以是习见的并列式词组,也可以是偏正词组,“重”为“重新”,“叠”为“折叠”,并无不妥。“重”作“重新”讲,司空见惯,毋庸赘言。“叠”作“折叠”讲较为少见,尚需指出。杜甫《端午日赐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谓折叠的香罗轻如白雪。王建《宫词》:“内人对御叠花笺,绣坐移来玉案边”,谓宫人在皇帝面前折叠花笺。薛昭蕴《谒金门》(春满院):“春满院,叠损罗衣金线”,谓罗衣长久折叠,上面的金线恐怕已经磨损。以上三例中,“叠“均为“折叠”之意。又南北朝时庾信在《镜赋》中亦写到起床的过程:“天河渐没,日轮将起。燕噪吴王,乌惊御史。玉花簟上,金莲帐里。始折屏风,新开户扇。朝光晃眼,早风吹面。”清晨起床,必要“始折屏风”,即把屏风折叠起来。这与《菩萨蛮》所写女主人公早起的情形是一致的。“小山重叠”就是把床上的屏风重新折叠起来;“折”即“叠”也。历来对于“重叠”二字,要么轻易放过,不置一词,要么按照习惯,解作“层层堆叠”。殊不知,把“重叠”解作“重新折叠”与“层层堆叠”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前者所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后者所写是一幅静态的景象。这一动态的过程,不仅吻合全词依次写女主人公由起床到化妆的过程的内容,而且只有这样动态的过程,才会进而有下文“金”的“明灭”不定。
“小山”既然是屏风,那么“金”必与之相关。顾夐《玉楼春》(柳映玉楼春日晚)云:“画堂鹦鹉语雕笼,金粉小屏犹半掩”,此处提到的屏风称作“金粉小屏”。何谓“金粉小屏”?即绘有以金粉为颜料的图画的屏风。金粉是唐代常用的绘画材料。唐齐己《题画鹭鸶兼简孙郎中》云:“何妨金粉资高格,不用丹青点此身”,说的是用金粉画鹭鸶。甚至有时候金粉可以用于书写,唐景审《题所书〈黄庭经〉后》云:“金粉为书重莫过,《黄庭》旧许右军多”,说的是以金粉书写《黄庭经》。可见,金粉为当时颜料之一种。以此成画,应该就是刘永济先生所说的“金碧山水”。唐代盛行的“金碧山水”就是以石青、石绿和金粉为主色的。“小山重叠金明灭”一句中的“金”,当是指屏风上绘画所用的金粉。
最后说到“明灭”。上文曾征引刘永济先生之说,以“或明或灭”对译“明灭”,又征引夏承焘先生之说,以“有明有暗”对译“明灭”,这都是似是而非的理解。准确地说,“明灭”之为词,应解作“忽明忽灭”,即因为光线或事物的活动,形成一种忽而明忽而暗,甚至忽而有忽而无的、变化不定的动态视觉效果。兹举数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杜甫《北征》:“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温庭筠《故城曲》:“游丝荡平绿,明灭时相续。”以上诸例中,凡“明灭”者,如“云霓”、“ 旌旗”、“ 游丝”等,本身皆系柔软飘忽、容易变化的事物,故而才能给人以“忽明忽灭”的视觉感受。又:韦应物《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白居易《湖亭晚望残水》:“清渟得早霜,明灭浮残日。”在这两个例子中,因为流水的波澜起伏,水中的日影载沉载浮,才有“忽明忽灭”的变化。因而,屏风本为坚牢之物,若是静止不动,附着其上的金粉绝不应该“明灭”不定。只有把“小山”解作“多扇可折叠的床上屏风”,只有把“重叠”解作“重新折叠”,使屏风动起来,才会有金粉在初日的光芒里“忽明忽灭”的视觉效果。
总之,“小山”即“多扇可折叠的床上屏风”,“重叠”即“重新折叠”,“金”指屏风上绘画所用的金粉。“明灭”乃“忽明忽灭”之谓。如此解读,全句才前后贯通而毫无窒碍。试想:晓日已生,歌妓初醒。她打开闭合的屏风,随着屏扇的移动,屏风上的金粉明灭变幻,这是多么鲜活生动而富于生活气息的图景。
[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俞平伯.读词偶得[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
[3]唐圭璋.唐宋词简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夏承焘.唐宋词欣赏[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6]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7]王子今.温庭筠词《小山重叠金明灭》图解[J].四川文物,2005,(2).
[8]浦江清.浦江清文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