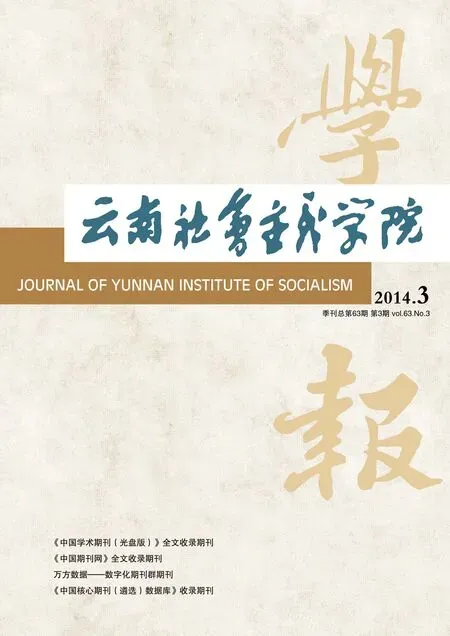越南苗族妇女跨国通婚及国家认同意识变迁研究
曹薇娜
(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国家认同是指拥有某一个国家公民身份的人们对自己所属的国家所具有的一种归属的意识,主要表现为人们自觉的身份意识以及和这种身份相关的文化归属感、国家感情、国家政治意识等。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历史上“羁縻制度”到现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政府始终强调多民族文化共存的政治体制。在中国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个体在各自传统文化的濡化作用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对于他们国家认同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而跨国通婚中的少数民族妇女面临的认同选择可以说是多个,她们的归属感可以建立在出生国家、嫁入国家和自己的民族,我们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跨国婚姻中少数民族妇女的认同归属也是不同的。基于此,我们以少数民族妇女的跨国婚姻作为切入点,在分析个案的基础上,探讨她们不同时期的国家认同意识变迁。
一、田野点概况
云南省马关县老刘寨共有62户293人,其中男性154人,女性139人,劳动力178人,目前村民们的主要生计方式仍是农耕,还有部分养殖业、手工业、商业等。村民们在高山地带种植八角、核桃、李子、板栗、花椒等作物,在河谷地带近年来推广经济作物,包括香蕉、龙眼、荔枝、柑橘、西瓜等。除占据最为重要位置的农业之外,外出打工也逐渐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村民最主要的消费是盖房,其次是重要节庆、婚礼、丧礼等仪式活动中的消费,最后才是一般日常生活中消费。
老刘寨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反映了一个特定族群在特定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等多元语境中的独特文化形态。老刘寨位于云南苗族聚居的东南部区域,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村民们日常生活中基本上都使用苗语,大部分人掌握多种语言,主要是苗语和云南方言,部分村民还熟练使用壮语、越南语等。传统节日仪式的保留也较为完整,包括春节、踩花山(农历初三至初六)、“祭龙”(农历二月初一和六月初一)、清明节、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鬼节”(农历七月半)、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等节日,以及婚礼、葬礼、出生礼、“叫魂”、祭祖、“祭门猪”、“砍火星”等仪式活动,春节可以说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老刘寨是一个紧邻越南的边境村寨,苗族边民的社会文化交往极为频繁,且置身于苗族多个支系以及彝族、壮族、汉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区域之中,从而突出体现了云南苗族与其他族群的相互交融渗透的关系,但是在婚姻上各家族均实行家族外婚制,家族内部严禁通婚,而各家族、各支系之间都可以自由通婚。
在老刘寨一带,苗族男女青年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寻找结婚对象:一种是亲戚介绍,与汉族门当户对的传统方式类似;再一种是自由恋爱,通过踩花山、赶街等传统社交活动,男女双方在对歌的过程中寻找意中人,大多数苗族男女青年以此方式来选择配偶;第三种是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形式,多数是姑舅表优先婚。20世纪80年代以前,老刘寨的苗族青年男女有着较为严格的通婚习俗,同姓之间不可以结婚,不能与其他民族结婚。直到1980年代以后,老刘寨一带不同民族之间才出现通婚现象,1990年代后这种现象更为普遍。现在,各民族之间可以实现自由通婚,但对象的选择依然有层级划分,村民的择偶对象首选苗族,然后是汉族,其次才是壮族和其他民族。
调查中,一位苗族老人告诉我说:寨子里有两个男的上门去到M那边了,一个是李家的,媳妇也姓李,像我们苗家,同姓是不结婚的,但是他们相互喜欢么,也就结了;还有一个是杨家,媳妇是汉族。他们两个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其他人要么出去打工,要么在寨子里住着,他们大都娶中国这边的苗族女孩。我们寨子里实在找不到或者岁数大了才娶越南媳妇。
老刘寨目前共有13户由跨国婚姻建立起来的家庭,2户家庭中的越南媳妇通过买卖婚姻嫁到中国,6户家庭男女双方经自由恋爱结合在一起,5户家庭的越南媳妇是中越战争时期的越南难民。国界划分之前,中越两国苗族男女通婚,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国界划分之后,老刘寨传统的婚姻观不仅仅受到苗族文化的制约,当地的苗族男子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对于女方的国籍亦有所考察。
二、跨国婚姻中越南苗族妇女国家认同意识变化
苗族传统中较为封闭的通婚规则,是经过久而久之的文化实践,逐渐形成一种模式化的婚姻观。这种观念的改变需要外在作用力的影响,能否实现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是建立在双方对各自既有文化的适应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位苗族已婚男子告诉笔者“你们汉族不太容易和我们苗族结婚,我们这边的苗族寨子很穷,汉族都不愿意嫁过来。”如今,老刘寨苗族姑娘嫁给汉族男孩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汉族姑娘嫁给苗族男孩却很少见,苗族的土地和家庭观念比较强,大多数男孩都会在本寨成家,与父母同居一处,这也是他们选择与同族人结婚的主要原因。在亲缘社会下,人们拥有相同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民族认同在经年累月的共同生活中建立起来,民族内部的无障碍交往,通过民族认同这个隐性力量,使得他们共享的集体价值观得以世代传承。
国界即国家疆域划定之初,并无跨境婚姻这一概念,通婚是少数民族世代延续的生存方式。在调查点笔者了解到,之前本村苗族间的通婚主要是在赶花山、赶街等民俗活动过程中,男女双方结识并产生感情。在同一个民族内部,民族认同感是促成通婚的主要因素,这个时候,不论住在中国还是越南,国家疆域没有完全划分,因为同是苗族,大家不分彼此。在国界划定之后,跨境婚姻的概念产生。原初的血缘亲属纽带,共同血统的部落政治制度,为一种地域联系所取代。据村里的一位周大爷讲,“早时候,界碑数量少,不是中国也不是越南立的,好像是法国,离的也很远,多远才有一个,现在(界碑)多多的呢。”地域划分不仅仅是一个物理行为、一个简单的政治作为,更多层面上促进了人们对地域范围之内文化环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和人们对民族与国家有所区别的确定性心理,人们开始从一个高空俯瞰的角度去认识周围的人。也因此,跨境婚姻成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
(一)中越自卫反击战(1979-1989)期间,“华侨”从越南逃难嫁到中国
中越自卫反击战(1979-1989)期间,由于越南政府的排华政策,此间有被称作“华侨”的苗族姑娘与老刘寨男子结婚,这也是跨国通婚在特殊时期的一些典型特点,即出生于中国的越南籍苗族妇女返嫁回中国。
个案:邹某(男,57岁)说,我媳妇是在马关县老刘从(音译)出生的,那个时候,中国这边要交粮,生活不好过,她爸爸就带她们跑去越南,他们的寨子叫六古井。后来中国越南关系不好闹矛盾了,他爸爸就被越南抓了,抓的时候他爸爸比我现在还老,抓去快到河内那边,一直到死都关在牢里。她待在老刘寨之后,她亲大舅的大姐是我妈的兄弟媳妇,她大舅来给我们说媒,我就去她家提亲了。我们1981年结婚,讨她之前还没有登记户口,讨过来之后才登记的户口,她现在有中国户口。中国越南关系不好了,越南排华,他们这些华人就过来相当于逃难,我们边境上有好多难民,大部分都是苗族、还有汉族,但是汉族很少。
若问到邹某媳妇她本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她会说中国挺好,这么多年来,虽然越南那边有亲戚,但她也很少过去,不觉得对越南政府有更多可依附的地方。熊某也是这一时期嫁到中国的难民媳妇,在笔者询问她关于越南蕉工事宜之时,她始终以“他们”一词来称呼这个群体,可见她已经接受自己的中国公民身份,这已是对一个国家政体认同的最直接表现。通过对老刘寨难民媳妇的细致调查,我们看出,上述邹某媳妇这一案例,在中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可被视为典型。这一时期越南苗族妇女的国家认同,在政治环境的构建之下,更倾向于中国,且因其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较长,已经积累了相当深厚的爱国情结。
(二)中越自卫反击战之后(1989-2000),越南苗族妇女通过自由恋爱嫁到中国
随着中越两国对外政策的逐渐缓和,两国边境村民的来往更加频繁,老刘寨苗族男子迎娶越南媳妇的情况也日益增多,虽然越南实施较为严格的户籍政策,但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和传统的民族认同观的影响,仍有较多越南女子嫁到中国,即便民俗习惯相同,她们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也需要进行不同方面的文化融合。
个案:杨某的媳妇(越南人,37岁)说,我老公比我大4岁,我们认识1年之后结的婚,结婚时我22岁。他家那时候也困难,没有给哪样东西就结婚了,几个哥弟吃吃酒就可以了。我们和他爸妈住了2年后分家出来住,我这个缝纫机是分家时候,他们哥弟一起吃酒,商量着分东西,他们说我嫁过来时候没得到哪样东西,就把缝纫机给我了,就没给其他的了。有缝纫机后,我就边学边做民族服饰,做好了就拿去卖,刚开始也做不好,做多了也就会了。他们很多人都不会,有的会也做不好。我一个星期能完成2、3件左右,做出来就会有人来买。他们越南的还是喜欢来买的,中国这边不喜欢越南的式样,越南他们也不喜欢中国的式样,我做的衣服都是卖给越南人的,一件550元左右。我自己穿的话,都是乱做,自己喜欢穿哪样就做成哪样。
老刘寨的杨某和李某,两人年龄均在四十岁左右,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人经常去越南做生意,之后都与越南姑娘结合。在老刘寨的跨国婚姻当中,老刘寨跨国婚姻中通过自由恋爱方式结合的家庭,所占比例较大,和平时期中越两国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形式呈现多样化的实践。通过此种方式结合的跨国婚姻,苗族男女青年在民族文化方面的相互认同是主因之一,这也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并纳入当地人的生活秩序中来。
(三)“买卖婚姻”或借由亲戚关系嫁到中国
从老刘寨的结婚状况来看,我们可知,现在的苗族年轻男子虽然有部分上门到外地去,但毕竟是少数,国家经济不均衡发展带来的短期效应,苗族青年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很多人都选择外出劳作,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形势限制了本地经济体的发展。寨子里的苗族年轻女孩都出去打工并嫁到其他地方,由此才促发了越南媳妇这一群体的诞生。这个群体不论在越南还是中国都属于边缘性人群,她们来到中国的时间如果达三个月以上,越南政府会撤销其在本国的户籍证明,而在中国,她们的户口、身份证等都无法办理,也由此落入既不属于越南公民也不属于中国公民的境遇。当他们有了孩子之后,一系列现实问题开始显现,诸多事情无法脱离他们所在国家的政治体系,孩子的户籍证明、日后受教育的机会,都牵扯着她们自身的国家认同,尽管她们对自身的国籍身份不以为然,但他们的后代是否能够被国家所认同的问题却显得尤为突出。
个案:冯某(越南人,37岁)说,我没有越南户口,也没有中国户口,算是黑户,但是我在家里头做衣服,也不去哪里,我也不管那么多,小娃娃有户口就好了。我们有结婚证,拿着结婚证去给小孩办的户口。这边亲戚也多,经常来往,不管中国还是越南,我觉得哪里都一样,都是我们苗族嘛。
跨国婚姻家庭中小孩的身份证明,需要拿着男方的身份证明,到镇上或州上去办理,费用一般都不少于一千元或者更多,流程比较复杂,大多数越南媳妇都表示出她们的这一忧虑。越南媳妇自身的国籍身份不一定代表她的国家认同,但她们在对于后代国籍身份的选择方面,国家形象在重复再现的过程中,认同感逐渐建立,因只能拿着男方的身份证明去办理,也只有中国身份才是她们后代的国籍所属,但这种认同并非建立在抛弃原有认同的基础之上,最后的结果是两者达到相互兼容的状况,主体的认同观念变得更加包容而实际。
三、越南跨国通婚苗族妇女国家认同意识变迁的影响因素
从老刘寨跨国婚姻的历史演变来看,苗族妇女的国家认同,并非仅仅受到国籍这一因素的影响,能否拥有对自己所生存的社区环境乃至国家的归属感,根本上源于她们能否融入当地文化。与此同时,她们嫁到中国的各自缘由,对于其自身的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亦有所影响。
(一)“跨国者”能否获得嫁入地给予的合法性待遇
从上述邹某的案例中我们可知,中越自卫反击战期间被称为“华侨”的许多越南媳妇,是这个特殊时期出现的难民,他们在越南遭到排华待遇,回到中国避难,受到中国政府的安置和照顾。在越南遭受的拒斥性认同,与在中国享受的合法性待遇,这一系列政治遭遇,已经在引导着她们的国家认同观,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对于这部分难民来讲,她们对中国的认同要强于对越南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建立在历史情境反复再现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体的归属,这也是长期以来,他们融入本地社区文化的体现。
(二)“跨国者”能否顺利重构嫁入地的文化环境
中越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以后,通过自由恋爱而嫁到中国的越南媳妇,无法顺利完全融入当地的文化,在对自己社会角色的定位上,倾向于排斥自己所生存的文化环境,制约因素更多的来自生存技能单一化与亲属关系的单薄,这两个关键因素制约着她们在陌生环境中去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网络,她们的生存状态无法得到保障性关怀,更多人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形。
个案:陶某(38岁)说,我家爷爷是从马关那里上门过来的,老刘寨就我们一家。我原来出去广东打工,回来后年龄太大,家里又穷,妈妈爸爸很早就离婚,我们兄弟三个跟着妈妈一个人,不容易娶媳妇。后来Q那边的亲戚给介绍,娶了越南那边的女孩,给了介绍费三千元,办酒席花了三四千左右,我媳妇嫁过来的时候,有十八岁,她爸爸姓杨,他爸爸早早就去世了,她妈妈后来嫁去古家,她是吃古家饭长大的,所以结婚三四个月之后,我就领着她在寨子里认亲戚,古家和杨家她都认了。
陶家媳妇通过“认亲戚”建构起的“拟制姻亲关系”,使得越南媳妇在夫家的生活空间里建立起拟制娘家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此获得文化归属感和社会归属感。也由此,越南媳妇获得一种融入当地社交网络的便捷途径。而其他越南媳妇,不若陶某媳妇一般幸运,她们之前的社交网络或被截断,或局限于越南方面的直系亲属,部分越南媳妇有姐妹来中国打工,更多是只身一人在中国生存,诸多生活与社交细节都需要依靠丈夫一方,这也是她们在婚姻中无法拥有主动权的表现,下述案例讨论的便是这个问题。
(三)“跨国者”能否顺利重构嫁入地的社会关系
语言,特别是发展完成的语言,是民族自我认知以及建立一个看不见的民族边界的基本特征。在对老刘寨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越南媳妇喜欢购买一些说苗语的碟片拿回家看,在中国,大多数电视台的使用语言都是普通话,她们听不懂。由此看出,越南媳妇的国家认同,与她们自身能否融入当地文化密切相关。
个案:陶某(23岁)说,我经常看电视,所以会听一些汉话,但很不会讲。我家那边有人结婚,我老公当时过来,他当时跟我说,过来会带我出去打工,不用下地,我当时信了,就跟我妈说我不想读高中了,我妈也就同意我结婚了。我在家没下过地,所以不会,嫁过来一年之后觉得很后悔,结婚五六个月左右有了第一个孩子,有了孩子之后,也就只能待在这边了。我不喜欢这里,他们天天都要下地,我老公不喜欢我,他爸妈还有其他人他们不喜欢我,因为我不下地。
村寨里的生产结构较为封闭,村民的生存根基便是庄稼,若不劳作,意味着无法生存,所以勤劳是外来媳妇必须具备的品质。越南媳妇嫁到中国,大都会跟着丈夫外出打工,这是新一代人对传统生计方式的突破,但对于她们自身来说,这种生活模式并不一定是较好的选择。
个案:马某(男,30岁)说,我初中毕业之后,在M打工,赶街的时候认识的她,结婚之后在家待了三年左右开始出去打工。我们在深圳那边的工厂里拉闸,我是拉长,一个月能拿不少于四千,她就要少一点了,拿两千左右。有什么事都是经理跟我说一声,我再给她说就行了。她能听得懂百分之二十的汉话,有时候她自己出去买菜,不然就是在家看孩子。我们经常在外打工,所以很少回家,她很想家,经常跟我哭。
由此看出,外出打工,越南媳妇的身份认同更显狭隘与局促,面对强大的汉文化,她们无法确立自己的社会身份,她们与周围人的交集很少,几乎全部依赖丈夫一方。如果生活在苗族地区,情况会好很多,但若远在广东、上海等地,在完全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里,国家认同更难建立起来。
四、结语
跨国婚姻中的越南妇女,从自己所生长的熟人社会团体中分离出来,进入一个陌生的空间,通常情况下,类似群体都被列入边缘人的范畴。这种边缘人的身份,首先来自国家政策与制度的排斥,其次是经济上的失衡和生活方式的不适应,这三方面对身处跨国通婚语境下的越南妇女国家认同感的塑造,亦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越南媳妇渴望一种归属,而最后她们把这种归属指向了民族认同,这种认同也是他们之所以跨境生存的最根本原因。可见,国家疆界并不会阻碍民族认同的发展延续,在两国政治经济制度并不平衡的情况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
老刘寨的这十多个越南媳妇,因为其自身的流动性及边缘性的特质,很难被设定为某个社会身份,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跨国婚姻中,越南媳妇扮演更多的是苗族妇女的身份,而非越南公民或是中国公民,由此,她们对身为一国公民所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在意,这也是苗族妇女国家认同感缺失的原因之一。但是从长远考虑,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公民本身又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由于这些越南媳妇缺少了身份的认同,她们在中国的生活和出行的自由等很大程度上就被限制了,甚至当涉及到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时便会放大这种限制。
越南媳妇国家认同的缺失与混乱,根本上来自于政治上的疏离、经济上的失衡和当地文化融入的程度。我们从跨境婚姻中少数民族妇女的国家认同方面看出的不仅仅是认同的重叠与错差,更重要的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如何降低这种不平衡的程度,还需要国家在政策层面做一调整。跨国通婚是长期以来边境民族通婚传统在遭遇现代民族国家时的一个适应性挑战,涉及到边疆治理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制定及边疆繁荣稳定,我们应充分尊重边境民族社会的复合多样性特点,以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元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