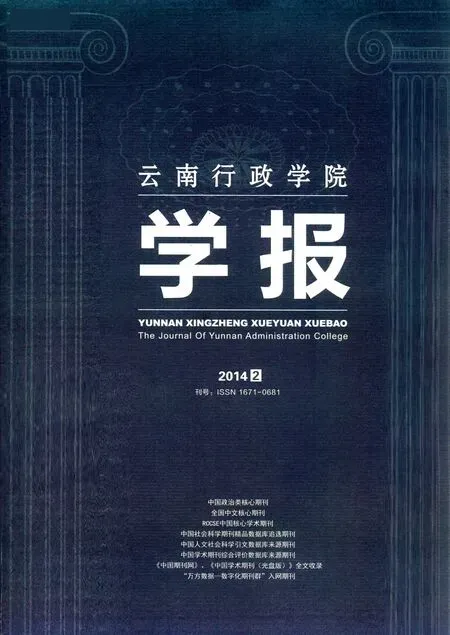试论明代云南社学与基层社会的软性控制*
付春,管卫江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昆明,650111)
试论明代云南社学与基层社会的软性控制*
付春,管卫江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昆明,650111)
社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府、州、县、司、卫的治所及乡镇里社兴办的初等教育学校。明代云南仿中原社学之制,于成化年间开始在其境内推广。社学不仅针对普通的汉族平民进行教育,也将教育面普及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因此社学在云南的开办就显得别有蕴义。明代云南的社学,正是基于国家一统、边疆稳定、民众启蒙与开启民智的立足点而设立的。它对于提高民间识字力和推动教育平民化,起到了儒学和书院无法比肩的历史作用,在推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体发展,促进全民社会文明化程度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及实现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维系与软性控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明王朝治边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云南;社学
明代云南社学自成化年间创立,在地方初等教育中发挥了府州县学和书院无法比肩的历史作用,对于推进汉文化,提高识字率,推行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了边疆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从维护边疆的稳定、巩固国家统一的角度看,在云南边疆兴办社学,普及汉文化,是明朝维护边疆统一安定,加速边疆社会进步和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方针政策,具有明显的政治教化、基层软性控制和民族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融合的蕴意。明代云南社学对于基层社会软性控制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学在云南的设立,是中央王朝在云南正式实施官办初等教育的开始。
宋以前的蒙学多由民间私学承担,诸如各种类型的私塾、族塾等。至宋代,中央王朝才开始重视初等教育,开了国家干预初等教育的先河。但是,由官方创办的初等教育在宋代还处于萌芽状态,既没有大规模的办学运动,也缺乏规范的管理规则,尤其是很少针对民间子弟来设立蒙学教育,使得教育的普及面相当有限。宋元明三代,官方逐渐加强初等教育的干预力度,在官方的倡导和管理下,初等教育逐步规范起来并不断扩大,这就为以后官办初等教育向基层、向边疆、向民族地区大规模推进的创新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云南地处边疆,自元代开始设省,并推广儒学教化,但是主要集中在为科举考试造就仕宦阶层,并没有设立以识字明理为目的的地方初等学校,蒙学教育也由民间私塾、族塾来承担,也就是蒙学教育并没有纳入官方的教育体系。明代在云南设立社学,才将此层级的教育第一次纳入了官方教化体系之中,自此,云南的学校教育从元代单一的路、州学,发展到了府、州、县、卫、社学及书院五级,云南也有了与全国一致的真正意义上的官办初等教育。
而明代立国之初,就十分重视发展地方初等教育。朱元璋提出:“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因此一再强调:“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即所谓的“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鼓励广行教化。朱元璋一直认为元亡的原因之一是社会风气“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高卿无异,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是度”,故其主张“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之为先”,希望通过教化来化导风俗,通过风俗的改善来治理国家,“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视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化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太祖又云:“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因此,明统治者希望把兴学立教作为端风正俗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社学成立之时,朝廷就规定“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分,各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务要各知孝悌忠臣,敦本抑末。依乡原例,出办束修,自愿立长学者听。若积久,学问有成者,申覆上司照验。”可见,明朝设置社学,是在朱元璋“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思想影响下,积极推行“乡村教化”政策,意欲于“习礼成俗”之中,贯彻国家意志,实现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维系与控制,即一种无形的软性控制,来维系社会与统治秩序。而从成化年间在云南兴设的社学,主要是由官府来主持的,是一种官办的初等教育。如姚安府在设立社学之时,官府“各给纸米,以助栋柱栟椽砖瓦”,其建筑规模“学正堂五间,左塾房四间……与儒学一致”,同时。“每一社学,择老成教读一员,训诲愚蒙,将党庠、家塾标榜灿然”,可见社学的创建,官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种初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教辅政,巩固思想文化统治,进行软性控制。因此,社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宣传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如姚安府知府张金在《社学记》中就云:“余以为孔子之道,无往而不在,如水之于地,无往而不有。故,水能生物,道能善人。水由源泉,然后能达江河而抵于沧海;道则有蒙童,然后能造圣哲,而入于圣人”,可见社学主要是以圣人之道教化边民蒙童,使之自幼就懂得纲常礼仪制度。即儿童初入社学,先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进一步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明政府还规定《御制大诰》及明朝律令为社学学生的必学内容。为了体现以教辅政的治国思想,朱元璋在洪武八年诏令全国创办社学时,就强谓“廷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部制大诰及本朝律令”,“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洪武二十年,又下令奖励社学中的优秀学生,“令社学子弟读浩律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育多寡,次第给赏。”而云南的社学创设及教学也是遵行中央王朝的规定的,如张金在《社学记》中所言之“广社学以启愚蒙,收放心,养德性,俾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躬行实践,以基作圣之功”,正是贯彻中央王朝以教辅国及对基层社会软性控制的思想。可见,明朝统治者在云南大力发展社学的教育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安分守己的“良善之民”,以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
第二,社学在云南的设立,扩大了教育对象的数量与范围,使更多的少数民族子弟得以就学读书。
在明代的官学体系中,正规官学学额有限,但是书院、社学不在限制之列,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就学的范围。入学的对象,不再局限于贵族子弟,明代的社学主要为化导边民而设,因此,当时的土官、土民子弟,甚至是当地民族的一般子弟均可入学。与内地一样在孔子“有教无类”思想指导下,云南各阶层的子弟都有权接受教育。如鹤庆府是明代云南社学设置较多的府,在康熙《鹤庆府志》中,所记社学共36所。分别为蒙圈(在蓬密村)、雪崖(右石头耳村)、义漰、南河、三台(俱在赤土河村)、龙溪(在大弄)、清潭(在河头村)、石潭(在石朵河村)、东村(在城东村)、象石、龙池(在城西村)大墩、迎楫、长康、环江(在求平乡)、陂邑(即孝康村)、临江(在开罗邑)、象山(在蜂木和)、南邑、松友(松梅曲村)、温泉(在曲罗邑)、中路(亦九所)、云峰(在三庄村)、松贵、西邑、七坪、东坪(在府南七十里)、鱼塘(在北衙厂)、班登、金堂、渡口、宣化(在西村)、龙桥(在观音山驿南)、清海(在罗牧社村)、化夷(在石碑坪)、梅城等。从这些社学的名称和所在地点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鹤庆府社学除少量设置在经济发达的中心城镇外(如设置城东、城西村的东村社学和龙池社学,在北衙厂的鱼塘社学等),基本上设置在村、邑等村社聚居区,呈现出一种由经济发达的中心城镇逐渐向村、邑发展的态势。且鹤庆府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其地“虽在夷倮,亦师以教之”,因此,社学也体现出由城镇及巨乡大堡向少数民族聚居区辐射的趋势。再者,从部分社学的名称来看,也体现出教化少数民族的一种趋势,如宣化社学、化夷社学等。这就促使了边地教育的一种普及化,体现出教育平民化的趋向。而在姚安府,也是明代社学设置较多的府,共28所,其地“军有汉人,民有爨僰”,也是一个典型的汉夷杂居区,且其地“以乡遂村屯人,染土俗之日深,被文教之化浅,抗悍鄙野,嶷嶷如是也”,文教未开,民风彪悍鄙野,因此在此地设社学28所,主要设于“城南关、牟地邑等处”,而设在府治的南关社学仅为一所,“为诸乡社学之首也”,其余则完全设于牟地邑等村寨。所以,从成化年间云南开始推广社学,因云南少数民族居多,因此办立社学不仅针对普通的汉族平民,也将教育面普及到了夷民,因此社学在云南的开办就显得格外有意义。
第三,社学在云南的设立,促进了边地民族教育的发展,增强了边疆人民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感。
由于社学不同于府州县儒学和书院,不以为国家输送科举人才为主要目标,社学主要是承担地方民众的初等教育的功能,达到识字明理而已。明代云南凡是设立社学的地方,都或多或少对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清代乾隆年间任职云南的陈宏谋所言:“社学之设,最有关于教化,故历代皆重其事。”从社学办学的宗旨来看,入社学就读者非仅为求取科名,“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培植根本,实行为重,非欲其专攻举业,求取功名”。所以,进入社学的孩童,能成材的则可以入书院或府州县儒学继续深造,参加科考,入仕为官,成为为统治阶层服务的一员。而大多数社学蒙童则可通过社学教育懂得伦理大义,提高了个人素质,学习了做人的道理和一些生产技能,最终促使云南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如,明代鹤庆府设置了36所社学,“昔司马张廷俊建社学三十余所,虽在夷倮,亦师以教之,于时盗贼潜藏,四境宁谧,化导之功也”。而在姚安府,由于是一个汉夷杂居区,社学设立之后,该地出现了“用夏变夷……以敷文教”,“文教之盛,猗欤休哉”的状况。在姚州的苴却,由于“滇云远居天末,而苴却又极末之末”,其地“异端邪说”、“惑世诬民”,在该地建社学乃为“阐明先王之道”,“入其门者,以讲以射,兴仁兴让,咸知君臣父子之纲,共晓春秋礼乐之义。人才蔚起,出为国桢”。可见中央王朝试图通过社学的教化,用夏变夷,在思想方面对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了有力控制,使其统治势力渗透到边疆地区,使边疆少数民族能够接受中原文化,缩小边疆同内地文化的差距,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整体发展和推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一体化进程。
第四,明朝在云南推广社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达到了化民成俗及实现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维系与控制。
从地缘政治学和国家边防的角度来看,云南对内居于西南诸省之上游,内接西藏、四川、贵州、广西各省,与之辅车相依,恰似国之犄角。对外则据印度支那之顶端,南凌越南,西控缅甸,若高屋建瓴,形势雄胜,地位冲要,为边圉之重镇,国防之要塞。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背景,一直以其独特方式对全国政局的变化产生着巨大影响。正如顾祖禹所言,云南“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但“云南之于天下,非无与于利害之数者也”。西南边疆无事则已,有事则云南首当其冲。云南一隅之得失,小则关系到西南诸省之安危,大则影响整个国家之兴废。史迹所载,斑斑可考。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帝国正式建立明王朝时,云南仍处在故元朝梁王巴匝剌瓦尔密的控制之下。大理段氏、麓川思氏以及滇东的“夷人”称霸一方,据地自雄。朱元璋意识到云南在整个中国统一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稳定中原,巩固政权的同时,朱元璋先后七次遣使诏谕云南梁王和大理段氏,但云南诸部自恃山高水险、地处边远,对明王朝的诏谕置之不理,反而杀害来使,拒不归附。朱元璋立国十余年,云南恃远自雄,朝廷屡派使诏谕云南屡抗命,拒不归附。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认为“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余孽巴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招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下定决心匡扶云南,乃于贵州设省,打通通往云南的交通沿线,并移民屯垦,准备军粮,以备征讨云南。朱元璋征讨云南的决定得到群臣响应。九月,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帅将士14万余人,大举进军云南。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傅友德三将军率大军由辰、沅趋贵州攻克普安、普定,进兵曲靖,击败梁王将领达理麻于白石江。明军乘胜而进,包围中庆城(今昆明市),梁王巴匝剌瓦尔密及其亲信驴儿达德等自杀,元右丞观音保等出降。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正月,傅友德率师进驻威楚(今楚雄),招谕段世投降。段世遣使致书傅友德表示愿意归附明王朝,“依唐宋故事,奉正朔,定朝贡,以为外藩”。大理依然独立自治,并维持其总管的地位。否则,兵久变生,于明军不利,“莫若班师罢戎,奉扬宽大”。傅友德严正驳斥段世谬论,命令段世及早降服。段世又致书傅友德威胁说:“西南称之为不毛之地,易动难安,即日春气尚暄,炎瘴渐重,污秽郁蒸,染成疬疫,拒汝不暇砺兵,杀汝不需血刃。四五月雨水淋淫,江河泛涨,道路阻绝,往复不通;则知汝等疲困尤极,粮绝气弊,十散亡八九,十患倒六七,形如鬼魅,色如黑漆,毛发脱落,骨脊露出,死者相藉,生者相视,欲活不能,凄惨涕泣;殆及诸夷乘隙,四向蜂起,弩人发毒箭,弓人击劲矢,弱则邀截汝行,强则围击汝营,逆则知之;汝进退果狼狈矣。莫若趁此天晴地干,早寻活路,全骸逃归乡里,但得父母妻子一日完聚之乐,可瞑目无憾也。虽以军律论,岂有尽诛之理哉!宁作中原死鬼,莫作边地逰魂,汝宜图之”。恫吓之势咄咄逼人。段世还附诗一首,“方今天下平犹易,自古云南守最难。拟欲华夷归一统,经纶度量必须宽”。又一次发出威胁,强调明王朝只有采取让大理依旧保持独立自治的办法才是上策。
段世列举汉唐宋元的历史案例,试图证明“依唐宋故事”是处理云南事务的良方。可是,时代不同了。明王朝同样回顾历史的教训。唐代处理云南事务失当,导致南诏政权的建立和云南的相对独立。南诏不断胁扰唐朝西南边疆,致使唐朝为之困弊。宋人总结唐朝的教训,错误地认为,“唐亡于黄巣,而祸基于桂林”。宋朝北有大敌,无暇顾及云南,加之将南诏看成唐朝覆灭的主要祸根,对大理国始终采取消极的防范,甚至编造出“宋挥玉斧”的神话,将大理政权视为外藩。公元1253年,蒙古军队强渡金沙江攻破大理国,将大理作为进攻南宋的军事基地,征调大理国的爨、僰“蛮兵”,利用大理的资源,从西南进攻南宋,与北方南下的蒙古军队相呼应。南宋陷于蒙古军队南北夹击的狼狈境地。此时,宋朝君臣方领悟到将大理划为外藩的失误。可惜悔之晚矣!南宋人错误地把南诏当成唐王朝灭亡的祸根,宋王朝放弃对大理的经营,使南宋王朝失去西南的屏障,给蒙古军队以可乘之机,将大理(云南)作为摧毁南宋王朝的西南根据地。唐宋王朝的教训,与明朝大兵压境的优势,使朱元璋清楚地意识到不可接受大理保持独立自治的无理要求,统一云南是统一整个中国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且日趋衰落的大理总管势力,早已无力招架强大的明朝军队的打击。他给傅友德、蓝玉、沐英三将军下令:“云南自汉以来服属中国,惟宋不然,胡元则未有中国,已下云南。近因彼肆侮朝廷,命卿等讨平之。今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当即进讨。……夷性顽犷,诡诈多端,阻山扼险,是其长计,攻战之策,诸将必酬之熟矣。若顿师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胜,乘胜进取,一举而定,再不劳兵可也。”蓝玉、沐英遵照朱元璋指令,一鼓作气,挥师进取,攻克大理,段世就擒。明军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由是车里、平缅等处相继来降,诸夷悉平”。大理之战,摧毁了自元以来在洱海地区割据130年的大理段氏政权。对于统一云南,巩固中央王朝在云南的统治,是至关重要的一次战役。
平定云南之后,怎样使云南保持长期稳定,不致再出现诸如大理政权之类的独立政权,这是明王朝平定云南后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朱元璋乃谕令傅友德、蓝玉、沐英说:“为今之计,非为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尔”。但怎样才能“使其无叛”呢?除了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手段外,最重要的就是需要采取一种柔性控制的教化手段,明王朝乃在云南大力设置社学。明代云南社学的设立也成为巩固明朝在云南统治的措施之一。虽然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还没有直接的材料来证明这一论点,但间接的材料却屡不鲜见。林超民教授在《白族形成问题新探》和《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等文中提出了大理国时期,云南出现了白族化的倾向,元代云南行省的建立及对云南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断了大理国时期云南“白族化”的进程。但元朝段氏仍为大理路总管,兼摄宣慰使都元帅,且参与行省职务,以至段氏为行省平章政事,成为云南的强权实力人物。大理总管与元朝对云南的统治相始终。整个元代,大理总管位高权重,统辖地区甚为广阔,统领着大理、鹤庆、姚安、蒙化、巍山、永昌、腾冲、顺宁、德宏及明代的勐养、木帮二宣慰司,孟密、蛮莫二宣抚司之地不过大理总管实际控制的地区以洱海区域为主,洱海地区成为大理总管统领下的一个自治地方。尽管元代统一云南的各项举措,对于改变大理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仅仅是相对于省会昆明等地区,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变动相较要少一些。洱海区域一直还存有白族化的趋势。所以明军进云南之后,师范在《滇系·典故系》中载:“自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于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手破天荒,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袁嘉谷在《滇绎》中,不仅转引师范之说,还将明初与元初忽必烈入大理后,命姚枢搜访保存图藉一事对比,谓明初之焚书可谓“得失霄壤矣”,对大理国可谓达到了“灭国先灭史”之极。即为了割断云南旧族的文化联系,明军平定云南之后,傅友德等人将其有关文献统统焚毁殆尽。焚毁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进行思想上的控制呢?由此,明王朝在云南大力兴设儒学,特别注重对洱海地区的办学,试图把儒家学说介绍到云南,从思想上进行控制。而社学也是明王朝进行儒家教化的一个场所。
从云南社学的分布情况看,社学也主要是分布在洱海区域的大理、鹤庆、蒙化、姚安等府。特别是在大理府,据天启《滇志》记载,仅有记载的社学就有7所,而“大理府社学,城内外皆有”还没有计算在内,鹤庆府则有36所,姚安府28所,这些也正是当时的大理段氏的统治区域。而整个有明一代,在云南所设立的社学总计169所,其在大理总管统辖地就设置了三分之一强之多,可见社学的设立对于明王朝化民成俗及对云南民族地区的软性控制的意图之明显。
[1]傅维麟.明书(卷20)学校志[M].国学丛书本.
[2]明太祖洪武实录.洪武八年正月丁亥条(卷96)[M].明会典(卷76)[M].元典章(卷23)[M].户部九·农桑·劝农立社事里[M].
[3]民国姚安县志(第七册)[M].文征·社学记.
[4][清]佟镇纂.康熙鹤庆府志(卷15)[M].学校·社学.
[5]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R].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6]陈宏谋.五种遗规·养正遗规·吕新吾社学要略[M].
[7]欧阳宗书.中国古代宗族教育管窥[J].江西大学学报,1992,(1).
[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南纪要·序[M].
[9]倪蜕辑,李埏.滇云历年传[M].云南大学出版社(昆明),1992.
[10]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卷)[M].
[11]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南诏传[M].北京:1975.
[12]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M].中华书局,1984.
[13]袁嘉谷.滇绎(卷3)[M].
[14]古永继.点校天启滇志(卷8-9学校六)统计[M].
(责任编辑 高云)
D691.71
A
1671-0681(2014)02-0013-04
付春(1978-),男,云南江川人,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博士;管卫江(1964-),男,云南宣威人,中共云南省委党校讲师。
2013-09-22
本文为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边疆民族地区的初等教育与基层社会控制——以明代云南的社学为例”(编号: 2010Y413)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