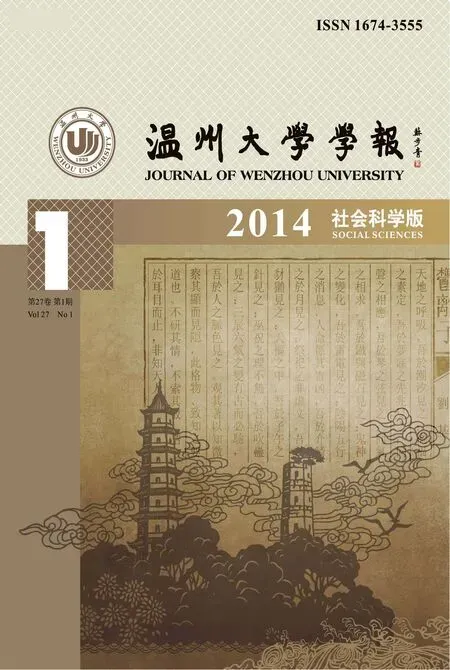集体行动、网络与温州企业家群体
陈 翊
(温州大学国际合作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集体行动、网络与温州企业家群体
陈 翊
(温州大学国际合作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集体行动对温州企业家群体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搭便车利益是集体行动集团形成的诱因,社会网络带来的额外收益是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高密度网络的情感交流是集体行动稳定合作的保证。然而,集体行动也为温州企业家群体带来隐形危机,即集体行动利益创造功能的弱化、集体行动结构分化和集体行动困境难以逾越。当这些隐形危机转化为显性危机时,集体行动又成为传导途径和放大器,将个体层面危机转化为群体危机。
集体行动;企业家群体;网络;温州
企业家群体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指拥有一定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借此从事流通经销、投资生产或提供相关增值服务等各种经营活动,以赚取利润一个经营者群体[1]。随着浙江产业集群的兴起,企业家大规模涌现,形成了数量较大的企业家群体。温州是中国最盛产企业家的地区之一。据统计,2009年底温州个体工商户29.69万户,私营企业6.45万户,合计达到36.14万户,其中每万人个体户数为381.08户,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9%①由《温州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所得.。另外,约17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从事工商业,近60万温州人在世界的131个国家和地区艰苦创业[2]。在温企业家、在全国各地的温籍企业家以及在世界各地温籍企业家共同构成了温州企业家群体。温州企业家群体有极其统一的行动模式,如温州人喜欢“炒”,炒房炒煤炒借贷,连企业外迁也统一行动。奥康去重庆璧山建立西部鞋都,众多配套企业跟着走;打火机的整个产业链迁移慈溪,合成革企业整体迁往丽水。温州企业家群体的这种集体行动是如何形成的?其对温州企业家群体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试图在考察温州企业家集体行动逻辑的基础上,将其置于网络的背景下,研究其形成过程和正负面效应。
目前,对企业家集体行动的直接理论探索不多,关注较多的研究是将企业家集体行动置于行业协会研究的框架之下。如黄少卿、余晖[3]考察了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证实行业协会在企业家集体行动中的积极作用。郑江淮指出[4],企业家集体行动必须由协会出面协调和组织才有好的效果。郑小勇发现[5],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受外生事件、外部反应、反抗意识、外部资源、组织水平及集体认同等因素的影响,行业协会对于外生事件、外部反应、外部资源及组织水平因素中的动员强度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郑慧认为[6],商会为企业家的企业提供所迫切需要的俱乐部产品——行业秩序、价格协商、企业声誉等,为资源配置制定着规则,弥补正式制度的缺失。还有一部分学者从企业家群体中的个体特性着手,研究集体行动动力机制和形成机制。朱宪辰、李玉连[7]通过引入异质性个体及其在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策略互动,证明企业家集体行动的实现机制是依靠规模存在差异的企业之间的动态博弈,实现的结果和路径是拥有最大规模企业的企业家充当领导者,规模较大的企业家跟随参与,其他众多小企业家选择搭便车。季元杰[8]提出,温州商人行为模式由“自利导向”转向“合作导向”,集体行动是面临困境时“被动的自愿”。
一、集体行动、网络和温州企业家群体培育
集体行动最重要的动力机制是集体行动成员的自我利益诉求。温州企业家创业的基础是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个人关系上的、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宗族纽带形成和维系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为企业家创业提供了信息、资金、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本这些基本资源和互助互利的空间。从个体层面看,在一个发育不完全的市场中,人们不得不借助社会网络来降低风险。集体行动既是理性个人最优化的选择,也是网络整体利益的追求手段。
(一)集体行动集团的形成
集体行动的困境之一是“搭便车”行为。奥尔森认为[9]13-14,典型的大型组织中个体成员的地位与完全竞争中企业的地位,或国家纳税人的地位相似:他个人努力不会对他的组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不管他是否为组织出过力,他都能够享受其他人带来的好处。奥尔森的理论针对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天然形成共同利益集团。然而,企业家并不是公共产品的必然消费者,若没有搭便车利益的存在,集体行动的集团还能否成立?对于温州企业家群体而言,以血缘、地缘、亲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是集体行动集团的基础。当他们将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网络后,社会网络就不再只有单纯的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双重叠加的网络。网络成员在做出判断时不仅要遵循社会网络规范,还必须要考虑经济利益诉求,做出合理的投入产出分析。所以,笔者认为,个体加入集体行动集团首先是理性的个体成员基于对自身的成本收益考虑而做出的选择。从事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是需要前期投入的,这个前期投入主要包括信息搜寻、可行性分析以及资金筹措。这些投入属于沉没成本,如果该项经济活动没能有效开展,那么这些成本就无法收回。就个体成员而言,当他们的知识和能力无法帮助他们做出成本能否回收并产生经济效益的理性判断时,加入企业家群体网络,遵循网络惯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纳尔逊和温特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识的分散性提出了惯例的概念[10]。温州企业家的日常行为是以惯例为基础的,诸如生产计划、价格确定、资金筹集都遵循以惯例为基础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随时计算最优解决方案。参照网络里的成功个体的惯例,复制他们的成功路径,甚至照搬他们的运作模式,既可以保证创业活动顺利开展,又将失败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这种搭便车产生的经济利益刺激个体不断加入集团,参加集团集体行动。所以,搭便车带来的经济利益促进了集体行动集团的产生。
(二)基于投入-产出理论的集体行动收益
集体行动需要支付的成本有直接资源成本、组织成本、监督成本和激励成本。直接资源成本是提供集体物品的生产成本,和集体行动的规模保持正比例的关系。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是协调人际关系、防范损害网络利益所支付的交易成本,和网络的规模相关。随着网络规模的增加,需要协调和防范的环节趋于增多,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会越来越高。激励成本是对集体行动领导者的额外奖励,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集体行动领导者所获得的收益与之付出的成本并不成比例,所以需要额外的奖励来对其成本进行补偿。激励成本主要与网络紧密度相关,高密度网络的激励成本往往较低。
对于温州企业家群体而言,集体行动中似乎不存在组织成本,即使存在,也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温州商人所处的商业文化属于“低本位文化”,人们更喜欢含糊和间接的交流,而且信息交流多依靠共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识[11]。徐淑芳认为[12],信任有益于经济活动,这是因为他能够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的合作。温州企业家群体网络联系非常紧密,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很高,仅仅凭一句话就可以达成一致意见,沟通、交流的成本非常小。血缘、亲缘、地缘所带来的天然高信任度有效降低了组织成本。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温州企业家群体中存在多边声誉机制。温州企业家群体网络是个熟人社会,声誉的传播在其间的传递采用了非匿名的方式,一传十,十传百。这种古老的传播方式借助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十分迅速和有效。一旦网络中的某个成员出现欺诈行为,声誉受损,整个网络可能就会采取孤立或者不合作的方式作为惩罚。这样的网络对成员产生群体压力,网络内成员意识到,良好的声誉能够给自己带来商业利益,一个愿意保持良好声誉的商人将得到额外收益。它强化了网络内部成员对声誉收益的预期,包括获得声誉收益的可能性和声誉收益的大小都得到了提高[3]。多边声誉机制有效降低了监督成本。
多边声誉机制不仅有效降低了监督成本,也是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奥尔森认为[9]41-42,某种迫使或诱使个人努力为集体行动作出贡献的激励机制(即“选择性激励机制”)是集体行动形成的必要条件。要克服搭便车行为,必须对集体行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给予奖赏。正式组织可以有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种形式,但是温州企业家群体属于非正式网络,只能给予精神激励,如良好的声誉。但是,良好声誉带来的商业利益会将精神激励转化为物质激励,刺激集体行动领导者进一步领导行动。不过,社会网络对集体行动领导者的激励功能的发挥依赖于群体成员的可见性,在一个高密度的网络之中,不仅行动者的贡献是高度可见的,而且他人对该行动者的奖赏或惩罚也是高度可见的,这就大大提高了奖惩的激励作用[13]。高度可见性恰好是温州企业家群体网络的特征,共同的文化、道德、价值观约束着网络成员,网络内部联系频繁,激励机制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
随着温州企业家群体网络的扩大,直接资源成本和集体行动的规模保持正比例的关系,即规模越大,直接资源成本越高,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却没有相应增加,而高密度网络将激励机制发挥到极致,这就导致集体行动的投入成本和产出收益之间,存在着“溢出”的边际收益。网络成员越多,集体行动越一致,溢出的边际收益也越大。这一溢出的边际收益成为网络扩大的激励。已有网络会欢迎更多的新成员加入,创造更大的边际收益,导致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反过来又带来网络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三)集体行动集团的扩张
温州企业家群体的集体行动不是一次性达成的,而是在创业实践中逐次达成的,遵循了“个体-小规模集体行动-大规模集体行动”的范式。个体的创业行为仅仅是一个试探,如果成功的话,个体创业行为立即会沿着血缘、亲缘关系展开,形成小规模的集体行动。小规模的集体行动的成功伴随着收益扩大,网络之外的其他人也被吸引。但是鉴于单独行动的经验不足,他们便会要求加入已成形的网络,增加了网络成员数量,扩大了网络集体行动的规模。而已有网络成员在对新成员的选择上,传统的亲疏关系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血缘、亲缘的关系,地缘、族缘的关系,以及已经经过实践考验的合作关系,也被允许进入这个集体。这保证了该网络的高度紧密性。
集体行动使得温州企业家群体网络能够持续扩张。网络外部成员在加入集体行动前,会凭借自己对收益和成本的判断来决定是否加入。如果其判断收益不能弥补成本,就不会加入集体行动的行列。当收益和成本判断不明确时,过去多次集体行动的成功就会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支持他们加入集体行动。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网络集团保持着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扩张状态。集体行动收益与集团扩张的关系见图1。

图1 集体行动收益与集团扩张
(四)集体行动集团的合作
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另一种解释是情感的作用。集体认同感、团结感对于集体行动发生有重要的作用。情感是通过人际互动来交流的,网络越是紧密,则情感的流动和交换就越可能达成[13]。温州企业家群体在情感上的交流密切而频繁,不仅体现在信息、资金、技术、人力资本这些无形资源的共享上,更极致地体现在地理空间的外在形式上。在国内外的众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温州村、浙江村(浙江村其实也都是温州村),这种群居方式是温州企业家群体所特有的一种创业现象。任晓认为[14],越是在远离家乡的海外,越是处在陌生的环境,温州人的族群自我认同感越强烈,圈子内“自己人”的身份成了贸易、融资时最高等级的信誉担保。群居至少在外在形式上强化了温州企业家群体的集体行动,可以帮助在外温州人获得必须的生活资源和创业活动资源,减少创业障碍。这一方面说明温州企业家集群对集体行动的严重依赖,集体行动的网络可以给创业成功带来最大便利,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企业家集群在集体行动中的亲密合作。
基于上述,温州企业家群体网络的集体行动属于内生型的集体行动,其初衷不是为了应付外来危机,而是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为提升企业家群体竞争力而采取的集体行动。首先,企业家个人在创业初始阶段因为资源和能力有限无法有效开展创业活动,理性个人选择加入企业家群体网络,通过集体行动规避风险;其次,企业家群体集体行动存在溢出的边际收益,这种溢出的边际收益属于额外红利,激励企业家群体经常性开展集体行动,这是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再次,为降低集体行动失败所带来的损失,集体行动采用“个体-小规模-大规模”的范式,保持集体行动的活力和网络的动态扩张,集体行动具有长期可持续性;最后,温州企业家群体集体行动中合作紧密,亲缘、血缘、地缘的天然粘性引导他们形成小圈子,在资金、技术、人力、信息各方面形成共享机制,有稳定的合作机制。
二、集体行动、网络和温州企业家群体危机
温州企业家群体网络中存在着群体危机。群体危机指集团出现了具有严重威胁的不确定性事件,其后果可能对集团、成员、产品、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损害。群体危机是集体行动集团内外部矛盾在集团成长过程中激化的产物。
(一)集体行动中的隐形危机
对集体行动的偏好给温州企业家群体网络带来的隐形危机存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温州企业家加入集体行动虽然做了成本-收益核算,但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惯例,因为以往经验证实加入集体行动总能带来收益。这就导致了决策的盲目性,即一旦发现新的获利机会,消息就会在温州企业家群体网络内部以非正规渠道迅速传播,大家蜂拥而入。结果从事同一经济活动的人数庞大,投资方向一致,资本结构一致。按照奥尔森的观点[9]25,集团越大,任一个体能获得的总收益份额越小。在获利机会不足以让庞大的网络成员分享的时候,恶性内部竞争出现,此时组织成本、监督成本就会急剧上升,超过溢出的边际收益,扼杀了集体行动的利益创造功能。
其次,集体行动集团会因为内部成员利益构成要素的变化和组合引起集团结构的变动,即形成结构分化。对于集体行动产生动员潜能的不仅仅是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同样可以引发集体行动。集团中的个体若对集团本身存在不满,此不协调因素可以通过群体网络得到传播和蔓延,而集团内部具有此类消极情感的成员会结成一个小集团。这些小集团不是基于特定的集体行动产生,也不会由于特定集体行动的达成而结束。虽然和大集团在达成目标上存在共识,但是小集团在其他方面却存在很大分歧。对于大集团的决策,小集团很可能会以正当的理由采取不支持甚至反对的行动。尤其是当某一集体行动本身会对他们之间的权力或地位格局产生影响时,他们就会在整个集体行动达成过程的某些环节上产生直接的冲突[15]。如果一个大集团中有若干个并存的小集团且小集团相互之间存在竞争,那么这些小集团对大集团的集体行动就构成了威胁。极端形式是,一个小集团退出大集团另外建立独立的集团。温州企业家群体网络对集体行动并不存在严格的约束机制。网络内成员依据经验、情感做出选择,个体成员进退随意,小集团退出的现象也经常发生。集团规模的随意变更使得预测收益成为一个难题。
最后,虽然温州企业家群体集体行动中存在着多边声誉的激励机制,但是激励结果与集体行动领导者的成本并非一一对应,完全取决于集体行动领导者的价值判断。若他们认为没有获得收益或者获得的收益不足以弥补他们为领导集体行动支付的成本时,他们的积极性就受到了打击。网络内部长期缺乏正规的激励机制鼓励集体行动的领导者,或者弥补机制补偿他们领导集体行动时可能遭受的损失,“搭便车”的投机主义便会盛行,挫伤创新的积极性,导致整个网络代际锁定。虽然理论界认为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有助于超越集体行动困境,但是正规的契约制度在解决交易成本的问题时往往更奏效。多边声誉机制作为非正式制度,能产生多大的约束力还有待验证。
(二)集体行动与危机爆发
危机的产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体。人类社会的任何特定组织必然会遭遇危机,这来自组织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复杂性和组织自身的局限性[16]。偶然要素的存在促使了危机的爆发,它将潜伏的危机诱发出来,对组织造成巨大威胁。
温州企业家群体网络存在于一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中。其间每一个个体都面临着一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风险发生的概率相同。若不同个体对周围做出不同反应,即每个成员采取不同的商业行为,则有的个体风险会发生,有的个体风险不会发生。而一旦集体行动机制发生作用,所有的成员在同一时间采取同样的行动,则潜在的个人风险就会转化成群体危机。
图2清楚地显示了个体风险是如何随着网络的扩散而传递的。集团中的第一级成员率先取得了成功,将自己的成功商业经验介绍给有直接亲缘、血缘关系的其他成员后,第二级成员加入了他的集团。这个时候,第二级成员和第一级成员在相同区域从事相同商业活动,经营手法、获利手段也类似,这样,他们就面临了和第一级成员同样的个体风险。在这个阶段,个体风险通过线性链条传递。当第二级成员介绍N个第三级成员加入该集团之后,个体风险便由两个人扩散到N个人。这种枝蔓丛生式的传播,使得个体风险实现了数学倍数的复制和流通,形成了树状链条传递系统。当第三级的N个成员各自以自己为中心,继续按照自己的关系网络介绍新的成员加入集团的时候,个体风险便形成放射传递机制,几何倍数地复制和流通,大规模向集团各个角落扩散。如果此时集团内部采取了集体行动,而该行动又恰好和外部环境不相协调的话,偶尔的事件就诱发潜在的风险,大规模的群体危机便爆发了。此时,集体行动不仅不能起到稳定网络、规避风险的作用,反而成为风险集中营和放大器。个体风险在网络内部叠加,然后通过集体行动机制放大,导致群体危机的发生。

图2 集体行动收益与集团扩张
因此,温州企业家群体的集体行动自身存在隐形危机,个体决策的非理性可能扼杀集体行动的利益创造功能,集体行动结构分化使得集体收益无法预测,依靠非正规制度约束导致集体困境的解决具有不确定性。一旦这些潜在的危机在遭遇外部大环境变化的导火索时,危机便从地下涌上地面,从隐形危机变成显性危机。更糟糕的是,集体行动是群体危机的集中营和放大器,危机会在网络内部按照“线性链条-树状链条-放射传递”的路径传播,将个体危机转变为大规模集团危机。
三、结 论
搭便车的经济利益是温州企业家群体加入集体行动集团的直接原因。因为社会网络和经济网络的双重叠加,温州企业家集体行动时的组织成本、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并不随着集体行动集团规模扩大而增加,所以存在溢出的边际收益,这鼓励了集体行动的持续产生。集体行动集团在动态中扩张,并保持高度亲密合作的关系。温州企业家群体集体行动具有内生性的特点。但由于集体行动中存在结构分化,以及非正式制度发挥功能的不确定性,集体行动为温州企业家群体积累了隐患,这种隐患一旦碰到导火索,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体风险,而集体行动此时就变成了放大器。
[1] 董明. 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社会的转型[D]. 上海: 上海大学文学院, 2010: 8.
[2] 郑海华. 2009年内外温州人互动大事记[N]. 温州日报, 2010-2-22(2).
[3] 黄少卿, 余晖. 民间商会的集体行动机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4): 66-73.
[4] 郑江淮. 行业协会职能配置与政策创新[EB/OL]. [2013-05-03]. http://club.topsage.com/thread-1236878-1-1.html.
[5] 郑小勇. 行业协会对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的作用机理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8, (6): 108-130.
[6] 郑慧. 商会的经济学性质与集体行动研究: 以温州商会为例[D]. 杭州: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2010: 45.
[7] 朱宪辰, 李玉连. 领导、追随与社群合作的集体行动[J]. 经济学, 2007, 6(2): 581-596.
[8] 季元杰. 被动的自愿: 温商集体行动的逻辑[J]. 特区经济, 2009, (1): 224-226.
[9]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 郭宇峰, 李崇新,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13-14, 41-42, 25.
[10] 纳尔逊, 温特. 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 胡世凯,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7: 25.
[11] 陈立旭. 特殊信任、关系网络与浙商私营企业组织模式[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7, (12): 3-10.
[12] 徐淑芳. 信任、社会资本与经济绩效[J]. 学习与探索, 2005, (5): 210-213.
[13] 曾鹏. 群体网络与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J]. 浙江学刊, 2009, (1): 196-199.
[14] 任晓. 温州民营企业的国际化: 一个样本观察[J]. 浙江经济, 2006, (6): 40-42.
[15] 刘玉照. 集体行动中的结构分化与组织化[J]. 社会, 2004, (11): 17-22.
[16] 胡百精. 危机传播管理: 流派、范式与路径[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0.
Collective Action, Network, and Entrepreneur Groups in Wenzhou
CHEN Yi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enzhou, China 325035)
Collective action exer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entrepreneur groups in Wenzhou. The hitchhiking benefit is the incentive of forming collective action, the extra profit brought by social network is the inner motive power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high density communication within network is the guarantee of stable coopera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However, collective action can also bring hidden crises to Wenzhou entrepreneur groups, i.e., the weakening of interests-creating function,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difficult to overstep. When these covert crises are transformed into overt ones, collective action will magnify them and transform the individual crises into groups ones.
Collective Action; Entrepreneurs Groups; Network; Wenzhou
F065.5
A
1674-3555(2014)01-0056-07
10.3875/j.issn.1674-3555.2014.01.009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封毅)
2013-03-21
2012年度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12wsk038)
陈翊(1977-),女,浙江温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温州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