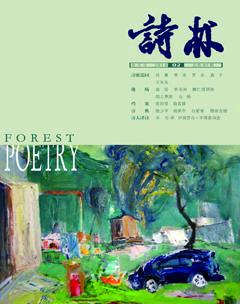静默如谜:一个诗写者的乌托邦
霍俊明
俞昌雄属于“70后”写作群体中一直保持着低调和谦逊态度的诗人。这样的好处在于他的诗歌处于自然生长却又能不断地实现自我调控。近期,俞昌雄的诗歌越来越迸发出一种强烈的命运感和时间体验,这从他诗歌的核心意象、精神向度以及观察视角都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来。作为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诗写者,俞昌雄有着属于他自己的诗歌国度,他是那种可以在文字里创建精神幻像的诗人,哪怕那是高高悬挂的乌托邦,他却锲而不舍。
世间万物静默如谜,甚至包括呼吸和存在自身也被诸多情势所缠绕和围困。而诗歌也不能不处于这个难解和难言的过程之中。正如俞昌雄面对“树”这样的自然植物,他可以在这小小的事物身上同时发现国家、岁月、灵魂和自我的忧伤。而与人相对应,自然就处于不悲不喜的静默和神秘当中——“我对一棵树撒了谎吗/这世界辽阔无边,它仍如此静默/神秘而安然,无知且无畏”(《对一棵树撒了谎》)。俞昌雄近作中有极其多的树木意象,而与这些树木相比,人更脆弱易逝、难抗岁月风雨。值得注意的是俞昌雄近期的诗作大体都是在黄昏、暮晚或黑夜的时间背景下展开的。我们可以关注由此漫延开来的诗人的精神导向——“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有庞然大物/在我的梦境里吼出声来”(《大象之诗》)。面对着时间的惨厉,诗歌中出现那些死去的人和事物的身影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就是命运。在时间的单行道上,诗人要具备预设人生晚景的能力,“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俞昌雄的《2071年的一个夜晚》就是这样的诗,也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诗人是要“向死而生”的。
就像俞昌雄所描述和想象的“苏兰河”,一条属于上个世纪,另一条在当下流淌。已逝和漠视、历史与当下实际上正如这条河流一样是难以截然分开的,而好的诗人恰恰时时应该面对和发现新旧融合一起的事物以及相近性质的事物形态。这多像我们的时代!在一个新时代的梦境中有多少人不是因为那些拆毁、消逝、已故的事物而落寞或不舍呢?在时间、自然、历史和时代混杂的河流面前,人和诗歌同样是虚弱不堪且不明就里的。而在俞昌雄这里,我时时与一个面孔阴冷而内心怀着火焰和谦卑的形象相遇。在闹市与喧嚣中,还留存着那些默默而自我取暖的“守夜人”。在《正月初三,与汤养宗对饮,月亮旁视》这首诗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文人古意和传统精神的讯息,比如三月三,比如对饮,还有月亮。与此相近的是俞昌雄诗歌中大量的关于“鸟儿”的意象或场景。这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诗人传统的书写方式。只是这些“鸟儿”在现代诗人这里已成为时间和更为复杂的命运的象征体。我们可以想象,当下诗人所营造的这种精神氛围是非常艰难的,因为生活和时代如此实实在在地时刻消解着这种诗意和古意的精神趣味。然而在《正月初三,与汤养宗对饮,月亮旁视》这首诗中,我们迎面相遇的是那些老旧的、温暖的又被这个时代的人们追怀甚至遗忘的事物,比如“往事”、“封存多年的书信”、“旧夹克”、“老屋”、“先祖的遗训”、“火柴”等等。由此,我们会发现近期的俞昌雄的作品深处所掩藏着的时间旋涡和中年式的回溯,甚至连那些闪烁的汉字都处于追挽当中。我们看到了不舍和不甘,也同时看到了憧憬和欲望。诗人就不能不是孤独的,可怕的是“孤独还在生长”,而诗人承担孤独的方式却是沉默。这种自我压抑就使得俞昌雄的诗歌更多的时候处于两个或多个声调的对话、互否和盘诘当中。
与此同时,这个时代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已逝的老旧的事物和故地,而是成为了集体性的命运。故乡和异地不再是文化和精神上的无病呻吟,而是成为实实在在的每个人时刻经历的切身命运和灵魂的撞击。诗人越是“向往一种生活”,越是频频使用祈祷和神佑式的诗句,就越来越陷入精神的形而上空间——因为现实强大到可以超乎每个人的想象极限。当诗句中不断出现“故乡”、“他乡”、“异地”、“故地”、“归途”、“陌生地”的时候,诗人就不得不处于出世与返世、介入与疏离、离乡与还乡的张力关系之中,“跟随午夜的幽灵/云朵洒落一地,从山下直到山顶/我不断捡拾,疑似返世的人”(《别云山》)。“还乡”如果是可能的话,诗人就必须要面对那些危险的游动悬崖。可是,对于一个新时代的诗人而言,可能永远都只能走在异乡的路上了——“我将独自站在陌生地/风从异乡吹来”。诗人还不得不学会透析时间和人世的无常和无情,这时候他的诗句不能不是冷峻的,甚至是充满忧虑和质疑的。当年的“朦胧诗人”顾城不断在诗歌中出现“眼睛”的意象,甚至他要给黑夜、墙壁都要打开一双双渴望童真的眼睛。但是,俞昌雄反向行之,“我愿意抹去无数双眼睛”,这是常人无法接受的一种方式,但充满决绝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俞昌雄近期诗作中的互文性特征。比如“只想要一根火柴”(《正月初三,与汤养宗对饮,月亮旁视》)、“我的中年仅是还未点燃的最后三根/火柴”(《迷魂阵》)。尤其是大量与“身体”相关的意象的出现,“躯体”(《别云山》)、“这世间的躯体我已/不再看管”(《2071年的一个夜晚》)、“躯体开始叫喊”(《对弈》)、“躯体漆黑一片”(《我所看到的寒葱顶》)。这是不是说明到了一定年龄,随着身体、感知方式以及经验程度的变化,“身体诗学”越来越成为可能与必然?尤其是这些与“身体”相关的意象群是否印证了俞昌雄自己所说的“诗,是身体的另一个家”?或者像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人是这一特殊家宅的守门人?这种互文性的词句和意象恰恰揭示了一个诗人主导性的内心视阈与精神状态。这些自觉或不自觉呈现的意象和语句也体现了诗人写作的某种“惯性”特征。我们可以将这种“惯性”看作是强化写作个性与表现自我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但是也要注意这种“惯性”对写作自身的一些影响。
面对着时间、故地、他乡、自我以及碎裂状的时代,面对着黑暗中的世间万物以及日渐老化的身体,诗人该如何面对静默如谜的自我和他物呢?我们的诗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时间能给的/它都一一保存了下来/而时间不能给的,它沉默/如暗夜里独自眺望的人/躯体漆黑一片,但眼神总是亮的”(《我所看到的寒葱顶》)。
2014年1月10日写于旅次,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