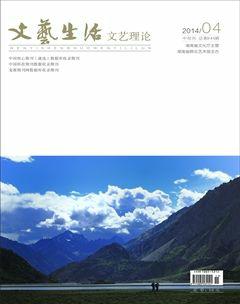文化霸权的牺牲者
——《最蓝的眼睛》中波琳的迷失
黄贝贝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文化霸权的牺牲者
——《最蓝的眼睛》中波琳的迷失
黄贝贝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托尼·莫里森以她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黑人身份迷失的根源。在她的小说《最蓝的眼睛》中,黑人生活在白人文化霸权隐形的统治之下。电影等大众媒体被白人当做推广自己意识形态的最佳载体。以波琳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则集体迷失在电影虚幻的世界里,她们放弃了本民族的传统,转而去崇拜白人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一味地模仿,直至失去自我。莫里森以此来警示同胞不要失去对黑人身份的认同。
文化霸权;白人意识形态;黑人
密西·戴恩认为托尼·莫里森给自己树立了多重身份。身为一个作家,她同时又具有种族身份,文化身份,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莫里森本人对此也十分认同。她的多重身份使得她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同样是关注非洲角色,莫里森的作品总是能够更精准地挖掘出那一个时代的隐藏矛盾。从而使她的作品从深度上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从她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开始,她这一特点就已经凸现出来。在这部作品中,莫里森入骨地揭示了一个现象:黑人在铺天盖地的白人文化包围中丧失了自我。这种迷失并不是那么明显,但对于深陷其中的人来说却是致命的。
布莱德拉夫夫人,波琳,是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所塑造的一个白人文化的典型牺牲品。与其女儿佩科拉不同的是,波琳是直接泯灭于白人所主导的大众媒体之手。戴茨认为,文化控制是实现意识形态霸权的最佳手段。因为它确保了在众多社会秩序中某种单一的舆论或者说“公众意识”的胜出。在美国,白人文化掌控着意识形态霸权。因此,在大众媒体的协助下,美国建立了阶级,种族,性别等方面的一系列不平等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生活的黑人会不自觉地被白人文化主导的大众媒体洗脑。他们自己都不会意识到,他们观察世界和评价他人的标准早已不再遵从黑人传统,而是来自于白人文化的灌输。波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众媒体摧毁了波琳作为一个纯粹的黑人女性的快乐。当她还居住在南方的家乡小镇时,她的生活是简单幸福的。怀揣着创造新生活的梦想,她与新婚的丈夫一起搬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北方小镇劳瑞因。小镇上数量众多的白人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当地的黑人女性也不太喜欢她。因为刚从乡下搬来,波琳的“老土”外表招致了其他女人的嘲弄。为了被大家接受,波琳尽一切努力学习当地女人的衣着和谈吐。从表面上看来这是为了入乡随俗,但事实上,这个“俗”早已经不是黑人的传统风俗了。当地黑人女性所崇拜、追随的“时尚”,包括她们用以评价彼此的审美观都已经深深地打上了白人的烙印。由于较早地接受了白人的统治,北方各州的黑人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白人意识形态的奴隶。“黝黑”不再是美丽的标志。统治者们白皙的肤色渐渐被认为是高贵的象征。黑人们无意识地开始厌恶自己的黑皮肤,自觉因此而低人一等。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黑人逐渐的丧失了身为黑人的身份认同。因此,当波琳开始追随当地女人时尚的同时,她也就开始渐渐地失去自己。她并不明白,破坏她简单幸福生活的不是当地人,而是当地生活方式背后的白人大众媒体。更荒谬的是,当波琳被当地妇女甚至自己的丈夫所排斥的时候,她选择从电影中寻求安慰。这更加深了她的悲剧。莫里森说,在接触到“浪漫爱情”这一概念的同时,波琳也开始关注“身体的美丽”。在莫里森眼中,“身体的美丽”几乎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思想长河中最具破坏性的理念。不幸的是,波琳深深地被这个“破坏性理念”所影响了。她学习白人影星的发型和着装,崇拜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她把自己隐藏在电影创造的虚幻世界里。
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大众媒体,电影对人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力。白人所引领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电影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征服是旧的殖民帝国崩塌后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改变。这些征服者们摈弃了野蛮的表象,转而采取温和的手段,使用绚丽的媒体包装。其实他们从本质上并无区别。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试图将世界转变为他们的方式。波琳从电影中所接触到的女性之美的标准显然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在将外在美等同于内在美德的过程中,她又束缚了自己的大脑,越来越轻视自己。虚幻的电影给波琳带来心理上的安慰,这是她从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帕特里克说,波琳为她心中被压抑的创造性寻找到的发泄方式是用好莱坞荧幕上的“完美”来代替自己心中原本的标准。她以此来逃避身为黑人女性的悲惨处境。她越是频繁地出入电影院,就会越来越觉得现实生活难以忍受。电影中每一个白人家庭都是富裕美满的:男人会照顾女人,他们衣着得体,家中装饰明亮华丽。似乎每一个人都洋溢着幸福。波琳喜欢看这类影片,她以这种方式过着自己梦想的生活。电影中虚幻的镜头满足观众的心理预期。但是却使得波琳这样的人越发无法面对反差巨大的现实生活。已经被改造了价值观的她与丈夫乔利的关系日益糟糕。他们经常争吵甚至相互打骂,曾经在彼此之间的温情荡然无存。为了买时尚漂亮的衣服,波琳去一个白人家里做女仆。能够进入像电影里面所描述的那种完美的白人家庭,这个工作极大地满足了她的虚荣心。更重要的是,当她代表费舍家出现时,曾经羞辱过她的人们表现出了畏惧。在费舍家,她能体会到权力,赞美和奢华,能找到电影中的那个优越、美丽的世界。为了保住这个美梦,她将自己的家庭隔离开来,沉浸于这份工作中,把自己变成完美的仆人。如果说沉浸于电影是波琳堕落的起点,那么与真正白人家庭的接触则加深了她对虚幻电影世界的痴迷。她已经完全沦为白人意识文化的奴隶。在她看来,真正的美丽只是存在于白人的阶层,自己的家庭则是丑陋不堪的。她为自己女仆的身份而自豪。对她来说,下班回家不是休息而是折磨。被白人文化洗脑的她无法接受贫穷、丑陋的黑人社区。在她眼中,她整个人生的意义就只存在于她的工作里。电影成功地将她推进了一个虚幻的完美世界。她开始逐渐忽略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发生在波琳身上最悲剧的改变就是她的母性的丧失。在佩科拉出生之前,波琳还曾幻想着她会很爱这个孩子。然而当她看到婴儿的第一眼她就由于自身变异的审美观认为这个黑黝黝的婴儿非常丑陋。长期的受白人文化的影响,她已经不会欣赏黑色的魅力了。因为她所钟爱的电影中只接受白皙,金发,碧眼的美女。波琳认同电影中的观念。她对费舍家的小姑娘更为喜爱。对她来说,自己的亲生女儿佩科拉就像一个养在家中的宠物,只需要喂饱就好,她毫不关心女儿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当着孩子们的面就和丈夫大打出手。在费舍家,波琳打骂烧伤的女儿。却心疼着被弄脏的地板。对于这样的波琳,苏珊·威尔斯说,一个女性逐渐异化的最大的悲剧就是对其母亲这一角色的影响。她的精神分裂开了,对雇主的女儿展示出爱和温柔,对自己的孩子则施以暴力和鄙弃。波琳自己对白人意识形态举手投降,她的孩子却也沦为了牺牲品。
主流社会通过大众媒体推广白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电影,书籍,商业广告和其他媒介充斥着白人的生活方式。黑人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占主导地位的白人霸主把他的政策包上虚伪的糖衣,悄无声息地渗透至每一个角落。统治的方式转变了却具有更深远的效果。一旦黑人认同了白人的意识形态,他们也就失去了自我。波琳接受了这一转变,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忠实地遵从那些规则。她甘心放弃自我,成为白人文化的附属。她也许因此而找到了安慰,但她的快乐却建立在整个家庭坍塌的废墟上。莫里森塑造波琳这样一个角色来给她的人民敲响警钟:全盘接受白人意识形态就意味着黑人身份的丧失和黑人传统的泯灭。
[1]Missy Dehn Kubitschek.Toni Morrison:A Critical Companion.NY: GreenwoodPress,1998.
[2]Henry Louis Gates and K.A.Appiah.Ed.Toni Morrison:Critical PerspectivesPastandPresent.NY:Armstad,1993.
[3]ToniMorrison.TheBluestEye.NY:PenguinBooks,1994.
[4]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I106
A
1005-5312(2014)11-009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