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遵森梦想的分量
谢志强
童遵森梦想的分量
谢志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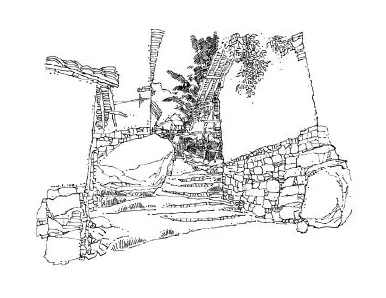
现在,有时髦的词语:中国故事,中国梦。故事包含着曾经的梦想,梦想搭载着未来的故事。童遵森这部短篇小说集《风雪夜中的女人》,写的就是中国故事,故事里有梦想,或者说,故事里的人物时常展开梦想的翅膀飞翔。小说表现的是存在的可能。梦想是一种可能。
童遵森在山村里长大,是个山里走出来的男人。他八岁丧母,十一岁亡父,跟祖母一起在山村里过着艰辛的日子,十四岁成了生产队年龄最小的社员,十七岁悄悄地写了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曾干过生产队的会计、植保员、种子员,还毛遂自荐,担任过村政治文化夜校的教师,后来,进了区供销社,当了农机辅导员,却总是脱不出父亲的阴影(黑五类),他还创业,开过服装厂,却盛极而衰,破产,而供销社这个“娘家”,已改制,出来回不去。于是,又回到土地:种地、养兔。埋藏二十
余个春秋的文学种子突然发芽。
我念师范时候,文艺理论教师说起中国文人,感慨:文人的不幸是文学的大幸。后来,我想,非得经历“不幸”换取文学“大幸”吗?其实,每个人在那个时代滚滚洪流中,被裹挟,被抛开,沉沉浮浮,身不由己。但童遵森却不甘心,一次又一次地跃入,他漫长的经历,使我想到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
童遵森仿佛抵达了彼岸,仅获得那一副大鱼的骨架。但是,他抱起了文学的梦想,讲起中国故事——他的经历,转换成乡村故事。譬如,《月亮畈》这个女儿祭祀父亲的故事,由他与祖母的故事转换。
作家的能耐,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写成别人的故事,把别人的故事当成自己的故事。一种隐秘的自传。我在这部小说集里,看出了童遵森经历的转换。
小说要讲一个故事。我想到小说的奇妙。为什么同样的故事,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似曾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竟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
其实,故事总是若干几种模式。童遵森的二十七个小说,我总能看出早已存在的故事母体。小说的历史里,同类的故事不知被讲了多少遍,而且,还继续在讲。
关键是,怎么在俗套的故事里弄出些许新意?从而拯救(激活)故事。
我关注童遵森小说里的小孩。《风雪夜中的女人》《老夫老妻》,都有一个小女孩。在大人的关系中,小女孩的作用和能量,使得故事的情节发生转机,或说逆转。
《风雪夜中的女人》,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相当纠结,这是一个通俗的婚外恋的故事。两个男人联合捉奸,而其中的女人却碍于面子,视名声为生命,后来,反被丈夫撞上。本来情节展开的方向是捉奸,却反方向运行,被捉,大人之间的逆转,是小女孩起作用——小女孩担心自己的玩具娃娃。丈夫冷漠了妻子,但对女儿的爱体现在玩具娃娃上,他放弃情人赶回来。
童遵森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写了风雪夜中纠结的女人的同时,还将雪赋予了寓意:疯狂的大雪,掩盖了人物的肮脏、不平。这是童遵森小说无意间的升华。他没刻意写雪,却出现的偶得效果。他写了雪的纯净无暇。在他别的小说里却难见。这个小说的元素,他可能还没意识到吧?白雪反衬了人物的行为,还含有另一层意味:雪的掩盖犹如他的面子。
《老夫老妻》,小女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对老夫老妻和一对小夫妻的纠结,由小女孩来决断——孙女同意不同意奶奶回家?
中国故事当然要装中国人物,其言行,要符合中国的方式。奶奶和孙女的一段对话,奶奶多小,孙女多大,孙女采用独特的方式留住奶奶,还表扬:奶奶真好,奶奶真好,奶奶比小乖乖还要乖。这种辈分、角色的颠倒有着童趣。这一段人物的语言相当妥当、有趣。
这个留住奶奶的情节,为后来公园发生的事件创造了情节合理的逻辑关系。本来是一个老农进城去儿子家的故事。童遵森已明显地把握着故事的方向,甚至一路留下他使劲、用力的痕迹。设置、营造着环境、气氛(玩笑、酒、电视、公园),把人物往浪漫的方向运作,如同弗洛伊德,样样都往“性欲”上挂,这种操作的高潮,已经可以预料,再推一步,导致悲剧。
两个小女孩,一个玩具,一种裁定,故事新意和转机含在其中。
童遵森小说的可贵之处,还表现在,他写村庄故事同时,虽然还没有自觉地建立一个文学的村庄(统一的名称、人物),但是,他已有一个统辖村庄的意象(或说一个主题):纠结。
纠结是他对村庄的发现。雷蒙德·卡佛说:一个作家如果有了看待世界独特的视角,那就成功了一半。童遵森的小说,所有的人物都陷入各种各样的纠结之中。《风雪夜中的女人》关于面子的纠结,《老夫老妻》浪漫的纠结。
《驼伯》中,夹在黄祁两大家族中的纠结。黄、祁两个姓的家族为了桥的纠纷,牵引出近七十年的沉重历史——世代家族根深蒂固的宿仇。驼伯作为一个正面形象,忍耐、宽容,力争超越“斗争哲学”,却陷入两大家族的纠结。他那驼背,使我想到无形的重负。
如果童遵森在“桥”和“驼”方面稍微加强
相关的细节,那么,是不是能够创造出“形而上”的内涵呢?有时,小说确实需要有一点“升华”,从而避免单纯地在故事的流程中推进。
《神猫》中,“我”与猫的关系,放与养的纠结。童遵森的小说里,这一篇独特在语言。幽默语言与荒诞故事构成相应的和谐。关于鼠害的细节很有趣。人屡败屡战,叙述中对鼠猖狂的那种无奈的幽默,渐渐演变成对猫关爱那种荒诞的无奈。宁可关养,也不让猫发挥“专长”,为什么?读者自可体会。主人公不也发挥不了“专长”吗?
人与动物的关系,《放过生命》,属另一种类型。童遵森有童年情结。这一回,主人公是个男孩——少年方智家境贫困,他趁暑假进山筑路,挣学费。就有了少年与麂子相遇,那是一只受惊受伤的麂子。这个故事使我想到福克纳的小说《熊》,一个少年和一头熊遇合的故事,那种遇合成了宗教般的仪式。而少年方智和受伤的麂子,渐渐有了仪式的苗头,但是,很快被世俗所侵犯(筑路的民工眼里,麂子被视为难得的肉)。《放过生命》停留在猎食的层面展开,少年也不得不加入其中。一个群体(《熊》里也有狩猎的群体)和一个少年,一起围捕,少年“放过生命”,落得个缺心眼的责备。
要进山才能出山——进山挣钱才能出山念书,这是又一层纠结。童遵森还设置了一个女孩的线索(关于同情的纠结,还有朦胧的爱恋),与围捕猎物形成了映照,构成少年成长的纠结。
同为少年与野生动物的故事。福克纳在另一个层面和方向展开故事,其中,安放了许多细节,例如怀表、猎枪、脚印,使《熊》的内涵丰富,有寓意有象征。我们常说的突破和新意,往往体现在小说的细节,而且,作家要规避俗套的情节打开的方向,让人物走一个“上升”的通道。
童遵森的短篇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心理写实。即使微妙的地方,他通过心理描写,也写得透明、清晰,难得有模糊、朦胧的状况。他时不时地描述出人物在纠结时的丰富心理,显示出作者的全知全能。有时夹杂着作者的议论和判断。这样描写的好处是,给读者呈现出完整、丰富的灵魂景象,但是,也潜伏着负面的影响。
心理描写是个双刃剑,它过度过量,难免导致节奏滞缓。节奏在当代小说中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作家怎样给读者留个“投射”的空隙?小说也是一种留白的艺术,因为,它探索的是“灰暗地带”。
童遵森给小说带来了一阵一阵浓郁的气息,而支撑他这一系列小说的是童年的经历、青年的艰辛。“不幸”成了他文学的“大幸”。至今未曾和他谋面,可是,我在友人转荐来的他的小说里,看到了他放飞梦想。幸亏有梦想。有梦就好。
他在一篇随笔里回忆儿童时代,看了一本古书,里边按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辰,测算一个人骨头的分量,以预测运程。他的骨头为四两八钱。其实,没有一种秤,能称出灵魂的分量,梦想的分量。童年的时代,他写作文,已放飞了梦想,梦想飞越了艰难曲折,我看到其中承载的沉重,但仍在轻盈地飞翔。我期待童遵森继续放飞他独特的梦想。
(短篇小说集《风雪夜中的女人》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