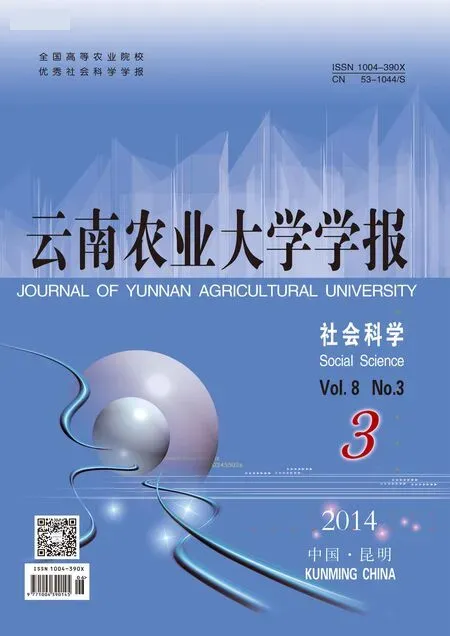试论北宋真宗朝翰林学士白体诗歌创作
汪国林
(安徽科技学院 中文系,安徽 滁州 233100)
宋人蔡居厚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1]可见,宋初白体诗流行的盛况。时至真宗朝,随着白体名家李昉、李至、王禹偁等人去世,诗坛风气发生巨大转折。正如陈元峰先生所说:“(真宗朝)翰林学士的政治风概为文坛带来士风与文格的重要变化。在颂美功德与缘饰礼乐的时代气氛中,以馆阁翰苑为中心,博学多闻的诗坛群彦聚集酬唱,完成了由白体向昆体的嬗变。”[2]但这个过程颇为复杂。宋初白体诗风并没有退出诗坛,真宗朝的不少翰林词臣们的唱和诗作仍然具有白体诗的风格,甚至不少“典型 ”昆体诗人也由白体“脱胎”蜕变而来。此外,中层文人把白体诗风推向民间,扩大了白体诗的题材范围。总之,西昆体与白体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的联系,白体诗作转入更深的层次的融合之中,并成为宋代诗歌的重要渊源之一。
一、宋真宗与翰林词臣应制酬唱诗集
真宗是好文崇艺的帝王,自身的文化修养也很高,其御作散佚严重,《全宋诗》仅收其诗歌二十三首,残句三则,以赏赐、送别臣子或诗僧的诗作最多,前后达十五首。诗作有的夸奖臣子聪颖忠孝,有的劝勉臣子恪尽职守,有的表达自己对佛道的理解,主旨显豁,心态雍容,语言平易通俗,有显著的白体色彩,如:
七闵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资。
初尝学步来朝谒,方及能言解诵诗。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千里有前期。[3]
——《赐神童蔡伯禧》
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他族未闻有,朕今止见胡。[3]
——《赞胡家》
礼闱选士古称难,都为陞沉咫尺间。较艺清时公道在,抡材应得惠人寰。[3]
——《赐知贡举晁迥》
止观心地法,色相本皆空。禅慧明宗性,超然万法中。[3]
——《赐僧义澄》
此外,《玉海》卷三十收录真宗的御制诗题甚多,更可以看出其诗作内容的闲适与华赡,现摘部分诗题如下:咸平赐宴《赏花诗》;咸平、景德、祥符《瑞雪诗》;祥符《赏花诗》;祥符《御宴观瑞物诗》;祥符《绿龟诗》;祥符《瑞石诗》;祥符《神雀诗》、《甘露诗》;祥符《赏花钓鱼诗》;祥符《嘉雪诗》;天禧《喜春雨诗》;天禧《赏花钓鱼诗》[4]等等,闲适优游与歌颂祥瑞十分突出,内容上具有白体诗的显著特点。
真宗朝翰苑词臣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新朝成长起来的文臣基本代替了前朝词臣。据陈元峰先生统计真宗朝仅翰林学士人数达二十二人[2]。其中颇有文名就有:宋白、王旦、晁迥、李宗谔、杨亿、钱惟演、刘筠、晏殊等。真宗朝翰苑词臣酬唱的富贵气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其中大多数都成为稍后西昆体的主干甚至领袖,但其中有不少文臣早期诗作具有白体性质,如舒雅、李维、李宗谔等,可以说是白体入而昆体出,丁谓、张咏、晁迥虽然直接抑或间接参与西昆酬唱,但其主流风格应不属于昆体范围。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张咏(946—1015)除写古风外,许多诗都很粗率,无昆体的华丽精细之风;……李宗谔(965—1013)是李昉之子,当王禹偁谪居商州时,他曾劝王‘看书除庄、老外,乐山诗最宜枕藉’,可见其欣赏趣味。”[5]真宗与翰苑文臣的应制唱和诗作更多,“真宗好文向学,孜孜不倦。祥符、天禧之际,宸章睿藻,宣示臣下者,不间于三、五日。自宰执至贴职于三馆者,皆得与赓载。”[6]留下的君臣应制酬唱诗集主要有《天禧明良集》、《天禧御制》、《天禧真宗御集》、《注释御集》、《天章阁御集》、《天禧承明殿御制》 、《天禧赐东宫御制》等。
二、宋真宗与翰林词臣应制酬唱诗作内容与宋初白体诗风格的分化
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的苦心经营,至真宗朝呈现出盛世之状。《邵氏闻见录》卷三云:“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间为盛,时北虏通和,兵革不用,家给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衢,谓之棚车鼓笛。”[7]这某种意义上造成君臣普遍存在的治平心态与享乐思想,就连真宗也说:“天下无事,而大臣和乐,何过之有!”[8]这使得歌舞行乐、宴游富贵之风更加兴盛,尤其是在应制诗中表现的更为鲜明。赏花钓鱼、观灯游赏、观书宴集等闲雅的诗歌内容与闲适的创作心态正合宋初白体诗的特征。真宗朝馆阁翰苑宴集应制数量甚大,以应制内容为标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赏花钓鱼应制——盛世中的颂歌
与太宗朝一脉相承,真宗朝君臣宴集中赏花钓鱼最为突出,欧阳修说:“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9]文臣们也为能入苑赏花而倍感荣欣,未能参加,甚是遗憾,宋庠竟私自作《奉和御制赏花钓鱼次韵私赋》以酬和,足现其追慕之心。“真宗御集有《苑中赏花诗》十首,内一首《龙柏花》”[10]关于真宗赐宴赏花钓鱼的记载甚多,如:
(真宗咸平)三年二月晦,赏花,宴于后苑,帝作《中春赏花钓鱼》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心殿,尽欢而罢。自是遂为定制。[11]
祥符元年三月九日庚午,召近臣宴后苑,帝作《赏花》七言诗。三年闰二月二十七日丁丑,召辅臣至宣圣殿,朝拜太宗圣容,帝作《赏景观花诗》,以赐从官,即席赋诗。……五年三月二十日丁亥,召近臣赏花后苑,以雨移御崇政殿,南轩曲宴命赋诗,有顷御北殿赐宴作乐,帝作《赏花》及《喜雨》诗二首,群臣即席和进。八年三月丙申,宴后苑上作《赏花》七言诗。”[4]
具体应制赏花诗作则不甚枚举,其中有似白体的君臣酬唱之作,只是颂美的成分愈加浓烈,如丁谓的残句《赏花钓鱼》甚有味道,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道:“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尝一岁临池久之,而御钓不食。时丁晋公(谓)应制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真宗称赏,群臣皆自以为不及也。”[9]本来鱼不上钩是极其自然的事,丁谓竟然说是惧畏龙颜,足显丁谓及其应制诗作的谄媚性。宋人吴聿说:“近世应制,争献谀辞,褒日月而谀天地,惟恐不至。古者赓载相戒之风,于是扫地矣。”[12]
但更多的是由闲适富贵过渡到歌功颂德,诗歌语言也有追求浅易流畅为主转化为华美富赡,讲究用典的新奇与意象的浓密,如:
宫花如锦水连漪,翠辇寻芳正是时。禁苑定知人未识,朱栏除有蝶偷窥。
艳烘晓日迷天仗,香逐轻风落酒巵。何幸微臣陪镐宴,蓬壶春漏正迟迟。[3]
——杨亿《后苑赏花应制》
上苑乘春启,奇花效祉新。连房红萼并,合干绿枝匀。翦献尊长乐,分颁宠辅臣。从游过水殿,凝跸近龙津。黼座临雕槛,文竿引翠纶。波香投桂饵,萍暖漾金鳞。湛露芳尊酒,钧天广乐陈。多欢千载遇,何以报严宸。[3]
——夏竦《赏花钓鱼应制》
杨亿是西昆体的领袖,而夏竦则是“后期西昆体”的俊彦,其诗作已经远离白体诗歌了。在诗歌语言运用上,西昆诸诗人爱用金玉之等的富赡华丽的辞藻,如上文杨亿的《后苑赏花应制》就使用“云罗”、“霞绮”、“琼圃”、“凤辇”、“龙津”、“仙葩”等华艳富丽的辞藻以表现帝王宫苑的富贵与华丽,正体现西昆体“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13]的语言风格。
(二)节日应制——盛世的恩典
真宗朝与前代相似,每至元日、端午、中秋、重阳、除夕等重要节日往往宴请馆阁翰苑词臣及其它名士诗酒宴乐,作诗祝贺节日,这类记载也甚多,如:
(咸平)二年八月壬子,侍读学士杨徽之等赴职,赐宴秘阁,上作七言诗赐之。九月戊子作《重阳》七言诗,近臣属和。[4]
五年正月己巳,朔,上作《元日》五言诗赐近臣和。癸未乾元楼观灯,作七言诗。六年正月癸巳朔,御乾元殿受朝,上作《元日》五言诗赐近臣。[4]
二年八月戊午,社宴近臣于中书,作《社日》五言诗赐之,属和。[4]
节日应制的诗作在馆阁翰苑词臣的别集中都保存一些,如:
宸居瑞霭重,阊阖正来风。憀栗惊秋气,丰穰美岁功。晓烟篱菊嫩,霄露畹
兰红。重九登高会,欢娱处处同。
——杨亿《奉和御制重阳五言诗》
仙掌凌空沆瀣秋,大田多稼似云浮。天边霁景芙蓉阙,江上残芳杜若洲。
东观群儒宣宴乐,南荆遗俗重嬉游。宸章忽降容瞻睹,疑是神龟负九畴。[3]
——杨亿《奉和御制社日诗》
这些节日时的应制之作,内容上由节日出发,对帝王的功业盛德甚是颂美,杨亿则由君臣重阳登高宴乐,转而歌颂圣德流芳,天下升平,承平之气浓烈。
(三)甘霖符瑞——盛世的骗局
真宗朝大兴符瑞之说,以重振帝王的威严,身为御用的词臣自然歌颂祥瑞也难以避免。这类诗语言进一步典雅化,诗歌内容多是颂美之辞,除诗歌内容与白体诗相似外,其风格已与白体越走越远,不少就是典型的昆体了。
这类诗题可详见王应麟《玉海》卷三十,如:咸平景德祥符《瑞雪诗》、祥符御宴《观瑞物诗》、祥符《瑞应诗》、祥符《瑞石诗》、《(瑞石)赞》;祥符《神雀诗》、《甘露诗》等等。其中“祥符御宴《观瑞物诗》”条记载道: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八日,甲寅,诏近臣观书于龙图阁,观瑞物于崇和殿,遂宴于崇和殿。帝作七言诗,侍臣即席皆赋。初观瑞物,史臣晁迥、杨亿曰:“此并圣朝受命之符,不载于史册,望内降名件,付史院。”从之。庚申,上作七言诗,赐永兴军王嗣宗。[4]
就连平素耿直的晁迥与杨亿,也不免奉承说要载于史册,付之史院。再如“祥符《神雀诗》、《甘露诗》”条记载道:
(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三日,丙申,恭谢玉皇于朝元殿。礼毕,帝作《朝玉皇观二鹤神雀诗》三首,近臣毕和。庚子,作《圣祖降临记》。庚戌,钱惟演言甘露降所居丛竹,上作五言诗赐之。[4]
此外,瑞雪、瑞石、甘霖、神雀、绿龟之类的诗作充斥在真宗馆阁文臣的集子中,内容空乏,创作心态带有明显的颂德歌功成分,语言的走向富赡,这些对宋初诗歌流变有着积极的意义。
(四)观文、论诗——盛世的文化推崇
真宗喜读书,更多的时候是带领文臣、宗室入阁观文论诗,赏画评书,文化气氛浓郁。《玉海》卷二十七《帝学》中有不少记载,如:“淳化元年八月癸卯朔召,近臣阅秘阁图籍”、“咸平崇文院阅群书,秘阁观太宗御书,馆阁阅四库书” 、“景德崇文院观四库图籍”、“景德太清楼观四部书”、“祥符观书龙图阁”、“祥符召宗室观书龙图阁”等等,类书《玉海》收录不少这方面的诗作,现略举几则如下:
祥符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戊寅,召近臣观龙图阁太宗御书及四部书籍。……帝作《观书》《开宴》五言诗,令即席皆赋。[4]
——祥符《观书开宴诗》)
(咸平)五年十月己卯,召近臣观书于龙图阁,于阁之四壁设五经图,阁上藏太宗书帖三千七百五十卷。[4]
——观书龙图阁
祥符三年八月甲寅,召近臣观书龙图阁。……上作七言诗,从臣皆赋。[4]
——祥符观书龙图阁
真宗在带群臣观书论诗的活动中,常伴有御制赋诗的环节,这类诗作也有部分留存至今,如:
仙禁开书府,纯毫纪格言。简编包舜禹,范围总乾坤。稽古崇邦教,斯文辟圣门。从游观奥秘,何以报宸恩。[3]
——寇准《应制太清楼观书》
非烟葱蔚苍龙阙,紫府深沈大帝居。群玉中天开策府,神龟温洛荐图书。
珠宫岑寂经行处,金简荧煌拭目初。曾是先朝受恩者,因探禹穴涕涟如。[3]
——杨亿《宣召赴龙图阁观太宗御书应制》
寇准是真宗朝名宦,其诗歌一般将之归入晚唐体,其实不少诗歌并不与晚唐体特征相符,倒与白体诗有相近之处。这两首诗是其观书应制之作,对帝王储书聚书的目的与作用有清醒认识,与己可以多闻释疑,与国则可兴教化,育俊才。同时,也盛赞君王能崇尚学术,以身作则,勤学不息,对自己能随驾观书的万分荣幸与感激之情。杨亿则先写藏书环境的肃穆,再写帝王所藏之书的珍贵,最后对自己能以屡受皇恩,随驾入阁观书身为感激。诗作内容没有多少可取之处,诗歌语言具有明显的富贵气息,应制之作由浅显明快逐渐向富艳华赡转化。这种风格在真宗朝其它馆阁文臣中也普遍起来,最终形成典型的昆体诗风。
总之,真宗朝的馆阁文臣的应制酬唱之作在内容与心态上与白体诗基本一致,在艺术追求上既有与白体一致追求平易流畅的一面,更有追求典实富赡的另一面,同时内容颂美成分浓烈。白体诗风在真宗朝馆阁翰苑的应制中渐行渐远。
三、真宗朝其它翰苑词臣的白体诗歌创作
(一)“翰林主人”——宋白
宋白(936—1012)字太素,大名人。太祖建隆二年进士及第。乾德三年授玉津县令,先后知蒲城、渭南二县。太宗朝迁左拾遗,拜中书舍人。太平兴国五年任知贡举,八年为集贤殿直学士,后召为翰林学士。端拱初为礼部侍郎,加知贡举。后因张去华坐尼安道事贬,至道初为翰林承旨。真宗时,以礼部侍郎判昭文馆,后曾权治开封府。至道四年以工部尚书致仕,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正月卒,谥文安。《宋史·文苑传》将其列为首位,被誉为“翰林主人”,可见对其文学才能的肯定。
宋白一身久居文臣之职,其诗文创作甚富,《崇文总目》记载:“宋白文集一百卷”[14]惜已散佚殆尽。其诗文流播情况,祝尚书先生说:“百卷本文集久佚,亦未见宋人序跋,在宋代刊布情况不详。……今仅存《宫词》一卷。”[15]《全宋诗》卷二十收其《宫词》一百首,其它诗作三十首,残句十三则。《全宋文》收其文二十三篇,另外,伍联群先生还辑得逸诗五首,残句八则,试题一篇;辑逸文存目三则,残篇一则,残句一则[16]。这是目前能见到的诗文概况。
宋白的诗歌从内容上看,首先是赞颂新朝,鼓舞升平的诗作最多。如前后达百首之多的《宫词》就是其代表。其前有序言说:“至于观往迹以缘情,采新声而结意,鼓舞升平之化,揄扬嘉瑞之征,于以示箴规,于以续骚雅,丽以有则,乐而不淫。则与夫瑶池粉黛之词,玉台闺房之怨,不犹愈乎?是可以锵丝篁,炳缃素,使陈王三阁狎客包羞,汉后六宫美人传颂者矣。援笔一唱,因成百篇。言今则思继颂声,述古则庶几风讽也。大雅君子,其将莞然。”[3]可见,宋白对诗歌的颂美与讽谕有明确的认识,其具体诗作略选几首如下:
万国车书一太平,宫花无数管弦声。近臣入奏新祥瑞,昨夜黄河彻底清。[3]
楼前宣赦掣金鸡,大礼新成彩仗归。万岁声高天地喜,庆云飞上衮龙衣。
玉殿金扉夜不扃,露华如水洗圆灵。昭阳女伴新承宠,心祝君王拜寿星。
除《宫词》外,就是送别诗如《送陈尧叟赴广西漕》开头也说:“莫辞征骑去迢迢,尽泻纯诚许圣朝。北阙皇恩从此布,南方沴气必然销。”对当今的圣朝皇恩充满敬意。
其次为节日游宴,登临咏怀之作,如重阳登高,中秋赏月宋白都有诗作留存,诗作流露出寂寞之情。如:
霜冷风清九月九,茱萸黄菊家园有。何时玉殿接千官,称觞共进南山寿。[3]
——《九日》其一
去年今夜此堂前,人正清歌月正圆。今夜秋来人且散,不如云雾蔽青天。[3]
——《中秋感怀》其一
再次为寄友之作,如《寄蔡昆》:“却忆醉相逢,云深太白东。离别经腊雪,魂梦又春风。芳草晴天阔,黄鹂细雨中。倚筇愁望处,烟树远蒙笼。”[3]
在诗歌语言上,宋白语言平易通俗,明白如话,一目了然。内容上略显宽泛,但仍然以颂德记游、赠寄感怀为主,也是白体常见题材。
(二)闲适悟道:晁迥晚年的白体诗歌创作
晁迥(951—1034),字明远,世为澶州清丰(河南清丰县)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释褐为大理评事。真宗朝累迁至右正言,直史馆、知制诰。景德二年任翰林学士,后累官至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仁宗为礼部尚书,以太子少保致仕。景祐元年卒,年八十四,谥号文元,《宋史》卷三○五有传。
晁迥太平兴国五年中进士,由于为人正直,太宗朝蹉跎下僚二十余年,诗歌收王禹偁影响明显,多为讽喻时事之作;真宗朝,官运显达,景德二年五月拜翰林学士,成为真宗的近臣,有机会参与君臣赐宴雅集与文臣之间诗酒酬唱,诗风沾染昆体风格;仁宗初,致仕后,闲逸安适、参禅悟道是其诗歌的主要内容。
儒释道兼修是晁迥一大思想特色,正如邓广铭先生论道:“晁迥确实是熔冶了儒释道三家学说于一炉的一个人;而他却始终是以一个儒家学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更须注意的是,晁迥的这种学术取向,不但为晁氏一族的学者所世代承袭,综观北宋一代的学术界,这种学术取向也是颇有其代表性的。”[17]漆侠先生也说:“晁迥从儒家思想向佛家思想渗透,有助于宋学的形成,倒是顺理成章,提供了方便的。”[18]晁迥对白居易的崇仰之情充斥于晚年的诗文之中,如:
愚夙慕白乐天之为人,虽才识不逮乎乐天,而志愿阃域其殆庶几乎?乐天有《新制布绵裘诗》其末句云:“安得万里裘?盖覆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愚有《击壤辞》其末句云:“安得大金柅,制彼日月轮。免同流水车,今人续古人。”[19]
——《昭德新编》卷上
予常爱白乐天,词旨旷达,沃人胸中,有诗句云:“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夫如是,则造化阴骘不足为休戚,而况时情物态安能刺鲠其心乎?[20]
——《法藏碎金录》卷一
晁迥还曾筑虚白堂,逍遥期间,神似白居易晚年居洛阳时的闲适逍遥。晁迥现存诗歌数量不多,《全宋诗》收录五十六首,绝大部分是从晚年所作《法藏碎金录》、《昭德新编》及《道院集要》中辑录出来。诗作自适悟道的色彩甚浓,现将晁迥晚年诗作略分以下三类,其中为突出他对白居易的追慕,特将其拟白之作单独分成一类,并分析其诗歌内容与风格。
1.拟白之作
晁迥晚年甚是推崇白居易,曾作十余首拟白之作,从不同侧面表达自己对白居易的赞赏,现移录部分如下:
求位不由己,求道不由天。位即无以求,道可使进焉。且务由己者,己能尽心源。勿问由天者,天高擅化权。
顺逆不由己,喜怒不由他。他即无奈何,己可存太和。且务由己者,克己谅非多。勿贵由他者,他心是我魔。[3]
——晁迥《拟白乐天诗》
晁迥此诗即拟白居易《咏怀》一诗,白居易诗为:“……穷通不由己,欢戚不由天。命即无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务由己者,省躬谅非难。勿问由天者,天高难与言。”[21]这是对白居易知天命,随任化人生态度的肯定。
晁迥还拟白居易《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心不择时适,足不拣地安。穷通与远近,一贯无两端。”[21]作《拟白乐天诗》诗:“心不择时息,书不择时观。达理意无碍,豁如天地宽。”[3]表达自己对理达的追求,明白此理即可达到自适无碍的境界。拟白居易《罢药》一诗,作:“自学养恬休用智, 从他名迹日衰微。我身不欲全高贵,高贵多乘祸败机。”[3]白居易求坐禅,不求全强健,因为强健多生人我之心,因而罢药;晁迥则主张恬养,不求高贵,因为高贵之中暗藏灾祸败机,这带有自足不辱的味道。晁迥拟白之作还有:
权要亦有苦,苦在当忧责。闲慢亦有乐,乐在无萦迫。[3]
——《拟白乐天诗》
角胜劳生不足云,滥传僧语亦非真。始知解爱禅中乐,万万人中无一人。
——晁迥《拟白乐天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质夫不至独宿仙游寺》
孟子四十心不动,定光四十心离尘。我到明年加一倍,如何此际尚因循。
已喜自逃名宦网,犹患长随造化钧。记得前贤有诗句,祖师元是世间人。
——《晁迥拟白乐天题赠定光上人》
多图果何益,只自劳奔竞。不如收身心,凝然成静定。[3]
——《拟白乐天诗》
具体诗法上,晁迥对白居易诗歌有明显的承袭,有的甚至只改动几个核心词语而已,其句式章法与白居易完全一致。至于诗歌所表达的理趣则与白居易极为相似,或是原理重释或改变角度“接着说”。其拟作的艺术成就并不高,大多是直接阐发道理,没有多少形象性可言。
2.对佛道教义的参悟
晁迥仰慕白居易,更偏重对白诗中佛教禅理的认同与汲取,他自己也说:“盖于经教法门,用此弥缝其阙,而直截晓悟于人也。” 除拟白之作有参悟佛理的成分,晁迥尚有大量的禅语悟道之作。佛教注重“定”、“空”、“幻”、“无”等等禅宗教义,晁迥许多诗作就是抒发自己对此的理解。
晁迥在《洞心情境定心篇》中说:“物来诱之而不随,物来触之而不动。不随不动自由心,何须结社询千众。万事悠悠过即空,追思岂异春宵梦。”[3]不随不动之自由心也即是佛教追求的心定,心定之后有何须结社问僧?晁迥还有直接阐释由静而定,定而生慧的佛教修行之法的诗作,如《三法自然歌》:“心本不愆自然戒,何用科条防毁败。心本不动自然定,何用勤劳止自兢。心本不迷自然慧,何用参寻叩伦类。即今知此三自然,奉以周旋无失坠。”[3]
晁迥在《反本观空无碍辞》中说:“形是幻,情是梦,寝兴视息随群动。当念元来一切无,豁然顿遣心中空。”[3]用诗直接宣传佛教“无”、“空”等教义,没有多少情感或形象的东西,以至于四库馆臣不把他们视为诗作。其实,这也正是晁迥晚年诗歌的特征之一,充满惊人的阐理悟道的色彩,这类诗作甚多,如:
心空如太空,豁然无可触。一真法界中,灵照常安住。[3]
——晁迥《偈》
起灭心不停,生化形无数。奇哉大丈夫,自在空中住。[3]
——晁迥《偈》
了知入道门,先从静为祖。静胜则心安,安久虚灵府。虚极发明灵,洞彻无不睹。天然法乐多,岂此闻箫鼓。[3]
——晁迥《静深生四妙辞》
3.对人生的感悟
晁迥晚年也有不少表达人生感悟的诗作,诸如对委顺的称赞,他在《知常委顺辞》一诗中说道:“纷然往事来,浮云经大空。喧然是非声,惊飚触灌丛。古今无奈何,委顺于其中。”[3]对自足、无欲的追求,如《书绅二法辞》:“心如常满杯,所以明知足。心似不燃火,所以明无欲。二法可行持,书绅聊自勖。”[3]对无所求的称赏,他在《无有所求歌》中说:“无所求,摆落人间万事休。有所求,安养衰年乐圣猷。不愿竹木林内隐,不愿莲花社里收。愿在清平仁寿域,含华守素得优游。” 如此等等,其人生感悟参杂着佛理。
由上述排比晁迥晚年诗作,可知其诗作内容尽是闲适悟道与修身参禅,创作方式极似禅悟似的偈语短颂,充满佛道教义的与人生感悟的味道,而且几乎排斥情感因素,这也伤害诗歌应有的艺术性,开后世道学体诗歌的先河。与稍前的白体名流徐铉、李昉及白体集大成者王禹偁都有极大的区别。这种只关注白居易的晚年的悟道之作,及由此而创作的抒发佛道之理与人生感悟的道情诗,这是他成为众多宋初白体诗人中极具鲜明特色的诗人之一。
真宗朝尚有不少文臣的诗歌也具有白体诗歌的部分特征,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只能是挂一漏万了。
总之,宋初白体诗人在真宗朝呈现分化的趋势,真宗与翰苑词臣们的应制酬唱诗作在内容与心态上与白体诗人并无二致,在艺术追求上既有与白体一致追求平易流畅的一面,更有追求典实富赡的另一面,同时内容颂美成分浓烈。白体诗风在真宗朝馆阁翰苑的应制中渐行渐远,并最终促使西昆体在真宗朝中期的风靡,这个过程具有复杂性与渐次性。不少昆体诗人,其风格也不仅仅就是昆体一种风格,他们有白体的成份。正如曾枣庄先生所指出的:《西昆酬唱集》的十七人并称具有偶然性,他们的政治态度、文论主张、诗文风格都不统一,统统算作西昆体诗人,显然是不恰当的,应该区别对待[22]。白体诗作在真宗朝没有消失,而是转入更深的层次的融合之中,并成为宋代诗歌的重要渊源之一。
[参考文献]
[1](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4.
[2]陈元锋.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与诗风嬗变——以杨亿为中心[J].文史哲,2012(5):44-57.
[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178.
[4](宋)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577-588.
[5]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85.
[6](宋)祖无择.龙学文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宋)邵伯温.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16.
[9](宋)欧阳修.归田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21.
[10](宋)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4.
[11](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269.
[12](宋)吴聿.观林诗话[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宋)阮阅.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0.
[14](宋)王尧臣.崇文总目(卷十一)[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9:8.
[16]伍联群.北宋文人宋白著作概况及其诗文辑补[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2):54-58.
[17]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0.
[18]漆侠.晁迥与宋学—儒佛思想的渗透与宋学的形成[J].河北大学学报,1996(3):56.
[19](宋)晁迥.昭德新编(卷上)[M].印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宋)晁迥.法藏碎金录(卷二)[M].印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06.
[22]曾枣庄.论(西昆酬唱集)的作家群[J].文学遗产,1993(6):5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