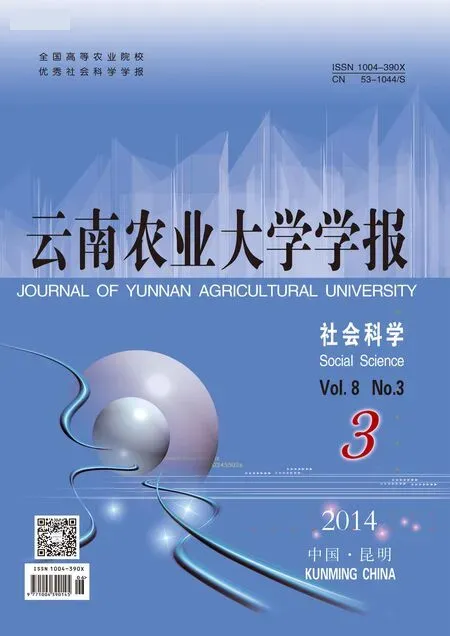主体的召唤
——解读《野草在歌唱》的他者建构
夏梅花,明 珠,杨 波
(云南农业大学 外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多丽丝·莱辛,被誉为继伍尔夫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1919年出生于伊朗,6岁时因父亲经营农场移民到津巴布韦,经历两次婚姻的失败最后回到伦敦从事写作。
莱辛善于通过悲剧性的人物命运揭示种族分离、种族歧视等观念与行为引发的道德冲击与社会危害。她的作品具有反对殖民主义思想、争取自由平等权利,讲述妇女的困境、奋斗与成长,直指社会尖锐矛盾等特点,尤其她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野草在歌唱》充分体现了其特点。该小说在1950年首次出版,并在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故事是以一起凶杀案开头,通过揭示案件的全部过程,揭露了白人种族主义的虚伪,展示了殖民统治的实质,唤起了人民对深陷苦难的黑人的无限同情。该小说一问世就受到众多国内外学者关注。国外学者多关注其主题与文学技巧,王乔伊宣称玛丽与黑人摩西的非正常种族关系是“白人殖民者发泄感情及自我救赎的一种媒介物”[1];维斯尔认为该小说是津巴布韦解放文学,其中“人类暴力是大自然力量人格化的表现”[2]。国内学者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及后殖民探讨女主人公玛丽的悲惨结局的原因,如张金泉指出玛丽的悲剧是受当时父权制的影响, “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要独立才能改变命运”[3];陶瑞萱对该小说进行了莱恩式的解读,玛丽“自我的分裂及无意识”[4]注定了是一个悲剧;莱辛的作品表现的都是反殖民主义,但有学者持相反观点如赵纪萍认为小说“在批评和反思殖民主义罪恶的同时未能超越殖民话语的限制,暴露出英国文学传统中所特有的殖民性对其产生的影响,呈现出殖民话语的隐性书写”[5]。学者对该小说的关注可谓是百花齐放,包罗万象,鲜有人分析该小说中主体对他者的建构。本文从分析作者在建构种族他者及性别他者这个角度出发,解读作者是如何通过“去他者化”及“他者还原”来处理他者身上的他异性,以此建构他者,从而表现出作者的真正立场。
一、 种族他者
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他者包括种族他者、性别他者、拉康、阿尔都塞等人提出的他者等,其定义为“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6]。种族他者指非白人民族,包括非洲人、亚洲人等。博埃默指出:“后殖民的理论家们将殖民地的人民称之为‘殖民地的他者’(colonial other),或径直称为‘他者’(Other)”[7]。他者建构也可称为他者召唤(interpellation),指处于主流社会阶层的人为了牟取利益,通过话语权对个人进行召唤,预先设定个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旨在服务于统治阶级。在《野草在歌唱》中,殖民者为了更好地管理殖民地,通过“去他者化”与“他者还原”方法从而去除他者身上的他异性(alterity)。
莱辛在小说中应用的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在小说开端部分就报道一起谋杀案,男仆谋杀了女主人玛丽·特纳,原因不详,疑似谋财害命,接着作者以嘲讽的口气写到每个读者看到这起报道时不免感到气愤,又夹杂着“一种几乎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种想法得到了证实,某件事正如预期的那样发生了,每逢土著黑人犯了盗窃、谋杀或是强奸案,白人就会有这种感觉”[8]。作者叙述故事时夹带嘲讽语气向我们展示了她对种族偏见和歧视的谴责。谴责白人自视的种族优越感及黑人野蛮低贱。小说不断地在揭露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本质,白人从来不和黑人打交道,除了以奴隶主的身份; “白种文化(white civilization)”[8]决不允许一个白种女人与一个黑人发生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尽管玛丽死了,但黑人们是不能去碰白人的身体的; 若有必要打死黑人亦在所不惜;说起黑人就像说起一大群畜生一样,看见有人打黑人或是望黑人一样都觉得反感等等,莱辛一一向我们展示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犯下的恶劣罪行,揭露殖民主义的本质,殖民主义者不是来救赎教化当地黑人,而是残害、侮辱、鞭打黑人、无视黑人的基本人权、不断地牟取利益等。
作者在揭露殖民者罪恶劣性同时对黑人外貌的描述不免让我们对黑人产生一种厌恶。种族他者构建的特点就是话语权的不对称性、人体外貌描写在视觉效果上的差异化以及其行为的古怪和不可理解性。迪克开了一间日用品商店,由玛丽自己来经营,玛丽看到黑人女人“她们裸露的穿着,她们那柔软的棕色身子以及她们那既忸怩又傲慢无礼的好奇面孔。她们那种带有厚颜无耻和淫荡意味的唧唧喳喳的声音(……the exposed fleshiness of them, their soft brown bodies and soft bashful faces that were also insolent and inquisitive, and their chattering voices that held a brazen fleshy undertone.) ”[8]。我们所看到的黑人不是整个人的描写,而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展示,如皮肤、面孔、身体等。“裸露”、“棕色的身子”、“忸怩”、“傲慢无礼”等词在描述种族他者时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变形或者说丑化。这些无不透着白种人优越,黑人的野蛮与未开化。正如康德在《自然地理》中强调地理环境对种族的影响,他说:“人类最完美的典范是白种人。黄种人、印第安人智商较低。黑人智商更低,部分美洲部落位于最底层”[9]。 “唧唧喳喳的声音(chattering voices)”这是动物才发出的声音。玛丽是学过土话的,她应该能都听懂她们的谈话,但小说叙述者把持了话语权,剥夺了黑人的表达权力,他们处于失语状态。向这些黑人出售用品的商店显示了英国人对非洲人的把握,也表现了对非洲黑人的教化的行之有效,进而加强了英国对非洲殖民主义统治的合法性。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在非洲的殖民主义不仅仅是为了谋取利益,也是为了对那些未开化的民族进行教化,引导他们走上文明之路,做一个文明人。另外迪克生病了,玛丽不得不亲自去农场监督黑人劳作,“只见那些赤裸的棕黄色脊背弯下去又挺起来,一条条的肌肉在布满了灰尘的皮肤下面滑动着,大多数人都用一块褪了色的破布当围腰,有少数人穿着咔叽布短衫裤,但是几乎所有的人腰部以上都是赤裸的”[8]。在描述土人的形体“赤裸(naked)”一词透露出土人的未开化、野蛮,事实上在告诉我们只有英国人才能引领他们脱离未开化的原始状态,走向文明之路。另外玛丽不得不去农场监督黑人干活时,刚上车又回去“……为自己找借口说,还需要拿块手帕。从卧室里走出来时,她看见了那条长长的犀牛皮皮鞭挂在厨房的两颗钉子上,像是一件装饰品。她已经把这件东西忘记很久了,现在她把它取下来,绕在手腕上”[8]。玛丽也是白人的代表,她所受的教育是欧洲中心主义式教育,即白人优越,黑人野蛮低贱。在她看来只有采取某种强制性,甚至暴力性行动,才能开化黑人,去掉黑人身上那些被白人认为不能容忍的他异性,使黑人成为白人接受的人物形象。
“他者还原”指“作家把他者身上的他异性搁置起来,把他者还原为自我民族的大众能够理解的人物形象——在思想上感情上与作者本民族读者成为同一的形象”[10]。《野草在歌唱》中黑人摩西和其他黑人不一样,虽然有了名字,但小说没有交代他名字的来源,可能只是作者给他取个熟悉的名字,其目的在于控制被呼唤的事物,使之成为主体可掌控之物。摩西第一次出现是在玛丽去农场监督黑人干活,摩西因歇息了一会儿,玛丽就抽打他,玛丽的行为是去除他者身上的他异性,维护其白人权威。摩西和其他黑人佣人不一样,他曾经在教会当过差,会讲英语,对玛丽说话表现的很绅士,行为举止得体,连迪克都这样评价他“他很干净,做事也主动。在我那些雇工中,他是最好的一个”[8]。摩西的这些言行举止都是从教会里的传教士那学到的。经过他者还原,殖民者对黑人摩西实施还原改造,让他成为殖民者的模仿品。另外摩西还会主动与玛丽探讨战争等问题及关注报纸,摩西问道“难道耶稣认为人类互相残杀是正当的吗?(Did Jesus think it right that people should kill each other?)”[8]殖民行为不仅改造黑人的生活及行为方式,而且也改变了黑人的信仰及思维模式。小说中虽没有确切的说摩西的信仰,但从这里不难看出他对基督教做了一番思考。估计他也信奉耶稣所以才质疑为什么世间还会有屠杀呢。这些都宣扬了殖民主义行为的合法性,读者所得到的信息是殖民主义的实质不是侵略而是拯救教化,只有殖民主义,黑人才能从低级、堕落、野蛮、无知及未开化的世界中拯救出来,从而走向文明之途。
综上所述,莱辛在对黑人的描写上,或者说非洲人的建构上,仍然难以避免英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就如萨义德说“我认为,作者不是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驱使;但是我相信,作者的确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也为他们的历史和经验所塑造”[11]。由此可见小说在揭露殖民主义罪行的同时也通过去他者化和他者还原建构他者。
二、女性的去他者化
性别他者即指女性,在该小说,在男权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作者也是通过他者还原甚至去他者化建构女性他者。迪克的懦弱,无主见,经营农场,养蜂,养鸡,养猪及开商店等的失败及半途而废都说明玛丽的能干。迪克卧病在床期间,玛丽行使了对黑人惩罚、雇佣的权利并一心盘算着,“该如何毫不示弱地控制黑人,如何料理家务,安排各种事情,使自己不在家的时候,迪克也能感到比较舒服。她同时也仔细地研究了农场上各方面的情况,譬如到底该怎样经营农场,可以栽种些什么农作物”[8]。“控制黑人”、“安排各种事情”、“经营农场”及“农作栽种”逐一告诉我们女性参与到本来由男性主宰的社会事务中,并不见得比男性差,相反是男性害怕失去驾驭女性的能力和控制权。玛丽对迪克的经营状况翻查透视着女性对男权的批判,挑战男性作为社会主体的地位及男性霸权地位。玛丽的出走尽管失败了,也显示女性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她们在不断地反抗,为自己的权利而争。西蒙·波伏娃于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提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12]女性知道她们是被建构的,不是天生由来的,不管是玛丽还是她母亲,都努力反抗争取权利。
虽然这些都传达了女性努力奋斗成长等主题,但小说《野草在歌唱》中玛丽最终以死亡的悲惨命运告终。作为一个女性他者,就如陶铁柱在《第二性》译者前言中总结了她对波伏娃“他者”概念的理解,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的人”[13]。波伏娃的他者指的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关系,意在揭露男性主宰下女性的从属地位。为了去除他者身上的他异性采取某种强制性、甚至是暴力性行动也是常有的。该小说中玛丽虽是一个白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妇女。玛丽的父亲是铁路局的小职员,收入低外加经常酗酒,维持不了日常生计。童年的她天天目睹父母的争吵,母亲因哀怨、辛劳和无奈最终憔悴而死;工作后的她看似每天过着平静而舒适的日子,无忧无虑,摆脱了父母过去的生活,实则生活在幻想中,不真实,试图逃离现实。直到30多岁偶然听到朋友谈论她为什么不结婚的怪行,“‘她有多大了?’‘总有三十出头了吧’‘她为什么不结婚呢’”[8]?这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意识到现实,意识到自己也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的。一直以来女性的身份不外乎两种:妻子与母亲,玛丽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容接受的,父权制已内化到每个人思维。随后玛丽开始做出外貌上的改变,内心也随着大流渐渐改变,使自己成为大众所能接受的形象,开始疯狂地寻找结婚对象。现实里女性作为一种对象存在于这个男性社会中,她们是一些没有主体性的物,是处于边缘化、非在场化的,被他者化的。鳏夫的要求应该是代表所有男性的要求, “他需要一个怡情快意的伴侣,一个孩子们的好母亲和操持家务的能手(He knew perfectly well what he wanted: a pleasant companion, a mother for his children and someone to run his house for him)”[8]。他只是父权制社会其中的一个。迪克也不例外,他的梦想就是娶老婆生孩子,“他孤寂。需要妻子,尤其是需要子女(He was lonely, he wanted a wife, and above all, children)”[8]。迪克理想的妻子是“一个讲求实际、易于变通和性格镇静的女人(a practical, adaptable, serene person)”[8],迪克对玛丽动心,也是因为“看见她外表上很沉静,带有贤妻良母的意味(It was to an apparently calm, maternal Mary that he proposed)”[8],男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想像来建构女性,把女人放置在他者的位置。另一方面父权意识形态深深地烙在人们心里,被他者化的女性也愿意接受社会给予的性别,即软弱、无助、需要男人并依附于男人,“她迫切需要这样对待她的男人。……其实这些年来,她都是在这样的优越感中生活过来的”[8]。就这样玛丽“被结婚”了。婚后生活的不如意,如玛丽要求迪克装天花板、洗澡过度用水和黑人佣人吵架等,使得迪克改变了对玛丽的最初的看法,他认为玛丽不懂事,耍小孩子脾气,无理取闹,没有思考能力和决策能力。主宰社会的男性,根本不管事实,凭着自己的想像建构出合乎自我需要的女性他者形象,当女性与男权所构建的女性他者相去甚远时,她只能成为牺牲者,玛丽最终以悲剧告终。
女性作为异于于主体的他者,仍然避免不了被他者化的命运。莱辛,一个女性作家,仍然避免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家只能负责唤起维护女性权利的意识,笔杆子仍然改变不了女性的命运。
三、 结语
在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里,他性一般是不受欢迎的,因而有必要将之还原为与自我的同一或有必要去除的。《野草在歌唱》虽然被认为是一部反殖民主义的作品,但作者在叙述黑人及摩西的一些言辞造句中就是在对黑人的召唤,建构种族他者。另外该小说描述女性为权利而挣扎奋斗,但玛丽的死亡正说明主体竭力去除他者身上的他异性,甚至采用暴力,直至他者的死亡。多丽丝·莱辛,一个英国女性作家,虽极力主张反殖民主义,并一直为妇女的权利奋斗,但其作品仍受英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小说《野草在歌唱》仍表现出对种族他者及女性他者的他异性的排他性和归化。本文通过对该小说中他者建构的角度的研究,揭示了作者莱辛的两难立场,并为该小说中的殖民主义、殖民话语及批评话语之间的争论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加深了我们对英国殖民主义对非洲黑人甚至白人所造成的伤害的认识。
[参考文献]
[1]WANG J. White postcolonial guilt in doris lessing′sThegrassissinging[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009, 40(3): 37-47.
[2]VISEL, ELLEN R. White Eve in the‘petrified garden’:the colonial African heroine in the writing of olive schreiner,isale dinesen,doris lessing and nadine gordimer.diss[Z].The University of Brithish Columbia,1987.
[3]张金泉,李爱琳.女性主义视角下《野草在歌唱》中玛丽的命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17-122.
[4]陶瑞萱.分裂的自我与存在的困境——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的“莱恩式”解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9(5):152-156.
[5]赵纪萍.殖民话语的隐性书写——重读《野草在歌唱》[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3):46-48.
[6]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18-127, 159-160.
[7](英)博埃默(Elleke Boehmer).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译.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22.
[8]LESSING, DORIS. The grass is singing[Z]. Perennial Classics,2000.
[9]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468.
[10]祝远德.他者的呼唤——康拉德小说他者建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
[11]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7.
[1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23.
[13]陶铁柱.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