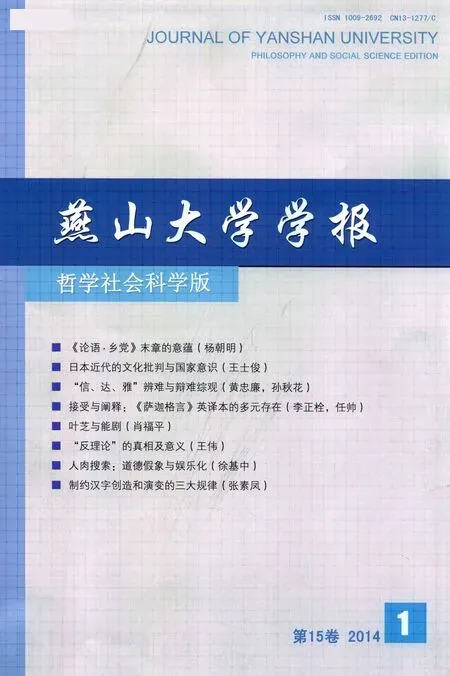论《金光大道》的文学史贡献
许 峰
(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浩然和他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个耐人寻味的特例。在文革那万马齐喑的年代,浩然不仅是凤毛麟角的能署名发表作品的作家,而且红极一时。无论是“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还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各式戏称的背后都反映了浩然和《金光大道》在当时难以比拟的影响力。这本和浩然的名字划上等号的《金光大道》全书共分四部:第一、二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2年5月和1974年5月出版,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同名电影,第三部和第四部分别完成于1975年11月和1977年6月,然而一直没有出版,迟至1994年才由京华出版社将四部本一次性出齐。出版后各方评价褒贬不一,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比如艾青:“作品虽然没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年代的‘路线斗争’”。[1]甚至还有这样评价《金光大道》的:“《金光大道》除了重复和眷顾,并未能向文坛提供任何新的价值。因此,本书的研究理当不包括这部小说”。[2]348呜呼!曾经风光无限的《金光大道》到今天居然连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的资格也成问题了。作为特定时期的作品,《金光大道》和其它小说一样,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硬伤,如人物形象脸谱化、对政治的图解、叙述方式单一、语言平淡等等,在这方面许多专家早已指出,众所周知,无须本文赘述。但是在批评的同时也应看到,《金光大道》在不少方面对前期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进行了超越,在当代文学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简单的否定和简单的肯定一样,都是廉价的。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景图
《金光大道》四部洋洋洒洒合计200多万字,有着恢宏的时空跨度和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容量,是一幅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景图。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来看,小说所反映的时代上溯自1932年,下至1956年,从土改(1950年)到互助组(1951年),再到初级社(1953年),一直写到取消土地分红建立高级社(1956年)。小说以主人公高大泉、朱铁汉等走合作化这条“金光大道”,与张金发、冯少怀等片面强调“发家竞赛”的个人自发路线作不懈的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展开故事情节,不仅讴歌了党,讴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而且塑造了高大泉、朱铁汉等一批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脱颖而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秀农村基层干部的光辉形象。在当代文学史上,浩然的《金光大道》第一次完整地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那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发展到后期,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严重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实际,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但在我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是有必要开展的。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有着这样的评价:“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3]
在当代文学史中,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或背景的小说可谓多矣,短篇、中篇、长篇,不一而足。就中短篇小说而论,除了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1953年)、孙犁的《铁木前传》(1956年)、赵树理的《锻炼锻炼》(1958年) 、李准的《李双双小传》(1960年) 等耳熟能详的名家名作外,1956年作家出版社从《人民文学》、《长江文艺》、《北京文艺》等全国各主要文学刊物中所选编出来的8卷本《农业合作化短篇创作选》,也是这一时期反映农业化运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集。该套丛书第1至8卷的书名分别是杨禾等著的《爱社的人》、吴梦起等著的《杨春山入社》、克非等著的《阴谋》、杨书云等著的《石板沙沟一家人》、西戎等著的《宋老大进城》、吉学霈等著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何永偕等著的《大风暴》、柳纪等著的《长辈吴松明》。从“入社”、“爱社”、“前进的道路”、“阴谋”、“大风暴”等标题中的关键词不难看出,在作家笔下,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合作社的建立为标志,是一场象征着光明和希望,波澜壮阔的改革运动,而在此过程中,又充满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和敌我之间的较量。
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中短篇小说异彩纷呈,长篇小说更是蔚为大观。“1955年完成的《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4]除了赵树理的《三里湾》,还有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58年) 、柳青的《创业史》(1959年) 、于逢《金沙洲》(1959年) 、胡正《汾水长流》(1962年) 、陈残云的《香飘四季》(1963年) 、浩然的另一代表作《艳阳天》(1964年) 、陈登科《风雷》(1964年) 等长篇小说,它们和众多中短篇小说一道,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各个阶段,在文坛上产生广泛影响。
事实上,反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反映合作社的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就已出现,柳青的《种谷记》(1947年)、欧阳山的《高干大》(1947年) 两部长篇小说就是先声。虽然源头可以上溯至现代文学,上溯到延安时期,然而,只有《金光大道》才第一次完整地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貌,《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这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四大金刚”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创业史》本来计划要反映全貌的,可惜柳青去世得太早。《金光大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完成了柳青未竟的事业。
说《金光大道》是一幅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景图,不仅是因为它在时间上历史跨度大,坦率地讲,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如果能一直把续集写下去,完全有可能写出比《金光大道》时间跨度更大的作品。《金光大道》的恢宏主要是因为它在空间上有广阔的社会生活容量,在这一点上远远超过同为长篇小说的《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香飘四季》以及《艳阳天》。
《金光大道》是以冀东一座名为芳草地的村庄为着眼点进行描写的,反映的主要是农村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但《金光大道》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本身,而是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主线,穿插着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以及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 50年代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涉及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其社会容量可谓相当大。
1951年芳草地所在的天门区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事例:县长谷新民发动工商界出钱出力,结果来自省城一家大鞋庄的副经理权某打着承做志愿军军鞋的幌子,用马粪纸做鞋底,以假充真,企图利用抗美援朝发国难财,事败后又想贿赂区委书记王友清来脱身。布店、粮店老板沈义仁为囤积居奇,先是停业封存布匹,后是不收钞票而要用“小米票”才可买布。发展到后来,他更利用天门镇居民因水灾面临断粮的危险,与冯少怀、张金发等勾结,见死不救,操控天门镇粮食市场。这次不仅是为牟取暴利,而且是落井下石,妄图借水灾和粮荒动摇、打击共产党的政权,妄想变天。若不是高大泉等及时将粮食运到,后果不堪设想。再后来为对抗政府的“统购统销”政策,他们又把一万多斤粮食偷藏在“滚刀肉”张金寿家的枯井里……对于不法分子哄抬物价,企图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动摇新政权根基等方面的暴露,对于投机倒把政治危害性的挖掘,《金光大道》的深度和广度远超《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创业史》中姚士杰、郭世富只是敢往麦子里掺次麦,缺斤少两,以次充好;在《艳阳天》中也只不过是马之悦在秋收分红之际拉拢“弯弯绕”、“马大炮”、韩百安等几户中农,与城市里的不法粮商勾结,把余粮偷运到城市倒卖。和《金光大道》相比,这些只是小打小闹。《金光大道》除了写冯少怀、张金发和“小算盘”秦富等平日间的投机倒把、倒买倒卖外,更写了在抗美援朝、水灾粮荒的危急关头农村中的不法分子如何与城镇资本家狼狈为奸公然与人民为敌,但却最终注定要失败的一系列激烈斗争过程,其中既有经济斗争,更有关乎政权稳定的政治斗争。虽然是在河北农村,但《金光大道》对共产党与资本家较量的描绘,紧张程度简直就是浓缩版、农村版的1949上海“米棉大战”。尽管在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金光大道》远不能与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等专题小说相提并论,但其中共产党与资本家斗法、新旧两种意识形态较量的过程同样惊心动魄。而对这方面的细致描写也大大拓宽了《金光大道》的社会反映面,增加了作品的内容涵盖量,为同类题材小说所罕见。
二、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警世通言”
除了是第一次完整地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貌外,《金光大道》的价值更在于其在指出并大力颂扬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正途的同时,也难能可贵地尖锐暴露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为陶醉在胜利中的人们敲起了警钟;不仅如此,还对症下药,指出改进的具体措施,从而将互助合作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这在小说的第三、四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小说的前两部主要是讲以高大泉为首的芳草地农村基层干部,如何一步步教育、组织和带领广大群众从个人单干到组织互助组,再到初级社,艰苦创业,最终走上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以及如何与以冯少怀为代表的地富反动分子和以张金发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蜕变分子、自发破坏势力作斗争。类似的情节早已在《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不能走那条路》、《铁木前传》等中出现过。如果仅仅是写两条道路的斗争,写如何从个人单干到组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写农业社的发展壮大过程,那么200多万字的《金光大道》即使写得再长,也无非是《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的扩充、翻版而已,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在文学史上也谈不上什么突出贡献。无非是把故事发生的地点从陕西蛤蟆滩、湖南清溪乡、河北东山坞改成冀东芳草地。人物无非是从地主马小辫、龚子元、富农姚士杰换成漏网富农冯少怀,张金发无非是郭振山、谢庆元的变身,秦富则是郭世富的远房亲戚,连高大泉也不过是把梁生宝、刘雨生、萧长春改头换面而已。至于情节更加一律是党员干部面对困难、面对破坏时顶天立地,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经过努力改天换地,最后取得胜利大伙欢天喜地。但是,《金光大道》超越《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前期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包括超越浩然自己另一部代表作《艳阳天》的高明之处在于《金光大道》不仅表现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这一当代文学中早已有之的主题,指出走农业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正途,才是“金光大道”,才能奔向“艳阳天”,而且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农业社已办起来,而且是越办越红火,群众生活开始富足起来以后,在农业社内部又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铺张浪费、贪图享受、嫌贫爱富、自私自利、各自为政等落后思想又开始抬头、作祟。这些都有可能给敌人以可趁之机。为了过年,“东方红”这个红旗社尽管总共才43户人就计划杀15头猪,而且连还没长满膘的猪苗“小花脖”也不放过。过年放假从腊月二十八开始一直到正月初十,半个月不用干活,就算干活也不如以往那么积极——反正有土地分红,少干一点怕什么?有好地、有缝纫机入股的常国瑞的媳妇想入社,五个农业社你争我夺“打篮球”;出生在芳草地的秦有力“游子归家”却因为没有土地作为股份,尽管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却长期入社无门,九个农业社你推我挡“打排球”。“团结”社五保户孔百千因批评干部铺张浪费,结果被以家中没有劳力又只剩下赖地为由逼迫退社。“东方红”社想到邻村梨花渡“团结”社挑沙改造土壤却遭对方百般刁难,差点要动武。邓久宽这个“东方红”的“开社元勋”、“老八户”,生怕别的穷社揩了“东方红”的油,损害了自己分红的利益,为此不惜当着支书高大泉和村长朱铁汉的面,以几斤猪肉为题,在年关公然向穷社“奋斗”社的社长秦方讨债,不仅大吵大闹,而且还觉得理直气壮。为了区区一个猪头就又掉进冯少怀设下的陷阱,最后居然搞到闹退社,硬把已入社的小黄牛拉回家……冯少怀、张金发、沈义仁、歪嘴子等坏分子正是利用农民的这些毛病大做文章,大搞破坏活动。如果说在《创业史》中郭振山乐于走自发道路,在《金光大道》的开篇阶段高二林反对高大泉接济刘祥,对借给刘祥的粮食斤斤计较——“三十八斤半,抛皮,三十八斤”[5]——主要是因为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才刚起步,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深入人心,应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还没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尚属于情有可原;那么这次邓久宽的问题却是出现在农业社红火以后,出现在堂堂的生产队副队长身上,情况比当初郭振山、高二林的更严重。种种不良现象表明,即使是农业社已经建立,但农民头脑中的小农意识、私有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并没有随着农业社的建立甚至是巩固而自然消亡。相反的是在通过互助合作初步脱贫致富后,农民尚处于创业阶段,别谈守业,内部也已有可能重新出现分化,走个人发家道路的旧思想仍有可能死灰复燃,从而有被敌人趁机钻空子的危险。在《艳阳天》里,写的是东山坞高级社建立后因为小麦丰收如何分配胜利果实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而《金光大道》的芳草地还仅处于初级社阶段,还远达不到《艳阳天》东山坞的发展程度就开始出乱子了。反过来说,这也是浩然在观察农村生活、反映社会现实方面,对旧作《艳阳天》的一个超越。在《金光大道》中冯少怀、张金发等虽被打倒但一直想等农业社内部出现问题以便伺机反扑,用冯少怀的话说就是:“(邓久宽)不跟我一个心眼,他得跟钱一个心眼。那玩艺能招他的魂。 过去的仇疙瘩,那是穷人的火碰上富人的水,水火不相容。如今,邓久宽也富了,囤里有粮,腰里有钱,也变成水了。只要他这水想往外流,不在地面上跟我汇到一块儿,也能在阴沟里跟我并在一起。”[6]66“历来的穷人造反,都是能够同受苦难,不能共享荣华;饱暖生闲事,一胜利,就得起内讧,就离垮台不远了。……今个光为分一个猪头,就吵露了馅了——原来那馅都快烂了。有希望喽!”[6]89反动分子冯少怀的恶毒攻击妄图变天从反面为善良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浩然长期在农村生活,敏锐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并用艺术的方法深刻地表现出来,写出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真实情况,光就这点,《金光大道》就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深刻的思想深度,并非如有的批评者所讥讽的是假大空之作,而是确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和突破意义。因此正如浩然自己在1994年《金光大道》首次完整出版时所说:“我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记录下那个时期农村的面貌、农民的心态和我自己当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和它的存在价值。用笔反映真实历史的人不应该受到责怪;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就应该有活下去的权利。”[7]我认为,这并非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浩然有资格对自己的作品做出这样的评价。并不夸张地说,浩然在《金光大道》中所暴露出的在合作化进程中农村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使《金光大道》超越了前期同类题材的小说,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取得类似于《甲申三百年祭》般的警示价值。
三、相对真实可信的主人公形象塑造
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作品,《金光大道》中“三突出”原则的流毒也不能说没有,人物形象的确有拔高,高大泉精明强干得近乎神而不是人,于是从高大泉晋升成了“高大全”。但这也是当时小说的通病非《金光大道》独有,梁生宝、萧长春不也如此吗?反而是在《金光大道》中,人物脸谱化的弊端大为修正,主人公形象塑造的模式从过去流行的“绝情泯欲”的孤家寡人,转变成同舟共济的“儿女英雄”,血肉更加丰满。
比较一下《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的主人公家庭人员组成,会有一个可悲又可笑的发现: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先进性、革命性、纯粹性,英雄人物多被塑造成逃荒而来的外乡人,如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而且一律被描写成幼年时家庭残缺,不是丧父就是亡母——梁生宝无(生)父,萧长春无母,高大泉则是先亡父后丧母,都是逃荒而来,解放时正值青年时期。这样写是为了突出共产党才是他们的父母亲,是党给了他们新生。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他们长大后理所当然地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更不可思议的是,多数英雄不仅幼年时家庭残缺、流落异乡,而且成年后个人感情生活又多受到创伤,有的则是自己主动抑制、扼杀。英雄人物的家庭总是破碎的,不是一直打光棍就是丧妻或是老婆离婚——《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先是亡故了一个并无感情的童养媳,后来为了不影响工作顾不上和徐改霞的感情,两人最终擦肩而过……无父无妻的梁生宝还不算是最惨的,最悲摧的要数《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他不仅无母,而且先后亡妻、丧子,和他父亲萧老大一样,年纪轻轻就成了鳏夫。所有的人伦不幸都让萧长春一个人给赶上了,萧长春被写得比梁生宝还倒霉!而他还要强忍丧子之巨痛投入麦收工作,真是难为他了!《山乡巨变》中刘雨生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工作积极公而忘私,结果妻子张桂贞受到冷落要求离婚,丢了老婆。还好,周立波还不算“心太狠”,后来总算让刘雨生娶了善良的盛佳秀,好歹又续上了弦。总之,英雄的家庭都是不完整的,为了革命工作,顾大家就顾不上小家。因为他们不是普通人,甚至已经都不是人了。那个时代的作家居然能心狠手辣到这个地步,能把心爱的主人公活活地往死里整,让他们个个家破人亡,实在不能不让后人感到唏嘘。与其说是在把英雄人物纯洁化、神圣化,不如说是在把英雄人物异化、妖魔化,如果说这样塑造出的也算是人的话,充其量只能算是机器人!另外,把英雄人物个个都塑造成心无旁骛、一心为公的孤家寡人,看似既纯洁又高尚,但仔细一想就会有个可笑的悖论:若主人公个个绝情泯欲,那么他们那优秀得不能再优秀、纯洁得不能再纯洁的革命基因又何以能代代相传?他们所奋斗一生的社会主义事业日后究竟有谁人可以继承?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从何而来?难道就不怕有朝一日“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会卷土重来吗?到时英雄们可就死不瞑目了。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试想一下,若一个人物业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纯粹孤家寡人一个,还把他写得精明强干、公而忘私,不仅能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且还干得有声有色、无所不能,这也太勉为其难,太不近人情,甚至是太残忍了吧?这样完美的人物形象塑造又有多少的可信程度?不是神,不是机器又是什么?父母亲是否健在是英雄人物自己无法左右的,但选择妻子组建家庭则是可以由自己决定的。在众多英雄人物里,在组建家庭方面,只有高大泉的婚姻家庭生活是正常的,只有他才有一个志同道合和他患难与共的元配好妻子张瑞芳,有一对好儿女小龙、小凤。张瑞芳不仅支持丈夫的工作,而且本人也积极投向农业社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夫妻俩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在上述多部小说中,只有高大泉的家庭还有点人味,还像是正常人在过日子,还真实可信。《金光大道》的主人公形象塑造的模式从过去流行的“绝情泯欲”的孤家寡人,转变成同舟共济的“儿女英雄”,血肉更加丰满。正如杨建兵在《浩然与当代农村叙事》中所说的:“不可否认,高大泉是当代农村合作化小说中最完美的农民形象,他综合了王金生、梁生宝、萧长春等农民形象的所有优点,同时也排除了这些农民形象身上所有的性格缺陷,但他并没有失去一个常人的生活和情感。”[8]113-114难道这还不算《金光大道》为当代文学所做出的贡献?要知道,在那个“文学是人学”受到猛烈批判的年代,写英雄人物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夫妻生活,这可是犯大忌的。
不仅如此,浩然也没有把高大泉写得精明强干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买“滚刀肉”张金寿的大车时,他同样疏于防范,没有想到要提防别人做手脚,结果在和邓久宽“风雨龙虎梁”时遇险,摔断了腿,差点连命也丢了。他也不像买稻种、割扫帚的梁生宝、抢收小麦的萧长春那样的不知疲倦,近乎刀枪不入,一样会因为工作繁忙积劳成疾,卧病在床……这些都是在写人而不是在写神,是在人物塑造方面对过往小说公式化、概念化的一次反拨,即使这次反拨的力度是有限的。说到底高大泉还是个凡人。相对于梁生宝16岁还在吕二细鬼家熬长工时,就知道并敢于以每月扣工钱的方式赊买地主的小牛犊作投资养大牛,而且不用和家人商量自己就敢把小牛犊牵回家,并称梁三老汉的小心谨慎为“那是个没出息的过法”[9]和无母丧妻的鳏夫萧长春能强忍丧子之痛投身麦收工作等,还是高大泉更为真实可信。神一样的萧长春就不在话下了,梁生宝也已经精明得够可疑的。要知道,梁生宝这样做可叫“买牛花”,跟今天的香港人“买楼花”其实是一个道理。1953年时年30岁的霍英东在香港发明“卖楼花”,1941年年仅16岁的梁生宝就知道“买牛花”,而且还是先使未来钱“分期付款”,其投资意识之敏锐、消费观念之前卫,别说是在小农经济时代,恐怕连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浸润多时的今人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梁生宝常常被评论界视为“新人”的典型,如果梁生宝算“新人”,那么相对而言,高大泉则应该称得上是“真人”。
四、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金光大道》论语言形象生动、乡土气息浓郁不及《山乡巨变》、《香飘四季》;论情节跌宕起伏不如《艳阳天》,论叙事技巧又不如《三里湾》的赵树理式评书体,而且还有着这样那样众所周知的缺陷和硬伤,但它以其恢宏的时空跨度和丰厚的社会生活容量,深刻的警示教育意义和较为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塑造为当代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并非真的就是“除了重复和眷顾,并未能向文坛提供任何新的价值”。如果说“在当代农村叙事这一题材的发展流脉中,浩然不仅仅是‘农村合作化叙事模式’的继承者,而且是这一叙事模式的‘终结者’”[8]1,那么《金光大道》称得上是“终结者”的终结之作;如果说“浩然:合作化的最后一个歌者”[2]327,那么《金光大道》就是浩然这个最后的歌者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后的绝唱。自延安时期的《种谷记》、《高干大》以来,特别是自赵树理《三里湾》所开创的农业合作化叙事模式以降,农业合作化小说的优劣短长、贡献与局限,都在其中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尽管浩然在文革期间受到江青的青睐,红极一时,但现在不能因此就因人废言,反过来全盘否定浩然,全盘抹杀《金光大道》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如果这样,又和当年“左”的做法有什么区别?不加分析,一味指责《金光大道》及浩然的创作是脸谱化、公式化、概念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脸谱化、公式化和概念化!
注释:
[1]艾青.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N].文汇读书周报,1994-10-29.
[2]杜国景.合作化小说中的乡土故事与国家历史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7.
[4]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上卷 [M].修订本.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6.
[5]浩然.金光大道:第一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345.
[6]浩然.金光大道:第四部 [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
[7]浩然.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 [N].文艺报,1994-08-27.
[8]杨建兵.浩然与当代农村叙事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9]柳青.创业史:第1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