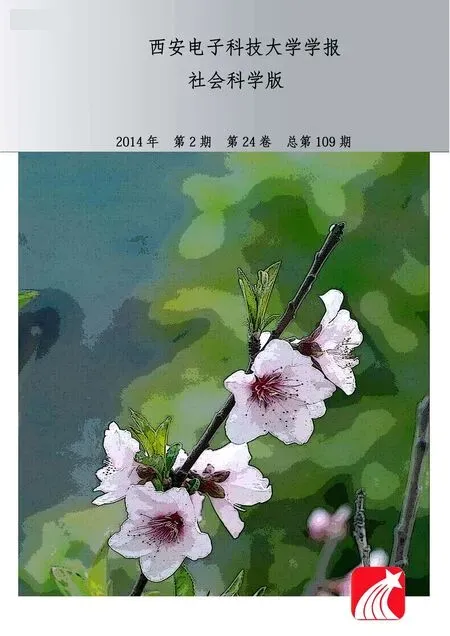美国法律过程学派对现实主义法学挑战的回应
刘翀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法律过程学派(Legal process school)是美国法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该学派在美国起于二战之前,盛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并随着哈特(Henry Hart)和萨克斯(Albert Sacks)《法律过程:法律制定与应用中的基本问题》一书的完成和威克斯勒(Wechsler)的演讲《迈向宪法的中立原则》的发表而臻于巅峰,引领美国法理学的发展达数十年之久①。法律过程学派对法律现实主义进行了批判性接纳,试图超越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并在欧陆极权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对自由主义法治的合法性进行了坚定的捍卫。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支撑法律过程学派的政治、经济条件急剧变化,其赖以存在的理想社会图景渐趋幻灭,法律过程学派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开始坍塌,但该学派的一些重要理论立场在学界至今仍备受重视,成为众多学者思考法律问题时的背景性知识和理论创新的起点。
一、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之争及法治合法性危机
自兰德尔(Christopher Langdell)以降,法律形式主义成为自由主义法治的正统理论。自由主义法治以公、私二分作为自身的结构性基础,强调私域优于公域,自由市场先于政治国家,试图以私法的形式理性化发展来确保法的安定性和法律调控结果的确定性,并使个人权利能免于公共权力的咨意侵犯。兰德尔的古典正统体系与此种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桴鼓相应并秉承理性时代的信仰,把普通法看成是一个去社会背景化的自治、中立的体系,由抽象的概念和原则构成,具体的规则来自于抽象概念和原则的推导,而司法则完全成为在封闭体系内进行的计算过程,法官只需运用演绎逻辑进行形式主义的法律推理即可排除外在的价值判断并为案件找到确定的答案。而制定法作为政治过程的输出物,反映着公共政策的变化和权力意志的要求,制定法是任意的、混乱的和主观的,并不属于“法律科学”的研究范畴。司法扮演的重要角色之一是要在私法领域区别欺诈、胁迫与自由意志并在宪法领域厘清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以此来维护公私二分的界限②。洛克纳案(Lochner v.New York)是法律形式主义臻于巅峰的标志也是其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在洛克纳案前后,一批年富力强的偶像破坏者,对公理与命题的体系、归纳演绎推理的价值及形式规则安排人类事务、组织社会生活的能力持普遍怀疑态度,试图复活内战之前司法的“宏大风格”。
为动摇兰德尔古典体系的正统地位,现实主义者首先对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结构性基础的公私二分图景进行了解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公私二分并非生活世界中的真实存在,不存在真正自治中立的自由市场,私域本身不过是公权力的创造物。因此自由主义法治能被理解成是以公私二分为基础的完整统一的图景只是一个欺骗。此外,现实主义者还提出“法律不确定性”命题,并以此为工具,从概念、规则与逻辑等多个角度对法律形式主义大加挞伐,试图揭开普通法那个绵密无缺又盱衡贯通的体系是如何矛盾重重并充斥着欺骗性的。首先,现实主义者认为法律形式主义所假设的抽象的概念和原则不过是“法律魔法”、“语言讹诈”和“概念杂耍”,这些“超验的废话”无法从经验层面来予以验证[1]。其次,现实主义者对规则普遍持怀疑态度,认为“抽象的规则无法裁判具体的案件”,并且普通法所谓的中立规则都可以重新解读成特定的政策选择。再次,现实主义者认为法官在裁判之前就已形成结论,演绎逻辑与判决理由只是一种操纵的技术,是法官在事后将结论合理化的方法,而不是案件判决过程的真实反映。在法律现实主义的激烈抨击下,法律形式主义成为“自动售货机式”的机械法理学,而其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法治的合法性也岌岌可危。现实主义对公私二分的解构颠覆了公、私的界限与次序,动摇了自由主义法治的结构性基础,私域不再是一个自治中立的非政治性领域可以独立于公域而存在,公私二分在表面上的形同陌路无法掩盖其事实上的殊途同归,“自由市场不过是管制的一种特殊方式”[2];法律是政治的,普通法只有经过与政策性判断的隐蔽勾兑才能成为可能,自由主义法治是确定的规则之治而非权力之治是一个欺骗;“法官只是发现法而从不制定法”成为一个神话,法律中的自由裁量权无处不在,在任何一个看似中立的判决背后都隐藏着法官的个性偏好与意识形态偏见。因此,秉承价值相对主义立场,对司法过程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至关重要,法律不过是对法院判决的预测,法官事实上的所为即是法律,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法律与道德需要分离,或至少为了法律研究的目的而暂时地二分[3];而作为美国法律制度拱顶石的司法审查制度也变得问题重重,司法机构与纯粹行使权力的机构并无二致,司法权并不比其它权力更为高贵,因而无权对作为民选的立法机关的意志进行审查并决定它们是否符合宪法。面对现实主义法学的凌厉进攻,法律形式主义者所精心构筑的理论大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现实主义法学也很快暴露出自身的问题。首先,厉行新政的罗斯福总统的“填塞法院计划”在美国国内受到了普遍的反对,而为罗斯福新政制造理论根据的现实主义法学也因此而招致不满;其次,现实主义法学对普通法形式主义的批判虽然孔武有力,但其理论上的建构却不足以为司法实务提供具体的指导,在现实主义法学的影响下,法官变得更加主观武断,日益轻视逻辑和说理③,而随着极权主义在欧洲的兴起,“现实主义法学在道德与政治上的逻辑内涵似乎昭然若揭并令人恐怖”[4]。反对者通过把现实主义的理论与极权主义政府的行为相提并论,认为现实主义法学的价值相对主义立场与经验主义研究方法 “为迈向极权主义准备好了智识上的基础”,因而是一种“绝望的法理学”[5]。
在极权主义兴起的背景之下,在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激烈争论中,自由主义法治深陷合法性危机,现实主义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及对整个法治理念的挑战成为美国法理学中挥之不去的梦魇,而在后新政时代,重回洛克纳主义,将普通法与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相勾连已不可能,美国法理学必须要发展出新的理论来应对现实主义者的挑战并在与极权主义的斗争中坚定地捍卫美国的民主与法治。
二、法律过程学派的程序主义转向与“制度解决的原则”
为将极权政府与自由社会,法治与任意的权力行使区别开来,政治哲学首先找到了折衷的方法,发展出“相对主义的民主理论”。杜威认为,伦理哲学已经放弃了形式主义、自然法之类经由封闭体系演绎出可证明答案的努力,而相对主义也并非通往法西斯主义的必然道路。恰恰相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哲学绝对主义的傲慢成为法西斯者将价值判断合法地强加于人的藉口”。社会科学无法把握终极真理与目标的命题建立在如下的规范主义前提之上,开放民主的社会优于封闭极权的社会,价值相对而非绝对暗示着如下的真理:民主优于专制,多元与宽容优于压迫与服从,自由与开放的探究优于专断的立场和信仰的强加。相对主义的假设意味着没有哪一种价值选择可以一劳永远逸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教条。相反,价值判断只能是一种理论假设,要接受民主过程的检测,并在时代变迁中与时俱进。相对主义民主理论诉诸自由开放的探究程序,对不同的目的与价值兼容并包,从而接纳了不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想像,宽容了不同人群的多元目标追求与价值判断并最终宽容了人类本身的差异。二战以后,要求在社会问题上放弃实体性立场进而诉诸自由开放的探究程序的相对主义民主观成为了美国知识界的流共识。
受相对主义民主理论在智识上的启示,法理学也开始了程序主义转向④。富勒(Lon Fuller)在坚决反对法律与道德二分的同时,提出了程序自然法思想,把法治看成是八个程序方面的要求。富勒认为,程序自然法即法律中的内在道德,“关注的不是法律规则的实体目标,而是一些建构和管理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系统的方式,这些方式使得这种规则系统不仅有效,而且保持着作为规则所应具备的品质”[6]。富勒之后的五十年代的法学家们沿着程序主义方向继续迈进,将视角从对实体内容的批判性评估转向决定作出的过程,试图以实体与程序的二分来对现实主义法学进行批判性的接纳并以程序中心主义立场来超越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和法理学中“是”与“应当”的众说纷纭。一方面,他们承认现实主义者在批判法律形式主义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深刻理论洞见,法律是政治的,法律论证最终将诉诸政策分析,法院的所为经常也不过是政策的制定,因此,在实体层面上,无法找到解决争议案件的中立、确定的基础[2]567;另一方面,他们旋即将此让步局限于实体领域,并坚信在程序层面,中立的、非政治性的理性法律叙事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法理学中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所导致的胶着不下的僵局在于二者均犯下了共同的错误,即以为法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实体内容之上。但恰恰相反,我们对法律的首要依赖不在于寻找到终局的实体答案,而在于发现能获致可接受结果的适当程序。基于此种理论进路,五十年代的法学家们重新审视美国的法律制度,认为美国的法律制度最好是从程序视角来理解,所有的实体性规定都包含着程序性要求或者在形成的过程中深受其影响,程序是实体性规定得以创制与适用的前提,因而决定作出的程序在美国的法律结构中处于一种更根本的地位[7]。对于这样一种理论进路,哈特和萨克斯用“制度解决的原则”(principle of institutional settlement)来予以概括并把它作为法律过程学派的指导性思想,哈特和萨克斯认为,法律的核心思想在于制度解决的原则,“瓦解诉诸暴力的替代选择是建立稳定与和平的决定方法,制度解决的原则表达了如下判断,即只要决定是经由适当建立的程序而适当获致的结果就应当对全社会产生拘束力,除非并直到它被适当地加以改变”[7]4。“当该原则明确地得以运用,我们说法律‘是’当如此,并不再讨论其‘应当’如何。然而此处的‘是’与其说只是‘是’,毋宁说是一种特殊的‘应当’”[7]5。
“制度解决的原则”是法律过程学派的纲领性概念,它对该学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一方面,通过将视角转向程序,结束了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并完成了对现实主义法学的批判性接纳。另一方面,“制度解决的原则”在传统的理性绝对主义与现实主义者的价值相对主义之间秉承中间立场,将法的合法性建立在与实体分离的程序主义观念之上,从而将“合法的权力行使与非法的权力行使,法律统治的自由世界与权力统治的极权国家”区别开来,并将是与应当,法律与道德重新勾连在一起。此外,“制度解决的原则”对法的合法性论证视角与方法之转变也为法学研究设置了新的主题,美国的法理学开始从对形而上的客观性的追求转变成对可认知的客观性的追求。
三、法律目的、“制度能力”与法律过程学派的理论框架
在完成程序主义转向之后,法律过程学派着力建构其宏大综合性理论的框架。为此,法律过程学派首先对社会与法律进行了目的性预设。法律过程学派反对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即把法律视为使原子式个人为免于割喉式火拼而达成的协议。富勒认为“法律中的各个部分所追求的任何特定目标,都毫无疑问地反映了对促进和提升人类共存条件,公正、平等地调控他们生活中各种共同关系的指引”[8],哈特和萨克斯认为,“人类的相互依存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人类结成群体的目的在于保护和促进此种共同利益”,国家则是代表至上善德和总体目的的群体,保护和促进共同体成员的最高的、根本的共同利益[7]2,“法律与社会的共同目标相互联结”,致力于促进社会中被认可的有效目的,“法律是做一些事情,是一种目的性行为,是解决社会基本生活问题的持续努力”[7]148。
为“实现有效人类需求总体满足的最大化”,各类制度应在功能上分化并应相互协调,通力合作。法律过程学派确信,社会纠纷与制度性程序可以分门别类成固定的类型,“不同的程序和不同资历的人员总是适合于解决不同种类的问题”,“在异质的纠纷与多元的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功能性的关联,不同范畴的纠纷可以同与之相因应的各类制度契合无间”[2]594。法律过程学派的主旨是如何识别适当的程序来解决各类社会争议,法理学的中心问题是,对于特定种类的法律问题,应由“谁来决定”,“以什么样的程序来决定”,“在彼此冲突之际,哪一个机构的决定将获得至上的地位”。对于上述问题,法律过程学派发展了“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ompetence)这一概念来作出回答⑤。法律过程学派认为,以促进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体中的每一部分都有特殊的能力或专业技长[9],制度能力意味着应按照制度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来分配纠纷解决的方式,如果每一个有待解决的纠纷均能分配给最相适宜的制度,则法律程序的运作能够产生确定和正确的答案。制度能力成为法律过程学派建构其宏大综合性理论框架的基石。
(一)官方的裁决不过是“法律秩序金字塔”的纤细顶端,私人秩序(private ordering)被法律过程学派看成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化安排,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成为民主社会中争端解决和“社会调控的首要程序”[7]161。包括几乎全部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法和刑法等在内的绝大多数法律都是自我适用的,仅疑难案件才会递交官方[10],仅当私人自治的程序被发现匮乏之处,对私人行为的公共管制方被许可。而私人决定的程序和公共决定的程序又是相互作用的整体,每一个私人决定都潜在的由公共权力予以保障。私人自治的普遍化,在哈特和萨克斯看来是有效法律体系的标志,有助于促进人类有效需求总体满足最大化的目标⑥。私人秩序的制度能力在于“灵活性”和“去中心化”,面对动态社会无限复杂的问题和难以预测的多样化,私人秩序能契合无数个体的特殊需求。
(二)立法机关的功能在于政策制定,其制度能力在于民主。实体性问题包含着价值判断乃至社会偏见,因而必定众说纷纭,没有确定、中立的方法能对实体性政策差别予以评价评估,因而此类问题只能交由民主的立法过程来予以决定,付诸于投票箱中票数的计算。对于洛克纳案,法律过程学派认为,无论是基于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法律形式主义判决,还是基于进步社会福利计划的现实主义批判都不过是价值判断的强加,因而值得商榷,法院不得侵犯立法机构的制度功能,自由市场与经济管制作为一种价值选择只能由民主的立法机关在民主的立法过程中来完成,舍此别无它途。
而立法机关的决定也并非任意,其既受到多元主义民主的保障,更受制于良善立法程序的制约。首先,五十年代的法学家受到“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影响,相信多元主义民主所保障的立法过程能产生良善的公共政策,因为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基于不同利益立场的多元观念的相互竞争,经由公共商谈所展现的正反观点及对利弊的再三权衡,使得立法机关能够从善如流,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理性的选择和明智的决定。其次,“检验良善立法的最好标准是看其是否是良善立法程序的产物”[7]695,法律过程学派认为,“经验已经充分证实了程序与实体之间极端重要的关联,程序与拟行使的权力琴瑟相应必将产生明智的立法决定,相反,程序与权力方枘圆凿只会导致闭目塞听和糟糕的结果”[7]154,良善的立法程序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信息充分的程序,仅当全部相关信息已经获得后,重大的立法决定方可作出;2、慎思的程序,仅当立法者已对论据、观念与政策蕴涵进行充分讨论后,立法决定方可作出;3、有效的程序,对所有立法建议的处理应予以充分的时间,重要的议题应优先讨论并根据其重要性程度分配合比例的时间[7]695。
(三)司法的纠纷解决功能是有限的,司法只适合于解决“两造对抗”(bipolar)的案件。而在“多中心”(polycentric)问题中,各种因素交互影响,形成了一种网状格局,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作切合实际的考虑都要求斟酌其它大多数乃至全部问题,如同棒球队的球员布局,任何一个队员位置的改变都会对其他队员产生一系列的间接影响。在以对错为二元编码的司法程序中,多中心问题很难进行理性的说理并进而获得符合原则的解决方法(principled resolution)。哈特和萨克斯认为,司法不过是“法律程序中制度性活动的一种形式”,有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乃至私人自治较司法机关更能胜任对某些争端的处理。司法的制度能力在于“理性阐述”(reasoned elaboration),“法院由它在美国各机构所组成的结构中的位置……命中注定了它是理性的声音”[11],凡无法理性阐述的问题就不适合司法解决,理性阐述的程序不仅界定了法院的角色,将法院与立法和行政等分支区别开来,而且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施以了制度性制约。
毕书清把媒介融合的模式分为四个方面:技术融合、内容融合、渠道融合和结构融合。技术融合是基础,数字技术支持下,给多种融合提供了内在动力。平台的多样化使得内容的呈现也变得多样化,报纸上的内容呈现不能满足网页新闻的要求,内容必须要适应融合。渠道融合指的是不同领域下的传统媒体之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共享合作。结构融合指的就是媒介内部组织融合以及媒介之间所有权的融合。本文对渠道融合和结论融合不过多阐述。只探讨媒介融合对教育的意义。
针对现实主义者对司法论证过程的怀疑与攻诘,哈特和萨克斯等法律过程学派的学者认为,虽然现实主义者在批判法律形式主义的过程中展现出深刻的理论洞见,但却将司法意见中合理化过程的功能不当地简化了,并无视理性阐述的过程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在法律过程学派看来,首先,论证过程是展现法官专业技长的工具,法官未能就判决给出理由不能满足公众评价其是否克当此任的要求;其次,司法推理中的论证揭示了美国社会与极权主义政体的根本区别,美国的法律致力于与民众理性公正的观念契合无间,而极权主义的法律不过是官员的命令。哈特断言,如果真若现实主义者所言,法官的所说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其所为,那么“可怕的结论将尾随而至,理性与论证,对正义的有意识的追求都是徒劳无益的”[12]。自1951年起,法律过程学派的主要学者就“理性阐述”的要求在《哈佛法律评论》的“前言”(Forward)栏目上持续撰文予以说明。按照怀特(Edward White)和温策克(William Wiecek)等人对上述文章的归纳,理性阐述包括如下四个层次的要求。首先,法官的判决应当说理;其次,理由应当详尽连贯;再次,理性阐述应臻于“共同思想的成熟”;最后,法院应“深入探究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和社会共同目标的合理蕴含”,充分证明其判决表达了当代社会的最终价值偏好。基于上述认识,法律过程学派对法院的判决进行了诸多的批判,“把一面放大了瑕疵的镜子举到最高法院面前”。
而对司法“制度能力”和“理性阐述”的强调并没有导致极端的司法抑制。相反,法律过程学派认为,法院负有促进法律发展的任务,在制定法汗牛充栋的当代,对制定法的解释是法院职责之所在。在制定法的解释上,法律过程学派要求理性阐述制定法的目的,既反对平白意义(plain meaning)的文本主义解释方法,又对纳丁等现实主义者对意图主义方法的批判作出了回应⑦。首先,法律过程学派认为,每一部制定法都应毫无疑问地被理解成是一种目的性行动。“制定法没有一个清晰目的的思想是与法的理念格格不入的,因而不能被接受”[7]1124,制定法总应被当成是“理性人在理性地追求理性的目的”[7]1125,因此,妥当的制定法解释方法首先是对这些目的的确证或添加。其次,制定法的目的不仅包括某个当下的目的,而且包括特定的制定法如何方能被置入到法律体系整体中去的更为精致的目的[7]1380,法院在制定法的解释上应发展出连贯的方式对此作出理性的阐述。最后,制定法的语言并不只存在唯一的意义,法院也并非只能对制定法作字面意义上的阅读与理解,但法院对制定法的解释又不能是任意的主观偏见。法律过程学派认为,目的维护了制定法语言的完整性,赋予制定法的文本以确定性,正是对制定法目的进行理性阐述的要求,赋予又有效限制了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并使得司法机关能最大限度地尊重立法机关的决定。因此,在制定法目的确定以后,法院应按照“最能实现制定法目的的方式来解释制定法的语词”,但应确证其“并未超越制定法语词所能承载的意义范围并不违反任何已清楚陈述的既定政策”[7]1374。法律过程学派对制定法的目的主义解释方法“既赋予解释者更新、发展制定法的任务,以合作者的姿态参与公共政策的生产过程,又竭力避免非民选的司法机关作出争议性的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13]。
(四)行政机构的制度能力是其“专业技长”(expertise)。在新政与后新政时代,随着经济与社会导控任务的日益复杂化,立法机关在规制经济活动时已疲于应对,对于具体而实际的问题只能泛泛而言,而司法机关限于自身的制度能力也常左支右绌,颇多力有不逮之处,因而数以百计的行政机构被建立起来用以执行爆炸式增长的经济管制方面的法律。行政机构被寄以厚望不仅在于行政程序较司法程序相比的诸多便利,更在于其“专业技长”这一制度能力。在现代管制国家,管制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性的而非对错问题,是实用主义的判断而无关抽象的原则,此类问题应付诸专门性的知识和经验来予以解决。兰迪斯(James Landis)认为,随着管制的兴起,对专业技长的需要渐成主导,管制某一行业的策术要求具备有关其运作细节的知识,随其指示的条件转变要求的能力[14]。弗兰克福特也认为“中立的专业技术是社会管制的引擎”[15],公共管制若能卓富成效,必须倚重一个高度专业和中立的常设性机构,承担将立法机关制定的宽泛政策予以实施的任务[15]145。专业技长来自于行政机构在管理特定行业时与具体问题朝夕相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专门知识与经验,因而此种专业技长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所无法具备的。法律过程学派的学者充分吸收了兰迪斯等学者对行政程序的认识,认为在制度解决的原则之下,一个行政机构的决定应获得尊重,只要该决定按照专业技长这一制度能力属于其主管的范围并遵循了“适当建立的程序”。
四、中立原则与宪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
按照法律过程学派“制度能力”的要求,民主的试验场是实体性价值的最终判断场所,政策选择只能由民主的立法机关去完成,而司法造法则僭越了立法机关的制度功能。既然如此,那非民选的司法机关为何能对立法机关的决定进行审查并决定其是否符合宪法呢?这是与司法审查如影随形的“反多数难题”⑧,也是法律过程学派基于“制度能力”这一概念建构其理论体系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传统的司法审查理论与法律形式主义所捍卫的自由主义法治相呼应,认为司法审查的功能在于厘清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限,保护一个免受立法机关实质性干预的私权领域,而司法审查所保护的自由私域的自治性、中立法与客观性又将司法审查本身正当化。但现实主义法学对此种公私二分的实体性理论已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认为不存在与公共权力相分离的私人领域,从而动摇了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基础。
在1959年4月7日的哈佛“霍姆斯讲座”中,威克斯勒作了题为《迈向宪法的中立原则》的演讲,对现实主义法学有关司法审查的质疑与挑战作出了回应,也完成了法律过程学派理论体系建构的最后一步飞跃。威克斯勒从批评汉德(Learned Hand)的司法审查观出发,坚定地主张联邦最高法院既有权力也有责任来审查包括民主的立法机关在内的其它政治分支所作决定的合宪性问题。但威克斯勒同样坚定地拒斥公私二分及经由私人权利来决定司法审查之恰当范围的实体性理论,认为此种进路必然与试图阻止或促进的利益纠缠不清,从而导致法院成为实现既定结果的“赤裸裸的权力机关”。威克斯勒认为,虽然司法审查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具有不可回避的政治性,都需要在竞争性价值或欲求之间予以取舍”[16],但仍有恰当的方式来审查其合宪性,“至关重要的并非问题的性质,而是法院能有效地给出的答案的性质”,法院应作为法院而行为,即将其决定建立在原则之上而非权力之上,政治过程可以是功利的结果主义的,乃至于可以别有用心地促进特定的实体利益,但“司法过程的主要构成正是在于它必须真正是原则性的”[16]15。原则首先是“理性”的[16]19,任何立法或行政机构都没有义务因其职能的性质而必须通过理性的解释来支持其价值选择,但这种解释却是司法行为所固有的,如果司法机关没有充足的理由去推翻联邦政府其它分支或州政府的价值选择,则这些选择就是合宪的,必须受到维持;原则还是“中立”的与“普适”的[16]19,决定的基础在可适用的其它情境中也应被遵循,而不应像政治家们那样,经常采用某些论据来捍卫特定的结果,但在这些论据可以适用的其它场合,又不愿给其相同或近似的份量;虽然法院只决定或应该决定他们眼前的案件,但法院处理案件的每一步都应建立在超越个案的具体情境与当下的特定结果之上,而不能只是出自于权宜的考虑。如果意见局限于个案的事实,而推理又对相关或类似情境的处理少有裨益,则不能满足普适性的要求。威克斯勒就宪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所提出的中立原则的解决方法体现了法律过程学派的主要理论立场,如程序主义取向,司法的制度能力,理论阐述的要求等。
五、结语:评价与启示
二战以后,美国社会曾一度形成普遍共识,那些竞争性的价值纷争似乎已随风而逝,当时多数美国人以为,美国社会各阶层“都在一个和谐的政治、智识和经济体系中拥有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法律过程学派无疑因应了此种对现实的乐观判断。然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支撑法律过程学派的政治经济条件急剧变化,其赖以存在的理想社会图景渐趋幻灭,法律过程学派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开始坍塌,其对现实主义法学所作的批判性回应逐渐丧失了吸引力。民权运动的兴起不断暴露出美国民主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美国社会各阶层并非都各得其所,种族歧视是如此得严重,作为法律过程学派程序主义转向前提的多元主义民主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保护那些“离散而孤立的少数族裔”,尽管斯通(Stone)大法官在三十年代末就已经在那个著名的“脚注四”中作过善意的告诫,但法律过程学派的理论家们似乎都选择性地遗忘了,哈特和萨克斯的那本超过千页的煌煌巨著甚至从未曾关注过种族平等之类的问题,其苦心孤诣的程序主义转向旨在小心翼翼地逃避对实体价值的任何承诺,因为洛克纳案的经验已经提醒他们彼处危险重重。然在六十年代普遍共识丧失,冲突与对抗不断加剧及对多元主义民主的信念已明显动摇的政治背景下,法律过程学派的保守主义立场和要求将实体性价值剔除出政治合法性判断要件的主张已经很难获得普遍的认同了。而“制度解决的原则”和基于“制度能力”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在批评者看来不过是一种“程序实证主义”,其在表面上弥合了“是”与“应当”的裂缝,但事实上却放弃了对现存规则及各类制度安排之正当性的质疑与追问,强调的不过是对现状的默许和服从,对现有权力格局的维护和将既定财富分配制度合法化的努力,只不过法律过程学派将这一切都披上了“适当程序”的外衣。但华服却越来越似皇帝的新装,到七十年代,哈特关于“不断增大的大饼”(expanding pie)的善意想像随着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的出现也无以为继了,支撑法律过程学派的现实经济条件遂不复存在。无须追问实体性价值判断,不用对分配正义问题进行独立评估,只需不断合作,戮力同心,大饼就会不断变大的预言成为了欺骗;而在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即便是最小份额持有者,其欲求也可不断获得满足的许诺已经彻底成为画饼,那些处境不利的亚群体显然对经由“适当程序”所获得的结果极为不满,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要求平等对待,而且强烈要求改革现有的财富分配方式以实现分配正义,而法律过程学派的程序形式主义强调的是对既定立法结果与行政决定的服从及司法的消极抑制立场,显然无力回应此种经济诉求。而更令人尴尬的是,自沃伦主事联邦最高法院以来,法律过程学派所鼓吹的那些司法技艺,除制定法解释者以外,就从未曾获得过重视。沃伦法院秉持积极能动的司法立场,在公民权利保护方面频频出手并颇有斩获,但在布朗案等标志性案件中,沃伦法院却并未进行过理性的阐述,或至少,其论证与说理并未臻于法律过程学派所要求的标准,因为沃伦法院自以为代表了美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以至于即便是哈特、萨克斯与威克斯勒等人,也无法从结果上否认沃伦法院判决的正确性。这群批评者,也曾殚精竭虑地要从过程上将布朗案正当化,但即使是威克斯勒力倡的“中立原则”也力不能逮,于是吊诡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诉诸理性与原则却不能将那些可欲的结果在法律上正当化,那强调理性阐述的司法过程又有何益?而某些结果或价值的正当性是如此地不证自明,那又何必再不辞劳苦地去从程序上予以证明?而沃伦法院信奉的显然是结果高于过程,因而其早早扔掉了华服,褪去了罗衣,向着“简单正义”的方向一路狂奔。即便如此,在美国学界,法律过程学派的许多重要理论立场至今仍受重视并成为众多学者思考法律问题时的背景性知识和理论创新的起点,法律过程学派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概念工具,如“制度能力”、“理性阐述”等被学界广泛接受,法律过程学派影响了美国的宪法理论、行政法理论、制定法解释理论等多个学科和领域的发展,一大批学者,如比克尔(Bickle),伊利(Ely),夏皮罗(Shapiro),斯图尔特(Stewart),波斯纳(Posner),卡拉布雷西(Calabresi),德沃金(Dworkin),埃斯克里奇等,都从法律过程学派中受惠良多,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常被看成是“新法律过程学派”的代表人物。
法律过程学派的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有启发和参照意义。例如其认为各种法律机构和制度在类别上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差异,而是代表着社会追求其根本目标时的各种替代方法的思想及由此而来的多元主义纠纷解决思路显然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与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相契合;而其对司法制度能力的强调为认识时下“中国式能动司法”的可能性与正当性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对司法理性阐述过程不遗余力的鼓吹对中国各级法院改革法律文书写作,增强裁判的论证与说理成份等也大有裨益。更为重要的是,法律过程学派还为中国法治建设的程序主义进路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上的参照。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季卫东先生为代表的新程序主义者提出把程序作为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的核心和制度化基石的思想,特别强调中立、自治程序的理性选择功能、多元价值整合与共识形成功能、决定的正当化和秩序的正统化功能以及程序中蕴藏的“反思理性”的重要性⑨。虽然新程序主义的代表人物季卫东先生从未从法律过程学派中寻求智识上的支持,但新程序主义与法律过程学派在旨趣上却颇多近似之处。尽管应当承认新程序主义理论的积极作用,但法治中国的程序主义进路却不能绝对化,否则容易陷入程序浪漫主义的陷井。而法律过程学派兴起与衰落的历史则揭橥出经由程序的正统化策略(这也是国内新程序主义的核心主张)具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和明显的反事实特征。而在笔者看来,程序只在相当有限的程度上生产合法性,程序是结果正当性与秩序正统性的微调节器,而不是万能的大功率转换机。程序微调节功能的有效发挥以基本实体正义的存在为前提,当基本实体正义上的偏差尚未逾越社会可接受的程度时,程序能增强结果的正当性和秩序的正统性,而一旦基本社会秩序饱受诟病或在具体问题上经由程序运作所产生的结果并不能符合社会大众对基本正义的判断,则此时程序不仅无助于结果的正当化和秩序的正统化,反而极容易蜕化成一种保守乃至压制的力量,而许霆案、张海超案及“天价过路费”案等所激起的大众舆论的强烈反弹皆是例证,此一点,显然无论中西,都概莫能外⑩。而新程序主义者希冀经由程序中的反思理性来校正错误的愿景在中国既有的法治实践中也明显缺少经验性支撑,例如对上述案件中的错误进行修正的路径主要遵循的还是一种“压力与应对”机制,程序外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或许,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三峡”,更为迫切的仍然是直面现实并在实体性价值上勇敢地作出选择,而某种卡理斯玛型力量的存在也未必完全没有合理性。
[注 释]
1 法律过程学派在二战前后汇聚了一批具有哈佛法学院背景的学者,哈特和萨克斯是法律过程学派的集大成者,其著作《法律过程:法律制定与应用中的基本问题》(The Legal Process:Basic Problems in the Making and Application of Law)是法律过程学派的经典文献,该书的雏形是哈特在哈佛的教学讲义,在1956-1958年的整理过程中四易其稿,曾命名为《美国的法律体系》(American Legal System),试用本(tentative edition)完成于1958年,但迟至1994年才得以正式出版。在此之前,该书已声名遐迩,长期以复印本的形式流传于学术界并被众多法学院当作教材使用。
2 在法律形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法院严格维护公私界限,如法院严格限制立法对垄断的控制,严格限制立法对财产权或雇主合同自由的干涉,法院判决支持“黄狗合同”(yellow dog contract)等。
3 例如对于United states v.Butler一案,批判者指责Robert法官的论证是“一个真正的逻辑上的灾难”。见COLLIER,Judicial Bootstraps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Clause,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1936(4):277.
4 程序主义理念在美国法理学中一直存在,参见DUXBURY NEIL,Faith in reason,the process tradition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Cardozo Law Review,1993(15).只是到了法律过程学派,其重要性才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5 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最早提出和发展了“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ompetence)这一概念。见ESKRIDGE WILLIAM,FRICKERY PHILIP,The Making of Legal Process,Harvard Law Review,1994(107):2033-2034.WIECEK WILLIAM,American Jurisprudence after the War:Reason Called Law,Tulsa Law Review,2002(37):869.
6 公、私二分在剔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后被法律过程学派整合进“制度能力”这一概念之中。在哈特和萨克斯看来,私人安排和公共调控均服务于将“人类有效需要总体满足最大化”的目标,与法律形式主义不同,哈特和萨克斯并不试图将私域凌架于公域之上并将其作为一种规范性事实。相反,哈特和萨克斯将私域作为其理论起点在于社会争端首先诉诸私的方法可能获得最好的处理这一功能性原因 (functional reason)。见ESKRIDGE WILLIAM,PELLER GARY,The New Public Law Movement:Moderation as a Postmodern Cultural Form,Michigan Law Review,1991(89):720.
7 纳丁曾对制定法解释中的意图主义方法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见RADIN MAX,Statutory Interpretation,Harvard Law Review,1930(43).纳丁的批判引发了制定法解释领域较早的一次方法论之争。
8 耶鲁法学院的亚历山大·比克尔(BICKELALEXANDER)教授在其1962年出版的《最小危险的部门》一书中首次使用“反多数难题”(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一词来指称司法审查与美国民主体制之间的矛盾。
9 季卫东力倡新程序主义的代表性作品包括《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等。
10 许霆案、张海超案及“天价过路费”案激起了大众舆论的强烈反弹并非因为未遵循应当适用的程序,而是经由程序运作所产生的结果明显与社会大众对基本正义的判断不符。
[1]COHEN FELIXF.Transcendental Nonsense and the Functional Approach[J].Columbia Law Review,1935(35):821-824.
[2]PELLER GARY.Neutral Principles in the 1950’s[J].University of Michigan Journal of Law Reform,1988(21).
[3]LLEWELLYN KARL.Some Realism about Realism:Responding to Dean Pound[J].Harvard Law Review,1931(44):1236.
[4]PURCELL EDWARDE.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Theory: Scientific Naturalism & the Problem of Value[M].Kentucky: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3:172.
[5]MECHAM PHILP.The Jurisprudence of Despair[J].Iowa Law Review,1936(21):692.
[6](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114.
[7]HART HENRY,SACKS ALBERT.TheLegalProcess:BasicProblemsin theMakingandApplicationof Law[M].Eagan:Foundation Press,1994.
[8]FULLER LON.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J].Harvard Law Review,1949(62):621.
[9]ESKRIDGE WILLIAM,FRICKEY PHILIP.The Making of Legal Process[J].Harvard Law Review,1994,107:2033.
[10]DUXBURY NEIL.Faith in Reason:The Process Tradition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J].Cardozo Law Review,1993(15):659.
[11](美)亚历山大·比克尔.最小危险的部门[M].姚中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7.
[12]HART HENRY.Holmes’Positivism:An Addendum[J].Harvard Law Review,1951,64:933.
[13]刘翀.论目的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以美国法律过程学派的目的主义版本为中心的分析[J].法律科学,2013(2):33.
[14]LANDIS JAMES.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M].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1938:23-24.
[15]FRANKERFURT FELIX.The Public and Its Government[M].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1930.
[16]WECHSLER HERBERT.Toward Neutral Principle of Constitutional Law[J].Harvard Law Review,195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