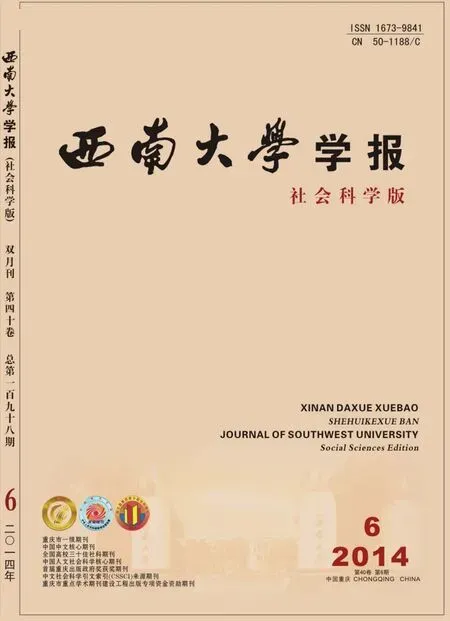浅析世界舆论对肯尼迪核试验政策的影响
温 强,吴 建 华
(1.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2.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20世纪50年代末,美苏关系时缓时紧,核试验是双方针锋相对的重要领域。作为世界和平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国民众始终呼吁签署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国际公约,1961年以开拓内政外交“新边疆”口号上台的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该问题上面临着新的考验。学术界以往大多从他分裂中苏和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角度来分析其核试验政策,但对舆论因素所发挥的影响却未能引起应有关注。*相关论述参见Noam Kochavi, A Conflict Perpetuated: China Policy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 Connecticut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2.;朱明权:《部分核禁试谈判过程中的“中国因素”──历史的回忆与思考》,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詹欣:《试论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评估与对策(1961-1964)》,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对肯尼迪而言,舆论形象几乎就意味着一切”,他认为世人对美国国力和国际形象的认识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冷战国际地位[1]49。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历史事实,笔者认为对肯尼迪外交和防务政策中的舆论影响因素决不应忽视。本文主要根据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新近解密涉及舆论的档案,以美国新闻署当时所作的民意调查为中心,解读世界舆论与肯尼迪核试验政策之间的关系,及美国当时如何利用舆论因素既维持了自身核威慑的可信性,又将世人指责的矛头引向苏联的决策过程。
一、肯尼迪在核试验问题上的世界舆论观
美国是最早开始国外民意调查的西方国家之一,而肯尼迪政治观形成的时期正值此事被逐步引入美国外交领域并日益显露重要性之际。肯尼迪对世界舆论的重视早在入主白宫前就已形成。这与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有关,也同他理想主义政治思想密不可分。他任内的美国外交、防务主张无不透露出世界舆论作用的影子,核试验政策即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案例。
20世纪初,舆论调查在美国起步并被逐渐引入政治领域,盖洛普(George Gallup)领导的调查机构于1936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大选民意测验[2]162-163。二战期间,舆论调查由国内拓展到国外,调查结果迅速反馈回政府相关部门,成为外交情报来源之一,用以引导广播、报刊等方面的宣传活动。它在美国对德日两国的轰炸政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背景分析作用[3]174,176。二战后,美国的世界舆论调查方式更加多样化。此种调查主要用于配合美国发动的冷战攻势,并成为美国外交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而负责舆论调查的部门则由战时情报局转归国务院下属的一个专门机构。该机构1952年被命名为美国国际新闻署。第二年,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正式将其定名为美国新闻署。为最大限度预防主观偏见和在数据上弄虚作假,同时为政府外交决策提供客观信息,截至50年代初,美国的世界舆论调查已逐步形成一套比较标准的操作规程[4]479。适时的调查结果日益明显地作用于核武器发展决策。
当1954年3月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试验大当量氢弹的消息被披露后,世人出于核试验对人体和环境损害的关注以及对核战争的恐惧,纷纷要求美苏谈判禁止核试验。但美国军方不顾反核声浪,横加阻挠1958至1960年的美英苏三国核禁试谈判,致使全球首轮核裁军无果而终。美国的全球声誉因此严重受损。1960年,美国新闻署在10个国家围绕美国国力及国际形象的民意调查显示:苏联导弹开发技术已悄然领先西方,其国际声望也反超美国。由于美苏“导弹差距”观点对共和党大选不利,艾森豪威尔下令减少世界舆论调查活动,声言“美国充满活力,必将拥有光明未来”;而全力冲刺总统宝座的肯尼迪对此却看法相反。他认为世人对美国在上述领域的差距完全一清二楚[5]。《纽约时报》于是年10月25日以此前多份民意测验为依据,在头版刊登“经调查,世人认为苏联更行”一文称:世人觉得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已对西方构成挑战,而美国并未就此做出回应;当美国人仍迷信自己国家拥有强大实力之际,苏联已不知不觉缩小了同美国的经济差距,并在军事领域赢得领先地位[6]。这篇文章同肯尼迪对舆论的认识口径完全一致,而对共和党“美国国际地位和声望处于历史最高峰,苏联则处于最低谷时期”的大选言论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7]。
50年代中后期,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后的苏联在与美国缓和关系的同时,也与其展开了更广泛的争夺;西欧和日本随着经济恢复和发展,普遍要求摆脱美国控制,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遭到了严重挑战,其在世人心目中的威信急剧降低。肯尼迪认为这种舆论趋势对美国的消极影响非同小可,“如果世人认定美国正在走下坡路而苏联在上行;如果世人觉得美国的黄金岁月已是明日黄花,而苏联却掌握了未来发展方向,那希望取得胜利的人们将离我们远去,投入到苏联、中国的怀抱”[8]。艾森豪威尔不愿正视已开始出现的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实际,还授意美国新闻署发表一篇美国在全球影响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报告,但遭拒绝[9]115。1960年的世界舆论对美国空间探索、核军备、国际形象等方面的低认同率帮助肯尼迪赢得了大选,但这种低认同率却也成为其任内施展外交抱负的障碍。
从肯尼迪的政治思想分析,即使外界对美国的认识并未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他同样会对世界舆论重视有加。他早在1940年即以《英国为何沉睡?》为题出版了自己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认为英国在二战初期实行的“绥靖”政策实际是英国公众对政府施压的结果[10]2。他任参议员时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自己的世界舆论观,力主通过分析和判断一国民众的意愿,可大致推测出该国政府将做出什么外交决定。综观其整个政治生涯不难发现,肯尼迪更愿将冷战视为围绕世界舆论而展开的斗争:“冷战是一场了解和征服大自然的战争,宏观广致宇宙,微观细及人的内心世界。”[11]对他而言,美国所处的冷战不利局面以及阻挠核禁试谈判而受损的国际形象无异于双重挑战,变化了的国际格局自然会作用于其核试验政策。据他手下官员回忆,总统在该问题上对世界舆论动向始终十分关注[12]56,58,256。他在总统任内采取了诸多系统手段去感知舆论脉搏,并以此作为外交和防务决策的必备依据。
关于肯尼迪的世界舆论观,现在可从相对较为特殊的众多档案,比如肯尼迪图书馆数量不菲的民意测验报告中窥见端倪[9]77。他非常信服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就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关系的评价:“我们既不可跟着群众跑,也不可加以嘲弄,而是为群众和我们自己寻求稳健的建议。”[13]258美国学者宁柯维奇(Frank Ninkovich)指出:肯尼迪的外交风格可以理解为威尔逊遏制政策在新时期的再现,是一种倚重于世界舆论来实施遏制战略的“新威尔逊主义”[12]192。他十分清楚提升美国国际形象,尤其是赢得新兴民族主义国家民心对获取冷战胜利的特殊重要性,这对美国而言并不亚于一场实战。他担心苏联在空间以及核领域的成就不仅会在军事上赢得巨大优势,而且还会给世人留下共产主义代表未来世界潮流的印象[14]349。肯尼迪据此认定,只要自己在世界任何地区、任何问题上表现软弱,都会对美国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正因为他对美国国际形象如此重视,所以像在核试验等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军事领域,自己无论如何不能示弱和落后[12]272,302。受冷战多米诺骨牌理论左右,世界舆论在其核试验政策中的分量尤显突出。
肯尼迪也像威尔逊一样清楚意识到,推动和塑造舆论的能力是总统外交权力的重要来源。大选期间他对世界舆论的倚重,已预示着舆论因素必将在其当政后的外交、防务决策中占据重要地位。面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他上任后立即任命弗里(Lloyd Free)和戴维森(Philips W. Davison)组成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包括裁军、核禁试等涉及美国安全利益的各类问题提出决策参考意见。该委员会建议:政府处理国际事务时应充分尊重亚非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精神,对世界舆论善加引导和利用远比采取仅仅反共的姿态更有效,应对铁幕控制或影响的地区进行更积极、更富创造性的心理战。鉴于核问题当时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肯尼迪指示各部门在考虑美国具体核试验政策时,应主动寻求美国新闻署的建议[9]121,142,从而明确将世界舆论与自己的核试验政策联系在一起。
二、美国新闻署对核试验政策的建议
肯尼迪巧妙借助世界舆论达到权力顶峰,他在施政过程中对其同样寄予无限期望。但60年代初世人对美国国力及国际形象的认识并不令他乐观,如何借核试验问题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成为其任内的关键问题。为此,他大大提升了美国新闻署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为回应共和党对民主党政府是否恢复了世人对美国信心的诘问,肯尼迪多次表示绝不隐瞒涉及美国国力及国际形象的民意测验数据,这些数据将在一定时期后向外界公布[14]203。他于1963年宣布,民心向背并不存在保密问题,即便涉及敏感问题的世界舆论调查结果也将于数据出来后的两年内公开[9]77。他广泛征集如何借核试验问题提升美国国际形象的建议,并要求新闻署新任署长穆罗(Edward R. Murrow)为相关部门提供外国公众对该问题态度变化的追踪报告,用以引导和塑造有利于美国的世界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的宣传机器必须和我们的核子库一样随时做好准备,比以往得到更充分的利用。”[9]121,145可见,即使没有来自政敌和新闻媒体的经常提醒,肯尼迪仍旧会保持对世界舆论始终如一的关注,他不希望公众昔日在核试验问题上对前总统的指责和失望同样落到自己身上。
60年代初是美国新闻署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期。穆罗深得肯尼迪重用。“随着岁月的流逝,总统对穆罗和美国新闻署的赞赏之情与日俱增;该机构除每周定期向他提交报告外,穆罗与白宫之间还有一部被肯尼迪称为‘燃烧的火炬’专线电话。在讨论外界对美苏核试验政策立场的看法时,他经常与穆罗交换意见,遇到不清楚的专业词汇或其他疑问时就直接与后者取得联系,并且还经常要求取阅这方面的所有文件资料。”[9]128-129尽管舆论因素在肯尼迪核试验决策过程中不可能独占首要角色,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1961年夏季开始,美国新闻署的官员几乎参加了政府所有的重要核政策会议[15],足见该机构及其舆论报告与肯尼迪核政策之间的联系确实非同寻常。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新闻署围绕核试验的全球民意测验显示:尽管多数国家对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部署总体上抱积极印象,但也同时对美苏在核武器、常规武器领域的军备竞赛感到不安。它向总统提交的第一份世界舆论调查报告指出:“美国国际声誉虽整体好于苏联,可世人心目中美国的积极形象大多属于软国力范畴。许多地区的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如需在美苏之间选择的话,与美国更为一致,美国更值得信赖。然而他们觉得苏联在空间计划及核军备方面依然领先于西方。当被问及再经过25年发展,美苏中三国谁将成为最强者问题时,世人的观点则差异较大,各种复杂看法莫衷一是。”[16]褒贬参半的美国国际形象,造就了肯尼迪双管齐下的核试验政策心理。
大选期间,肯尼迪一再以所谓“导弹差距”诋毁共和党的公众形象并赢得大选,但恰好是民意这柄双刃剑也成为其施展外交抱负的障碍。为凝聚国内外民心,他上任后虽反复澄清“导弹差距”的失实之处,但世界舆论仍普遍认为美国军事上不如苏联强大。美国新闻署基于一系列民意测验判断,美国国力形象在1961年降至战后最低点[9]141。穆罗甚至还危言耸听地称,西欧民众也感觉苏联军事实力胜过美国,美国国力与几年前相比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肯尼迪首次把舆论调查范围延伸到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可来自这些国家的民意测验同样显示美国国际形象堪忧。伊朗、印度民众支持苏联的程度远大于美国,这令他非常震惊[16]。鉴于肯尼迪的冷战战略十分看重上述国家,他认为美国国力和国际形象的低认同率,将对美国掌握冷战主动权构成致命冲击。为此,他当年不无忧心地特意致函国会称:“冷战不仅涉及生命和边界,而且也涉及人的心灵。”[17]397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McGeorge Bundy)在国会作证时也说:“美国必须有所作为以扭转舆论颓势,只有这样,美国而非苏联代表了世界发展潮流的看法才会不言自明。”[18]肯尼迪在核试验决策时,一只眼睛盯着中苏举动的同时,另一只眼睛总是盯着世人对美国国力和国际形象的认识。
穆罗十分清楚肯尼迪的决策心理,即便没有专门敦促,涉及核试验话题的舆论调查材料总能及时摆到总统案头[19]。肯尼迪图书馆新近解密的档案显示,按照肯尼迪的要求,美国新闻署所做的全球民意测验报告几乎都是在下午4点左右准时送达白宫[20]。此类报告往往不受体例、范围局限,对世界舆论的前瞻性分析通常涵盖其间,而这正对肯尼迪的胃口。穆罗的建议在肯尼迪对美国核试验政策的公开表态,以及与苏联、英国的核禁试谈判中均被派上了用场。不管后世学者如何解读世界舆论同肯尼迪最终核试验政策之间的关系,众多这类档案至少表明:它们是应总统要求而写,并是其核试验决策时最密切关注的情报来源之一[21]。
1961年,美国新闻署调查研究办公室主任克雷斯比(Leo Crespi)在《公众舆论季刊》上撰文,重点阐述了一国真实和假想实力日益突显的区别,“比之于美国客观政治、经济力量,其在核试验问题上姿态的重要性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外交、防务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于遏制,这与其说同军事有关,还不如说它根本上是一个心理问题,美国军事能力与军事遏制姿态在世人心目中的印象同等关键”[22]116。真实和假想实力的区别,正是困扰肯尼迪核试验政策的结构性难题。就像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说:“他国民众对美国军事实力的印象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决不应向共产主义示弱。毫无疑问,只有当我们的军备足够充足时,才会在世人心目中树立起有利于自己的形象。”[23]38但世界舆论对美国国力和国际形象的低认同率与他更多赢得盟国和中立国家信任,并掌握冷战主动权想法完全背道而驰。
肯尼迪分析,部分出于世界舆论对苏联国力最新的积极认识,苏联领导人才敢在柏林等地放手采取更大规模的好战行动,这将极有可能分化大西洋联盟[24]359。其战略顾问指出,政府有必要改变美苏在世人心目中的不同国力形象,核试验就是提高对美认同率可资利用的最佳手段。兰德公司还专门提交“姿态选择的政治含义”报告,力主美国应加强军事实力,借此最大限度地在国内外得分[25]73。立足于美国新闻署的建议,肯尼迪在做好履行美国军事承诺准备的同时,以核试验政策为契机树立美国强大、负责任的形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提升美国国力和负责任形象的核试验政策
争取扭转美国因阻挠1958-1960年核禁试谈判而受损的国际形象,并提高世人对美国军事实力的认同是肯尼迪核试验决策时两个并行不悖的目标。正因为如此,他在核试验问题上所能做出的让步必定具有明显的有限性。
就如何利用核试验问题提高美国国际形象及世人对美国军力的认同,穆罗1961年8月提交的报告指出:“自1960年中期美欧首脑巴黎会议以来,西欧对美国承诺的信任度有所提升,这有利于巩固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但它们对美国军事实力的信心并未明显回升,对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前景也存在隐忧。”[26]他认为肯尼迪上任后重塑更积极的国家形象虽取得了某些进展,可在至关重要的军事尤其是核武器领域却未能根本扭转世界舆论,包括盟国民众的对美悲观看法。美国新闻署即使到1963年仍判断:西欧民众即便认为美国总体军力已从1961年的谷底走了出来;但他们依然觉得苏联比美国拥有相对优势[27]。尽管穆罗坦承:“当时调查机构的分布并不足以保证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民意评估,翻译和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也有可能妨碍对世界舆论做出精准定位和预测。”[16]但类似报告无疑强化了肯尼迪固有的冷战多米诺骨牌意识,促使他在核试验问题上对共产主义采取强硬态度。
肯尼迪深知自己的不示弱心理与希望核裁军的民意相违,但这是他试图影响并争取对美国军事实力感到悲观国家民众的必然选择。当1961年8月30日苏联宣布暂缓核试验到期之际,肯尼迪的高级幕僚,特别是军方代表力陈保持美国核优势的重要性,应马上采取对等举措,即便这意味着逆舆论潮流,必要时需打击苏联核试验场也在所不惜。但穆罗却反对立即恢复核试验,因为这不利于孤立共产主义阵营,也将触犯反核的盟国舆论,进而动摇美国巩固在西方领导地位的机会[28]149-150。他9月1日专门向总统提交备忘录称,“全球主要新闻媒体纷纷谴责苏联恢复核试,最近一些未曾透露身份的评论预测,美国将马上做出与苏联相同的反应。我觉得假使政府果真那样做对自身并无好处,时间对我们而言仍然有利”[29]。在是否以及何时恢复核试验问题上,肯尼迪面临以军方和美国新闻署为代表的两类相反意见。
肯尼迪的多数军事顾问始终主张:为促进自身核能力,美国有必要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否则苏联就有望在该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在军备竞赛中领先。国防部认为此举尽管不是确保美国遏制政策成功的根本途径,可一旦遏制失效,类似试验仍有利于减小美国遭受的形象损害。与军方不同,穆罗明显担心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可能给美国带来的舆论冲击。他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抗议苏联的好战举动,总统如采取相同作法,世人无疑也会将愤怒的矛头转向美国。为争取世界舆论,我们最好避免步苏联后尘;苏联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已使其在拉美的影响大大削弱,即便美国采取的是对应防御举措,也会被认为是激化军备竞赛的步骤。”[30]直至肯尼迪遇刺,美国新闻署提交的报告总体都持上述看法。
面对各种不同建议,肯尼迪权衡再三后采取了折中策略。在苏联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四天后,他于9月5日宣布美国将重启地下核试验。为证明美苏核试验的区别,他一方面授意美国新闻署大造舆论宣传声势,强调大气层核试验对人身健康损害更大[31]29-30;另一方面公开呼吁苏联不要进行大当量试验,还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广为散布,苏联核爆炸乃不负责任的非人道之举。肯尼迪双管齐下的策略意在诋毁共产主义形象,并使自身核试验政策赢得世人认同。穆罗稍后给他去信说:“政府在争取世界舆论支持美国核试验问题上取得了成功,许多国家的民众相信苏联的举动只能证明它是一个侵略、好斗的国家;正是我们的舆论宣传在美苏这场冷战交锋中的及时反应确保了美国最终获胜。谁先发言,谁就能够赢得世人更多的信任和支持。”[30]肯尼迪选择跟进苏联的相对克制核试验政策,客观上确实有利于树立美国求和平、负责任的积极国际形象,应该说穆罗在其中“功不可没”。
军方认为仅凭地下核试验并不足以确保世人对美国军事实力的信心,它并不满意总统上述决定,而是要求择机重启大气层试验。穆罗对此建议:鉴于舆论对核试验已十分敏感,政府要么赶在苏联之前完成大气层核爆,避免使美国日后单独成为世人指责的焦点;要么相对较晚宣布恢复大气层核试验,美国新闻署这样就有充足时间做说服和引导工作[30]。肯尼迪最终选择了第二种方案。1962年4月25日,在苏联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半年多后,他才宣布美国也将采取同样举措[28]337-339。现在回过头来分析,他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才步苏联后尘,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要给自己的宣传机器预留下足够的解释时间。此前,美国新闻署围绕外国民众对美国大气层核试验的可能反应提出了预测分析;为尽力争取舆论理解和支持,它还向重要国家的民众广泛散发了阐述美国立场的背景材料[31]29-30。穆罗8月3日致函肯尼迪说:“最近在西欧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政府阐明恢复大气层核试验的理由在当地获得了普遍理解和赞同,但这并不表明盟国政府完全支持美国的行动。”[32]应该说,美国的宣传减弱了来自世界舆论的巨大冲击,可众多新兴民族主义国家仍然对肯尼迪的核试验决定感到失望。
肯尼迪并未在决策时把舆论视为一种束缚自身的道义力量,他认为自己推进美国强大军力形象并不必然意味着会丧失世人对美国其他方面的良好印象。当自己的行动有利于使他们确信美国比苏联更强大时,他不惜逆世界舆论潮流而动,效法苏联最终也恢复了大气层核试验。需要指出,肯尼迪此举决不意味着他对美国新闻署作用的忽视,正是为让穆罗有充足时间开展工作,他才延缓了宣布恢复核试验的时间。他希望世界舆论知道美国比共产主义更讲人道;美国的核威慑力也毋庸置疑。他宣布恢复核试验也何尝不是为争取民心,使世人尤其是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民众认识到,美国核军备有能力抗衡苏联。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共产主义在冷战中已取得优势的观点蔓延,因为这事关美国能否赢得冷战主动。
四、结 语
肯尼迪的核试验政策说明,他关心美国国际形象与利用舆论调查报告之间实际存在着细微差别。他非常在意自己上述决定将在全球产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对来自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抗议也早有预知。但世人对美国军事实力的低认同率,使他意识到美国在空间探索、核武器发展等问题上抗衡苏联更具象征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美国核试验政策将经受铁幕两侧的考验,它是衡量本届政府目标和决心的标志。假如我对苏联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世人会误认为美国在军事领域越发落后,苏联各项军备成就将对他们消极的美国军事实力看法产生进一步冲击。身为总统,我并不能判断什么是美国战略的非重点”。由于他对世界舆论有如此先入为主的看法,这就导致其在核试验政策上妥协的余地并不大;即使在他当政的黄金时期,因为相同的舆论因素,也还导致了对美国产生灾难性影响的系列外交方案[12]267-275。向南越派遣军事顾问直接导致后来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即为明证。
世界舆论之所以同肯尼迪核试验政策紧密相关,很大程度是出于他想扭转美国不利的国际形象,保持美苏业已取得的战略平衡。另外,他越来越关注两国军事实力受世人实际认可的程度。正因为如此,他给穆罗一段舆论铺陈和引导期后,最终也采取了与苏联对等强硬的核试验立场。如果要在美国国力和国际形象之间做出选择,肯尼迪当然把前者看得更重,后者很大程度上是为前者服务的。为获得世人对美国军事实力的认同,为尽可能多地赢得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对美国的积极印象,他甚至不惜与共产主义阵营走到战争边缘。他在核试验政策上的作法,从侧面展现了美国新闻署及其舆论调查如何作用于美国外交、防务政策的过程,也清楚表明了美国对世界舆论一贯的“工具主义”作法。
参考文献:
[1] Michael J. Hogan & Thomas G. Paterson,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2nd ed[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Archibald M. Crossley, “Early Days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57,21(1).
[3] Elmo C. Wilson, “World-Wide Development of Opinion Research.”[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57,21(1).
[4] Leo Bogart,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Overseas Information Campaign.”[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58,21(4).
[5] Dwight Eisenhower in “U.S. Survey Finds Others Consider Soviets Mightiest.”[J].New York Times, 25 October 1960.
[6] “Text of Confidential U.S. Survey on Prestige Rating Abroad.”[J]. New York Times, 25 October 1960.
[7] Richard Nixon in William Jorden, “Campaign Issues-V: Debate on Status of Prestige Rouses Sharp Conflicts at Home and Abroad.”[J].New York Times, 31 October 1960.
[8] JFK speech, Muskegon, Michigan, 5 September 1960, Pre-presidential Papers, box 910[Z]. Kennedy Library. Boston, Massachusetts.
[9] Thomas C. Sorensen, The Word War: The Story of American Propaganda[M].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10] Ernest R. May & Philip D. Zelikow, ed., 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M].Massachusetts: Cambridge, 1997.
[11] JFK, “The New Frontier: Acceptance Speech of Senator John F. Kennedy,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July 15, 1960,” Pre-presidential Papers, box 910[Z]. Kennedy Library.
[12]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 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4.
[13] 阿兰·内文斯.和平战略——肯尼迪言论集[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14]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3[Z].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15] Thomas C. Sorensen to the president, “Latin American Book Programs,”16 April 1962, refers to the president requesting USIA information by telephone.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91[Z]. Kennedy Library.
[16] Donald M. Wilson to the president, “First Effort to Measure ‘World Opinion,’” 10 July 1963,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91[Z]. Kennedy Library.
[17]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Z].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18] Memo from Bundy to the president, 13 February 1961,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125a[Z]. Kennedy Library.
[19] “I thought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in our latest June Surveys,” Murrow to the president, 8 August 1962 and Memo from Murrow to the president, 16 August 1962,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91[Z]. Kennedy Library.
[20] Memo from Wilson to the president, 11 July 1963,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91[Z]. Kennedy Library.
[21] Donald Wilson to the president, 6 July 1961, 20 October 1961; Edward R. Murrow to the President, “Requested Summary of Foreign Reaction to Telstar,” 31 July 1962; Donald Wilson to the president, 11 July 1963,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91[Z]. Kennedy Library.
[22] Leo Crespi,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oncept of Image.”[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61,25(1).
[23] Richard Reeves, President Kennedy: Profile of Power[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24] 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5] Herbert S. Parmet, JFK: The Presidency of John F. Kennedy[M]. New York: Bantam Dell Pub Group, 1983.
[26] USIA, “The Current State of Confidence in the U.S. Among the West European Public”, August 1961,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91[Z]. Kennedy Library.
[27] USIA, “Trends in Western European Estimates of U.S. and Soviet Strength,” July 1963,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91[Z]. Kennedy Library.
[28]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61-1963,Vol.7[Z].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5.
[29] Murrow to the president, 31 August and 1 September 1961,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91[Z]. Kennedy Library.
[30] Murrow to the president, “Reactions to Nuclear Tests,” undated,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91[Z]. Kennedy Library.
[31] USIA, 18th Report to Congress, January 1-June 30, 1962[Z].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32] USIA, “West European Opinion on Nuclear Inspection and U.S. Resumption of Nuclear Test,”3 August 1962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91[Z]. Kennedy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