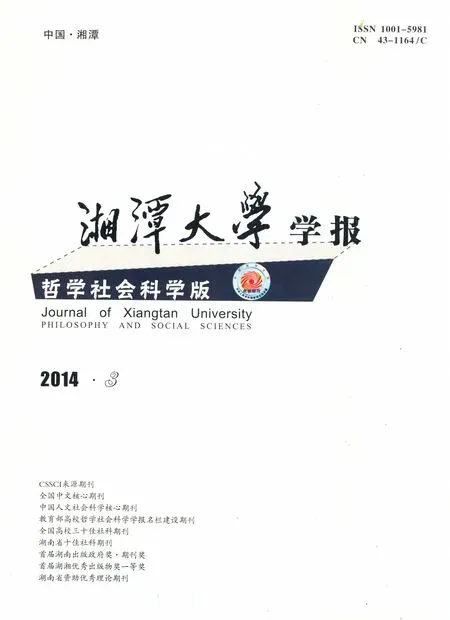报应不应成为刑罚的目的*
邱帅萍
(湖南科技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关于报应,尽管迄今无法查证到任何刑法条文对之进行界定,刑法学界也很少专门研究其定义——仅仅在论述中简要地提及,定义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是,纵览各刑罚理论,可以达成共识的是:报应是基于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应对其无条件强制施加的、与其所犯之罪相应的惩罚。
言及刑罚目的,必言报应与预防。依绝大多数刑法学者所见,刑罚目的理论可以分为报应刑论、预防刑论和以报应、预防为基础的综合刑论,它们在刑罚目的思想史的长河中呈“三足鼎立”之势。报应刑论源远流长,它经历了神意报应论、道义报应论以及法律报应论等的流变,它始终主张刑罚的目的是报应,即便在不同历史时期,报应的内容可能会有所变化。预防刑论则立足于反对刑罚的目的是报应,进而主张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在批判吸收报应刑论和预防刑论之精华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又提出了具有折衷性质的综合刑论,认为刑罚的目的应是兼顾报应与预防。
在当代,报应刑论已经被刑法学界抛弃,预防刑论亦遭到多数学者的否定,目前盛行的刑罚目的理论当属综合刑论。综合刑论虽然兼顾报应与预防,然则二者却有主次或者先后之分,其中,认为刑罚目的应以报应为主、预防为辅的观点最为有力[1]87。在此,本文并无意于争论刑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是,笔者认为报应可以成为刑罚目的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的观点值得商榷。
从历史的维度考察,在中外刑罚史上,占主流的并非以报应而是以报复(复仇)、预防或者其他为目的的刑罚。
(一)西方历史上,主要盛行以报复(复仇)或者预防为目的的刑罚
在西方早期历史上,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法律都对刑罚做出了具体规定。《汉穆拉比法典》规定,“倘自由民宣誓揭发自由民之罪,控其杀人,而不能证实,揭人之罪者应处死……倘自由民击落与之同等之自由民之齿,则应击落其齿”[2]10,92;《中期亚述法典》规定,“如果未曾分产的兄弟中有人杀死了人,死者的家主,如果愿意,可以杀死他,如果愿意,也可以赦免他,[而]取得他的继承份额”[3]45;古罗马《十二铜表法》甚至规定,“如果他损害了他人肢体,除非他为之做出赔偿或与受害者讲和,否则就允许同态复仇”[4]63。
上述法律规定的刑罚,均属于具有报复(复仇)性质的刑罚。如此的刑罚,不仅其外在特征与报应刑无法等同,其所体现出的内在文化内涵也与报应刑存在较大差别。该种刑罚所体现的是一种同态复仇文化,“同态复仇文化总是荣誉文化……研究荣誉文化的学者都知道,荣誉与复仇并不仅仅只着眼于过去已然发生的事物,尽管它们确实表现出对已经贬值的损害一种非理性的着迷;荣誉游戏中的优秀参与者还知道如何着眼于他们的未来……明智的血态宿仇复仇者无需对他受的每个伤害做出激烈回应……他只需确保人们相信,如果下次谁要冒犯他,他完全有能力血债血偿”[4]29,70。因此,在西方早期历史,主要盛行的是以报复(复仇)为目的而非以报应为目的的刑罚。
西方中期以及近现代历史的较长时间内流行的则主要是以威慑或者矫正为核心内容的预防刑。不过,有两段时期的刑罚值得关注。一是中世纪时期,中世纪时期的刑罚具有典型的神权性质,并呈现出神意报应的特征。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刑罚徒有报应之表,而缺乏报应之实。二是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刑法(罚)的近代化时期,该段时期倡导刑罚的等价,强调罪刑的相称性,以致被有些学者称为“刑罚的等价时代”,并认为奉行的是等价报应主义刑罚。[5]39但是,倡导刑罚等价并非意味着刑罚就是以等价报应为目的,刑罚等价的着眼点在于刑罚的力度而非刑罚的目的,换言之,不论何种性质的刑罚,都可以为了各自的目的而提倡刑罚等价。反观该段时期的刑罚改革浪潮,倡导刑罚等价的主要是一些预防刑论者,他们是为了预防犯罪的目的而提倡等价刑。
(二)我国历史上,主要盛行以预防为目的的刑罚
我国的历史上,主要盛行相对主义的目的刑,尤其是预防、威慑刑,刑罚多为预防犯罪、维护统治秩序之所需,重刑主义思想严重。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指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行”;《商君书·开塞》也指出,“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汉书·晁错传》更是明确指出,“其立法也,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以之兴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其行刑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国者也”。[6]330上述“以刑去行”、“立君之道”以及“兴利除害,尊主安民……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国者”都表明,刑罚并不以报应为目的,而是为了除奸臣、维君主、安万民,刑罚被视为预防犯罪、维护统治之术;而且从刑罚的力度上来说,“重其轻者”、“莫深于严刑”都意味着刑罚宁重不可轻,也就不可能符合报应的要求。汉高祖刘邦曾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刘邦所“约”之法(罚)不可谓不严厉,甚至带有报应的性质,但从约法三章的背景来看,当时刘邦还军霸上,急于笼络民心、消除当地百姓对他的戒备、排斥之心,因此,约法三章也只不过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统治之术,实为具有重刑主义思想的威慑刑。
由上可见,在我国古代,从《周礼》到《唐律疏议》,从法家学者到儒家学者,其所规定或者主张的刑罚均主要体现出一种对“刑期于无刑”而不是报应的追求,“那种所谓‘刑期于无刑’(《书经·大禹谟》)的法律谚语,就‘以杀止杀’即通过处罚一人以威吓和警戒社会上的万人从而期望达到没有刑罚的(一般预防主义、威吓主义的)意义而言,法家学者自不必说,就是在自古以来的儒家学者也是存此用心的,从而体现出了很强的一般预防主义、威吓主义的传统”。[7]67自清末以降,受西方刑法思想的影响,刑罚越来越追求矫正改善罪犯的目的,从清末刑法改革所颁布的各种律例到民国时期的《中国民国刑法典》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劳动改造条例》,各类法律规定均在不同程度体现了该目的。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的刑罚传统,但也只是纠正重刑主义、威吓主义,而非摒弃预防主义,如此的刑罚也是另一种意义上即刑罚和德行教育相结合意义上的“刑期于无刑”,而非报应。[7]68
(三)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刑罚也不是以报应为目的
历史上,还存在着因其他原因而实施的刑罚,但它们远非以报应为目的。例如,中古时期,凯尔特人崇拜各种各样的神,并且希望通过拿活人尤其是罪犯作为祭祀品的方式来满足神的需求,以获取生产上的丰收以及治愈身体上的疾病,等等。凯尔特人相信,处死那些犯下盗窃、抢劫及其他罪过的人会让不朽的神灵高兴,但当没有犯人可用时,他们甚至会处死无辜的人。在古罗马时期,暴君卡里古拉当政期间,他时常毫无理由地杀人,甚至把最残忍的刑罚视为一种消遣,从毫无准备被任意宣判为死刑的臣民的惊慌和恐惧中,寻求刺激、乐趣[8]12。很显然,不论是取悦于神灵,还是取悦于君主,抑或是为了丰收、治病,都意味着刑罚有着不同于报应的目的,刑罚的发动及其幅度也与报应刑有着较大的差别。
不但刑罚历史上少有贯彻报应目的的刑罚,即使报应刑论者也并不主张刑罚的目的是报应。
根据学界的通说,报应刑论可以分为神意报应论、道义报应论和法律报应论,然而,无论是哪种理论,其代表性的观点或者论者都没有真正地将报应作为其理论的核心。
(一)神意报应论并非追求刑罚的报应目的
神意报应论被认为是报应刑论最早的理论形态,可以分为替天行罚论和赎罪论。替天刑罚,顾名思义,便是代表神(天)来对犯了罪的人进行惩罚。该种刑罚理论最早可见于中国远古法史的《尚书》以及西方的古埃及和古希伯来法等。如古埃及的神罚观念根深蒂固,所有犯罪行为均被视为触犯神明的行为,被害人乞求神的庇护,而犯罪者也因其冒犯天神而接受天罚。赎罪论则把刑罚视为拯救犯罪人灵魂的工具,该理论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有着较为深刻的渊源。根据基督教义,人生而有罪,而且人的一生中又在不断地犯罪,可谓罪孽深重,人只有受苦才能赎回自己的罪恶,而刑罚无疑是较为“理想”受苦方式。[9]17-18
神意报应论可谓是宗教国家或者宗教盛行时代的产物,但这种观点实质上很难成为一种报应理论。替天行罚论其实是一种将神的意志取代国家意志或者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意志,但国家对罪犯的惩罚不一定就是一种报应性的惩罚。罪犯因为触动神的威严、违背神所拟定的秩序而遭受处罚,与触动国家法律、违反法律秩序所遭受的处罚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只是一种基于秩序违反而接受的惩罚。神的秩序经过法律的转换,便成为了法律秩序,神罚所体现的对神的秩序的维护,亦转变为对法律秩序的维护,而这种对秩序的维护仅仅在形式上是报应性的,不足以使替天行罚论成为一种报应目的的刑罚理论。替天所行之罚在多大程度上是报应性的,主要取决于神的目的,在世俗世界中亦即国家的目的,但替天行罚论并未表明神对罪犯所要施加的惩罚仅以报应为目的,并未表明神只注重行为人之前的所作所为而不论行为人之后所可能发生的情况。赎罪论虽然是人基于其所作所为而遭受痛苦,但赎罪的思想由于与矫正思想较为接近,以致于报应目的与矫正目的在这里纠缠不清。行为人遭受痛苦而赎罪,意味着行为人在洗清自己的罪孽,而罪孽并不仅仅限于有罪之行,更在于有罪之心。如果行为人得到了赎罪,便意味着行为人有了悔改之心,这便实质上等同于行为人得到了矫正。
(二)道义报应论(者)和法律报应论(者)并不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报应
报应刑论者中最彻底、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康德和黑格尔,他们分别代表了道义报应论和法律报应论。然而,即便是他们,实质上都没有将报应作为其理论的核心。
虽然康德认为刑罚是一种绝对命令,刑罚的适用应该坚持平等原则、追求正义等,但是,正如他所言,“在某种意义上,纯粹正义的位置,必须在伦理学中去寻找”[10]201。伦理与法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但是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康德本人也予以明确区分。因此,康德的话语可以理解为:在法律中,不存在纯粹的正义。康德甚至直接指出,“所有的惩罚或者是威慑性的,或者是报应性的……所有的当权者实施的惩罚都是威慑性的,或者威慑违法者本人,或者以他为示例警告他人……当权者的惩罚,不是因为已然之罪,而是因为未然之罪”[11]81。康德所言及的“当权者的惩罚”就是指国家刑罚,由于刑罚的目的是国家动用刑罚所应追求的目标,因此,康德直接否定了刑罚的目的在于报应,而认为刑罚目的在于威慑。
虽然黑格尔指出,刑罚是对犯罪的否定、对强制的强制,刑罚应与犯罪保持价值上的等同,进而使得其刑罚目的理论形似报应论,但是,暗藏在“否定”、“强制”与“等同”之后的,却是依照刑法来维护法律的有效性,并最终表现为矫正罪犯的意志,而不是无条件地追究均衡的刑罚。《法哲学讲演录》中,黑格尔深刻地提到:“罪犯的定在的意志必须受到影响,这一要求与如下实际相关:惩罚一定要给罪犯留下印象,否则,他的定在的意志就不会受到它的侵害”[11]141。为此,刑罚可以允许/应当要求不对某些谋杀犯判处死刑。
此外,以报应为目的的刑罚缺乏实践合理性。
以报应为目的的刑罚,是一种完全着眼于已然之罪、着眼于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的刑罚。不可否认,行为人的行为对于刑罚具有重要的意义,刑罚的施用考虑到既成的犯罪事实,这也符合刑罚的正当、合理性要求——毕竟刑罚不能凭空适用,但如果只着眼于已然之罪,便会令刑罚走入歧途。这样的一种刑罚视野,割裂了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联系,而且,不关心现实和未来的人很少会去关心历史,也很少懂得历史的意义,因而这样的刑罚观容易脱离社会实践,容易忽视行为以及刑罚对于社会所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效果。倘若刑罚理论是根据一定原则、程序所编辑而成的软件,如果抽象化输入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以及相关情况,就会得出是否应该惩罚以及如何处罚的大致结果。比如,可能存在的一种推论是,生命权是人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生命权具有绝对性,不存在比生命权更重要以及与之相比较的权利,因而,对所有的犯谋杀罪的人都应当处以死刑。如果某人谋杀了他人,那么根据该推论,谋杀者就应当被判处死刑,而无须考虑为什么杀人、杀人行为已产生并且将会产生何种具体影响以及对其判处死刑是否合适并会产生什么具体影响等等其他情形。正如罗宾逊教授在评价应得惩罚中的道义惩罚时就指出,“其超越了特定的人和具体情况,它包括建立在基本价值之上的一系列原则和正当与善的原则,进而产生正义而不考虑政治、社会或其他具体情况的特殊性”[12]149。
不可否认,这样的刑罚在许多时候都是合理的——否则据以建立的原则是否合理就会很值得怀疑,然而,它的弊端终究会显现出来。暂且不论它所依据的原则能够穷尽所有的社会现象——这很值得怀疑,至少它拒绝了俯视社会现实,也拒绝对社会的发展表示关心,甚至它可能也因此否认应该回顾社会的历史,因为在它看来,最重要的是原则与被抽象化的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这样的一种报应过于强调理论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忽视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且最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它将理论置于社会实践之上,反而要求社会的发展变化必须要符合它的要求。实际上,有哪种理论不依赖于实践呢?即便是著名概念论者笛卡尔所提出的经典论断“我思故我在”,不也是建立在“我在思考”这一基本事实之上的吗?
总之,如果报应无视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定当无法合理地回答现实社会中刑罚的发动及其幅度问题;而一旦报应考虑社会现实及其发展,那么它也就不再是报应。这也正是报应不应成为刑罚目的的症结所在。
[1]蔡一军.西方刑罚目的观的整合与修正[J].社会科学家,2013(9).
[2]汉穆拉比法典[M].《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何勤华,夏菲.西方刑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美]威廉·伊恩·米勒.以眼还眼[M].郑文龙,廖溢爱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5]龙腾云.重提刑罚进化论的缘由及其研究现状述评[A].赵秉志.刑法评论[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6]周密.中国刑法史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日]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M].牟发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英]凯伦·法林顿.刑罚的历史[M].陈丽红,李臻译.太原:希望出版社,2003.
[9]董淑君.刑罚的要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1]Jean-Christophe Merle.German Idealism and The Concept of Punishment[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12][美]保罗·H·罗宾逊.刑法的分配原则——谁应受罚?如何量刑?[M].沙丽金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