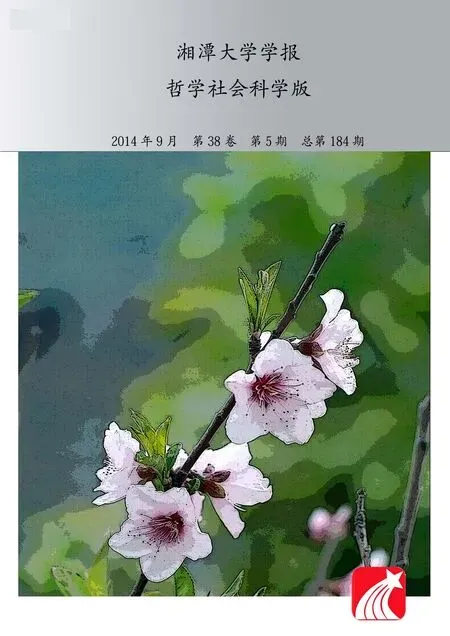华语大片身份叙事的可能与限度*1
陈明华
(广东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伴随20世纪90年代亚洲电影的崛起,韩国电影、伊朗电影、中国电影等作为富有东方特色的文化符码越来越为西方主流电影节所接受和认可,华语电影人国际影响力也获得大幅度的提升,“第五代”的民俗叙事和第六代的个性书写似乎成为中国电影可以辨识的文化身份。然而2000年之后,大片的比拼成为国族间新一轮电影实力的标识,在好莱坞主流电影制片商纷纷以大制作来确立自身在全球的影响力的同时,华语电影人也意图依托大片赢得市场与文化的双重征服效应。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及《金陵十三钗》;陈凯歌的《无极》;周星驰的《功夫》等等,华语电影人以大片角逐贺岁强档,更是吹响了进军全球电影市场的号角。当《英雄》成为华语电影市场化操作的教科书,纷纷为华人导演仿效时,大片在传媒中的轰动效应与人文的隐没再次成为知识精英们探讨的核心话题。自然,大片“展现出一派文化‘博弈’的锐气与风采,具有历史自身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1],大片对于民族电影产业化的引领自然功不可没,但是民间的喧嚣和精英的冷漠恰恰建构了大片在域外和本土的认同错位,大片的想象,说到底,“是艺术想象与文化想象的矛盾,是西方想象的东方与中国东方中国自身想象的矛盾。”[2]华语电影的身份叙事如何在商业与人文之间抉择成为华语电影人与批评家们交锋与碰撞的恒久话题。
(一)视觉的狂欢与文化品位的沉落
在视觉主宰的文化消费时代,“第五代”导演以民俗叙事完成来自西部的加冕之后,李安凭《卧虎藏龙》圆梦奥斯卡再一次激发了华语电影人对于大片叙事的热情。张艺谋以《英雄》为肇端相继推出了《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及《金陵十三钗》;陈凯歌则以3亿元人民币倾力打造《无极》,之后又重金打造文艺巨制《梅兰芳》;何平以强力阵容演绎《天地英雄》;此外,港台电影人中,李安相继拍摄了《色戒》、《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并凭借《少年派》一举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最佳视觉效果奖和最佳原创音乐奖4项奖项;陈可辛的《投名状》,于仁泰的《霍元甲》、吴宇森的《赤壁》(上、下)、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都纷纷走上好莱坞式的大片路,华语大片的间歇性“勃兴”催生了华人受众对本土电影与世界主流电影同步的幻觉,华语电影人瞬间卷入与好莱坞制片商们靠大片博弈的浪潮。
如果说,依靠民俗叙事获得国际认同的“第五代”以好莱坞主流的制作方式满足了国人对于本土大片的渴望,在影像的构图、色彩、光影、空间、运动等方面凸显了“第五代”电影人新的美学追求,视觉元素在新的影像空间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尤其是特技元素的有效介入,进一步强化了视觉符号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英雄》里把两军对垒的森严、万箭齐发的壮观、庭帐帷幕的飞泄烘托到了亦真亦幻的佳境。透过《英雄》所提供的视像,诸多陌生化的自然景观也同样给予了观者非凡的审美体验,从鬼斧神工的敦煌魔鬼城到黄沙漫天的戈壁,从绿波如镜的九寨沟到层林尽染的胡杨树,从森严整肃的秦王大殿到诗意奇绝的书法馆舍,在红与黄、黑与绿之间,张艺谋有效地调动了颜色在视觉方面的表现力;《无极》中陈凯歌更是将视觉的冲击推向极致,鲜花铠甲、海棠树、大草原、千羽外衣、金面具、黑袍组合成为视觉的万花筒,作为深谙中国文化之道的陈凯歌在视觉传达过程中有意识地将静与动、中与西、远与近、舒缓与激烈等对立的审美元素巧妙地并置,同时又在东方沉静典雅的审美传统中注入了西方张扬与动感的视听元素,在凸显影片独特的东方文化感知力和表现力的同时,意图尝试跨越国族文化的壁垒,通过叠化并置的手段消解审美差异的裂痕;《天地英雄》、《金陵十三钗》、《赤壁》、《梅兰芳》等片则尝试将视觉与历史进行巧妙的缝合,以富有国族特色的历史资本作为国际化征程的重要行销策略,只是历史成为人物和故事的背景板,并大胆地进行了消费主义的改写。“酒坊”、“磨坊”和“染坊”为意象的寓言性叙事未能提供更多的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有意无意的疏离以及雷同的主题取向贬损了类型片应该有的意义和价值。反观以商业化著称的好莱坞经典名篇,《乱世佳人》、《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师》、《勇敢的心》等影片不但不会远离政治,而且会通过艺术的手法来直接或间接地表现政治,表现政治对人性的塑造和影响力。其影像固然有鸿篇巨制的大气磅礴,但是在激荡人心的悬念冲突叙事背后,是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深度的人文思考。《教父》表面上只是一部黑帮电影,有着血腥的杀戮和冷酷,但是其对人物的塑造和对政治的揭示是十分深刻的。由此看来,影像革命中所推崇的视觉元素的凸显,绝非以思想的陷落为代价,接受视觉的狂轰滥炸日渐出现审美疲劳的影像受众,依然寄望于视觉奇观背后潜在的思想传达。作为国产大片,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们自然是期待它获得全面的胜利,寄望于这些电影人以东方的文化厚度、精英阶层的批判力度和认知深度最终实现对西方和本土的全面征服。华语大片作为华语电影人涉足全球的突围尝试,似乎难以负重如此多元的审美期待。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最重要的是内容的支撑,而不只是动画特效秀、时装秀和身材秀。视觉表象的趋同无法掩盖与西方主流商业电影思想内涵的差距,也因此华语大片被知识界将其作品视为殖民主义的西方艺术视觉符号。
(二)商业的突围与人文的退守
《英雄》成为中国电影市场化的一个教科书,上映仅两个月,国内票房达到了2.4亿人民币;北美等地发行2000万美元;日本800万美元;香港2670万港币;韩国票房1000万美元;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票房700多万美元;国内贴片广告2000万人民币,音像制品版权费1780万人民币。[3]客观地说,在华语电影发展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部影片赢得如此辉煌的全球的影响力。张艺谋让华语电影以如此风光的方式叩响了世界电影市场的大门。作为此部电影的制片人,张伟平以商业化运作的模式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文化产品的营销。可是商业上的成功并没有满足国人对这部大片的审美期待,尤其是精英阶层,除了票房,知识分子总是期待着张艺谋们有着人文的坚守,继续肩负启蒙的重任,成为艺术忠实的殉道者。面对国外形容“《英雄》经典得就像中国的《红楼梦》”的热捧,很多电影评论家开始质疑张艺谋电影的人文内涵,认为他的电影在文化内涵上开始在走下坡路。电影的物质外壳越来越强,其精神内涵却是越来越苍白的。“不杀”的主题取向违背了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对秦始皇的历史改写也“有意”迎合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平心而论,植根于5000年悠久的华夏文化,华语大片并不缺少史,也不缺少诗,但是史与诗的简单相加却无法成就富有宏阔历史画卷的“史诗”大片,商业层面的无限风光委实无法掩盖人文的退守。跨国视野带给华语电影人新的叙事方略的同时,也无形中消解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电影人对本土的真诚关怀。我们呼唤中国本土史诗片的出现,也期待以此为契机寻找一个振兴国产电影的机会,但也呼唤大片在纷繁富丽的影像背后寄予华人特有的人文情怀和精神积淀。
单就纯粹的商业与营销层面而言,中国进入营销行列的电影依然停留在电影本身的宣传和企业的赞助上,后电影产业的开发还远远不够,过于单一的盈利模式使得大片的商业突围也是很有限度的。纵观每一部经典好莱坞大片,几乎都有着与这部电影相关的后电影系列产品开发,从小说到玩具、时装、游戏、主题公园等一应俱全,以迪士尼和梦工厂的动漫电影为例,他们几乎将后电影产业开发到了极致。他们会充分发挥电影本身的品牌影响力,挖掘品牌背后孕育的商业资源,通过整合营销让带有品牌意味的文化消费成为可能。很显然,好莱坞大片的商业意图几乎都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文化包装,依托强大的营销团队进行全球化的运作,通过网罗全球的影星、改写其他国族文化故事原型以及到世界各地取景以获得其在全球行销的通行证。由此看来,华语大片的运作模式尚缺少真正的国际化视野和文化想象力,在迎合与退守之间的纠结使得其影像无法弥合受众的审美落差。
(三)华语大片身份叙事的可能与限度
当张艺谋、陈凯歌们以历史的酥皮包装的大片铩羽而归的时候,李安却凭借《卧虎藏龙》、《断背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屡屡问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很显然,从国人惯常的视角来看,《卧虎藏龙》绝对不是中国武侠的经典,与早期《新龙门客栈》、《精武门》、《黄飞鸿》系列影片中的“真功夫”相去甚远,但其在跨文化的解读中却得到了超乎想象的肯定,至今仍然是华语电影在北美电影排行榜中的佼佼者。究其根本,正是李安跨文化视角使得其作品获得华语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再造基因,李慕白缺少杀气的儒雅更兼具了中国武侠内在之精神要义。《断背山》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则彰显了李安对国际题材的驾驭能力,如何在影像中寄予东方式的情感,如何在画面中凸显东方美学的神奇被李安拿捏得非常有分寸,既有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大片”的磅礴大气,又不乏华语电影叙事特有的文化因子,承袭了东方美学的文化底蕴。梳理李安的早期作品,《喜宴》、《推手》、《饮食男女》同样是选择了文化碰撞背景下的人伦亲情作为叙事母题,直面文化冲突,却最终又在华语文化中完成灵魂的救赎。相较而言,吴宇森的《赤壁》同样是对华人耳熟能详的“三国”进行了大胆的好莱坞式的改写,“企图融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香港文化等,做成一个亚洲最大范围的华语电影,成为全球华人都可以共享的文化大餐,将中国古老的故事传奇置换成为全球文化共享价值的精品。”[4]结果不难想象,这次肆意的改写并未让其获得行销全球的通行证,在美国和亚洲本土市场均遭遇了恶评,导演在主流价值观传播和艺术家个人追求之间显然没有找到平衡点。相较而言,《赛德克·巴莱》是值得致敬的一部华语大片,该片由《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筹划12年,跨国动员2万人拍摄完成。电影分为《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和《赛德克·巴莱(下):彩虹桥》两部分,讲述的是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原住民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率众反抗日本政府而发动雾社事件的故事。《赛德克·巴莱》再次掀起台湾本土观众的观影狂潮,在国际影展上也是好评有加,其魅力除了具备大片的基本元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其植根于本土,依托“雾社事件”展开创作,没有刻意的升华,没有曲意的迎合,影片用不事做作的朴实塑造了一批保家卫国的血性男儿,以“不自由,毋宁死”的誓言,捍卫国族不可侵犯的尊严,堪称世界级史诗性作品。《赛德克·巴莱》所诠释的主题,获得了跨界的表达和认同,在华语电影饱受质疑的时期,它几乎是以雄起的姿态,宣告华语电影精神不死,捍卫着华语电影在世界电影面前的尊严。《赛德克·巴莱》以“十年磨一剑“的沉潜精神,倾力与本土历史文化元素的挖掘与呈现,用真诚和坚持建构了华语电影身份叙事的可能。
好莱坞电影发展史上,“西洋镜”中的“华人形象”常常是扭曲的,他们常常是唐人街的黑帮和混混,要么就是长辫子吸食鸦片的“烟鬼”。自华语电影诞生以来,华语电影人一直未放弃通过影像输出的文化媒介传递华人世界的正能量,拥有世界人口1/5受众面的华人社区也理应在国际电影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华夏悠久的历史文化也为我们提供了以电影为媒介进行文化交往的资本。如何推动华语文化更为自信地走向世界,向世界传达独特的华语文化价值谱系,塑造有文化底蕴的国族形象,是每个华语电影人肩负的重任,在好莱坞知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和詹姆斯·卡梅隆向美国大片潮发出警示的时候,华语电影人理应有更为审慎的认知,不能仅仅以“大”博弈,更应以“质”突围,秉持多元化的发展策略,拯救华语电影叙事失落的文化品位。
参考文献:
[1]黄式宪.大片“博弈”——以弘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与世界对话[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9(6).
[2]陈晓明.21世纪:如何想象中国[J].电影艺术,2001(4).
[3]陈晓云.对中国当代电影文化结构的思考[J].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5).
[4]陈旭光.中国电影大片的海外市场推广及其策略[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