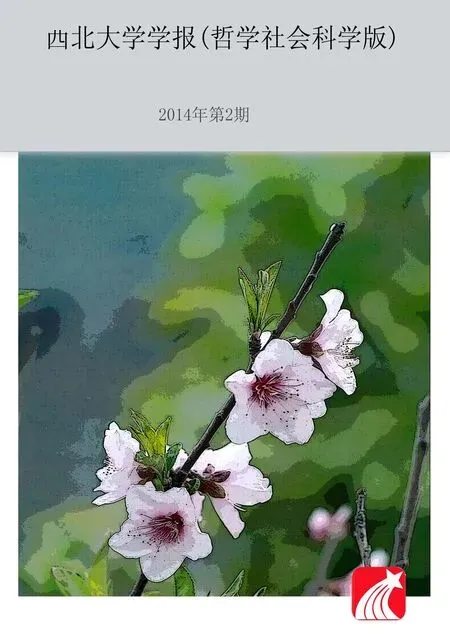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考证方法
赵 涛
(河南大学 文献信息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是在编篡《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完成的,成书于考证学风高涨的乾嘉时期,在目录编篡体例、文献分类、提要撰写、文献考行等方面成就巨大,因而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地位极为重要。参与编写《总目》的四库馆成员大多学养深厚,他们“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1](卷首《凡例》P17),因此极其重视考证。《总目》的撰写者在开展史学批评的过程中,“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作史、读史皆“资考证”[1](卷45《史部总序》P397),形成了系统、严密的历史考证方法。前人和今人对此已有研究,但主要是在讨论其史学思想时附带涉及,很少从一般方法论意义上揭示其考史方法。同时,《总目》提要与其分纂稿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分歧,这在学术界业已形成共识,主要体现在对提要内容考证上的不同。经笔者统计,现存四库馆纂修官邵晋涵、姚鼐、翁方纲、余集四家史学类分纂稿有261条。通过对四家分纂稿与《总目》提要的对勘比较分析,能够较为全面地看出《总目》在史学批评中的考史方法。本文拟通过对现在仅存的四库馆纂修官邵晋涵、姚鼐、翁方纲、余集四家分纂稿与《总目》提要的比勘,析理《总目》史学批评中的考据学方法。
一、实学考证的方法
明中叶以降,陆王心学浸染日深,“心本体”论主宰史学领域,史学学术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具体历史事实而空洞褒贬议论的不良学风。清初以来,学者一反明人空谈心性、束书不观之习而重实学、重经史。清代史家受此影响,以求真求实的史学意识发覆纠谬,征实考信,开创出实学考证的治史学风,回归了史学批评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治史传统。这种治史方法采用治经的方法治史,以求真精神考证史书和史事,主张史家应当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不失历史的真相。《总目》在进行史学批评时,多次宣明要“谢彼虚谈,敦兹实学”[1](卷首《凡例》P18),“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1](卷45《史部总序》P397),并在实践中广泛使用了这一方法。
(一)自觉的求真考实意识
《总目》考证历史,强调求真考实。《总目》认为治史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真实和确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因而把实学作为考史的目标,并在历史考证中自觉地予以贯彻。
《总目》考史务求切实,不迷信前人,力求考证清楚历史事实的真相。如元脱脱的《辽史》,邵晋涵撰分纂稿[2](卷12),《总目》则增改材料:
观袁桷修《三史议》、苏天爵《三史质疑》,知辽代载籍,可备修史之资者寥寥无几……特以无米之炊,足穷巧妇,故不得已而缕割分隶,以求卷帙之盈。势使之然,不足怪也。[1](卷46《辽史》P413)
邵晋涵分纂稿与《总目》的最大区别是:邵氏不顾历史事实,认为《辽史》或“重见叠出,瓜分缕割”,或“敷衍成文”因而“难以配宋、金二史”。而《总目》则通过求真考证,理性分析了造成《辽史》“重复琐碎”的原因主要在于辽代的文化政策“书禁颇严”:“凡国人著述,唯听刊于境内。有传于邻境者,罪至死。”所以就使得辽代典籍无法“流播于天下”,后来在烽烟四起的战乱环境下,便“旧章散失,澌灭无遗”以至于“可备修史之资者寥寥无几”。后代史家面对“无米之炊”的困境,不得不采取“缕割分隶”的方法,“其间左支右诎,痕迹灼然”,也就在所难免造成“重复琐碎”。正因为《总目》尊重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按照当时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开展史学批评,才使得后人看到了历史的真相。
(二)尊重古人本来面目
《总目》重视实学的考史方法,重视治史应尊重前代史书本意,而不能罔顾事实而轻率訾议前人。《总目》对于前代史家任意褒贬历史、玩弄书法剪裁历史事实的做法极为反感,对前代史书不能如实记载历史事实提出强烈批判。
《总目》在其史学批评中,一以贯之地按照这种批评理念进行史学考证,以澄清历史真相。对于北齐魏收撰的《魏书》的考论,最能反映这种考史理念和方法。《总目》丰富了邵晋涵分纂稿[2](卷12),进一步增加材料:
“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收书为据。其为收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其必有所见矣。今魏澹等之书俱佚,而收书终列于正史,殆亦恩怨并尽而后是非乃明欤!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多为魏澹所驳正。《北史》不取澹书,而澹传存其叙例。绝不为掩其所短,则公论也。[1](卷45《魏书》P407)
对比《总目》与邵氏分纂稿可以看出,《总目》侧重以求实精神对抨击魏收的种种错误看法进行详悉考证,意在恢复历史的本相。历代史家认为魏收撰修的《魏书》是“秽史”,攻评不已。所举显例之一是《魏书》完稿后,“前后投诉,百有余人”,其中以范阳卢斐的攻击最为猛烈。卢氏认为自己的父亲在魏官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但与魏收无亲,遂不列传,而博陵崔绰位至本郡功曹,本无事迹,因是魏收外亲,故立佳传。《总目》较之于邵氏,其差别是经过一番求实考证,指出卢斐之父卢同党附元义,多所诛戳,后来被罢官职,并非“功业显著,名满天下”,崔绰官位虽低,却是“贤俊功曹,冠冕州郡”,自然应当立传。卢斐以官位大小作为立传的标准,“未足服收也”。而对于诸如“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的错误看法,《总目》也如实一一批驳,认为杨愔先世杨椿、杨津,高德正先世高允、高祐,均是“魏代闻人”,必须立传,并非魏收攀附权贵。以实事辨析,断然否定了《魏书》“秽史”说,并在辨析时阐释了自己独到观点。同时,《总目》在辨析《魏书》非“秽史”的过程中,也没有回护后者短缺,指出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收恃才轻薄”等做法是不足取的。
(三)辨析附会的伪史
《总目》用实学的方法考辩史学真相,意在揭开后人附会的伪史,还原古史的真实面目。在具体的历史批评中,对后世附会的伪史进行求实的考证。如对于梁萧子显《南齐书》,《总目》增改邵晋涵分纂稿[2](卷12),进一步阐释其理念:“齐高好用图谶,梁武崇尚释氏,故子显于《高帝纪》卷一引太乙九宫占,《祥瑞志》附会纬书,《高逸传》论推阐禅理。盖牵于时尚,未能厘正。”[1](卷45《南齐书》P406)与邵氏分纂稿相比较,《总目》更重考证辨伪。《总目》指出,《南齐书》很多地方“推阐禅理”“附会纬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齐高好用图谶,梁武崇尚释氏”,而萧子显“牵于时尚,未能厘正”。又如对于明人徐纮撰《明名臣琬炎录》,较之于翁方纲分纂稿,《总目》更为强调历史事件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翁氏认为,《明名臣琬炎录》“仿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而作,所辑自洪武迄弘治九朝诸臣事迹”。一些被后世视为奸邪的人物,如李景隆、张升、陈泰亦被收录,“谓之名臣”[4](第6册P404)。《总目》虽然承认“究不免彼此矛盾”,但并没有就此点到为止,而是求实辨析了影响史家思想和看法的客观原因:“明自成、弘以前,风会淳厚,士大夫之秉笔者,类多质直不支,无缘饰夸大之词,尚属可以取信。”[1](卷58《明名臣琬炎录》P524)
《总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辨析历史,改变了宋明理学影响下史学的空疏不实学风,扭转了注重儒家义理而歪曲历史事实的学术倾向,逐步形成求实征信的考史方法论,从一定意义上端正了古代史学的发展方向,甚至影响到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和进步。
二、溯源考证的方法
《总目》运用溯源考史的方法评论历代史籍,主要是通过考察史料流传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匡正舛误,以此揭示史料的起源,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总目》溯源考史过程中的所重,一在强调历史记载原始材料的价值;二在意识到古史系统中羼入许多后人臆度附会的成分,因而有必要进行疑古辨伪。
(一)重原始材料价值
“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则见闻必确。”[3](卷24P356)《总目》根据这个原则,非常重视考察史料来源,由兹以确定史家史著的历史意义。如对于司马迁的《史记》,邵晋涵所撰分纂稿重在叙明义例及其史注源流[2](卷12),而《总目》则重新拟定提要,在考证方面以辨明版本存佚及其真伪为重点。其中重新拟定的提要,十分重视原始资料的价值:
《汉书》本传称其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注以为迁殁之后,亡《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刘知几《史通》则以为十篇未成,有录而已,驳张晏之说为非。今考《日者》《龟策》二传,并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为补缀残稿之明证,当以知几为是也。[1](卷45《史记》P397)
这段文字是对张晏之说与刘知几的看法进行考证,认为张晏之说因缺少史料来源而不可信,相反则认可刘知几的看法。主要通过追溯史源,“考《日者》《龟策》二传,并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为补缀残稿之明证”,由此考证清楚了刘知几之是和张晏之非。
《总目》不仅注意到原始史料的考证作用,还特别关注原始材料的史学价值。如对于明王世贞所撰之《嘉靖以来首辅传》,改易翁方纲分纂稿[4](第12册P42),详核考证明代首辅的渊源,阐明“至嘉靖间,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而王氏的《嘉靖以来首辅传》“断自嘉靖为始,以明积渐所由来”,从而进一步凸显了此书的“源头”的史学价值,即“其所载始杨廷和,讫申时行,皆以首辅为主,而间以他人事迹附之。于当时国事是非,及贤奸进退之故,序次详悉,颇得史法”[1](卷58《嘉靖以来首辅传》P524)。由于《总目》重史籍的原始材料的价值,故而凡在史学上有所创新的史著,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二)溯源疑古辨伪
“古人多贵精,后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5](卷上《崔东壁遗书》P7)鉴于后世历史著作内容驳杂失真,《总目》认为,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流变过程,要辨析其真伪,就必须从其发展流变中追根溯源。《总目》中的不少地方,显示出这样的批评思路和考证方法。比如对于清朝孙之騄所撰《考定竹书》,翁方纲分纂稿认为:
《竹书纪年》……梁沈约注,起黄帝元年,迄今王二十年。所谓今王者,《晋书·束皙传》以为魏安厘王,荀勖、和峤以为魏襄王,《隋书·经籍志》以为魏哀王。是书从荀勖、和峤之说……此等处有关于竹书之源流同异者,果能厘核折衷,方可谓之考定。今之騄是编不过杂取古今诸书所载事语之可附注者辑于条下,非有所考据是正也。……则所少者考定耳。[4](第13册P1151)
而《总目》则重新拟定曰:
(《考定竹书》)是编以沈约所注《竹书纪年》未为详备,因采摭诸书别为之注。然之騄爱博嗜奇,多所征引,而不能考正真伪。如帝癸十年地震,引华严合《论大地有六种震动》,所谓遍动、遍起、遍涌、遍震、遍吼、遍击者为说,殊为芜杂。又刘知几《史通·疑古篇》中,排诋舜、禹,以末世莽、操心事推测圣人,至为乖谬。而一概引用,漫无辨正。沈约注出依托,尚能知伊尹自立之诬、太甲杀伊尹之妄。之騄乃旁取异说,以荧耳目。云能补正沈注,未见其然。[1](卷48《考定竹书》P432)
二者相较而言,翁氏分纂稿缺少疑古辨伪的考证,而《总目》则以“帝癸十年地震”“排诋舜、禹,以末世莽、操心事推测圣人”为例详为考证,认为孙之騄“一概引用,漫无辩证”,对其缺少溯源辨伪的考证进行批判。其他如元吴澄撰的《春秋纂言》,由于其中吉、凶、军、宾、嘉五例与宋张大亨撰的《春秋五礼例宗》近似,被众多史家怀疑剽袭后者,《总目》未信前言而立足门户分源别派,从其出入中仔细辨析,证明吴澄未袭张氏:“盖澄之学派,兼出于金溪、新安之间,而大亨之学派,则出于苏氏。澄殆以门户不同,未观其书,故与之暗合而不知也。然其缕析条分,则较大亨为密矣。”[1](卷28《春秋纂言》P225)《总目》中类似上述关于溯源考证的方法,对于考证中国古代各种制度和古史传说中的各类成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使得史料辨析和考证达到了更加成熟的境界。
三、比较考证的方法
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是复杂的,如果孤立地进行考证,推研出的历史发展趋势及其意义,很可能是片面甚至错误的。因而考核史事或历史典籍,通常都注重采用史学比较方法。这种方法具有学术传统和渊源。《总目》对于比较考史方法认识上有独特的观点,如“比而观之,可以知其才力之强弱与意旨之异同”[1](卷187《坡门酬唱集》P1695)“互相参考,可以观古今人运意之异同,与遣词之巧拙”[1](卷195《优古堂诗话》P1782)等等,都意在说明比较考史的方法有一定的功能和作用,能够从中发现史家才气的大小、文章笔法的拙巧以及学术旨趣的差异等。
(一)共时比较方法
共时史学现象的比较就是对记载同一时期内容的历史著作所作的比较考证。《总目》在对史学问题进行考辩以及评价史书价值时,大多采用此种方法。如对于汉班固撰的《汉书》,邵晋涵撰分纂稿[2](卷12),《总目》则修改为:
然一经考证,纰缪显然。颜师古注本冠以《指例六条》,历述诸家,不及之遴所说,盖当时已灼知其伪。李延寿不讯端末,遽载于史,亦可云爱奇嗜博,茫无裁断矣。固作是书,有受金之谤,刘知几《史通》尚述之。然《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无其事也。又有窃据父书之谤。[1](卷45《汉书》P401)
《总目》与邵氏对刘之遴所获所谓“真本”《汉书》“灼知其伪”原因的解释各有所据,但前者对班固著述有“受金之谤”和“窃据父书之谤”分别进行对比考辩,却是邵氏分纂稿里所没有的。《总目》进行原因阐释时,进一步深化了邵氏的对比考辩,达到了很好的史学批评效果。再如《总目》在对于欧阳修《新五代史》和薛居正《旧五代史》开展史学批评时,完全推翻邵晋涵的《五代史记》提要分纂稿而另起炉灶进行重写。《总目》在旧、新《五代史》提要中对二者进行详密周全的比较,对于纪事比较,认为《旧五代史》是“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新五代史》则是“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而事实则不甚经意”。又指出《旧五代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该具,而断制多疏”。从风格方面看,《旧五代史》“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新五代史》则是“其词极工”“文章高简”[1](卷46《旧五代史》、《新五代史》P411)。进而精辟地指出“盖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于偏废”,既清楚明白地揭示了旧、新《五代史》的不同特征,又不偏废任何一方,比较公允地评价了两者的史学价值和意义。
(二)历时比较方法
历时史学现象的比较就是对记载不同时期内容的历史著作所作的比较考证。《总目》在比较学说异同以见不同学术流派的意旨时,常用此种方法。比如《春秋》三传,左氏古文派与公羊、谷梁今文派长期互相排斥。《总目》通过历时比较,辨明学术异同,归纳三传特点:
左氏说经,所谓“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经意。然其失也,不过肤浅而已。公羊、谷梁二家,钩棘月日以为例,辨别名字以为褒贬,乃或至穿凿而难通。三家皆源出圣门,何其所见之异哉?左氏亲见国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据事而言,即其识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谷梁则前后经师,递相附益,推寻于字句之间,故凭心而断,各徇其意见之所偏也。[1](卷29P244)
这样的历时比较,简要地归纳出了左氏征实而肤浅,公羊、谷梁穿凿而难通的不同特点,深刻揭示了古、今文歧异的原因。
《总目》在历时史学比较时,往往通过梳理学术发展源流以辨析其异同,揭示其优劣短长,使得批评更为深入。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对“古人法书真迹”流变进行梳理,颇有价值。对此《总目》改易翁方纲分纂稿[4](第15册P1349)并增加材料:
古人法书惟重真迹。自梁元帝始集录碑刻之文为《碑英》一百二十卷,见所撰《金楼子》,是为金石文字之祖,今其书不传。曾巩欲作《金石录》而未就,仅制一序存《元丰类稿》中。修始采摭佚逸,积至千卷,撮其大要,各为之说。[1](卷86《集古录》P733)
由此可以看出,《总目》与翁氏对于金石流变的历史梳理是有分歧的:翁氏只是强调欧阳修“嗜古金石之文,有历代金石刻一千卷轴而藏之,据其大要为之说”;而《总目》则在评中运用了历时史学的方法,对梁元帝的《碑英》、曾巩拟撰的《金石录》以及欧阳修之《集古录》进行对比,从而梳理出金石辑录的渊源流变。通过比较史书纪事优劣和历史事件性质的异同,加深和拓宽了对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时代特征的认识,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四、辩证考证的方法
《总目》运用辩证考史方法,主要是对前人的历史文献或研究成果加以纠谬、考信与求真,对历史著述或历史人物作了一分为二的考证,从而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和考史方法论的丰富做出了新的贡献。《总目》史学批评实践中运用的辩证考证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整体考评,即是在对史学现象进行分析、归纳的基础上评价整部史书的优长劣短;另一种是局部辨析,即是通过对史书各部分的辨析以揭示史书的价值和意义。
(一)整体考评方法
《总目》采用整体考评史书的方法概貌性地阐释整部著作,对史学现象予以总体的、明确的辨析。如对于明黄衷撰的《海语》,翁方纲撰分纂稿[4](第6册P408),《总目》在其基础上增加评论:
此本实三卷,分为四类:曰《风俗》,凡二目;曰《物产》,凡二十九目;曰《畏途》,凡五目;曰《物怪》,凡八目。所述海中荒忽奇谲之状,极为详备。然皆出舟师舵卒所亲见,非《山海经》《神异经》等纯构虚词、诞幻不经者比。每条下间附论断,词致高简,时寓劝戒,亦颇有可观。……是尤可订史传之异,不仅博物之资矣。[1](卷71《海语》P632)
在以上增加的评论中,《总目》详核考证,从而得出《海语》“每条下间附论断,词致高简,时寓劝戒,亦颇有可观”“是尤可订史传之异,不仅博物之资矣”的结论,从而为该书整体定性。再如评价杜佑的《通典》:“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1](卷81《通典》P694)评价司马光的《稽古录》:“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复开陈,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于治道者甚深。”[1](卷47《稽古录》P422)如此等等,都是对整部史书做一总体评价,从而揭示该著在史学领域中的地位或作用。
(二)局部辨析方法
史学批评中采取局部辨析的方法,能够辨明史书的优长和短缺,从而帮助后人正确认识史著的价值和意义。《总目》尤其擅长采用此法。如对于《宋季三朝政要》,姚鼐撰分纂稿[6](卷2),《总目》在此基础上增加评论:
然宋末轶事颇详,多有史所不载者,存之亦可备参考也。其以理宗、度宗、瀛国公称为三朝,而广、益二王则从附录,体例颇公。卷末论宋之亡,谓君无失德,归咎权相,持论亦颇正。而忽推演命数,兼陈因果,转置人事为固然,殊乖劝戒之旨。[1](卷47《宋季三朝政要》P427-428)
所增材料从局部考评《宋季三朝政要》的价值,认为“卷末论宋之亡,谓君无失德,归咎权相,持论亦颇正。而忽推演命数,兼陈因果,转置人事为固然,殊乖劝戒之旨”,可谓的见。又如《宋史全文》,分纂稿为翁方纲撰写[4](第10册P853),《总目》在此基础上增评:
其于诸家议论,采录尤富。如吕中《讲义》、何俌《龟鉴》,李沆《太祖实录论》、《足国论》,富弼等释、吕源等增释,陈瓘《论大事记》诸书,虽其立说不尽精醇,而原书世多失传,亦足以资参考也。[1](卷47《宋史全文》P428)
《总目》所增评论,是对《宋史全文》采录“诸家议论”进行考评,认为“其立说不尽精醇,而原书世多失传,亦足以资参考也”。
《总目》编纂者能够自觉地运用辩证方法考证历史,避免了认识历史问题时形成的片面之见,对历史事件得出了较之前人更加全面的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历史著述或历史人物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
五、参互考证的方法
余嘉锡曾评价《总目》说:“观其援据纷纶,似极赅博,及按其出处,则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即晁、陈书目,亦未尝覆检原书,无论其他也。”[7](卷首《序录》P49)意在说明《总目》的征引之博,且赞叹纪昀在“援据”时“未尝覆检原书”,随手征引但无意中却道出了《总目》史学的参互考证方法:在开展史学批评时常常旁征博引,大量收集相关史料,在此基础上参互考证,援据融会,屡屡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一)本证参互考证
《总目》参互考证中的本证方法是利用一部或多部正史参互考证,以辨明历史记载是否真实。如对于唐魏徴撰的《隋书》,《总目》删改邵晋涵分纂稿[2](卷12),并增加材料:
根据质量通病及控制点,重视对关键复杂节点防水工程,预留预埋隐蔽工程及其他重难点项目的技术交底,传统施工交底是通过二维图纸,然后空间想象。但人的空间想象能力毕竟有限,不同的人想法也不一样。BIM技术针对技术交底处理办法,是利用BIM模型的可视化、虚拟施工过程进行技术交底,使一线工人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复杂节点,有效提升质量相关人员的协调沟通效率,将隐患扼杀在摇篮里。
是当时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本连为一书,十《志》即为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编入《隋书》,特以隋于五史居末,非专属隋也。后人五史各行,十《志》遂专称《隋志》,实非其旧。乃议其兼载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1](卷45《隋书》P408)
认为“十《志》最为后人所推,而或疑其失于限断”,是因为“十《志》即为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编入《隋书》,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专属隋也”。这里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本证以上观点,进而考证出历史事实。再如对于唐李延寿撰的《北史》,《总目》修改邵晋涵分纂稿[2](卷12),其中把“文章有首尾”句改为:
参核同异,于《北史》用力独深。故叙事详密,首尾典赡。如载元韶之奸利,彭乐之勇敢,郭琬、沓龙超诸人之节,皆具见特笔。[1](卷46《北史》P409)
《总目》提出“叙事详密,首尾典赡”的观点,遂引本书内“元韶之奸利,彭乐之勇敢,郭琬、沓龙超诸人之节”等史实与本证参互考证,以辨明论点。
(二)正史与野史参互考证
《总目》参互考史方法除利用各种正史旁参互证之外,亦利用野史与正史参互考证。如对于宋陶岳撰的《五代史补》,翁方纲撰写分纂稿[4](第18册P1576),《总目》推倒翁氏分纂稿重新拟定提要,提出《五代史补》“虽颇近小说,然叙事首尾详具,率得其实”的观点,并以欧阳修《新五代史》和司马光《通鉴》《通鉴考异》《薛史》等相互参证,证实野史文献亦有可资利用之处,引用野史文献可补充正史记载的史实[1](卷51《五代史补》P464)。《总目》以金石碑刻、稗官杂史、笔记文集与正史记载相互参证,或考证史书谬误,或订补史书缺漏,其成就达到乾嘉历史考证学的顶峰。其利用多种辅助学科会通考证的方法,启发了中国近代新历史考证学派的考史方法,为传统历史考证学向近代历史考证学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邵晋涵.南江文钞[M].清道光十二年胡敬刻本.
[3]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 ]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
[5] 崔述.考信录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 姚鼐.惜抱轩书录[M].清光绪五年刻本.
[7]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