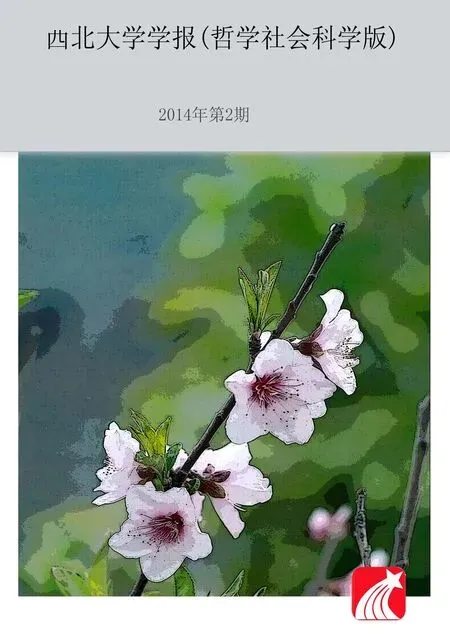超越原创与典范
——康德关于艺术的天才创造思想再阐释
(美)劳拉·奥斯特里克(Lara Ostaric) 谷鹏飞 译
(天普大学 哲学系,美国费城,19122)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似乎认为,“艺术规则”是一种决定艺术家在其创作中所遵照的法则,惟如此,其作品才能唤起欣赏者的审美反应。在康德看来,对作品恰适的审美反应,源于欣赏者愉悦的情感与心意诸机能之自由和谐统一——这当然还需要天才作品表现出一种合目的性的自由形式。但是,设若将艺术规则的意义等同于艺术作品的合目的性形式,那么,艺术天才的规则就很难区别于仅仅基于趣味的艺术规则。这样,那种为了唤起欣赏者审美反应的艺术规则就只是天才艺术规则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以此故,康德提出天才艺术的合目的性形式须要具备两大特性:第一,它不能藉由决定性的规则而产生,因而,“原创性是其首要特性”[1](P186)。第二,“作品同时必须可以成为模型,亦即典范,因此,其本身必须不是模仿的产物,恰恰相反,它应作为判断力的标准或规则而成为模仿的典范。”[1](P186-187)据此,康德认为,尽管天才的作品不能根据那种可传授的决定性规则而产生,但其作为其他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规则,却可以催生出其他的艺术风格或类型;也就是说,天才的作品作为其他艺术天才的典范,“可以唤起一种原创性情感,使艺术家能从艺术的强制性规则中解放出来,获致一种新的艺术规则,藉此使自身成为一种新的典范”[1](P195-196)。这也意味着,对于后继者而言,天才的作品表现为一种规范性,后继者要使其作品亦具有原创性,就必须在其自身的创作中,革新原有的艺术法则。
虽然康德关于艺术创造规范性的阐释亦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获得理解,但本文仍然愿意循着康德形式美学的视角进行阐述。依此思路,本文的基本主张是,天才创造规则所展示的特殊规范性身份及其典范性的原创性,难以通过天才的那种单纯基于趣味的模仿而获得理解。在康德看来,天才的创造并不同于简单的模仿创作,而是基于自由的人性活动与自然的超感官基质的理念之特殊联接而生。因而所谓的“自然”,在这里主要表现为一种超越的、创造性的主体性。但遗憾的是,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对于艺术规则问题讨论所潜藏的美学意义,迄今尚未被阐扬出来。这些讨论多隐藏在康德第三批判只言片语的注释中,表现在前批判时期关于人类学问题的讨论中。本文将以此为线索,重新追寻康德在1770年代中晚期关于艺术天才问题讨论的踪迹,揭示康德对于此一问题讨论的整体面貌,说明其早期关于天才问题的讨论,对于理解其在第三批判中的艺术天才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精神”:天才的创造才能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指出,“天才是天生的心灵禀赋,通过它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1](P186)设若此一定义仅为语源学的界定,那么它就很难逃脱将天才的创造囿于规范性的指责。拉丁语词“心灵”(ingenium)一词原指人先天秉有的一整套才能——诸如人之爱好、天赋、性格等,而基于此一意义上的“天才”概念迟至法国古典美学中才流行起来,并且主要意指一种自然而然的原创性活动,它与基于文化趣味的创作活动相对。英国美学在接受这一概念时,又赋予其心理学与经验主义的双重内涵:称某人为“天才”,那就意味着某人天生秉有超感官的才能与独特的性情。最为显著的例子是当时苏格兰哲学家亚历山大·杰勒德(Alexander Gerard)写了一篇名为《论天才》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对天才的概念作了详尽的阐释,认为“天才”是将诸多转瞬即逝的理念在想象中重新连接的才能。这种阐释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对古典“理念”说的时代别解。
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康德关于“天才”的观念是受了氏作的影响。事实上,康德明确地反对杰勒德的诠解,认为“天才并非如杰勒德所言,是一种特殊的灵魂的力量,否则,它就有其具体的对象;相反,天才是使人性渴望的所有对象理念有生气的法则。”*Kant,The pre-critical Reflection,949,15·421,dated c.1776-8无独有偶,康德的这种将自己从自然主义的天才观念论中区别出来的思想,亦表现在如下的论述中:“我并不赞同对天才作身体化的诠解,诸如想象—记忆之类,相反,我要追寻那种导致天才力量形成的形式法则。”*Kant,The pre-critical Reflection,960,15·423,dated c.1776-8康德在前批判时期对“天才”问题的如上分析表明,我们不宜过分强调其在早期“天才”观念界定中援引“心灵”概念的重要意义。因为根据康德,展现在天才作品中的规则,并非是一种特定心理学的产物,而是基于一种所有艺术创造都应遵循的“形式法则”。
由此来看,天才创作所需要的“精神”,就只是一种天才的“创生性机能”,一种天才的灵感来源,一种使心灵有生气的法则[1](P191)。康德认为,天才的认知机能、想象及知性,当且仅当其能够自由和谐地彼此作用,作品才能在欣赏者面前表现出和谐,才能被普遍地判定为美[1](P316)。而“精神”的作用,则在于引发艺术家诸心意机能自由和谐地运作。但是,一旦将天才的创生性机能简化为唤起欣赏者适当审美反应的必要条件,那么,就很难将天才的创造性机能与仅仅基于趣味的艺术创作活动区别开来。毕竟,前者与后者一样,都可以引起欣赏者心意机能的自由和谐,表征一种适当的审美判断力。
为了将天才的创造与那种仅仅基于趣味的创作区别开来,突出天才“精神”在天才创造中的重要性,康德不厌其烦地阐述了二者的具体活动过程。在康德看来,那些仅靠趣味而进行艺术创作的作家,遵循的是创作的模仿原则。他们绞尽脑汁,反复摸索,为的是要从那些已被公认为经典的作品中,寻找一种适合自己作品的合目的性形式。此类模仿创作,如康德所言,是从业存的作品中抽取“规则”。而天才的创造,则并不需要进行模仿,不需要为自己的作品寻求一种合目的性的形式,恰恰相反,它是“自然给艺术确定规则”[1](P309)。天才艺术的这种“规则”,非常类似于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对道德法则的界定:一种源于理性的自然存在而非任何决定性的规则,其由任何有理性的人类基于自我本性的道德自觉而生。艺术法则与道德法则的这种理念类似性表明:天才的想象力及其感官自然,常与其知性处于一种自由和谐的状态。而天才的“精神”,亦即使心灵有生气的法则,因而就是一种自然合目的性的法则。天才的作品,也并不承载艺术家特定的意图,并不展现特定对象的合目的性观念,而是体现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一如自然美与道德美那般。
由此不难看出,那些仅仅基于趣味的创作,要么传达的是一种有目的的合目的性,要么是一种特定对象的合目的性观念;而其作品,即使偶尔满足审美鉴赏力的要求,也难免有人工斧凿的痕迹。而天才的创造,则不仅能够体现自然合目的性的形式法则,而且能够蕴含自然合目的性的质料内容。所谓“自然合目的性的质料内容”,根据康德,主要是指超感官的自然,或自然的超感官基质,它经由天才的想象力而催生,可以超越常人有限的知性内容。在作于1777至1778年间关于人类学的系列讲座中,康德还对天才的精神与自然的超感官基质间的联系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精神是一种使理念有生气的才能,……理念之所司在知性,但并不是通过抽象,否则其就成为概念。理念作为规则的法则,它与精神的关系是一种双重的统一,亦即分别统一与集合统一。”*Kant,The Pillau Lectures on Anthropology,in Akademie edition,vol.25.p782这里所谓“分别统一”,是指知性概念联接多种经验与经验对象的可能性为一个整体;而“集合统一”,则是指理念在观念中将自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后者并非是关于世界的理性理念,抑或宇宙论理念,它毋宁是自然存在整体的理念,抑或可能存在的自然整体的理念,主要作为前者的先导而存在。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又进一步将“理念的分别统一”发展为自然的系统统一观念,它作为表征人类认知的自然而存在。这样,理念就成了自然合目的性法则的先导。
通过以上分析,康德得出结论:天才作品是其超感官基质感受性的产物,他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直觉与非知性活动。但康德同时也承认,天才的创作还有其终极目的性的一面,亦即它终究难逃规则的统治,它本身仍需停驻在有限的人类知性边界内。那么,如何协调这一明显的矛盾?
二、天才的创造:在有限的人类知性与无限的超越之间
在《判断力批判》第77节,康德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人类一般知性的直观知性,它以非推演性为其特征。康德认为,人类一般的知性具有推演性,它以感官经验事物及其经验直观为其演证来源,服膺于抽象的概念或“分析的普遍性”;而直观知性,其质料内容则由“综合的普遍性”而来,因此毋需理智在个别与普遍之间进行专门联接。康德由此就将直观知性的无限性,与人类一般推演知性的有限性区别开来,并限制了理性的超验使用。
为什么要提出直观知性?因为直观知性可以以其范导性功能,将推演知性所分解的事物联接为一个有机整体。康德认为,我们不能将有机物视为单纯目的或最后目的,而只能将其视为自然目的,否则我们将不能把机械装置中的整体及部分关系,与有机物的整体及部分关系区别开来。后者的独特性在于,它难以根据独立存在的各部分的简单运动获得理解,而必须基于各部分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整体的机能。因为在有机体中,“原因与结果互为自身”[1](P292)。直观知性在这里的作用正在于,它以其范导性理念与形而上学的优先性,将有机体的各部分联接为一个整体。
然而对于有限人类知性而言,有机体自组织的法则仍然神秘难测,就如天才作品的创作法则一样。人们惯于用机械决定论法则解释事物,用外在目的性解释事物存在根据,然而这对于有机体与天才创作而言,都于事无补。天才作品与有机体的类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展现了事物的自组织原则,都体现了部分与整体的互为因果关联,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天才作品分解为各个部分予以单独理解。而天才作品的创作法也很难被我们有限的知性所完全理解。由此便产生了一个悖论:天才的理智最终仍然是人的有限知性而非无限的超越性,因而其作品中所展现的超越内容就非其有限的知性所能理解,既如此,天才作品是如何产生的呢?康德对此的解释是:天才的创作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不能用科学的步骤将其创作过程描述或表征出来”[1](P187)。假如天才能够洞悉其作品的内在理念,那么他就能抽绎出其作品的结构规则,明晓其创作的具体步骤与细节要求。但另一方面,天才的作品又有其有限性,它一旦完成,就立即成为具体作品,因而其创作法则就会或多或少地成为决定性规则,尽管其仍然葆有无限超越性的一面。换句话说,天才的创作法则虽然不能被公式化,天才的作品虽然是无意识的产物,但其作为天才判断力的产物,仍然是有意识的,因为天才可以判断其创作的成与败。
也就是说,正是判断力,在解决天才创造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悖论之间起了关键作用。何以如此?因为既然艺术创作的目的性、决定性规则及其杰出形象并不先于天才作品而存在,那么,那些曾经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艺术创作规则,也就不外乎传达了艺术家认知机能的合目的性和谐。一个基于非决定性原则的天才的“洞见”,虽然不经由判断力,但却可以导致判断力的产生。这一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作了集中阐述:“假如将普通知性解释为一种给定规则的能力,那么判断力就是将特殊归摄于普遍之下的能力。”[2](P268)据此,天才作品的创造,就是天才基于自我认知的机能而精心安排艺术作品的细节并将其纳入合目的性之形式的进程。这也意味着,尽管康德认为天才的作品不能完全归于趣味,但天才创造却预设了趣味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概由于趣味在康德美学中居于特殊地位:它可以判定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是否传达了一种合目的性的法则,并继而唤起观赏者的审美反应。因为根据康德,天才创造与平庸艺术家创作的区别就在于:后者仅仅基于趣味而创作,而前者则并不将自身的诸认知机能归入业已存在的经典艺术规则,而是将其归入自我认知机能的普遍法则之下,目的在于使自身的各项认知机能实现合目的性的和谐。这当然需要灵感与想象力的参与,需要一种知性直观或智的直觉的先验幻想的逻辑存在。
事实上,本文更倾向于认为,康德关于判断力问题的实践论理解,同样适合于对天才问题的分析。康德说:“尽管知性是一种由规则统摄的能力,判断力却是一种更为特殊的才能。一个医生、一个法官或一个政治家,可以在观念上很好地理解病理学的、法学的或者政治学的规则,但是,由于在判断力方面的欠缺,他在具体应用这些规则,或者在确定一些特殊事例是否能归摄于它们之下时,常会犯错误。更进一步,他由于未能在判断力方面受到具体的、范例的抑或实践的足够训练而裹足不前。”[2](P268)而天才的判断力,虽然仍具有抽象的规定性法则意涵,但却必须经由实践的训练与足够的学习而得以纯化与提升。这也就是何以康德要将趣味的习练作为合目的性的天才判断力导向的基本原因。换句话说,除非天才在自然合目的性的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对其业已存在的创造性才能加以训练与学习,否则,其灵感与创造性才能就极易走向衰竭。
由此可见,康德在天才问题上实际留有双重通道,亦即经验的艺术实践与超越的自由创造。前者遵循知性认识的一般规则,因而是有限的人类活动;后者则超越一切已有的定则,在艺术家认知机能的和谐形式引导与灵感激发下,实现无限的自由创造。
但依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既然天才的创造暗示了自然的超感官基质的存在,天才作品表征了将特殊规则归于普遍法则之下的认知机能,那么,不同天才的不同艺术创造,又如何保证其可以传达不同的艺术理念而不至于雷同?
三、天才作品的原创性
西方当代美学关于康德美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就是天才的原创性问题。然而对于天才的原创性到底从何而来,它有什么独特内涵等关键问题,其研究却并不深入。如美国美学家彼得·基维(Peter Kivy)将天才的原创性根源归于天才拥有一种不受概念约束的想象力的自由和谐才能[3](P108),而保罗·盖伊(Paul Guyer)则将其解释为人类理性活动的自然产物,它以偶发性与新奇性为特征,并不遵循现有的艺术规则[4]。实际上,如上两种阐释可谓是关于天才“原创性”问题的主流阐释,但其基本上是对康德文本按图索骥的结果,意在说明,天才的原创性基于天才能够超越固定规则而保持想象力的自由和谐的才能,正是想象力精鹜八极、驰游万仞,不受羁绊的自由活动,才决定了其可以自由地表达不同的审美理念,从而体现出原创性。
这当然没错。事实上康德也认为,天才是一种想象力按照合目的性原则自由结构的能力,亦即将诸多自由概念统一为一个单一理念的能力。它因其超越于具体特殊概念之归摄而表现为心意诸机能之合目的性的自由和谐,从而体现出艺术规则与艺术样貌的原创性,后者不能由前代的艺术范例或艺术规则推演而来。然而设若天才作品仅仅基于其不受规则约束的自由想象力,那么就很难将其与那种根据固定法则而制造的新奇东西区别开来。天才的作品之所以为天才作品,一定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天才的规则入手,来讨论这一问题。天才的规则是自然合目的性的法则,这暗示出,它超越任何人类认知规则的特殊限制而体现出一种自然的超感官基质的理念,亦即一种可以表征其规则的自然原型。正是这种自然原型,才是天才作品原创性的根源。康德在解释这一点时再次援引了有机体的结构方式进行比对说明。按照康德,一旦我们将新组织与其原始物质材料加以拆解,我们就会发现自然存在物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因为人们很难按照有机体自身的结构原则而将其重新组织为一个有机整体。部分之和不等于整体。有机体之中暗藏了某种原创性。康德认为,如同有机体的神奇结构一样,任何人类创作的规则,即使是无限自由组合,都不足以创造一个如同自然造物一样精巧的有机组织,其必有超出人类创作规则之外的自然超感官基质,而后者对我们有限的人类知性而言,仍然神秘难测,一如天才艺术的超感官法则一样。
如果说天才创造的规则只是在形式上与有机体的自组织规则具有类似性的话,那么,天才创造的审美理念,则在结构上与理性理念具有对称性。康德认为,审美理念是理性理念的感官对应物,二者具有结构上的类似性[1](P192),它们都难以由知性概念与知性直观根据确定法则而组合成为知识。理性理念不能产生知识,是因为其没有相应的知性直观;审美理念不能产生知识,则因为它本身就是直观,缺乏相应概念。用康德的话说,审美理念是想象力的象征,没有任何决定的概念可以适应它[1](P192)。在此意义上,审美理念与理性理念都不过是一种消极性的原则。但二者同样有其积极作用,那就是它们都可以超越现象界经验的束缚,表现出超越性的特质。
因此,超验性是审美理念的本质,它决不允许各种经验性概念的浸染,否则,天才作品的原创性就会失去其存在根据。审美理念只能是超验的,只能是一种不同于逻辑概念的审美属性,不能下降为经验主义的心理机制。正是通过此一限定,康德才在根本上切断了其与杰勒德等人关于天才理论的自然关联,使审美理念成为一种由先验原则统摄的创造性想象的产物,而非模仿性想象的结果。审美理念中的这种创造性想象,如康德所言,既不同于理智在纯直观中产生的观念对象,也不同于在超验想象力在对象综合中产生的范畴图式[2](P151),它产生的是一种呈现在直观中的全新自然图像,这一图像虽由自然而来,却在想象力的自由作用下,成为一种迥异于真实自然的艺术自然,此即艺术作品的原创性。
一旦我们把天才作品的原创性问题归结为天才规则的原型属性(archetypal nature),那么,我们就可以解决当代康德研究中惯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天才的悖论”。所谓“天才的悖论”,是指将天才作品的原创性问题归结为审美理念的感性呈现时,自然出现的感官经验表现的有限性与天才作品理念的无限性之间的悖论。因为感性呈现的新奇性,将随着感受次数的递增而逐渐变得陈旧,因此作为审美理念感性呈现的艺术作品,也终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变得平庸,它将不再是“经典”,而事实上,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天才作品视为经典,认为它不会过时。如何解决这一悖论?实际上,只要我们将天才作品的原创性来源归结为审美理念的原型属性,那么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举例来说,就如乔托(Giotto di Bondone)与马萨乔(Masaccio)的绘画可以成为不断被模仿的典范,但正由于其作品的原型本质,它才并不失去其原创性特性,而是持续地激发后代艺术家的无限灵感。这也说明,天才作品还有其另一方面的重要属性:典范性。
四、天才作品的典范性
康德将天才作品的另一个特征界定为典范性,以此进一步区别于那种基于单纯模仿的作品。而所谓“典范性”,是指某艺术作品可以作为该类艺术的标准或者鉴赏判断的规则[1](P186)。作为一种艺术的典范,天才作品既可以在艺术创作的形式与风格方面成为一种模范,又可以为其他的艺术天才提供创作法则,凭此法则,其他艺术家就同样可以创造出具有原创性特征的作品。换句话说,天才创造与模仿创作的另一个重要不同在于,后者遵循的是模仿法则,而前者依照的是遵照法则。而所谓“模仿”,也并不是对艺术模式的盲目机械复制,而是融入了创作者的积极思考与鉴赏判断;这种经由模仿而成的作品虽然在形式和风格上还不能成为艺术创作的典范,但却可以成为检验艺术家创作天才的试金石。而所谓“遵照”,则可以同样创造出能够成为后代艺术家模范的典范作品。如康德所言,“天才是一种在主体认知机能自由运用下所激发的主体自然禀赋的典范原创性;天才作品作为一种典范,既不能习得也不可以教授,而只能归功于天才的某种独创性才能。天才作品并不是用来模仿(因为否则就会丧失其基本精神),而是用来作为其他天才仿效的对象,经由此种仿效,它就可以唤起其他艺术天才的原创性精神,凭此精神,后世艺术家就可以摆脱前代艺术家所创造规则的束缚,创造出同样可以用作艺术典范的新的天才作品来。”[1](P195-196)
天才作品的典范性精神,其重要作用在于,它能唤起后世艺术家的原创性精神。然而对于这种前代艺术与后世艺术的具体唤发关系,康德却语焉不详:“前代艺术到底如何唤发后代艺术,这很难解释清楚。设若在后代艺术家身上同样秉有与前代艺术家一样的精神力量,那么,前代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就可以激发后世艺术家产生类似的创作理念。”[1](P188)实际上,我们可以援引康德关于道德典范的论述来对二者的关系作出细致阐释。诚如康德所警告,我们绝不能将美德的“典范”用作行动的榜样,因为道德榜样仅是道德规则可行性的一种标示,而不是具有美德属性的道德规则来源。可用作原型的道德规则只能是人类的理性,一旦将具体的道德典范作为模仿的榜样,势必导致道德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淖。道德典范因而就绝不是“模仿”的对象,而是“遵照”的对象。道德行为固然可以由道德榜样所激发,但却最终要在道德理念的指导下,调整自身的道德行为,使其适应理性的诫命。同样,在天才创作的典范性情境中,后代天才也要批判性地袭用前代天才艺术的精神,以此实现自身艺术的典范性价值,此其一。
其二,就如现实的道德榜样可以用作强化那些早已存在于人类身上的道德倾向并将其按照理性的方向付诸实践一样,天才作品同样可以提升那些具有天才禀赋的艺术家潜能并使其实现出来。当然,二者在理性理念上并不等同:前者作为一种道德的理念,能够被明确界定并施用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后者则是一个非决定性概念,不能被明确界定,不能施用于每一个理性存在,而只能施用于那些具有天才禀赋的理性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天才作品只有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完成。在此之前,天才只是尽力创造一种不同于现有天才艺术的新的艺术原型,它与先前经典艺术相比,很可能显得是一个另类。那么,如何获得这种机缘呢?条件有二:一是后世天才须将自身置入特定的艺术史情境中,成为艺术天才链条的一环;二是后世天才须抱有一种谦逊的态度,尽力发现前代艺术家的创造性法则与原创性规则,在对前代艺术家创造性法则与原创性规则的继承超越中,实现自我艺术的典范性再创造。
实际上,古往今来的天才艺术典范性创造,无不如此。以视觉艺术为例,文艺复兴时期的视觉艺术遵循的是艺术形式的平面二维创作原则,并通过平面的延展来表现空间的纵深,以此传达静默、和谐、明确的艺术创作理念。然而17世纪的巴洛克艺术终结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前景与后景的不同物象措置来表现空间的纵深,这样就可以使观赏者的视线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持续联系中,此即透视法则。提埃坡罗(Tiepolno)的《最后的晚餐》之不同于达·芬奇(Leonardo do Vinci)的《最后的晚餐》,正在于他将巴洛克艺术的透视法则融入其作品创作中,以此区别于达·芬奇所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创作的平面风格,尽管他们在艺术题材上并无不同。
所以,天才作品的典范性并不意味着天才作品的专断性,恰恰相反,不同艺术类型、不同艺术题材、不同艺术风格往往表现出普遍的联系。这样,天才艺术作品最后就表现为由不同艺术标准、不同艺术类型、不同艺术风格所共同组成的五光十色的艺术世界。
五、结 语
康德关于天才创造规范性问题的讨论假定了自由人性的创造性活动与一种超越创造性主体性的自然超感官基质存在。这两大悬设在天才艺术中表现出来,就是其独创性与典范性。对于前者,本文通过分析天才作品的结构法则,亦即对于我们有限的人类知性而言,其仍然保持着神秘面纱,因此对于任何观赏者而言,它就往往表现为未决定的、偶发性的与原创性的。对于后者,本文阐述了虽然天才作品必须基于自身的艺术传统与时代情境而实现典范性,但是天才艺术的“谦逊”精神却使其允许其他优秀的艺术风格与艺术类型的共同存在,以此实现艺术的繁荣发展。
仍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康德天才创作规则问题的阐释更多地是一种本体论的担当而非普遍知识论的理解。因为只有前者,才可以为阐释康德天才观念对后康德主义哲学家的影响提供丰富资源。但本文并不止于后康德主义哲学家关于康德天才观念影响的解释,而毋宁是要在康德本人与其后继者关于天才问题的解释之间作出区别。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将康德关于天才艺术创造的问题作狭隘诠解的倾向,根据这种诠解,天才艺术创造的有效性限于其自身所处的时代,亦即其独创性与典范性都不能超越天才艺术家自身所处的时代,对于后世艺术,前代艺术很难再起到典范性的作用。本文的一大目的,就是对这种论调进行驳解。
因为我们不能忘记,科学主义中所流行的进步主义叙事,并不适应于艺术领域。康德曾反复谆谆告诫:“艺术领域的天才风格创造,常有一些难以超越的法则,一旦其到达巅峰,就再也难超越一步。”[1](P188)显然,康德明确指出了天才艺术有其止步的地方,一切天才艺术的创造,一旦达到最高峰,那么对于后世艺术家而言,就很难在同类艺术类型与艺术风格上作出超越。换句话说,艺术领域的创造不同于科学领域,它并不导向一种决定论的认知,因此不能将科学领域的进步主义观念,施用于艺术领域,认为后世艺术是对前代艺术水平的提高,是对前代艺术家面临艺术难题的解答。实际上,按照康德,新的艺术风格并不否定其与前代艺术的相关性,并不是对前代艺术的否定发展,前代的天才作品只是由于其自身拥有的原型特质与非决定性本质,才会超越历史,成为激发后世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灵感的无限源泉。
参考文献:
[1] KANT.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M].Trans P. Guyer and E. Matthews, ed. P. Guy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M].Trans. and ed. P. Guyer and A. W. Wo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PETER KIVY. The Possessor and the Possessed: Handel, Mozart, Beethoven, and the Idea of Musical Genius[M].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
[4] PAUL GUYER. Autonomy and Integrity in Kant’s Aesthetics[J].The Monist, 1983,66(2).
——开阔的价值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视野
——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