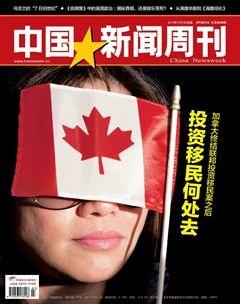“小人物”的罪责
徐贲
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里有一个令人同情的女纳粹罪犯,名叫汉娜。她曾经是奥斯维辛的党卫军看管,在1944年的“死亡跋涉”中,300名犹太妇女在一教堂过夜,大门是锁住的。在空袭中,教堂起火,但汉娜和另外5名看管为了防止囚犯逃跑,没有打开教堂的大门,囚犯们除了一对母女幸免,全部被烧死了。
1960年代,汉娜因这一罪行在法兰克福审判中受审。她在回答法官问题时说,她没有打开门锁是出于警卫的责任,不让囚犯逃跑。一个人尽忠职守,这可以解释为是一个“良心决定”,也就是个人行为的意愿或动机。其他几名受审者的律师把责任推到她的身上。法官要求汉娜写字来看她的笔迹,以决定是否是她写了囚犯死亡事件报告。结果她没有写字,而是直接认了罪,被判了终身监禁的重刑。
汉娜这样做是为了隐藏一个秘密——她是一个不会写字的文盲。这个秘密左右了她的一生。战时,她在工厂做工,被升迁到办公室工作,为了不暴露自己是文盲,她报名去当党卫军的集中营看管。战后,她有了一个电车售票员的工作,也是在从电车售票员被升迁到办公室工作时,因同样的原因不辞而别。让小说叙述者米高·伯格不解的是,“暴露自己是文盲,这样的小事难道比承认自己是杀人主犯更严重吗?”
汉娜由于是一个文盲而犯下了人生的大错,这是否意味着,她犯的罪行因为“无知”而成为可原谅的罪行(即使不是首犯,她仍然对300名囚犯的死亡负有责任)?惩罚一个因为讨生活而误入迷途的小人物,一个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罪犯,这是公正的吗?一个人做一件事,意愿和行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做了坏事,罪过是属于意愿还是行为呢?这样的问题困惑着伯格,他说:“我不是说考虑和决定不影响行为,而是说,行为并不只是考虑或决定的结果,行为有它自己的理由。”
行为有它自己的理由,一旦开始,便不受行为者意志的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人犯下这样的行为罪过,他也就有了免受惩罚的理由吗?他们的行为是否可以用“行为有它自己的理由”,用服从命令、尽忠职守来免除罪责呢?
类似的问题对于许多在其他特殊情况下发生的暴行也是适用的,因此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罪责追究问题。例如,“文革”中,在“阶级斗争”和“文攻武卫”这样的号令下,许多人手上都沾了别人的血,甚至背负着人命。又如何追究这些人的罪责?
在体制内因为“执行工作任务”而犯下的罪行,个人负有怎样的责任呢?施林克在《朗读者》里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对它给出明确的答案。这是因为,法兰克福审判追究的是“谋杀”罪,而谋杀是需要有个人动机和意愿的。以动机和意愿界定谋杀阻挠了对“执行命令者”的审判。如果把谋杀只是界定为故意杀人,而不是扣动枪扳机或把人送进毒气室的话,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荒唐结论:一个人出于自己的意愿杀死一个人,他的罪行要比一个服从命令把成百上千人送进毒气室的罪更加严重。
那些在制度中作恶的人们,如果只有出主意的人才负有“谋杀”的罪责,那么岂不是整个体制中所有其他人员都可以被赦免杀人或残害之罪?法兰克福审判的重点从纳粹的制度性暴行转移到个人的残忍行为,因此受到后来历史研究者的诟病。
在纳粹的作恶机器里,那些直接开枪屠杀或扳动毒气开关的往往是最低层的人员他们是纳粹机器上的小螺丝钉,但是,比他们阶层高的人员也都是一些小螺丝钉,正如阿伦特说的,“就无条件服从元首的命令而言,纳粹机器里的所有人都是小螺丝钉。”
纳粹机器里的每个小螺丝钉,无论他是向下传达上司的命令,还是扣动扳机把子弹射向无辜的受害者,他是否只是在执行命令并不能改变他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罪恶后果,那就是夺走了无辜者的生命。这个个人的“罪”是从他行为的罪恶后果,而不仅仅是从是否有个人动机而来的。任何一个非故意杀人的行为,只要杀了人,就是有“罪”的。
考虑动机涉及的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问题不是他有没有罪,而是什么性质的罪,是否需要考虑到别的原因而(例如“一级谋杀”与“二级谋杀”的区别)。因此,“接受命令”也许可以成为一种减刑因素,但不可以当作脱罪或无罪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