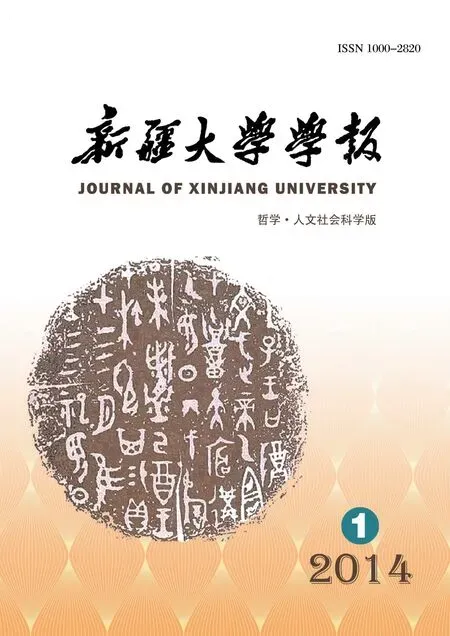都市文化建构与文学书写
——以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写作及她生活的巴黎为中心∗
周仲强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浙江台州318000)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中,出现过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地点:法国巴黎、中国北方、英国、德国、广岛、温哥华、印度支那等等。可以说,这些在文本世界中的空间转换,对于杜拉斯而言,不仅是一种物理和地理的简单变更,这其中还存在着诸多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体验。可以说,巴黎既是杜拉斯生命孤独的牢笼,也是她欲望和想象驰骋的原野,这个世界性大都市记载着杜拉斯的文化体悟、抗争历史与情感记忆,而杜拉斯的生活情怀和生命姿态,以及在此过程中孕育的文学热情和写作实践,也同样都参与到了巴黎的都市想象和文化建构中。
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杜拉斯在与巴黎结缘及其对这个世界之都的理解和书写的过程中,主体历史与都市历史所共同参与的文化精神建构,呈现出怎样的断裂与延续?通过杜拉斯与巴黎的依存、隔膜甚而体现出来的反抗意识,都市文化建构中,边缘与中心的想象性转换如何在杜拉斯的身上得以体现?不仅如此,通过杜拉斯在巴黎的欲望追逐与抒情呈现,可以揭示情感建构和精神升华的必要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都市生活与历史延续所面临的文化省思。
一、历史断裂与精神延续
杜拉斯在法国巴黎有三处属于自己的住所,分别是巴黎第六区圣伯努瓦街5号、诺夫勒城堡和特鲁维尔黑岩区,从她以杜拉斯为笔名进行文学创作开始,这些以巴黎都市内外为空间的城市生活,记录了她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和写作岁月。在杜拉斯的一生中,城市呈现的作用不仅仅为作者提供了赖以生活的空间并以此空间作为生命驻留的痕迹记录,还提供了创作者集中思考人类情感和生命的思维空间和情感流淌的路线空间,更进一层讲,城市是杜拉斯写作的精神之根。巴黎创造了杜拉斯,而杜拉斯也用她的想象创造了巴黎新的形象及阅读这个都市的形式。在杜拉斯的小说中,对都市人的生活,不是简单地对他们作现实性的陈述,而是通过与城市精神或文化的对接、契合,来介入他们的生活,以及以逆时空的方法,再现他们对于现实和生命的不懈追求和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伴生的精神迷茫和困惑。从空间的角度而言,地理意义上的都市是一个固化的整体,记载着其衍化的历史和现在,然而都市文化的存在又体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指示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性;不仅如此,都市历史和文化的形成,往往承载着个体生活历史和情感书写的延续,都市文化的浮现与基于主体性而进行的文学书写之间,存在着互为建构的关系。
巴黎,这个梦幻之都,缔造了杜拉斯的反抗精神和生命诗意,她在这里漂泊求索,无所归依,陷入了敌人和死亡同在、情爱与激情并存的困境中。巴黎的圣伯努瓦街,在法国大革命时,作为革命精神的标志和象征,一度成为法国人心中的念想。在这个曾经的革命前沿,法国共产主义以此为战斗基地,历经风雨如晦的岁月洗礼,最终成为行动成功的实践典范,以其盛名和传说流播于近代法国历史,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法国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世界的电击。”[1]而且诸多文学写作者也齐聚于此,见证了巴黎历史文化的断裂与延续,这个具有多元历史意义的空间之于杜拉斯而言,同样举足轻重——“那就像是一间启蒙之屋”—–圣伯努瓦已然成为了杜拉斯内心永恒不灭的精神圣地。圣伯努瓦街5号公寓,从空间和地理的角度而言,虽则只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但它早已超越自我的界限,化身为革命精神的象征。李平认为:“地域化、个别化的东西演化为国家的艺术形态,接着影响了全球,这是西方现代都市文化的重要特点。”[2]虽然李平是从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海拔来论述空间的延伸和拓展功能,但两者所体现的道理基本相似。尽管这里偶尔被杜拉斯冷处理,《外面的世界》中公寓被描绘成波德莱尔式的“恶之花”,正如她在《巴黎》一文中将巴黎形容为一个充满“巨大失误”的大城市一样,让人无法忍受,但巴黎和圣伯努瓦街仍无疑是她毕生感念的生活空间,也是她思想和言说的精神根基却是不变的。杜拉斯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完全居住在一个地方,一个女人的存在充满了一个地方。一个男人则是穿过一个地方,并不真正居住在那里。(《话多的女人》)”。与男性对空间的疏离不同的是,空间对女性的独特意味,更多地通过女性对空间的依赖得以呈现,而寄寓于期间的情感言说,可以为女性的文学书写提供饱满的精神蕴藉,巴黎这一世界性都市之于杜拉斯,即为如此。
列斐伏尔在其著名的《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空间作为一种生产的对象,其建构依赖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材料[3]。都市空间与主体书写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呈现的关系,而且倾向于以意识形态为旨归。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个互为生产的过程,却并不总是以直接而迅捷的方式而存在,体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复杂性。带着“殖民地来的孩子”这样尴尬的“身份”和矛盾的心情回到法国的杜拉斯,履历和情感的表现出现了断裂。这种生活经历和由这种经历产生的情感因此让杜拉斯对印度支那情感讳莫如深,这种隐性的回避可以从她的前两部小说中看出:在小说《无耻之徒》、《平静的生活》中,小说叙述的是她刚回法国时,在外省的家庭生活和自然环境中,所体验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身关系之间的剑拔弩张。在这里,印度支那这个名字以及杜拉斯自身在印度支那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在其文学书写中出现了“断裂”,这其实是杜拉斯起初对自己生活历史的有意无意的“排斥”,然而,刻意的规避使杜拉斯小说的想象力和生命力无法得到凸显。而当杜拉斯将目光转向她的生命源头—–东方,以及她最初的情感根基——童年时,《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为她指明了写作的方向。事实上,当她的笔触移到那片遥远的东方土地,无论是童年的欢歌笑语,抑或湄公河边的无眠之夜,无论是太平洋南岸的南亚丛林,还是海水浸泡的大片沼泽,以及小说世界中亲切自在的人物关系和细腻周全的个性心理,都存在着一种尘封的记忆和奔流的情感豁然打开之后的自然天成。在杜拉斯回归自我历史的书写过程中,生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不仅作者的情感因此变得更为自信与丰腴,而且小说中的空间和人物也同样获得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杜拉斯来到了巴黎,进入了这个世界之都的历史一角,却无法以一种最为直接的方式,通过正面描述巴黎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现实,实现都市与个人之间的有效接续;而当她返归自我历史和主体身份,并在这种元认知中,切入自身最熟悉的东方生活,进行延续个体历史的文学书写时,却能够传达出更为深刻的启示。其中似乎与她在巴黎的生活现实和文化想象存在着某些深层的龃龉,但这恰恰能体现出都市文化的宽厚与广博,及其在建构过程中所蕴含的包容性和可能性,这正如沃尔思在《都市社会与文明》中所说的,“城市并不单单指大量的人集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它也是一个由彼此不同特征上表现出超常多样性的人所形成的区域。”[4]从这个角度讲,多样化的生活经验与都市文化发展历史是同构的,前者可以通过想象性的建构来阐述后者,尤其针对都市的存在状况,其自身必然有着光鲜夺目的历史或现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变迁和动荡是无处不在的,即便是历史发展的延续性遭遇断裂,其本身的精神文化属性却仍会一以贯之。而对于城市中的精神主体——尤其写作者而言,只有直面生活历史的断裂,才能在与都市历史的对接中,实现更为深刻的精神重组和接合,虽说只是一种想象性和形式化的铺延,但这不仅为都市的文化历史实现整一性,而且恢复生活于其中的民众自我的主体感觉传统,有利于形成统合性的知识主体和精神构架,从而使都市文化在其历史沿革中不至于缺失市民化和传统化的根基。
二、边缘态度与文化省思
刘易斯·芒福德在提到城市对人类的贡献时提出,城市以其高度集中的物质和文化要素,作用于人类的生活和精神场域,进而协调和加速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城市(尤其是现代都市)的存在,必然坐拥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并且在文化的传衍和播撒中,体现出并依赖于人的能动性,因而在这个过程中,固然需要通过正面的建构,达到直接的物质生成和精神延伸,但另一方面,往往需要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冷却,通过重置或虚设的方式,重新以边缘化的视角观察自身,以实现冷静思考和潜心创造的可能。不仅如此,拥有一种边缘的态度有助于现代都市进行自我的反思与文化的创生。由于变动和改革,城市的肌体总是不可避免地伤筋动骨,因而也需要持续性的自我疗救,在这种情况下,“边缘”则体现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客观而清醒的注视、倾听和诊疗方式。事实上,地理空间本身的重要性实际上蕴含着文化权力的隐喻,而文学的存在,则是以一种“主观性”的姿态,触及特定空间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意义。巴黎是一个充满着优越感的都市,占据着法国文化的中心地位,无论是谁,只要进入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可以说,这个人不但肉体已经进入这个空间,而且精神也与城市文化高度融合。对于杜拉斯而言,相当于文化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入世”,可以想见,如果她一直生活在越南,那么无论她怎样努力写作,都难以成就后来深深嵌入到巴黎文化甚至整个现代都市文化中的那个杜拉斯。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地域转换,实现的是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化调置,这也使得杜拉斯具备了多重的体验和视野,而其中所产生的断裂和接续,则让作为文学写作者的她获取了审视的眼光和省思的意识。
不仅如此,在远离中心的虚荣与迷狂之后,带着经历创伤绝望后平静的心情,杜拉斯选择了旁观和侧望的姿态来省思巴黎这一现代都市的存在。诺夫勒城堡是在杜拉斯的文学写作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个场域。1958年,杜拉斯在这幢浓荫环绕巴黎郊外的房子中“疯狂地”写作,空间上的与世隔绝也助推了她内心的孤独感,小说《副领事》则是这一期间最为重要的作品。可以说,杜拉斯远离了巴黎的政治文化喧嚣,这不仅代表着在她身上的种族和精神界限得以打破,不再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所制肘,而且以“边缘”化的姿态回归主体并以此参与审视“中心”的写作,也揭示了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的杜拉斯的精神旨向和政治策略,可以说,杜拉斯所坚持的“边缘化”立场,恰恰是作为写作者的她的主体内部所坚持的“中心”,然而这种态度并不是抽象的,而是融入了她的精神内核,衍化为日常存在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以此生发出范围更为阔大的直面和关怀。在这个过程中,反抗的介入让写作主体获得了一种由内而外的文化探索的能量,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则表现为对新的文化图景和社会价值的想象。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都市文化的建构过程中,以权力和真理的面目出现的“中心”,往往以一种支配和控制的形式出现,面对这种空间的霸权和文化的“真理”,杜拉斯并没有选择正面地抗击,也没有着力于通过投身于革命的实践,来达到改良社会政治生态的目标。她的出发点是借助于文本形式,展现女性的坚毅和柔性,通过层层剖析,让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改善社会面貌的欲望来寄寓自身的精神旨归和文化建构,并以此作为她对都市文化建构思考的归宿。在《副领事》这部小说中,杜拉斯不仅着重塑造了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女乞丐和斯特雷泰尔夫人等主要人物,而且描述了诸多的白人男女如夏尔·罗塞特、米歇尔·理查逊、彼得·摩根等人在“亚洲”的举止言行。其中,小说讲述了副领事三次毫无缘由地离开巴黎,而来到印度之后的他却并没有完整的性格和形象,他对大使夫人存有匪夷所思的爱恋,夹杂着许多令人无法揣测的思绪和莫名其妙的言语,而至于他为何突然开枪杀死麻风病人,又如何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作者似乎都无意回答这些问题,在杜拉斯笔下,呈现出来的只是一个意识涣散、精神碎片式的个体形象,人物的存在充满了荒诞意味,这对于“新小说”的创作目的而言,似乎是要让传统处于边缘地位的读者参与其中,加入到文本世界的中心,发挥自身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以填补和提升作品的意蕴。除此之外,与此相联系的还在于作者通过副领事随意辗转于巴黎和印度两地,以这种象征性的空间转换,实现对来自法国巴黎的白人男性的审视,显然,从西方文化中心来到东方印度的副领事,带来的并不是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优越,恰恰相反,当他来到印度之后,“毛病”就开始发作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变得毫无生活章法和情感逻辑,可以说,这种意义上的精神架空,代表了杜拉斯对“中心”文化的深刻反思。
可以说,杜拉斯以“边缘”知识分子的角色,参与到巴黎政治历史的建构中,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她更多的是以精神流浪者的身份出现,在她内心似乎存在着一个随处飘移无法安置的灵魂,然而也正是以这种生存、思考和实践的姿态,杜拉斯为自身的言说争取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场域,并进而以此参与到巴黎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建构中。
三、欲望表达与抒情建构
当年狄更斯、巴尔扎克、德莱塞们通过忠实、客观、淋漓尽致的细节描绘刻画了“触须般神秘发展着”的、作为人类欲望和意志搏斗战场的19世纪的大都会,而当代作家既承继了历史又只能浮光掠影表现都会碎片式的感官体验。一方面,巴黎空间本身所蕴涵的人文意义和价值深刻影响了几代作家,另一方面,消费原则对都市审美的巨大影响让人无所逃遁。都市的作家和人群深受现实和想象文化的双重影响。身体及感官的欲望表达、都市的想象抒情体验是作家参与都市文化建构的主要手段,也是文学书写的必须。都市通过色彩、音箱、气味、空间等诉诸感官,都市细节转化为主体的感受,人的审美方式和审美体验更多地表现为破碎的、平面的、晕眩的、浓烈的刹那体验。都市和商品改变了人群的审美模式,当下审美模式特别关注客体对象的审美性,感官、感性、肉体的崇拜是重要特点,身体和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身体、欲望成为都市景观的一部分,供人欣赏、浏览、陶醉。外部的世界、人的欲望如何转化为内心的抒情内容,就构成不同作家深刻地差异性。杜拉斯这样有着深厚生活沉淀的作家在欲望表达和抒情中就彰显历史反思、不同地域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塑造,成为不可多得的名家,而新生代作家就只能是“感时花溅泪”而鲜有历史的内涵了。但有一点应肯定,那就是,建立在欲望基础上的抒情都具有鲜明的当下都市文化的特征,这是身处其中的作家所无法回避的。
杜拉斯在晚年还遭遇了“迟来的春天”,在特鲁维尔的海边公寓,这个与哈佛港对望的著名建筑,茕茕孑立的杜拉斯被她的情人亚恩·安德烈亚所打动,蜚声中外的小说《情人》即以此为关键要素。可以说,热烈的情感与杜拉斯的写作和生活相依相伴,使她沉浸在身体的依恋与精神的圆融中,生命欲望与创作激情重新被点燃和喷发,并写出了《劳儿之劫》、《死亡的疾病》、《埃米莉·L》等作品,一定程度而言,欲望不仅贯穿了杜拉斯的整个生命,而且还是她生活和写作的重要动力。在杜拉斯的小说中,生活空间衍化为文本世界的中心场域,“自己的房间”变成了“作品的房间”,这是在经过了炽烈的想象升华之后,形成的既“真实”又“虚构”的情感世界和言说空间。
空间场域的转换、现实政治的选择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对于作家而言,都面临着种种难以克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文学书写和文本建构的方式,以抒情为名义实现自我的意义转向,并最终寻求自我的精神救赎,成为了置身巴黎的杜拉斯的必经之路。正如菲利普·巴格比所提到的,“我们除了可以在时间中,也可以在空间中置换位置来寻求拯救。毋宁是去墨西哥或者南海,而不是去美弟奇的弗罗伦萨或伯里克利的希腊。我们甚至可以在我们自己社会的不同阶层的生活中寻求逃避,可以去模仿农民,电影明星或者匪徒的生活。”[5]与其说这是“逃避”,不如将其作为一种以文学书写的方式进行的想象性补偿和拯救。在空间转移与置换的过程中,贯穿着杜拉斯的欲望、孤独和反抗,杜拉斯在远离中心的边缘处境里,体验着革命的激情与激越的反抗,并在炽烈的爱情达臻情感和意绪的峰值,进一步组织起针对欲望本身的书写,以此实现对于自我内心的精神救赎,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回到杜拉斯的边缘和反抗主题,即便个体生命在欲望的挣扎甚或遭受破灭致使“绝望”的过程中,依然可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生命的绝望,以“硬”的姿态回望生命,借以抵御这个世界的“阴晴圆缺”,希冀重回生命的极致和辉煌。在杜拉斯看来,任何形式的自我欣赏和自我满足,不仅不是一种精神的“伟大”,反而是一种精神上侏儒式的显现,当一个人处于精神和欲望的沙漠之境时,唯有通过文学的方式,重回生命的诗意之所,以文本形式的抒情建构,照亮混沌而幽暗的心灵,并进而实现特定涵义的文化建构。
可以说,在都市文化的建构过程中,空间的现实历史和文化涵蕴为文学的发生和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思想素材和写作冲动。繁荣的经济、发达的出版条件和开放的文化环境,为文学活动在现代都市空间中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然而在文学文本所构造的世界中,空间的意义并不单单限定为人物生活和行为的地点,更重要的还在于,写作过程中由于主体意识的存在与活跃而营构的叙述空间,以及写作者思维领域的广度与精神维度的拓深,为都市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具有人本色彩和人文意味的启发。对于杜拉斯而言,现实的巴黎都市生活形成了她最直接的感觉经验、最主要的情感生发和最深沉的现实省思,而虚构意味浓厚的文学文本书写,则显示了作者的反抗意识、欲望延展和抒情建构,这种不断延展的扩张在杜拉斯的文本世界中开辟出了一条宽阔无比的道路,文学则以其广阔的情感空间和深沉的精神寄寓,与真实的都市文化建构实践交织在一起,以经验历史与现实实践为底基,以想象的欲望、话语的延伸和抒情的建构完成主要的支撑架设,进而筑垒起坚实庞大的都市文化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