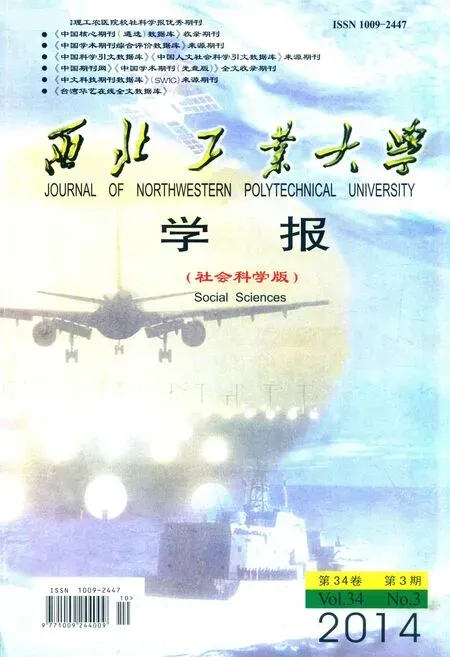存在主义文学视阈中的哲学话语
唐永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江苏 南京 210003)
宗教的祛魅与世俗化,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戕害与异化,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启蒙理性的重大危机,这一切都使现代人陷入了对人的存在意义、本质和前途命运的深度反思之中。存在主义正是在现代人迫切需要新的价值尺度来化解存在的危机感时应运而生,并与其文学形式一起迅速填补了世人的价值真空,成为重塑西方世界价值体系的及时雨。它在法国思想文化界迅速崛起,并曾一度蔚为状观,邀约了萨特、加缪等一大批追随者。
存在主义主要滥觞于克尔凯郭尔的神秘主义,并广泛承受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等思想的激荡,经历了从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过渡到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的理论塑造。本文鉴于研究视阈所限,将存在主义的内涵限定为以萨特为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并兼顾其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存在主义者认为,人是世界的立法者而不是神,自我是宇宙的中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因“自我”而存在。但是,存在主义也承认渺小的人在面对沉默着的非理性世界对“自我”的限制时挥之不去的“恐惧”,并侧重于告诫人们要在荒诞世界中“自我选择”,自我造就,自我定义存在的意义,从而摆脱无意义的人生困境。
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形象化图解的存在主义文学,正是筑基于“恐惧”“冷漠”“荒诞”“自由选择”“责任”“行动”等哲学蕴涵之上,并调动相关的文学符码构成强磁性的哲学-文学场域,从而在文学与哲学的双向互动中沉淀出各自的澄明。正如安德烈·莫洛亚所说,存在主义的成功之处乃是“把这种哲学运用于小说和戏剧,为小说和戏剧增加了分量,带来了反响。而反过来,小说和戏剧赋予存在主义在现代思想中一种不经这些作品体现便永远不会有的威力”[1]。
一、普遍境遇下的个人
存在主义哲学从其始祖克尔凯郭尔开始便突破了西方滥觞于古希腊的从概念到概念的理性思辨哲学的藩篱,将个人作为中心范畴引入哲学体系,并把他们放置于荒谬世界的灰色图景之中进行考察,进而在个人与世界之间紧张的共存态中摩擦出烈焰般的哲思。与此相一致,在这桌由哲学大师烹饪的文学大餐之中,作家们将笔墨直接介入“面对荒谬的赤裸裸的人”“被异化的、被改变的、被神化的个别的人”,以此在人的姿态与荒诞处境之间巧构出冲击性的艺术张力。
存在主义文学往往将主人公置于人类的普遍境遇之中,并在想要获得存在意义的个人和沉默的无理性的世界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态中,在对同一情境下做出不同选择的人的褒贬分明中,直捣生存的本质。正如萨特概括的那样,存在主义作家要“迫使人物陷入这种普遍的和极端的处境,只让他们二者择一,别无他法”(生与死、善与恶、是与非等),并关心“极限的情境以及处在这种情境中的人的反应”[2]。当然,存在主义文学中创设的“境遇”,不同于以往现实主义小说的客观化“环境”,即仅仅是作为人物活动场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它着力表现的是一种人的环境,“即只为存在主义的人物提供一个主观感受和自由选择的客观条件”[3]的主观化环境。这其中,首推死亡这一人类共同面临的境遇最具普适性和严峻性。
存在主义文学作为一种直面生存意义的文学流派,死亡成了其不能绕开的重大话题,并被视为达到存在主义哲学高度的契机。存在主义不像宗教那样虚构一个永恒的天国作为精神麻醉药,而是激励人人像西西弗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并葆有“踏着沉重而匀整的步伐走向永远不知何时才会结束的磨难”[4]式的悲壮精神,在热爱生的情况下自觉地走向死亡。在加缪的代表作《鼠疫》中,身处奥兰这个因遭受鼠疫而被窒息被隔离被流放的城市,只有do or die 的抉择,在主人公贝里厄医生与死神奋力搏击的感召下,一切听凭上帝安排的神父帕纳鲁、追求个人幸福的热恋青年朗贝尔等都最终加入到反抗的阵营中。这样,小说通过人物的“自由选择”,构成了与《墙》《局外人》《苍蝇》《恶心》等类似的境遇对个人的压迫与个人对境遇的反抗的二元对立模式。
不过,正如小说结尾揭示的那样,“每个人身上都带有鼠疫,世界上没有人是清白的”,“鼠疫杆菌不会灭亡,也不会永远消失……也许有一天,它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5]。可见,在人与世界的较量中,人类永远都是暂时的胜利而永远的失败,进而在“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中顿生荒谬感。因此可以说,存在主义是将死亡悬搁在一边,在“没有道理”的出生和“没有道理”的死亡之间的短暂人生中以自由行动来模铸自我的意义。
二、心与行的交错叠加
存在主义的“存在”重点关注的是与社会存在和个人的现实存在相对立的个人的精神存在,强调把想要获得存在意义的渺小个人在面对沉默的非理性世界时最复杂最隐秘的内心赤裸裸地呈现。因此,存在主义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以便于作家更自由地进入“我”的“自我”世界,便于作家更细致更深入地描摹“我”对外界的情绪体验。此笔法的纯熟运用,显示了对西方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这一小说传统的继承,更为之后的意识流小说的诞生开拓了新的艺术视界。
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存在主义文学的惯用伎俩是把外在的行动与内在的心理分析交错叠加,把日常生活表象的叙述与人物思想意识的袒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既有作为行动铺垫的心理剖析,也有行动之后心理的突变,充分展现了自我与自我以外的一切之间的激烈冲突与相互作用。随着文本的展开,书中的人物也跟着作者一道,对世界、对人生不断追问,不断探索。这种探索因结论的荒诞而悲颓,因过程的不断反抗而壮丽。纵观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萨特和加缪一生的创作,前期的创作因倾向于荒诞而悲(对现存世界和人的解构),后期的创作则因倾向于反抗而壮(对世界和人的理想态的建构),是对存在的单纯体验向实践的过渡。不管是解构还是建构、顺从还是反抗、悲观还是乐观,这一切都凝念在了人物心与行的双向互动之中。
例如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采用日记体连缀而成的形式,通过主人公洛根丁的内心独白来表达人们对环境的陌生感、恐惧感、厌恶感等莫能名状、不可驱遣的内心感受(恶心)。如小说以一次照镜子的经历展开了两页有余的心里独白,从而完成了主人公的自我审视:
墙上有一个白色的洞,那是镜子。这是一个陷阱。……镜子里照出来的面孔是我的面孔。……我对这个面孔一点也不了解。别人的面孔都有一定的意义。我的却没有。我甚至不能决定它到底是美或是丑。……也许一个人要理解自己的面孔并不可能。也许这只是由于我是一个孤独的人?那些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学会了在镜子里看自己的面孔,他们看出来的面孔和他们显示给朋友们看的面孔完全相同。我却没有朋友;是由于这样我的肉才显得这么赤裸吗?[6]
在“我”与“我”面孔的疏离背后,是身体和精神之间意义链条的断裂,是主人公对整个世界的陌生以及跻身其中的难以排遣难以摆脱的孤独、恶心之感。此后,“恶心”愈加牢牢地抓住了主人公,甚至霸占了他之前唯一的避难所。“还有我——软弱,疲惫,下流,胃里在消化着和脑子里翻腾着一些忧郁的思想——‘我’是多余的。”照镜子——恶心——去咖啡馆寻求解脱未遂,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从行动到心理再到行动的多米诺骨牌的联动效应,是对人物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多角度透析,从而给人物以鲜活的血肉。
此外,诸如《墙》《局外人》《一代名流》《艾罗斯特拉特》《堕落》等通篇都是主人公心理独白式的情绪体验,其间穿插琐碎的生活细节,并将之纳入一个荒诞非实的框架中,以此表明世界的破碎、不合理与缺乏逻辑,人处境的荒谬与绝望。这既区别于西方传统小说以叙述为主、心理描写作为陪衬的理性架构,也不同于意识流小说用心理活动侵占叙述话语权的情感线索,而是把心理描写浑融于叙述之中的理性与情感的互补,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文学向后现代文学过渡的艺术表征。而这一切,都深深地镌刻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印记,贯穿了外在世界与内在心灵之间激烈对抗的主旨。
三、自由选择酝酿情节突转
存在主义者虽然浸润了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无意义的”悲观色彩,却将对待荒诞的态度作为重点,执着地追寻荒诞境遇中人生的意义。他们认为,在人类幻想的主宰上帝退休之后,人被抛弃在了绝对自由的境地之中,可以自由地做出任何选择以确定自身的本质,但也必须为之负责。为了强调“自由”和“负责”,存在主义作家们在情节的安排上,常常把人物逼到一个不得不做出选择的境遇,构成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连锁式突转的契机。此外,偶然因素的叠加也从另一侧面增添了世界的荒诞性和人生的无常性。
自由选择是萨特存在主义的精义所在,而他的文学创作则是对这一命题的形象化解说。在他的名剧《苍蝇》中,俄瑞斯忒斯本是一个奉行“永远也不介入才是上等人”的青年,在踏上故土的时候得知他的母亲和奸夫密谋杀害了其父篡夺了皇位,人们不加反抗地接受了这一切,因此集体受苍蝇(象征悔恨)的责罚。在复仇与忍让之间,他没有听从朱庇特叫他忍让离开的指示,勇敢地向奸夫淫妇举起了杀戮之刀,从而开创了自己的未来也改变了臣民的命运。萨特通过朱庇特疲软的叹息“一旦自由在人的灵魂里爆发出威力,神对他也无能为力了”与俄瑞斯忒斯勇敢的宣言“朱庇特,你是众神之王,宝石及星星之王,海涛之王,但你却不是人中之王”之间的对比,向世人表明,“世上没有什么上帝,也没有什么宿命,人要成为什么,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不再局限于个人,还包含他人的自由”[7]。
在他的短篇名作《墙》中,作者用命运的偶然来戏谑主人公严肃的选择,将情节的突转巧构于谎言成真,点出人生处处布满限制自由的“墙”,揭示人的存在与死亡的偶然性与荒谬性。“我”的本意是牺牲自己、保全战友,结果却歪打正着出卖了他,变成了“叛徒”,“整个斗争过程一下子失去了意义,变得不可理喻”[8]。一墙(不可抗拒的命运)之隔,构成了“想生者必死,想死者独生”式的追求目的与结果之间的激烈冲突,将整个世界对人价值的彻底否定凸现于读者的视界。从而与存在主义文学东方化的经典表述《围城》之中“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的荒诞意念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名剧《禁闭》则在自由选择的框架下,从“世界上的确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生活在地狱里……因为他们太依赖别人的判断了”反面论证了自由选择:人没有先天的本质,应该勇敢地抛弃过去的负累与他人的成见,去展开人生的“无限可能性”。
俄瑞斯忒斯反叛了神的意志选择了复仇,从而结束了苍蝇对阿耳戈斯城臣民无休止的折磨,然而却不被其姐和臣民理解;贝尔纳·里厄医生选择了与鼠疫殊死地抗争,最终挽救了奥兰全城人的生命;马蒂厄·特拉吕选择了直面战争风暴和民族危难,完成了人生价值的升华;海兰娜选择了孤身一人营救同志,最终以生命为代价赢得了爱情;默尔索选择了对生与死,对亲情、爱情和友情漠然处之,以此作为对世界的混乱、伦理的伪善、司法的荒诞、宗教的虚妄的绝望的反叛和自我放逐,成就了“没有任何英雄行为,却是为真理而死”[9]的荒诞英雄。在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中,自由选择实者是对自己命运的主宰,选择之后的情节突转实者是人物命运的突转,两者都诉诸于存在主义宣扬的人的绝对自由。
四、冷漠的叙语与情绪化的对白
在语言艺术上,为了更好地表现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存在主义小说与戏剧各展所长,呈现出冷漠的叙语与情绪化的对白之间鲜明的异质性。
存在主义小说因为不讲求情节的复杂曲折和性格的鲜明,而更侧重人物心理状态的剖析和人生哲理的阐释,所以存在主义小说的语言常常是客观的冷漠的,迥异于传统小说理性的均衡的叙述节奏,突破了叙述者的话语霸权。作家们忠实地赤裸裸地叙述,自觉抵制“渲染”“概括”“集中”等典型化的艺术手法,不雕琢“细节上的真实”,不塑造“本质上的真实”,而是近乎自然主义的“真人真事”,在荒谬世界与讲述荒谬世界的冷峻笔触之间对比出强烈的艺术张力,在琐细的生活片段中真实地传达出孤独、焦虑、空虚等情绪,表现了世界的不合理性和人的精神困境。在《墙》《局外人》《恶心》《一个企业家的童年》《艾罗斯特拉特》等之中,这种冷漠客观的叙述笔调在小说荒诞氛围的营造上助力不少。这其中的经典片段首推《局外人》的开头: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楚。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乘两点钟的公共汽车,下午到,还赶得上守灵,明天晚上就能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样的理由,他不能拒绝。不过,他似乎不大高兴。我甚至跟他说:“这可不是我的错。”他没有理我。我想我不该跟他说这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可请求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后天他看见我戴孝的时候,一定会安慰我的。现在有点像是妈妈还没有死似的,不过一下葬,那可就是一桩已经了结的事了,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10]
简练得近乎枯涩的笔触,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口吻,强烈地撞击着读者的审美感官,使读者一下就揣摩出小说的情感基调,并以此调整阅读时的情感距离。
即使在加缪“反抗哲学”最精彩的文学呈现《鼠疫》中,作者依然将自己主观的因素巧妙地藏了起来,赋予笔下人物“自我选择”的自由,而不是用作家的自我置换人物的自我,干预人物的行动和命运。加缪曾说,“用真实的感情进行叙述,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象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11]。萨特也认为,作家一旦把他笔下的人物牢牢控制住,人物就成了没有自然生气的物件。像小说《墙》中,作者并没有塑造高大无畏的革命英雄,而是写了一个一样怕死,之所以不出卖战友只是因为固执的普通革命者。主人公不再是像传统小说那样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真实的人,不拔高,亦不贬低。
在戏剧方面,存在主义戏剧能够在大师如林的西方剧坛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归功于萨特的“情境剧”①。在《苍蝇》《禁闭》《死无葬身之地》等戏剧中,萨特给剧中人设置了特定的情境,并把人物的命运逼迫到非此即彼的选择中,从而构成强烈的戏剧冲突,人物的性格也在不断地生成之中。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以人物的对白连缀成篇的戏剧语言,与小说客观冷漠的叙语相比呈现出明显的情绪化,“散发着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主观意志论的气息”[12]。正如不阿德福尔指出的那样,“与叙述文学不同……解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必须让人看见。戏剧艺术比其他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更要求有自己特有的手法:情节简化快速,心理动机夸张,语言要使观众迅速地从形象到象征……”[4]。这种情绪化的人物对白,在戏剧《魔鬼与上帝》之中展示得淋漓尽致:
诺萨克:农民在你眼里算老几?说穿了,你要的是我们的命。
舒尔汉:你想用我们的血来洗刷你娘干下的丑事?
诺萨克:你想充当德国贵族的掘墓人?
格茨:兄弟们,我最爱的兄弟们,我简直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
里歇尔:你不知道你的举动是在往火药桶上点火吗?如果我们不立时把土地、金子、直至贴身衬衣都给农民,外加对他们的祝福,他们会成为一群疯子。这你知道吗?
舒尔汉:你不知道他们会在我们的城堡里来围攻我们吗?
里歇尔:你不知道我们同意了就得破产,拒绝了就得掉脑袋吗?
(第二幕第四场)[13]
主人公格茨在极恶与极善之间摇摆,最终于极端的抉择中与上帝分道扬镳,形成了自己的性格。正如《魔鬼与上帝》,存在主义戏剧之中常常贯穿着一条跌宕的变化线,情境在不断变化,人通过自由选择也在不断生成自己的性格,而连缀情境与情境、行动与行动之间的,则是人物之间剑拔弩张的矛盾与饱含情绪的语言。由此可见,在语言艺术方面,存在主义小说更显对传统小说的反叛与疏离,而存在主义戏剧则更显对传统的继承与吸收,即古典的戏剧艺术形式与现代的哲理——存在主义哲学——的嫁接。
通过以上的文学技艺,存在主义哲学元素被巧妙地浇铸于字里行间,被词语的音响和形体吸收,形成了存在主义文学强磁性的哲学-文学场域,奠定了其在人类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总之,作为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人悲观、失落、找不到出路等心曲的哲学化和文学化表述,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这对并蒂莲,从兴起到鼎盛再到衰落不过短短几十年,最终因没能开出根本的救赎之路而被搁浅在了历史无情的洪流之中。不过,这些左手写论辩、右手作诗文的存在主义大家们,从假想的上帝之光中挣脱,直面荒谬人生,进而摈弃“个人”投入马克思主义行列的精神探索过程,将留给后人怎样永恒的人文关怀和理性启迪?人类对存在矢志不渝的叩问与跋涉,又将凝结成怎样的思想链条与心路历程?
【注 释】
① 加缪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鼠疫》和《局外人》上,戏剧创作因结构不太理想、对白寓意过深被后人提及的不多,主要有《误会》、《卡拉古力》、《戒严》、《正义》等。
[1]柳鸣九.萨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3]王林.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真实性[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
[4]加缪.西西弗斯神话[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5]加缪.加缪文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6]柳鸣九.萨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7]王金梯,李玉双.从《苍蝇》看萨特存在主义文学[J].山东科学大学学报,2001,(12).
[8]朱维之等.外国文学史(欧美卷)[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9]郑克鲁.存在主义文学、加缪和《沉默的人》[J].名作欣赏,1981,(1).
[10]加缪.加缪全集(小说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1]刘雪芹.反抗的人生——论加缪的《鼠疫》[J].外国文学研究,1992,(4).
[12]杜小真.萨特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3]曾艳兵.文学化的哲学与哲学化的文学——论存在主义文学[J].外国文学研究,19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