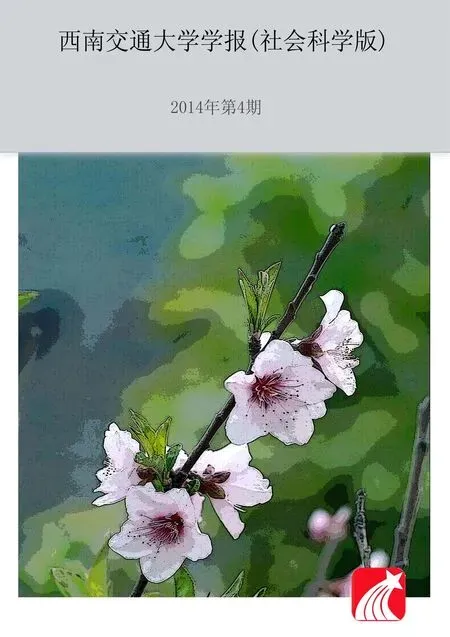历史叙事的口传范式——以苗族古歌为例
李一如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由于在历史上经历过五次大迁徙①,又没有掌握自己的文字,苗族只能靠口耳相传的方式记录和叙述其艰难的迁徙史。作为记录苗族历史的口传范式的长篇叙事史诗,苗族古歌的内容和传承方式被赋予了神秘色彩,被喻为“苗族社会的百科全书”。
一、苗族古歌的叙述范式
苗族古歌历史悠久,传播广远,内容广博精深,种类复杂繁多,形式多种多样,不同地区、不同方言区的苗族传唱的古歌内容和形式大致相同。其内容都以从人类诞生到苗族迁徙,历经艰险走向繁荣发展的历程为主体;以口头传唱和口耳相习的特殊方式传承。苗族以苗话为传承语言,一代代历久弥新地传唱着作为其精神支柱和民族认同纽带的古歌,并以之作为精神交流和感情互动的媒介,于是,古歌就成了支撑苗族整个历史和精神世界的符号。
人类文明所经历的漫漫长路,可以说就是人运用符号承载文化、传递知识,并将人自身的劳动过程浓缩于符号系统的漫长历史②。萨特认为:“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人的生活包围在他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他通过故事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过日子像是在讲故事。”③苗族就是运用古歌这种文化符号和口传范式讲述自己曾经的“故事”,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苦难史。历史“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④。苗族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古歌语言⑤来叙述本民族的历史发展线索,其特别之处在于口传范式的相承,而古歌语言的择词是根据格律和特殊句义取舍的。
语言的出现较文字更早,口耳相传理所当然地要比成文记事更早。但在人类初始阶段,口耳相传的内容并非传说,而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由于没有办法记录下来,人们只能凭着记忆一代一代地传述〔1〕。苗族就是将此种神话般的故事以口头唱述的形式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演变成为今天苗族人民耳熟能详的古歌的。《苗族古歌》又称《苗族史诗》,由《金银歌》、《古枫歌》、《蝴蝶歌》、《洪水滔天》和《溯河西迁》五大部分组成,共1. 5 万行⑥。神秘的古歌篇幅宏大,内容包罗万象,包含宇宙的诞生、人类和物种的起源、苗族的大迁徙、苗族的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等,而贯穿这一经典的主题是对生命的歌颂。它大多在苗族鼓社祭、婚庆活动、亲友聚会、节日等场合演唱,演唱者多为老年人、巫师、歌手等。古歌的特点是五言体,盘歌问答、歌骨歌花交替演唱,运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叙述;每段歌词可以反复吟唱。
苗族古歌不仅是民间文化的宝库、苗族口传文学的典型代表,更是苗族的精神标本和心灵记忆,在苗族社会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部有影响的古歌之一,苗族古歌这一天才作品是研究苗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除具有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神话学、音乐学、美学的价值外,还具有教育、审美和娱乐等方面的价值。这是因为苗族历来不会用自己的文字或没有自己的文字,就只能用口传的方式来传承这些经典的历史。古歌作为苗族历史的叙述版本,流传在苗族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中,铸成了苗族的经典文化和历史典籍。并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演化为苗族的“日常必备知识”,成了苗族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突显标识与符号。
当一种语言表现成为被接受的日常用法之后,它有可能被编码为寻常的描述〔2〕。在苗族社会,古歌是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可的一个特殊工具,也是苗族人自己在特殊场域演绎历史、演唱和抒发苗族文化特质的一种情感宣泄渠道。“在有些情况下,语言是不可穿越的……表现是具有独立本体地位的语言实体,其与被表现对象是同时到场的,表现之外并无它物。”〔2〕阐释以语言为媒介,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传的,其表现功能和符号意义是等量的,都能够表达叙述者的心声与情感。由于本族人最能够感受和体验到本民族的厚重文化,并对之加以深刻解读和体悟,所以一旦古歌被传唱时,对历史和先人的经历的敬畏只有歌者本人最能深刻领会,能够理解歌声所述内容的受众也会被深深打动。通过传唱古歌,就可以让在场的受众得到苗族历史文化的感化和教育,使其认同自己的族源和血缘。苗族以古歌这种传唱方式叙述苗族的辛酸迁徙史,以古歌作为苗族历史文化教育文本,用古歌语言作为载体,叙述了古远的苗族历史。尽管今天古歌已经被他者文化挤兑和误读,但在场的受众还是能够通过体味传唱者的唱词与古歌内容而感受到苗族历史文化的辛酸遗事,得到别样的文化教育和情感感染。
我们可以有脱离世界的语词,但是却不可能有脱离语词或其他符号的世界⑦。苗族古歌是苗族人用用朴素的歌词构筑出来的人类(苗族)早期的历史〔3〕,被世人认为是神话。但没有文字的苗族人仍然将这些口传古歌中的故事看作真实的历史,并一代一代为之感动着。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苗族古歌所唱述的世界是无中生有的,因为在人类无史(文字史)的远古年代,历史就是通过口传方式延展的。
长篇的叙事内容和宏大的故事展演以及其所唱及的远古时间使苗族古歌具有史诗的性质。例如燕宝搜集整理译注的《苗族古歌》⑧有:
Hfab hxid dliel lot ot,mux hxib dol bongt wat,waix qend gid diangl dangt,dab qend gid diangl dangt,ob liul dail yut yut. (回望那远古,时代太久远,天刚刚生出,地刚刚生出,天地还嫩得。)
这节古歌唱述了人类起源的遥远年代,历时久远,具备史诗的特定性质。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史诗,是民间叙事体长诗中一种规模比较宏大的古老作品。它用诗的语言,记叙各民族有关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传说,以及关于民族迁徙、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所以,它是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一起生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4〕苗族古歌在不同的版本中也有译为苗族史诗的个案,但不论怎样译释,其性质都不会因此而改变,即与其他民族史诗都具有同样的性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苗族古歌靠口传的语言叙述着苗族的历史“故事”,也把苗族的不屈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这种口传的方式尽管在历代的正史中未予记载,但苗族人却把它视为精神寄托和历史教育的最佳途径以及理解历史和解释社会生活的有效方式。因为归根到底,叙述是人类理解和阐释世界的基本模式〔2〕。每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有其独特的表达和抒写方式,是不容诋毁和藐视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评价苗族史诗:“开篇宏大,具有创世意味。通篇结构流畅大气,程式规范庄重,节奏张弛分明,远古气息浓烈,历史信息密集。细细读来,便会进入远古苗人神奇浪漫又艰苦卓绝的生活氛围中;大量有待破解的文化信号如同由时光隧道飞来的电波繁渺而至。”⑨著名文化学者刘锡诚、朝戈金等也认为,苗族史诗《亚鲁王》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新发现,其文化价值堪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它的发现和出版,是当代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重大成果,其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的研究价值无可估量⑩。这就是发现不久的苗族史诗《亚鲁王》留给世人的印象和感受。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苗族古歌的口传范式在历史书写中曾一度被遗弃或蔑视。但口传范式的历史叙事并非没有价值,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它的存在价值和历史地位。站在今天的学术背景和话语场域下,我们应该看到口传史诗的范式作用:它承载着(一个民族)太多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或听到一个民族的情感、经历、历史事件、不同历史人物的命运、荣与辱、喜怒和哀乐〔5〕。研究口传史诗的范式,可以发现没有文字前的史实叙事的传承价值,复原史前人类遗迹,为我们研究上古历史提供口传材料借鉴。
二、他者立场的苗族历史叙事
“他者”(the other)和“自我”(Self)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并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所以,“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以一种语言为中心描述世界,那么其他语言就变成了他者。而在他者的描述或抒写中,被描述的对象往往被歪曲或误读,甚至被扣上野蛮和落后的帽子。如相对于英语世界来说,非英语的世界就是他者,所以英语殖民地的人民往往被认为是野蛮和落后的,要靠殖民者以救世的责任去“拯救”。非汉语世界或民族在在汉语描写的世界中也同样被歪曲和误释,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
在他者的眼中(汉语、英语叙述等),苗族是没有文字的民族,是不会书写自己历史的民族。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很多(除了少部分了解或者深入研究苗族的学者外),既包括非苗族群体,也包括少部分苗族学者[11]。苗族历来被视为野蛮和落后的同义语,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历来是一种帝国叙事[12],苗族在中国的正史或野史中的记录都或多或少与“蛮”字有关联,这导致历代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等误读和讹写了苗族的整个历史,以致世人对苗族和苗族历史文化产生了认识上的偏颇。
曾经有不少学者,不管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都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有过误解和讹传,以致产生了很多不恰当的叙述。一生从事苗学研究的李廷贵教授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国内外学者对苗族都有所研究,而且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习俗和人种诸方面,但不够系统,更谈不上深刻〔6〕。因为他们在研究苗族时往往带有“汉语眼光”或“印欧眼光”,很少从苗族本身出发来认识苗族、研究苗族。特别是一些不懂苗语的人,想当然地带着猎奇的心理研究苗族的历史和文化,并成为了所谓的“苗学专家”。殊不知其“研究成果”往往是对苗族及其历史文化的误读,是对苗族这个族群集体的严重亵渎和歪曲,侮辱和贬低了苗族[13],更有甚者污蔑和诋毁苗族。
从国家正统的眼光来看苗族或西南其他民族,其结果往往会将其边缘化、落后化,甚至野蛮化,而忽略了他们安分守己、勤劳持家、自给自足、默默奉献的一面。这种偏激看法很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尤其是从事民族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最不应该如此。长期从事西南民族研究的徐新建教授认为:在中国大一统的王朝进程中,“边地”几乎总是被视为蛮夷之地,其特点不是“落后”就是“野蛮”,中心与周边的区别往往被看作“文”、“野”差异。对待少数民族便是征讨、羁縻与经营,而其中的核心乃在“教化”,即通过治理,使边地“文明化”、“内地化”、“一统化”〔7〕。
从下面两则记录中,我们就会发现徐新建教授提及的“史实”:
康熙四年贵州总督杨茂勋的一则上疏云:“贵州一省……苗蛮在山箐之中自相讐杀,未尝侵犯地方,止须照旧例,令该管头目讲明曲直。或愿抵命、或愿赔偿牛羊人口,处置输服,申报存案。”[14]
康熙四十年十月,“兵部等衙门议覆贵州巡抚王燕疏言,黔省熟苗为盗,与生苗潜入内地行劫者不同。其文武官弁处分,请照汉民为盗之例。嗣后应将生苗为盗,地方官仍照苗蛮侵害地方旧例处分。若熟苗为盗,地方官不行缉获,及隐讳者,俱照民人为盗之例议处。从之”[15]。
由于历史的局限,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往往带有不客观性,往往把少数民族视为必须“征讨、羁縻与经营”的对象。在这种狭隘的“边民”思想指导下,自然就产生了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民族间矛盾激化,甚至引发战争。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由于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实情与民族政策,外国的一些名家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认识也充满偏见。黑格尔在其名著《美学》中即认为:“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关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式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起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大障碍。”[16]
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1735 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对“苗人”描述如下:
苗人散居在四川、贵州、湖广、广西诸省及广东与上述几省交界之处……湖广西部和贵州北部的苗族比倮儸人更凶狠、更不开化,他们对汉人的威胁远甚于倮儸人。为控遏他们,汉人花费难以置信的气力在地势险极处修建大型堡垒和城镇,切断苗族各部之间的交通,致使苗族人中最强大的部落被这些屏障所阻隔。被征服并与汉人比邻而居的苗人不置土司,他们被认为是驯服的[17]。
在外国人眼中,苗族也应该是被“征讨、羁縻与经营”的对象。受这一思想影响,相关书著中就不乏错误的记载,在此不一一列举。
当然,一页书是可以从两面去读的,一张纸币也是可以从两面来看其面值的。在苗族研究史上,正确解读苗族历史文化的著作汗牛充栋,涌现过不少有很高历史价值的成果,对苗族研究产生了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具有引导和启发意义。但也不乏戴着有色眼镜的研究者,他们往往误读苗族历史文化,其成果也带有负面的影响。这是今天从事苗族研究或者重写苗族历史的人应该引以为戒的。站在新世纪的学术舞台上,我们要避免想当然地用他者的眼光和观点主观和武断地对待和认识西南少数民族,对待跨世界的苗族,而要力图做到客观和公正。
三、口传范式的苗族历史叙事
苗族古歌几千年来传唱不衰,虽无文字作为可视介质供学习和传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口传范式的局限性,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自明的),但其口传的苗族历史具有一定的史实性,对研究苗族的真正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古歌中,口语的叙事,讲述的哲理,口传的文化,唱诵的历史,使得人和人的情感得以面对面的交往中展开,群体之间的凝聚通过语言的沟通传递”〔8〕。这种“歌唱时代”的文化特点和社会生活成就了苗族人的精神传播与历史文化传承。这种特殊的口传范式的历史表述与苗族历史的传承可算是苗族的民族志特殊的书写方式。
苗族古歌叙事庞杂、宏大,内容广泛,长篇巨牍,对苗族迁徙的过程描写得尤其淋漓尽致,不得不让人相信古歌是一种史实叙事,而不是歌者虚构、杜撰的。如燕宝整理翻译的《苗族古歌》第二部分为“枫木生人”,包括“枫香树种”、“犁东耙西”、“栽枫香树”、“砍枫香树”、“妹榜妹留”、“十二个蛋”五首长歌,着重描写万物与人类的产生,即枫树种从天上来到人间,由枫香树变成世间万物,枫香树心中生出妹榜(即蝴蝶),“妹榜长大要谈情,她和水泡沫谈情;谈情谈了十二夜,妹榜生下十二蛋”〔9〕。
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如今不能原原本本地复原。即使是有文字记载,历史的真实场景也不可能毫厘不爽地再现。因为语言叙述是一种概括的手段,不可能像图像再现那样完全展示历史的真实面貌。口传的历史也好,文字记载的历史也罢,终归只能是有限的记述。“历史叙述作为赋予过去以特定存在形式的语言手段,不是对历史实在的指实性摹仿,而是包括分类、立义在内的形塑与阐释”〔2〕。将对历史的口传范式的考察与文献的记载相结合,也许是一种“二重证据”的新阐述范式。
“历史叙述在文本层面上的根本语义功能并不是传递关于过去的知识(虽然它具有这样的功能),而是构造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2〕。苗族古歌的传唱场所是由其所唱述的内容决定的[18],苗族歌手编唱创世史诗的情况有以下几种:第一,为了通过叙述民族历史,歌颂英雄祖先,好让子孙后代不忘“民族的根谱”,便把过去传下来的神话诗、叙事歌和历史传说以史为线索,按创世过程编纂为史诗,在重大庆典和节日里演唱;第二,丧葬祭祀时,祭师要歌颂亡人生前业绩,然后把亡灵送到祖先发祥地去与祖先同在,这时就要唱到祖先的来历和功德,而送亡灵的路线就是祖先迁徙来的路线,古歌所唱的内容就是追述民族的历史;第三,在婚姻仪式中演唱《开亲歌》、《换嫁歌》,叙述苗族古代婚姻发展变革的历史;第四,理老在说理判案时,要追溯民法的历史,进而追溯天地日月和人类起源的“历史”(神话),这一方面可以炫耀理老知识渊博,一方面为说理判案引经据典,叙述古理古规的来历〔10〕。通过古歌的唱述,我们可以了解苗族艰辛的迁徙历程与坚忍的民族精神,认识苗族的社会历史面貌和生活场景,苗族的历史文化遂因之得以传播。这种特殊的教育和熏陶方式一直在苗族乃至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中延续着,只是未能被大众认可与宣扬,从而陷入沉寂,甚至于销声匿迹。
为达到创造或加工历史的目的,古歌或者史诗的歌者往往将自己对历史的解读通过唱述的方式传达出来,所以古歌可以有完整的历史故事情节。尽管如此,“但远去的历史事实,古歌只能靠抽象概括的方式或手段予以编唱历史叙事向我们表现的是一种假定性的完结(putatively finished),没有消解、没有离散,历史故事总是完整的,能够有故事的结尾,展现故事情节,他们赋予真实的是思想(ideal)秩序”[19]。
今天,我们重读苗族古歌,研读其内容,揣摩其历史,不难体会到其思想精髓。它以歌唱的形式详细描述了苗族的迁徙与发展史,不乏史实性,这也是其能够打动后人的价值所在。为什么苗族古歌有这样的效果与魔力呢?因为历史就是事实,即使我们所读到的史实是抽象的,甚至是经过歌者加工虚构了的“事实”,带有虚构的文学创造痕迹。但带有文学色彩的叙事并非仅仅是历史的表述方式,它也构成了历史本身,是一种超越了所有历史概念的最为本质的“元历史(Metahistory)”[20]。苗族古歌的口传叙事研究也会带给世人这样的“真元”价值与视野。
四、余语
审视人类历史会发现,不管是呈现于书面,还是仅用于口传,所有历史都是人类利用语言再现的事实。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不同的典章制度、思想概念以及社会形态,它们均具有时代特点,有着各自产生、发展及消亡的演变历程。同样,语言词汇也是一种历史现象,作为信息传递的工具,语言的服务性决定了其必然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每个时代都拥有与其社会特定需求相适应的语言,随着社会的变迁,每个语言词汇也均有各自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因此研究语言的历史性,成为我们了解和考察人类历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11〕。苗族古歌的口传语言,就是一种历史性的苗族史唱述方式,有其特别的魅力和影响功能。
研究无文字记录的少数民族历史时,如局限于某种特定的视角或方法,肯定会陷入死胡同,因为人类史是一个从无文字记载逐渐走向有文字记载历史的过程。在这条久远的长河中,经历口传的历史叙事阶段是必然的。我们不能武断地忽视和去除这个必不可少的历程,而要学会客观公正地看待和评价它。“历史事实及其在特定历史叙述中的适当性本身亦包括内在的语言维度,这就要求我们须在文本整体中获得规定,加以理解”〔11〕。
换言之,对少数民族史诗或古歌传承和发扬的各种范式的研究,可以补充中国以往历史书写的不足。“苗族古歌的传承研究是苗族古歌研究的基础,我们应当改变过去孤立的、平面的、表层的纯作品研究模式,将研究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即把苗族古歌视为苗族的一个文化系统、一个有机体,将其创作者、传承者、受传者、传承渠道置于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中去进行宏观的综合考察,以揭示苗族人民的心理特征、生活习俗、审美意识以及苗族古歌在苗族人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在苗族文化史的地位……目的是为了深入一步研究苗族古歌提供材料和理论依据。”〔12〕因此系统、全方位地深入研究苗族古歌的方方面面是很有必要的,研究也应该及早启动。
对苗族诗歌系统的研究,既不像无反馈考古,亦不同猎奇式采风。对这一活生生的文化现象的分析判断,应尽可能接近事实,这有助于复杂的现实选择。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从苗族文化的本体出发,由内及外进行反思,即关注外来文化冲击对其形成的种种挑战和影响,以最佳选择实现本民族文化的连续与发展;一是由外及内,即从非苗族的外部文化着眼,寻找和发现苗族文化中所蕴藏的丰富资源,以充实各自的固有模式〔13〕。
对无史的苗族及其古歌内容的研究和论证虽有困难,但利用今天的便利条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收获。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总论”中也指出:“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因为“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信古固然有过,疑古也有过,后者“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由此,他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4〕“二重证据法”就是“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互相结合,彼此印证〔15〕。研究苗族古歌以至其他民族的史诗,能够利用的不仅仅是“二重证据法”,因为苗族古歌这样的活历史至今还存活在苗族人的口中、心中,可资挖掘和利用。作为苗族历史研究的活材料,它们自然会在新历史时期显现出更大的价值。
徐新建针对目前中国人类学的囿限提出了“超越”的概念:“若从制度性的、整体性的、观念性的指标来衡量,中国人类学还需要超越既有的框架,也就是要超越从严复以来的过度本土化、过度世俗化、过度应用性以及过度实证性所导致的既有基点和格局”〔16〕。显然,不论是研究中国历史还是古歌古史,我们都应该具备这样的胆识。
苗族古歌的历史叙事有其特殊的历史场域。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叙事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叙事并不囿于狭隘的小说领域,它的根茎伸向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叙事在时间上具有久远性,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它与抒情、说理一起,是推动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基本动力,并与抒情、说理一起,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标志”〔17〕。苗族古歌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就是因为苗族以至人类时时刻刻都在通过创新展现其鲜活而旺盛的生命力。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洲塔指出:“口传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遗存,也是一个民族的整体记忆。随着传唱艺人的离去和后继乏人,口传文化在逐渐成为历史的绝响,亟待加强整理保护。”〔18〕
当前,及早研究苗族古歌之类的口传史诗或古歌,深入探讨和研究古歌的价值及历史意义,是传承与保留人类文化的一项重大事业,刻不容缓。通过对苗族古歌历史叙事范式的分析和比较研究,解读与阐释历史叙事的不同范式和体例,比较人类发展历程中无字史与文字史的叙事价值,以前人研究成果反思口传史诗范式的研究意义和场域作用,有助于我们在新时期、新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以客观、公正的历史视角考辨叙事的不同方式及价值,为将来口传史诗的研究提供全新的历史价值视野和思考维度。
注释:
①参见石朝江《世界苗族迁徙史》的有关内容。
②见卢德平·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原点与延伸》,引自http://www.semiotics. net. cn/Articles_Show. asp?UserID=235&Arti_id=817。
③“A man is always a teller of tales;he lives surrounded by his stories and the stories of others;he sees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to him through them,and he tries to live his life as he were recounting it.”Jean-Paul Sartre,Nausea,New York:Penguin Mordern Classics,p12. 转引自赵毅衡《符号》第319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④见海登·怀特《元历史: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第2 页“前言:历史的诗学”,约翰斯·霍普斯金大学出版社1973 年版。
⑤英年早逝的李炳泽把古歌语言分为非口语和口语两种,本文认为应以诗歌用词代之,因为其是否口语很难鉴定,标准也很难统一。
⑥此处所论及的古歌流传于贵州黔东南地区苗族中。其他方言或其他地区的苗族流传的古歌大体与此相同,但在名称和细节上有差别,这可能是后人在流传中添加了不同的内容或形式所致。
⑦见Nelson Goodman Ways of Worldmaking,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78,p. 6. 转引自周建漳等《历史叙述:从表现的观点看》,刊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1 期。
⑧见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编、燕宝整理译注《苗族古歌》第22 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年出版。引文后翻译为笔者所译。
⑨冯骥才《民间文化遗产抢救 最大的快乐是发现》,见http://culture.people.com.cn/GB/87423/17186889.html。
⑩http://culture.people.com.cn/GB/87423/17224875.html。
[11]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分苗族人士总是歪曲一些事实,或看不起自己是苗族,或认为别人毁了苗族人,他们被三苗网的部分网民戏称为“苗奸”。
[12]此术语是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2010 年7 月27 -29 日在贵州大学召开的“西南地区多民族和谐共生关系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的。
[13]《中国西部》杂志原登载了李麦所写的《苗族鬼师》,该文极力侮辱、贬低苗族,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针对此文,苗族进行了合法的申述。
[14]见《清圣祖实录》卷十六“康熙四年七月乙未”条,中华书局影印本。
[15]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康熙四十年十月壬申”条,中华书局影印本。
[16]转引自刘冬颖《诗化的历史——〈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02 年第1 期。
[17]转引自吴莉苇《18 世纪欧人眼里的清朝国家性质——从〈中华帝国全志〉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描述谈起》,刊于《清史研究》2007 年第2 期。
[18]苗族古歌的演唱是有一定限制的,古歌在什么场所能够演唱,要根据它的内容来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古歌的内容决定了演唱的场所。
[19] White,H.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in Critical Inquiry,Vol. 7,No. 1,1980.转引自郑向春《叙事: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并接策略》,刊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3 期。
[20] White, H. Metahistory: the History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转引自郑向春《叙事: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并接策略》,刊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3 期。
〔1〕丁 波.略论中国历史上的口传历史时期〔J〕. 学术研究,2007,(2):105.
〔2〕周建漳等.历史叙述:从表现的观点看〔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35,136,138,137,137.
〔3〕李炳泽.口传诗歌中的非口语问题——苗族古歌的语言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8.
〔4〕钟敬文.史诗论略〔C〕∥赵秉理,编. 格萨尔学集成(第一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581 -586.
〔5〕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活态的史诗传统与历史的互动——与口头史诗《玛纳斯》相关的历史文化遗迹〔J〕.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10,(1):53 -55.
〔6〕李廷贵,等.苗族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10.
〔7〕徐新建.边地中国:从“野蛮”到“文明”〔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6(2):24 -27.
〔8〕徐新建. 苗族传统:从古歌传唱到剧本制作——《仰阿瑟》改编的文化意义〔J〕.民族文学研究,2004,(2):91-94.
〔9〕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编.燕 宝,整理译注.苗族古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486.
〔10〕潘定智. 从新编《苗族古歌》看创世史诗的几个问题〔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l):39 -42.
〔11〕陈 桦.语言与历史:清代“人丁”概念的异变〔J〕. 清史研究,2006,(4):87 -93.
〔12〕杨正伟.苗族古歌的传承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季刊),1990,(1):24.
〔13〕徐新建.试论苗族诗歌系统〔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3):31 -39.
〔14〕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3.
〔15〕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2(5):5.
〔16〕徐新建.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人类学需要的大视野〔J〕.思想战线,2011,37(2):15.
〔17〕龙迪勇.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叙事学研究——读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J〕.思想战线,2009,35(2):封二.
〔18〕张春海,等.莫让千年口传成历史绝响——将口传文化视作“文化物种”加以保护〔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6-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