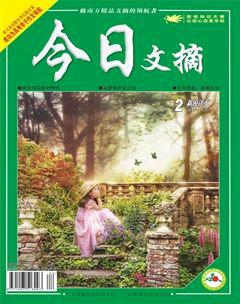未知的黄药师
沈嘉禄
头痛的痼疾已折磨了我三十余年,朋友同情我,经常介绍我服用民间偏方,多年来,我吃过的草药大致可堆满一间十平方米的房间,蝎子、蜈蚣、僵蚕、眼镜蛇等也领教过了。
有一年(此话约有十年啦),朋友老王很兴奋地告诉我,他认识了一位神医,已经看过一回,效果非常明显。老王早年在草原上骑马,不招牝马待见,屁股一撅就将他掀到地上。老王从此脊椎弯曲,躯干越来越像一个问号,他下周打算再拜神医,一定要带我同行。我对老王的信息并不全信,但老王是理科出身的大学讲师,知识分子,最后他的一句话说动了我:“以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人类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研究,我们对未知的事物一定要有足够的尊重。”
神医姓黄,大家都叫他黄药师——这是不是有点八卦呢?但这位黄药师不在桃花岛,而是在苏南农村。一早,老王和我,还有几位病友,包括一位资深军医,一位练太极功夫的温州人,三位生意老大的企业家和一位入了美国籍的美女金融家,分乘两辆越野车,从沿江高速一路北上,到丹阳一个陌生的村庄已经日头偏西了。
与村民的楼房相比,黄药师家的四间平房危危乎欲坠,给人治病的那间偏房中间用一根木头撑着,窗子比一张A3纸还小。老王说:你看,黄药师只顾为病人看病,房子都想不到盖。
黄药师身材瘦小,脸色黝黑,看上去快五十岁了。据老王讲,黄药师是外乡人,十几岁那年外出流浪,在湖北偶遇一位神医,即一路追随,采药研药学了二十多年,出道后回到江苏为大家治病,有次救活了一位被大医院一脚踢出的姑娘,从此就有了老婆。黄药师的老婆脸颊通红,不善言辞,此刻正忙着洗菜煮饭。
终于轮到我了,黄药师看我一眼,五脏六腑似乎即被洞穿,一句话也不问,就埋头调起了膏药。黄药师对所有的疾病都是以膏药这把“万能钥匙”通吃,区别只在三四瓶药的调用比例。而那几个瓶子里的膏药全是黑乎乎的,什么成分谁也不知道。
脱衣,巴掌大的膏药热乎乎地敷在背上有一种体贴感。但为何头痛病要从背部入手?黄药师解释:“你这个病,根源就在背上。”
我还注意到黄药师在配膏药时,从瓶子里撮取一小团,搓成条子点火烧着后抛在半空。事后老王告诉我,这是他在征求他师傅的意见,黄药师在给病人看病时,他师傅其实是在天上看着的。
半夜时分,我们总算回上海了,高速公路上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足十米,还不断有厚密的雾团涌来眼前。这一切就像悬疑电影里的铺垫,不可预测的折转即将出现。
敷了膏药后五天内不准洗澡,我忍了。半个月后我又跟老王去了一趟,一个月后又去了一趟。每次,病人都在增加,回上海的时间也往后推迟,但是我的头痛依旧。半年后我问老王:你的脊椎到底好点了没有?他回答是好多了,但口气不那么坚定。
后来我们再也没有提起。但有一种眼神长期铭刻在我的脑子里,那是黄药师的邻居们,一语不发,翘起嘴角,表情比黄药师还含蓄。
对我而言,黄药师至今是一个未知领域。不过像老王这样的知识分子,以及不少业内资深人士都去拜见黄药师,也并非出于无知:一,黄药师明说是不收钱的,但你给三五百药费他也收了,不算离谱。二,许多人是在大医院看不好才去寻找民间偏方和神医的,希望奇迹发生。三,黄药师给的是外敷药,与胡万林叫喝的五味汤不一样,风险较小。更关键的是,有人善意引荐,你作为朋友就得诚意地表示一下。
世界上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为了对某种善意给予真诚的回应,可能抑止了质疑的自觉,其结果就铸成了一个错误。胡万林得以重出江湖,也因为他在五味汤里兑入了当今社会稀缺的某种“善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