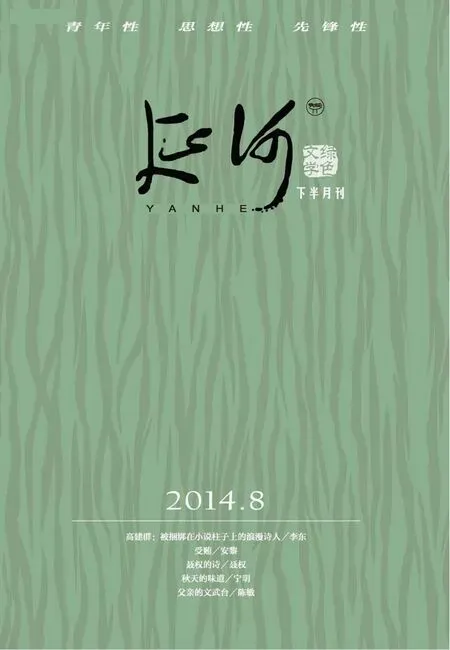聂权的诗
△ 聂 权
聂权的诗
△ 聂 权

聂权,山西朔州人。有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青年文摘》等刊物及《2003中国诗歌精选》《2010中国年度诗歌》《2013中国诗歌精选》《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朱零编诗》等选本。
理发师
那个理发师
现在不知怎样了
少年时的一个
理发师。屋里有炉火
红通通的
有昏昏欲睡的灯光
忽然,两个警察推门
像冬夜的一阵冷风
“得让人家把发理完”
两个警察
掏出一副手铐
理发师一言不发
他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他等待他们
应已久。他沉默地为我理发
细心、细致
偶尔忍不住颤动的手指
像屋檐上,落进光影里的
一株冷冷的枯草
午后
我们相拥躺着
不知不觉睡着了
阳光照在我们的肌肤上
像黄金,像跳跃着的金子
它们慢慢消失
像沙粒,像人生的温暖与微凉
像水的跳跃
像水融入哑然无声的水中
我们终究要分开
像水,不溅起一滴水花
但薄窗纱似的暖和,这个午后之后
在我们的心中存留下来了
蒲公英与影子
他老了,眼神昏浊且痴滞
似乎什么都听不懂了。
女导游说了两次
尊胜寺的接引僧也说了两次:
踏入佛门
不要踩门槛,否则
就是对佛祖的大不敬
他却软软地
一脚踏在大雄宝殿的门槛上
迟迟不把它放下来
罪过啊罪过
似乎连尚未生出新叶的树枝,和枝上的一只鸟
也在微风中
这样说。这老人
却无动于衷
他的瘦身体颤啊颤
移动到殿门外,偏离人群的甬道上
那里,几株小小的蒲公英
在砖缝间落下自己的影子
阳光正炽烈
去窑洞看姥爷
看见那张尘封的脸
高耸眉骨
看见那堆满褶皱的
再不能一动的面颊
在窑洞的遗像框里
他享受长者应得的睡眠。
深得不能再深的睡眠,
我用藏着无尽的悔的眼光
擦拭他思维陷落的睡相
但突然,他的目光蓦地
转亮
宛如昏睡人转向了世界
嘴唇抖动,抖动
要说话:
——润儿,你来了
昏黄而斜的光线中
他要牵当年的我的蓝布衣裳
再带我去买糖
于是,他一拐一拐地
动身
要拄着拐杖
走出来
年前某一天的清晨
院中的大灶台有着黄泥与草秸涂抹的粗糙
铁锅里升腾的热气舔着灰蒙蒙的清晨
屠刀已备好 接血的铝盆已备好
几个壮汉累出一身臭汗
吭唷吭唷 终于将一口大猪
面朝天 紧紧绑定
猪不甘心的哼哼 一声接一声的嗥叫
一阵一阵地
抽紧着天宇
嗥叫声使人越聚越多
女人们的手在桶里浸得通红
它们不断地抱出粗粉条、细粉条
一会 就可以做好
猪肉土豆炖粉条,热气腾腾地
用大碗端放在桌上
这个早晨只有猪。
几只芦花鸡无疑不谙世事
急急缓缓地踱着步,伸缩着头
在散布着糠粒的地上 和雨雪浸得发黑的柴草堆间。
人群间,间或便传来几声笑语
而天空,冷着脸
它不说话
好时光:八月十五
我们在自己灯光温和明亮的家。
不看明月,但知道
它正在用深色的天幕,和微冷的金黄
高高地、一如既往地为我们
送来一年之中最美最好的时光
那是使我们内心幸福而湿暖的好时光
月饼和果蔬承载着它们
瓜子和花生承载着它们
红宝石一样的酒酿和杯盏承载着它们
精心烹制的菜肴承载着它们
它们在温馨涌动的洁净小桌几上
闪着光
被这微光照耀的我们,我们一家人
幸福啊,箸筷此起彼落
我们的脸上
都荡漾着微笑
仿佛 只有幸福的团聚
再没有尘世间的
愁忧与劳苦
午后
漫空飞舞的叶片的雪
秋阳在其间有着异常明媚的脸
明晃晃的干燥的味道。
风声荡过去
又扫过来
又有斜射入心中的暖
又有身体的微凉。
就是这样,每个季节
都将两把不同的斧头
交在你手中,教你如何使用
我握起斧柄,学着那巷口屠夫的模样
砍削心头的枝叶
嘘——,秋天说
请,请温柔些
拯救
洪水滔滔,滔滔
隆隆水声扩成通天之鼓
呼救与互相找寻之声已渐弱
收拾不起盛水的瓦盆
那个农妇一脸的绝望与凄惨
满身满头泥水
抱着一块木板荡漾着浮去
家已残破,家园已毁
内心的壁垒无助地
坍塌,天空中低低地奔涌黑灰的噩梦
大风不停地卷起水浪与挣扎的牛羊
一切都是无可抵御的漩涡。
佛,在端庄与慈悲之中
在山门之外,您怎样拯救
这颠覆的众生
和您自己?泥、草叶木根、石头、水
已浸至巨大的佛颈……
童年纪事:山洪
这一刻,它为什么这么汹涌呢?
干涸得 如村人因焦渴而黯淡的黑眼睛的
河沟 堆垒大大小小的卵石的沟
老人拄杖穿过 一声叹息会吹来暮色的沟
孩子采摘野花野草
见一汪积水都要惊喜的沟
我在如此的惊喜中
淤泥里,五六日不倦,捕捞蝌蚪的沟
劈开山岩、山缝
滚滚黄浊水流奔跑、奔跑
漩涡啊,圆圈啊,斜纹啊
奔涌。无比的巨力,湿凉的水气
拍打着整个村子的耳朵
嗡隆隆 嗡隆隆
谁敢打捞那些偶尔现出的木具
谁敢打捞那些翻滚沉浮的牛羊?
“被山洪淹了的牲口有毒”
一定有人吃过这些有毒的馈赠
留下了悔恨轻信神灵施与的遗言
而有谁,敢冲到河心去救那年尖声呼喊的放羊娃
水啊,深厚、冰冷冰冷、无比湍急
它没有给过村子一滴有用的水
它把水都隐藏起来
然后,某一日,交给了泥土、石头
轰然而下,雷霆
不可阻挡。但人们
仍然爱着它啊!他们在岸上不远处
对它的到来指手划脚,大声地
评头论足
洪水消歇后,他们便踩着水高高低低的残痕
赶着牛羊,走上自己坡上的田地。
泥脸
风动,雨不来
树动,雨不来
草动,雨不来
天空久已阴沉,雨不来
箍紧的阴沉世界
在狂甩自身的风的怀抱中
颠荡,雨不来
北方的干土唇齿焦渴
而此刻,倾盆倾天的暴雨
正在南方,噼哩啪啦,用它们不断绝的脚
悬起一座又一座沉重的城池,此刻
暴雨冲垮的山峰,正无限地低着它们
泥石流的哀伤的浊脸
淹没着那么多再无法哭喊的和醒着的人们的
人间。
这一年
在大地上劳作的我们
都看见也听见
这一年的人间
天空用暴雨和大火折腾过了
大地也折腾过了,轮番
用翻卷、破碎和堵住口鼻的泥脸。
目光似龟裂的寸草不生的褐色田地
干渴焦灼,想找到
蓝空深处一滴活命的清凉的水
身躯这只空空的水罐,不知不觉萎缩
颤抖了一下,又一下
仿佛难以被赦的罪人
但是,苦孩子都抱着自己的茁壮
此年夏天,一身翠绿的西瓜一律熟透了
又红又艳,快到秋天,结实的玉米
吃过的人都说香甜
保卫之战
枝条和花在窗口晃动
一阵疾风过
看不见的生死就上演
这个下午,我只能看见不停动弹的窗子
但我知道
空中正回旋着万物在秋天
慢慢地改变的各色气息
一团团的暖流
与一窝窝的寒流
正如大火般涌动,有质无形地
激烈地交锋
如果我们细听,
那剧烈的坼裂之声
可以被天空下的我们
听到。如果它们可以被看见
我们就会知道
那是多么凄美而残酷的
保卫之战
生命在其中
从未放弃抵抗,与不屈的希望
和盛荣谈诗
说到了他的怀念。
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痛断肝肠之诗,又名
致亡妻,写给
被车撞得飘起的女孩
他的大学女朋友小小。
他说当时他真的很难过。
我有转头间的黯然
我一直希望
轻飘飘的小小
只是一种完全的虚构,如他某首诗中
虚构出的已上小学的孩子
我一直希望,那残破的青春红颜
只属凄美的梦幻世界;我一直期冀
一首肝肠寸断之诗,并不源于
肝肠寸断的生活。
——我多希望,尘世间的痛苦,不是
一首首美仑美奂的诗歌的
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