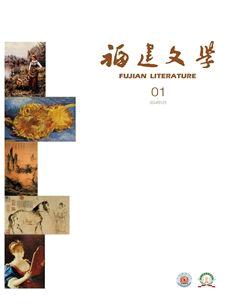城市边缘的漫步
欧阳德彬
秘密会所
下了校外宿舍楼的旋转楼梯,沿着马路步行百米左拐,便走进一条幽深的背街小巷。那里是浪游人的乐园,小饭店的灯光持续到午夜,随时都有热腾腾的饭菜温暖晚归的路人,花上几元钱即可果腹。在那些上层人士的眼里,那确实是不入流的地方,垃圾随随便便地堆在硕大的塑料桶里,宠物店里传来猫狗的哀鸣,按摩店的姑娘们在门口张罗顾客。那是一片遗忘之地,隐藏在繁华的都市里,展示着城市更真实细腻的纹理。
有一段时期,生活中最为快意的事情,莫过于邀上三五个聊得来的兄弟,走进那家叫“经济小炒”的饭馆,搬出桌椅放在店外,点上几盘小菜,叫上几瓶啤酒,个个推心置腹,海阔天空地交谈,可以嘲讽学术,可以品鉴身边经过的女人,可以拍桌子骂娘。白天遇见不顺心的事,碰上行为下作的人,听了污人耳目的课,晚上边喝酒边骂狗日的。
饭馆炒菜的女人天天站在店门口,左手端着铁锅,右手拿着铁铲,下面的炉火烧得正旺。铁锅晃动,锅铲翻飞,一盘盘味道可口的小炒便由她的男人端到了客人的桌上。她挥着柔臂,步行街上便有了人间的烟火气,让人觉得温暖惬意。真想不明白,她细白的手臂,怎么能日日夜夜承担起硕大铁锅的重量。她看上去只有二十七八岁,面容端庄,衣着质朴,稍稍过耳的黑发挡在耳后,后面还扎了一个麻雀尾巴样的小辫,在她炒菜的时候顽皮地跳来跳去。几丝浸了汗水的秀发搭在前额,添了几许妩媚。她唇边总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让人想起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见过奴颜媚骨的笑,奸诈卑劣的笑,一本正经的笑,冷漠无情的笑,就会觉得她的笑有一种超尘拔俗的美丽。旁边桌上几个打着赤膊喝酒的民工看到我们几个戴眼镜的学生喊操骂娘一脸惊异,我们便邀请他们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干了几杯。他们乐呵呵地讲述起乡村的奇闻异事以及置身城市的惶恐不安。奇怪的是,他们的讲述并不比某些教育工作者的课堂讲述差,那些原汁原味的乡村语言有着惊人的表现力。
女主人的孩子穿着白色连衣裙,追逐着饭桌旁的一只长着水汪汪眼睛的猫咪。女主人刚把一份葱花煎蛋倒进盘子里,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便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来。看到她笑,我们也忍不住笑了。男主人知道我们是常客,递上几支香烟来,桌旁便多了几缕烟气。即便是平时不抽烟的兄弟,这时也难抵诱惑,眯着眼睛安静地吞吐。有人牵着两只巨大的藏獒从街上经过,旁边宠物店笼子里的小狗竟呲牙咧嘴地怒吠起来。我们又笑起来,好像它们不是狗,而是人。
在镶金嵌银的城市里,那是一处秘密会所,藏在城市边缘,也是一处欢乐之地,难忘如同手纹。
夜园
落雨的午夜,园子里,暗黑的丝缕弥漫着。空气趁着雨滴打扮自己,桂花的香味流向土地。虫子躲进洞穴,黄犬伏在窝里,它们缄口不言。雨滴融进草丛的声响,是这里唯一的声音。
此时的园子,横无际涯。站在这里,目光流浪无依,雨夜把视觉推向迷茫和虚无。黑暗是另一种阳光,悄悄照亮我。行走在白昼的阳光下比行走在黑暗中更需要勇气。阳光下到处是假面,我们无从把握,只能成为一只只等待审判的蝼蚁。在这样的黑暗中,邀不用化妆的鬼怪共舞也是一件乐事。
长久以来,我对黑夜的嗜好如同绝症,无法医治。这时候,最容易不用镜子看清自己。走进人群恰是走进荒园,一个托钵的僧人独行在枯枝败叶中。毕竟,再多的言语也无法使两颗心靠得更近。
在遥远的乡村,每个黑夜,爷爷总会用摆在堂屋的红漆木盒伪装自己,咬着纸卷旱烟,琢磨躺进去的最佳姿态。他是慎之又慎的,生命里没有哪场仪式更加盛大。他终于没有自己躺进,父亲和叔叔们把他抱起,把一个白发苍苍的孩子放进红色的摇篮。我伸头注视了他一眼,他的前额出奇地平静。记得最后一次他在冬风中靠着木门咳嗽,边扭头瞧了瞧槐树杈上的日头,边把那件黑粗布棉袄裹了又裹。我只当他出门远行了,消失在寒冬的沉沉夜色里。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相信,他有一天会从黑夜里归来,嘴上咬着纸卷旱烟。
白天落叶纷纷的树木化身为黑黢黢的山峦。秋叶在夜晚更加依恋枝头,不舍得凋落。池塘也睡意朦胧,只有涟漪,没有波涛。即使有狂风漫卷岸边的垂柳,它也顶多漾起几痕波纹。它洞察周围的隐秘,却习惯于缄默。在这样的夜里,它没必要保持清醒。黑夜,比白天更安全。我和它意味深长地对视。它说,秋天从我身边走过;我说,我愿作浮在你水面的一片黄叶。
白天,人群带来喧嚣。晚上,尤其是这样无月无星的黑夜,这是独属于我的园子。我成为它的一棵树,直到白昼来临。
两座城的雪
整整一天都在收拾东西,一件件地,散漫地,把旧物中蕴藏的精灵放出来。书中的枫叶掉落下来,上面的诗句隐现在叶脉中。
几年前,我喜欢过的第一个女人,她拿起那片枫叶,白纱衣飘拂在古城的春风里。我的诗人,为我写诗吧,耳边仍回荡着她的声音。一只天蓝的卡通杯,她送的生日礼物。杯子是一辈子的隐喻吗?我依然用那只杯子喝茶,只是杯中之水,经年不能平静。她临别时的笑靥,多么美丽,多么神秘,让人如醉如痴,又让人隐隐作痛。
许多个黄叶纷飞的秋天,我手执一片黄叶,久久地徘徊在古城的边缘。
现在,我写够了九十九首情诗,只是再也寻不到她的踪迹。我怀揣着秘密行走在河畔,寻找一个穿白纱衣的女子,她拿着一片枫叶,长发飘拂在古城的春风里,说,我的诗人,为我写诗吧。可是,所有的寻找只是徒然。
许多次,我惊喜地走过去,呼喊一个名字,转过身来的不过是另一个女人。或美或丑,或老或少,都与我无关。
打算离开这座城市了,在这个第一次相遇的时节。也许,我已经没有勇气承受这里哀伤的记忆。
走出房门的时候,漫天纷纷扬扬的雪,把好端端的春天盖住了。它是要掩埋我在这座城市的记忆么?它知道,我累了,也老了。玻璃橱窗映出的那个男人,满头的雪,满头白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方男人,要到遥远的南方去。分不清是只身远去,开始新的生活,还是躲避忧伤的追杀,亡命天涯?
古城的雪真冷,抢夺着脸上的热量,乘着北风往脖子里钻,我只好竖起衣领,把手藏进衣袋里。
在开往远方的列车上,那个多年来在黑夜辗转反侧的人,终于在颠簸拥挤的车厢中酣睡了,梦见无边的绿树青山洒满金黄的阳光。
下车的时候,这座陌生的城市竟下起雪来,没过多久,草木皆白。只是这座城市的雪不冷,不用竖着衣领行走。这座温润的城市,是不是也充满哀伤?
一座城用一场雪掩埋杂乱的记忆,静穆地哀歌。一座城用一场雪铺展一张白纸,我不知道该在上面写下什么。
脚步
我把一双皮鞋埋进背包里,走向小区里的修鞋摊。那双鞋陪我走了很长的路,我不舍得丢掉它。这几年,没有谁比它陪我走得更远。也没有谁,比它更清楚地知晓我近年来的颠沛流离。边远小城的一个夏日黄昏,我买下它,自北向南,抵达这座海滨城市。它陪伴着我,行走在城市的边缘,犹如猎人身旁忠实的猎犬。
鞋匠摊摆在小区铁栅栏的内侧,我掏出那双鞋,透过栅栏递给鞋匠。鞋匠是位生着两道浓眉的中年汉子,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鞋子,继续他手头的活计。
“你的鞋哪里病了?”他问。
“我穿着它走了很长路,鞋底磨破了,鞋帮还好好的。”
“大多数鞋子的病是开胶。”
“我在很多座城市修过鞋,刚来到了这里,生意还不错。”
“我也是刚来到这里。”
“不管你信不信,我一听来人的脚步,不必抬眼看,就知道客人的情况了。”他说。
他干完手头的活,拿起我的鞋翻看了一圈。“得加一个垫底了。”说着,他拿出几种垫底供我挑选。他用打磨机细细打磨我挑选的垫底,用胶水将它粘在鞋底上,又用一把锈蚀但锋利的剪刀剪齐。
“有的鞋匠修的鞋很容易开胶,我修的鞋不会。”他说着,从打磨机下面的破布上捻起一撮鞋底碎屑细细塞进鞋底与补鞋材料相接的缝隙里,又用胶水封住。
中年汉子修好了一只,拿起了另一只。
“没想到你在这里。在干嘛?”来了一个女人,她手里提着一大包东西,大概是刚逛完街。
“我在修鞋。”
“破鞋有什么好修的,再买一双不就得了。”女人坐在旁边的矮凳上,东西放在脚边,摆弄起她时髦的手机来。
我没有回答,注视着修鞋师傅,他正专注于那双鞋,皱起的眉头,像我曾经路过的崇山峻岭。
“鞋修好了,还能穿很久。”汉子两道浓眉舒展开来,咧嘴笑了,露出几颗烟草浸染过的黑牙。
我付了来时谈好的价钱,他又找回一半,说是今天的第一位客人只收材料费。我便从背包里掏出一本看过的书,送给汉子。汉子谦恭有礼地双手接书,不紧不慢地讲起他的家乡,他途经的城市,以及城市见闻。
女人不耐烦了,起身提起东西走了。
“相对于她,你更懂得珍惜。”汉子看了一眼女人离去的背影。
“我跟她是在两条永远不会交叉的路上行走。”我站起身。
“没有什么比独行时的脚步声更动听。”汉子说。
我把皮鞋装进背包里,向他挥手告别,走向一条树木掩映的小路。
寂静的石榴
午后的阳光溜进房间,它是一缕缕金黄的琴弦,享受着秋风的弹奏,而知了此时唱得正欢。我不由自主地半掩屋门,走进院子,那一排石榴树扑面而来。院子里的花木不少,牡丹、月季、石竹、香樟、葡萄、还有桃树。在这天高气爽的时令里,最吸引我的是池塘边的石榴林。称呼它们石榴林有点夸大的意味,其实只有十几棵,只是那硕果累累枝繁叶茂的景象,大有蔚然成林的势头。
秋风过处的石榴林才别有韵味,枝叶摇摆的时候,几个石榴几乎吻在一起了。那一颗颗石榴,在秋风的撩拨下伸长了嘴,趁着纷乱追逐自己的情梦。但总是与意中人若即若离,牛郎织女般满怀清愁。
韩非子曾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他身为法家,擅长论理,言辞有失风情,远不如曹植描绘洛神的那句明眸善睐惹人喜爱。在我看来,秋风中那一颗颗红脸的石榴,倒是长嘴善吻了,石榴是世间痴情的果儿。它们是寂静的,没有渲染假象的花言巧语,彼此想把心事编织成珍珠项链奉献给对方。石榴树拄着杨木杈子做成的拐棍,莫非是情重压弯了枝头?注视着它们,形影相伴的自己不感觉孤独。
太阳落到杨树杈上去了,我返回房间,展开纸面,想勾勒石榴的倩影。
我看见道路
每天经过天桥的时候,我总凝望下面的道路。那是一条笔直的柏油路,东西走向,一眼望不到尽头。我没有把它同城市中别的街道混为一谈。正是它,把我的生活一劈为二。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必须到路的对面去,一条大路不应该成为阻隔和镇压。周围已经有了太多貌似直线的东西把人们划归到不同的世界,皇孙贵胄抑或山野草民。在许多个躁动不安的梦里,那些直线飘动起来,长蛇般蜿蜒,甚至还会为一些有特殊关系的人打开一扇小门。我站在路边,盯着脚下,那条大路依然是规规矩矩的直线。
“大路的笔直或弯曲”是一个危险的问题,如果有人问及,我情愿不回答。
我抬起脚,走到对面,带着反叛者的得意和嘲弄。不绝如缕的歌声低回在开满木棉花的街道上,是夏夜里的窃窃私语,还是树枝间的风声?夜幕汹涌,淹没了来路。我不知道那些歌声的寓意,没有人告诉我那是快乐还是痛苦。
在桥这边的居所里,我常不敢久留。噩梦将我从睡眠里驱赶出来,接下来彻夜难眠,只好用夜色打磨自己。手背上停靠的一只长腿细腰的花蚊子,会轻易把我带进一场遥远而疼痛的爱情。
房间狭小闷热,窗户无法完全打开。在一个窒息之夜,我找来一根铁棒,盗贼一样跳上窗台,撬弯铁窗棂,再用木棍支起,引诱凉风进来。房东闻声赶来,一脸威严趁机敲诈。
“又没敲在你头上。”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赤裸着上身,握着铁棒的手臂咯吱作响。那个刚才还一脸严肃的中年人举着双手递烟,直到我关上房门他还在门缝里嬉皮笑脸。我骗过了他,其实,我连一只蚊子都不忍心伤害。
居所里,除了失眠就是怪梦。我梦见自己行走在空寂无人的道路上,身后一只四条腿的动物紧紧跟随。我转过身去,伸出手掌,抚摸着它的头顶。它便把猫头深深地俯下去,眯起眼睛,下颚贴到地面上。后背高高隆起,蓬松着黄毛大尾,它有一条狼的身体。
第二天黎明,我从住所走出,踏上天桥,穿过一条空寂无人的大街。踏进单位的伸缩门,打开电脑,正要起草一些枯燥公文的刹那,我明白了昨夜的梦境。那猫头狼身的动物,正是我现在生活的隐喻。
当我写下几段规规矩矩的公文,静悄悄的办公室突然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天蓝色的窗帘四处飞舞。房屋和装饰消失了,四周延伸着无际的荒漠。一座座新竖的墓碑林立着,上面的铭文模糊不清。我清楚地知道,墓碑恰恰是为自己心中的语言竖起。一些语言一直在我的心湖游弋,如金色的阳光抚慰着绿草。这时,我是幸福的,即使多年来孤身一人。
我每写下一句公文,周围的荒漠便竖起一块墓碑,作为死去语言的最后佐证。那些在大众面前放言要对我好好培养的人,并不清楚我需要什么。培养是奴役最好的代名词。
办公室里,世袭的职员不停地聒噪,到底是什么话题让他们嘴唇抖动如轮?永无休止的絮叨,是他们活着的要务之一。我努力让听觉专注于窗外的风,但还是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交谈:俗艳的女人、华美的衣服和美味的饭食。我不想说话,伪装成聋哑人,对着屏幕组织掩人耳目的文字。
办公室里的另一名雇员腰间别着的一把硕大的钥匙,他几乎与他等高,以致把他衬托得有些渺小。他行走在满是荆棘的道路上,钥匙成为他的兄弟。他腰间别着一把钥匙,那是他唯一拥有且必将失去的东西。
恍惚之间,我看到自己倒在未来的荒漠中,漫漫风沙把我堆成一粒坟冢。我的世界,是一片枯萎的树叶。离去的时刻来临了,我该到远方去了。
责任编辑 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