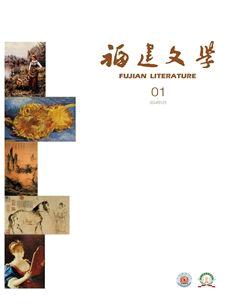万斤苕
刘益善
从一个人的本名看不出这个人的为人,从一个人的绰号却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特征。《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个个有绰号,个个绰号都符合它主人的性格。
万斤苕是他的绰号。
他并不姓万,他姓张,叫张发子。如今,村里没有一个人喊他张发子,都喊他万斤苕。弄得年青人真以为他叫这个名字,还说,什么名字不好叫,偏叫万斤苕,多难听!
要知道红薯有好几种叫法,有叫番薯的,有叫山芋的,有叫地瓜的,在张发子家乡一带,偏偏叫苕。乡里人还把傻子,心里不通窍的人也叫苕。苕变成了形容词,像“这个人苕里苕气”,“这人是个大苕”,意思就是这个人傻里傻气,这个人是个大傻瓜。他叫万斤苕,一万斤,多大的一个苕。
那是在火热的、沸腾的、共产主义前脚跨进了中国的一九五八年。在金水河畔的金水大队,一群从武汉来农村锻炼的大学生,在吃了半个月的不要钱的三菜一汤,雪白的大米饭后,给金水大队房屋的山墙上留下了形形色色、花花绿绿的壁画:稻堆子堆到了天上,堆稻的老头正就着太阳点烟;一个娃娃抱着西瓜大的芝麻嘻嘻笑着;十轮大卡车拉着一只大包谷棒子,轮胎都快要压瘪了;一个社员正用一把锯子锯一棵稻子,那个拉锯的社员真像张发子。嗯,不能叫张发子,否则就是不尊重他,应该叫张连长,他是金水大队的民兵连长哩!前天有人喊他张发子,他装着没听见,不理人家;人家赶快改口喊张连长,他才满脸笑容地答应,还敬了那人一支喇叭筒烟。
大跃进的年代,户户无闲人,炼钢的炼钢,生产的生产。唯有张连长穿着从部队复员时带回的那件黄不黄、白不白的破棉大衣,领子油腻腻的发黑,倒背着一支套筒枪在村里溜达着,他在维护治安。虽然是共产主义时代,共产主义听说还有警察呢!他感到不满足的是,当一个连级干部,却背着这种老套筒枪。当年,他在部队时,他们连长挂的是闪光的盒子炮,可威风了。现在,他统领的这个民兵连,拢共才五支破枪,他还是挑的一支好一点的。
他在村里溜达着,碰到有人,上前喝问两句:干什么的?为什么不劳动去!没人时,他就靠墙坐一会。今天,他的心绪很不好。他是村里唯一从部队回来的,他还到过朝鲜呢!可惜革命了好几年,连个党也没入上。回到村里,大伙热情地欢迎他,在大队当书记的是他本房族的一个弟弟,叫张富子。他从小就看不起这个张富子,穿个破裆裤鼻涕吊了半寸长,哼,还当书记哩!我张发子论水平比你高,凭资格比你老,这个大队书记应该我来当。可惜他还不是党员。他一回村就申了请,准备一入党就代替富子当书记。他的这个思想,富子似乎看出来了,偏偏不发展他入党,老是说支部通不过。还好,他多少弄了个民兵连长当当,连级干部啊,不容易哩,部队里的连长带百把号人啦!当连长也当的憋气,富子一点权力都不给他,只让他维持一下治安,好多会也不让他参加。昨天,当他打听到富子又要在大队部召开干部会后,就耐心地等着,直到晚上也没见到有人通知他,这下他生气了。
“妈的个×,开什么玩意会,把老子撇了,老子偏要去看看。”
他背着他的套筒枪,气冲冲地推开大队部的门时,几个大队干部正油光满面地喝着鸡汤,这香味使他暗暗咽了一口涎水。他愤怒了,狗日的们,躲在这里享口福,也不叫老子一声,太小看我这个连长了,老子叫你们也吃不成。他挥起他的套筒枪,把桌上的碗哗啦啦扫了个精光。
张富子霍地站起来:“张发子,你要干什么?”
“我是民兵连长,为什么开大队干部会不通知我?我当兵去朝鲜打仗时,你们都躲在屋里偎老婆哩,到今天,你们排斥欺侮我这老革命,老子就是不答应!老子不干什么,要你们吃不成!”
张富子见他充起老子来,脸上发青,气得眼睛直冒火。
“你个混蛋,你给我滚出去!你不够格参加这个会,我们是开支部会!”
张发子一听,心里慌了,怎么不搞清楚呢?说不定他们今晚正准备研究我入党的问题哩!这下可完了,他们要同意也不同意了!他抬头看看在座的人,果然都是党员,大家把眼睛都瞪着他。他想糟了,赶忙背着老套筒,用破大衣裹着身子,溜了。
只听见身后响起哈哈的笑声与骂声:“神经病!”
他靠墙根坐着,想到昨天晚上自己的粗野行为,懊悔地用拳头擂着自己的脑袋:张发子哟张发子,你真是个混蛋,这次把支部的人都得罪光了,你还入得了党吗?想到张富子,自己能斗过他吗?想代替他当书记,自己连党员都不是哩。嘿,听说张富子的叔岳父是公社的书记哩,他有后台呀!
他叹了口气,朝对面望了一眼。对面墙上正好画着那幅社员用锯子锯稻子的壁画,那社员正锯得汗流满面,汗珠子画得有他家小宝玩的皮球那么大。嗯,都说这个人像我,他回忆了一下在部队照的一张照片上的他,还真有点像哩。不过,连级干部能够去锯稻子么?他还从来没流过这么大一粒的汗哩!哪有一棵稻子这么大?画画的学生娃娃真是扯他妈的蛋。
他从破大衣口袋里掏出了烟荷包,从另一支口袋里掏出一张小报,撕下一小块,很熟练地卷起一支喇叭筒,伸出舌头舔了舔,把喇叭筒粘住,划着火柴,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股浓烟。看看报上有些什么玩意吧,民兵连订了一分县报,这张县报就成了他的卷烟纸。他被一幅照片吸引住了,嗬,稻田里密密麻麻的稻子,亩产五千斤哪!高产!高产!这里的稻子过去最高产量也只能打个六百斤。嗬,全县劳动模范哩,一个中年汉子,在报上望他笑着;试验田里亩产五千斤,他成了全县劳动模范,县委书记和他握手,他上了报纸,全县有名。我也来这么一下,怎么样?亩产一万斤,那时不怕你张富子不叫我入党,我当这个金水大队的书记怕是稳当当的!嗯,我去种块试验田试试,说不定能成功。好主意!他高兴得一下从墙边站起来,懊悔的心情早被一阵风吹走了。他背起他的老套筒,一只手插在破大衣口袋里,哼起了两句汉腔:
“本帅打马下山林,要到唐营走一程。”
吃饭的时候,他又犯难了。别看这米饭好吃,可种起来难哪,他毕竟是农村人,知道一些种庄稼的事。要亩产一万斤,别说难达到,就是让他去耕田栽秧的,他也有点怕,那才是累人呢,他的勇气消失了一半。
回到屋里,爱人带着儿子小宝刚从河对岸的娘家回来。小宝的外婆在河那边的山里住,与这金水大队不是一个公社,爱人每隔个把月都要回去看看娘。
小宝穿着新衣褂,拿着一个苕在啃。
“爸爸,这苕好吃哩,外婆屋里蛮多!”
他在儿子拿着的苕上啃了一口,嗯,是还蛮甜。爱人说:
“我娘她们那里今年苕多哩,一个都有斤把重,一亩地能挖几千斤,就是没人挖,都去炼钢了。我娘看着可惜,自己去挖了几篮子回来,其余的都在地里怕要烂掉了。”
什么?一亩地能挖几千斤!种苕,这东西肯定能高产。岳母她们那里都是山地黄土,我们这里土地黑乌乌的肥得流油,种苕一定比她们那里挖的多,搞个亩产万斤不成问题。搞一块好地,多施些肥,一定能行。他高兴得身子直摇晃,消失了的勇气又鼓起来。他决定种苕,一呜惊人。
“小宝他妈,你再抽个空到你娘那里去一趟,叫她们给我留点苕种,我要种苕!”
“咳,你疯了!食堂的白米饭吃厌了,要吃苕么!你种苕?哼,我怕要苕来种你。”
“就我自己种,我要搞一块试验地,创一个高产纪录。哼,别小看我啦,我要叫你们看看我这个连长是怎么当的!”他这话不知是说给小宝妈听的,还是说给大队书记张富子们听的。
爱人好不容易才答应过几天再过河去说说。他这才背着套筒枪,晃荡着出门去执行他的任务去了。
经过几天的转游、侦察,他把认为比较好的几块地进行了选择比较,最后选定了大队学校门前的一块菜园地。这块地在金水河边,离水近;又在学校前边,离肥近,他可以把学校厕所的肥全部施到田里;同时还可以解决劳力问题,叫那几个老师和些小学生娃挖地、送肥也方便,学校门口不是写着“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么!
说干就干,第二天一早,他就披着他的破大衣,背起套筒枪,到学校找到了校长。
“刘校长,今天你们全体老师和学生都拿上工具,把那块地翻一遍,要深翻,挖三尺深。”他把下巴朝那块菜园地扬了扬。
小学校的刘校长领导着两个老师、三个年级的百把名学生。刘校长听到这位连长的命令,忙忙点头答应:
“好!好!张连长,你这是要种什么东西啦?”刘校长明白这连长的权力,半个不字都没说,反正学校这年头上课不上课都无所谓。
“嗯,我种苕,这里种试验地。”他眼睛望着河那边答应。
好热闹的场面,一百多个学生娃娃吵吵嚷嚷,哭哭叫叫,一年级的学生只有七岁,三年级最大也才十岁,张发子家的小宝也上一年级。刘校长带着两个老师挖地挖得汗流满面,学生娃子们的积极性也高得很,好像这挖地比坐在教室里听老师教那些头痛的粉笔字要好得多,虽然个子还没锹把高,他们也拖着鼻涕格嗤格嗤地挖着。两个小娃子打架了,一个娃子哭了,老师吼了半天,才止住。张发子闲悠地背着枪在地边踱来踱去,这里指点一下,那里指点一下,有时也从小娃子手中接过铁锹挖一阵,然后再蹲在地头卷起喇叭筒抽几口。他感到很快活,他的理想,他的希望,就要实现了啊!
这时,大队书记张富子从那边走了过来,大概是从野地里检查炼铁炉回来的。张发子老远就看见了,哎,书记还是不能得罪的,他只好迎上去,好像没发生过前几天晚上的事一样,打着招呼。
“富子,你这是从哪里回来?”
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书记的肚量也还大,见他主动打招呼,也笑着说:
“发哥,你这是搞么事呀?和娃子们玩得这大劲?!”
“嘿,书记,我准备把这块地翻出来做试验地,培育高产作物。”
富子书记惊奇了,这条懒龙大概闲得无聊了,今天出来汲水哩。管他的,随他搞去吧!
“种什么东西?”
“种苕!我要培育大苕,高产苕。”
什么?种苕。这可是金水大队的稀奇事了,这里过去从来不种苕。这家伙搞么新鲜板眼?嗯,随他吧!随他吧!
“那好,好!你弄吧,我走了。”书记匆匆离开了。
张发子望着书记的背影,心里骂道:看你小子神气的!
在他的亲自督促下,学生娃子和三个老师挖了几天,才按他的要求把一亩地深翻了三尺,倒把一些生土都翻出来了。随后,他又亲自督促老师和学生把学校厕所的粪肥全都弄到地里,泼了一层,刚好起南风,弄得个小学校上课臭了三天。
爱人到娘家要苕种也很顺利,那边生产队说,你们要多少就挖多少去吧!他和爱人一起,拣那个儿大的,背了两筐子回来。他小心翼翼地侍弄了一块地埋下去,只等苕藤长起来,他就可以把藤子剪成一截一截的。往试验地里插了。这些事,他没有要人帮忙,都是亲自动手,也难为了他。他后来又到他岳母那个队里,向有经验的人请教过苕的栽法、管理等技术,他感到胸有成竹。
往地里插苕藤了,他又去找校长下了一道命令,小学校又全体出动。这次只让学生娃从河里用脸盆端水,由他和三个老师往地里插苕藤,苕藤插下去后,只留那片芽叶在地面,再浇上水。他的要求是那样严格,棵距、行距都按尺寸来,稍微歪了一点,他都要重新来插,整整忙了一天。
真是老天也开恩助他,苕藤插下去后,下了两场小雨,那在野地里筑的炼铁小土炉都被雨浇灭了,而他的苕秧子长出来,绿油油的,爱人得很。他背着套筒枪,有事没事都到地头转几次。要松土啦,施肥啦,他就到学校给校长打个招呼,老师和学生就出动。他觉得他这个连长调动小学校的老师学生,比调动他统领的民兵要容易多了。妈的,那些民兵可不大听他的调遣,富子那小子说去炼钢,呼啦一声就把他的兵带走了,他都成了个光杆司令。不过,能调动老师和学生娃也可以,总比没人调动强。等着吧,等他的奇迹创造出来后,他的威信就会比富子高得多,那时看他们听不听我的吧。
他叫大队的木工师傅给他做了个大木牌子,牌子刨得光光的,他找来了红油漆,用他刚扫过盲学的几个字,在牌子上歪歪斜斜地写着:
牌子写好了,他欣赏了半天,觉得自己写的这几个字还蛮不错的,油漆红艳艳的,字儿歪歪斜斜的,这是一种体哩。欣赏了半天,就扛到试验地插起来。木牌桩子插进地里一尺多深,他用手摇了摇,丝纹不动,看来是不会叫人拔走的。
插好木牌,他又围着地边转了转,绿油油的苕藤已经快把黑色的土地盖住了,他似乎听见黑色土地里的苕正长得咔咔直响。快长吧,长吧,最好长得一个有南瓜大、磨盘盘大、石磙大。明天再叫刘校长带学生娃们施一次肥,舍不得施肥,苕长得大吗?
试验地正处路口,来往行人很多。人们看到这个牌子,觉得蛮稀奇的,都要停下来看看。
“亩产万斤,牛皮吹破天吧!”
也有人看到那绿油油的、翠绿欲滴的苕藤,也夸两句:
“这苕还长得不错哩!”
内行人却说:“这苕不能再施肥了,要疯长哩!”
一天,公社的王书记,大概是张富子的叔岳父吧,从试验地路过,看了牌子和试验地,找到了张发子,把他大大地表扬了一番:
“嗯,老张哪,你的试验地不错哇,这样搞很好嘛,你创造一条经验来,大面积推广嘛!亩产万斤,如果全公社都达到这个产量,那要增产多少哇?你放了个大卫星哩!”
这下可把张发子喜得屁股都要颠成两半了,见人就说:
“我那试验地可是大卫星哩!公社的王书记都表扬了我哪,我可要成为了不起的人了!伙计,将来得了好处,我决不会忘了你。”
被大跃进跃得有些头脑发昏的人们,谁也不能断定他的试验地就达不到一万斤的产量,说不定还要超过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们恭维他:
“张连长,这下可出名了,你怕要升官了吧!”
他嘿嘿地笑着,装得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连忙熟练地卷起一支喇叭筒烟,递给为他戴高帽子的人,然后又背起老套筒,乐颠颠地转到地头,嘴里又哼起汉腔:
“本帅打马下山林,要到唐营走一程。”
小学生们下课就跑到地边玩玩、看看,可谁都不敢动一动苕藤。有一次,一年级的一个学生娃子摘了一片苕藤叶子,被张发子看见,耳朵都拧得发肿了。小娃子们围在地边,不敢动苕藤,就念木牌上的字。大队书记张富子的儿子张小军读二年级,如今的学生读书认字都是横着一行行地念。张小军按木牌上横的字读着:
“干部试验地,试验人亩产品种,张发子万斤苕。”小军有些奇怪,又把第三行读了一遍:
“张发子万斤苕!”
娃子们轰地笑起来。“哈哈,万斤苕!万斤苕,张发子!张发子,万斤苕!”他们一遍遍地叫着、跳着。
“小宝,你爸爸是万斤苕,你爸爸是万斤苕,哈哈!”
小宝哭着背起书包,找到了正在村子里转游的张发子。
“爸爸,他们骂你是万斤苕!嗯嗯。”小宝边哭边说。
“什么?骂我万斤苕,哪个狗日的敢骂我?”
“是张小军骂的。”
小军,张富子的儿子,这不是他老子教的么?哼,老子今天要收拾你。他丢下哭着的小宝,从口袋里掏出根绳子,背起套筒枪跑到学校,教室里正在上课,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闯进二年级教室,把小军一把拧了出来,把娃子捆在了门前的电线杆上。小军扯起喉咙哭,教室里一下乱了套,刘校长忙跑过来。
“张连长,这是怎么了?”他结结巴巴地问。
“这小狗日的仗他爹的势,辱骂革命干部,说我是万斤苕,老子今天要教训一下这小狗日的!”
刘校长吓得不得了,早有另一个老师跑去喊来张富子。
书记赶到学校,看见自己的儿子被捆在电线杆上,火光直冒,上前对着张发子就是一掌,把他推了丈把远,把小军身上的绳子解了。张发子从来没受到这么大的侮辱,爬起来抓住老套筒,把枪栓拉得哗哗响,大吼一声:
“举起手来,狗日的东西,竟敢打老子,老子毙了你!”
这下可把刘校长和两个老师吓得脸都白了。刘校长哆哆嗦嗦地扑到张发子跟前:
“张连长,嗯,嗯,嗯,做不得!有话好说,好说。”
张富子冷笑了一声:“打吧,朝老子胸口打!”他把胸口拍得啪啪响。“你那破枪吓别人还行,吓老子可不行!狗日的神经病,小心点。”说完牵着儿子愤愤地走了。张发子懊丧地拍拍枪,枪里没有子弹。
书记和民兵连长的意见越闹越大了,两人结下了仇。张发子想,等老子的试验地打响了,看老子整你。张富子想,这狗日的神经病,等有机会,非把他的民兵连长撤了不可。他还想入党,白日做梦去吧!
书记和民兵连长闹崩了不说,万斤苕三个字不胫而走。万斤苕,哈哈,这名儿不错,加在他身上刚刚合适。看他酸样儿,芝麻大个官,露水大个衔,偏摆出个天大架子。哼,亩产万斤苕?真是个万斤苕。
人们只敢在背后议论,谁也不敢当面喊他这雅号,不知是人们怕他那支套筒枪,还是怕他是个连级干部。
这一年的雨水特别好,大片的田地里庄稼因没人管,荒草比禾苗长得还高。人们早出晚归去炼钢,谁还顾得种庄稼。张发子试验地的苕长得特别好,他三天两头命令刘校长带领学生施肥,翻藤,绿汪汪的苕藤长得有半人高,把黑油油的土地遮盖得连缝都没有,像一床绿绿的厚毯子。人们对这块地也来了兴趣,见了张发子的面,都要竖起姆指夸上两句:
“张连长,你这试验地亩产万斤没问题,只会多,不会少!”
“张连长,你这回创奇迹,放大卫星,要上报,出名哩!”
这些不知是奉承还是真心赞扬的话,把张发子抬到了半天云里,他像喝了一瓶汉汾酒一般,浑身飘起来了。天气热了,那件黄破大衣脱去后,身上剩一件白布对襟衫,腰里扣根从部队带回的武装带,老套筒仍然倒背着。他不断地给说好话的人卷喇叭筒烟,一天三遍地在地边转游,看着那一片绿色,抚摸着软乎乎的苕藤,肚子里像装了几斤糖水,都流出嘴角了。有时,他抱着枪打坐在地头,望着苕藤出起神来。啊,理想马上就要实现了,报上登着他背枪的照片,他在嘻嘻地笑着,一个像石磙一样的大苕放在展览馆里,苕上系着红绸带子,县委书记亲切地握着他的手。他入党了,他当了金水大队的书记。张富子因打击革命干部,打击模范被撤职了。张富子来了,朝他谄媚地笑着,“发子哥,发子哥”叫得那样亲热,他决定头也不回,从鼻子里哼一声。
“你哼什么?”张富子叫子起来,把他从梦中惊醒了。他懒洋洋地站起来,张富子果然站在面前,脸上并没有谄媚的笑,而是对他冷冷地说:
“你这民兵连长蛮负责哩,成天保卫着你这一亩试验地,不可出岔子哩。我说,发子哥,公社王书记来电话,要在你的试验地挖苕时开现场会哩,你是不是明天上午把苕挖了,下午通知开现场会的人来。”不等他回答,张富子就走了。
嗬,开现场会!啊,露脸的时候到了。张发子喜孜孜地背起老套筒,去学校安排明天上午挖苕的事。可是关键时刻啊,他一遍遍叮嘱自己,要稳重,万万不能昏了头,产量肯定能达到的,人家都这样说。他一身轻快,走着走着,连跑带跳起来。
第二天一早,张发子像迎接盛大节日一般,全副武装起来,穿起单军装,扎起武装带,带起老套筒,威风凛凛。百多名学生吵吵嚷嚷地挖着苕。学生娃子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可谁也不敢啃一口那甜甜的苕,张连长在地边监视着哩,小宝扯住他的衣角:
“爸爸,我要吃苕!”被他给了一巴掌:
“小狗日的,这苕不能吃,下午要展览用。”
挖着,挖着,张发子心里有点慌了。那石磙一样大的苕呢?没有!连磨盘大的也没有。最大的只有他只从部队带回的搪瓷杯那么大。哎呀,怕要出问题了,哪来一万斤苕?这怎么交差呀!一时,他心里发火了,妈的×,这地也跟老子作对。嗯,说不定大的都长到地底下去了。
“哎,龟儿子们,再挖深些,下面有大的!”
小学生们拿出了吃奶的力气,把地挖了三尺深,还是没有挖出石磙大的苕来。他急了,他慌了,他骂人了。
“妈的×,妈的×,这是怎么搞的?这是怎么搞的?”
学生姓们黑汗水流地挖了一上午,好不容易把一亩地的苕都挖出来了。堆成两大堆。他在堆子旁来回地估量着。嗯,好大两堆,苕是压秤,苕铁苕铁嘛,看样子有一万斤。他喊住了带着学生正要离去的刘校长。
“哎,校长,你说这有一万斤吧!”
刘校长把堆子估了一番。“有!有!肯定有一万斤,张连长你放心吧!”说完堆着笑脸,赶忙溜了。
他等大家都走光,又围着苕堆转起来。有一万斤吗?好像差不多。不,好像差得远,那怎么办?下午要开现场会,得想个么法子呀!他就这样在苕堆边转来转去,转了一个中午,连午饭都忘了回去吃。
下午,开现场会的人都来了,公社的王书记,各大队的书记们都和张发子打着招呼。
“伙计,来向你学习呀!”
张发子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腿肚子有些发软,他越来越觉得这两堆苕没有一万斤,肯定要砸锅了。他一边和开会的人应酬着。一边用两只眼盯着苕堆,希望苕堆突然变大,达到一万斤。
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张富子几个人很快用磅秤把两堆苕称了一遍,天啦,两千多一点,还差七千多斤啦!
公社的王书记说:“老张,还有苕呢?”
张富子说:“就这两堆,还哪里有啊!”
各大队的书记一阵轰笑。王书记气冲冲地拔木牌子,拔不动,张富子连忙上去帮忙,木牌子拔出来了,王书记把木牌子朝路上一摔:
“哼,万斤苕,你欺骗领导,吹牛撒谎,富子!”
张富子忙跑到叔岳父跟前:“在!嘿嘿,您有什么指示?”
“你们支部开个会,严肃处理这件事,处理结果上报公社。”张富子正中下怀,连连答应:“好!好!”
张发子脑子响成一片:完了!全完了!
王书记带着开现场会的人走了。
张富子狠狠地瞪了张发子一眼,意思是说,怎么样?你的期限到了。
张发子坐在地上,脑壳深深地埋在大腿下,嘴里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他干么事要找这个麻烦呢?民兵连长当得好好的,偏偏种他妈的么事试验地!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试验地的路边上,木牌被王书记摔成了两半,下半块上赫然地写着“张发子万斤苕”,显得格外醒目。
金水大队党支部在书记张富子的领导下,对张发子的处理一点情面都没留。张发子不是党员,无党籍可开除,把他的民兵连长撤了,由连级干部降到社员。张发子没什么话说,他想,算我倒霉,我又没有后台。连级干部撤了,套筒枪上缴了,连那县报也成了新连长的卷烟纸。嘿。提起那县报,张发子就一肚子火,要不是它,他的连级干部怎么会撤呢?他怎么会想着去种什么试验地呢?
张发子正式变成了万斤苕。没有往日的威风,没有老套筒,人们当面喊他万斤苕了。书记的儿子张小军见了他,边跑边喊:
“万斤苕!万斤苕!”
小宝从学校哭着回来:“爸爸,小军骂你是万斤苕,嗯,嗯!”
“哭你妈的鬼,老子还没死!”小宝倒挨了一巴掌。
共产主义的前脚跨进了中国的大门,后脚又从后门里跨出去了。什么原因?大约是没有好东西招待它。没日没夜的大炼钢铁,粮食没有收上来,人们一天三两米的定量,树叶、草根都吃光了,共产主义饿跑了。
万斤苕老了许多,他的腰弓了,人瘦得像只大虾子,那件棉大衣更破了,腰上紧紧缠着一根草绳,一来防寒,二来把肚子捆住,免得咕咕直叫。他仍然爱在村里转游,代替套筒枪的,是一只捡粪用的小粪扒。他走到那些学生画的壁画前,望望那些画,心里骂道:
“扯他妈的蛋,芝麻哪能长得西瓜样大呢!”
有人喊他“老万”,这是对他的尊称,代替了万斤苕。
“你吃过了吗?”
“吃什么,一碗稀汤屙泡尿,早没有了!”那人叹了一口气说:“要是真能一亩地挖一万斤苕,我们也不会饿了。”
他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找个墙根坐下来,掏出烟荷包,烟叶早没有了,烟荷包里装的是枯荷叶。他用枯荷叶卷了一支喇叭筒,卷烟纸是小宝的旧课本。他吐了一口浓烟,望见了对面那堵墙,墙上正画着一个社员拿锯锯稻子,那社员真像他。
多少年过去了,万斤苕的雅号再也离不开他了。
别人喊他万斤苕,他也习惯了,也能笑着答应了。张发子这个本名被人忘记了。
关于万斤苕的故事,当年的金水大队如今的金水村的老人都知道。张发子的孙子后来读了大学中文系,做了作家,他在家乡作乡村调查时,知道爷爷绰号的来历,写进了他的非虚构作品中去了。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