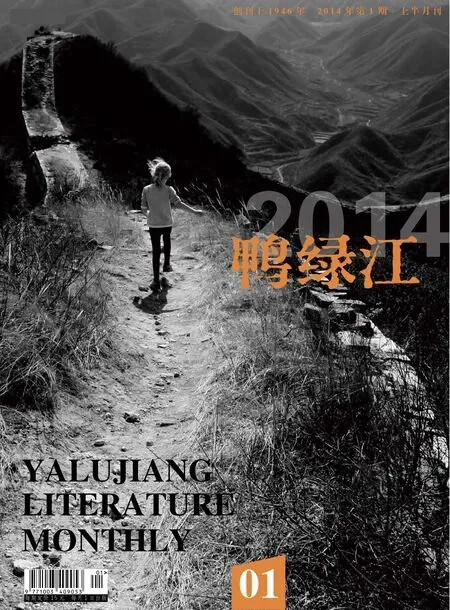走向魔性与灵光的天际
苏妮娜
走向魔性与灵光的天际
苏妮娜
ZOU XIANG MO XING YU LING GUANG DE TIAN JI

陈国峰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剧作家。他娴熟游走于传统戏曲、影视剧、先锋戏剧和理论批评诸领域。在传统与创新、感性与理性、规矩与解构之间,他常给我们一种灵性挥洒、汪洋恣肆的感觉。诸多领域里,他的先锋戏剧,是我们格外激赏的另类风景。《天堂或地狱》是他的所谓“超现实主义”话剧的三部曲之一,也是我认为最好玩的一部。这个感觉来自剧作本身的讽刺和幽默,也源于这部剧作巧妙的结构。但好玩显然不能概括它的品质,它的品质感来自于好玩后面那些严肃的东西,那种讽刺和幽默背后潜藏的格外强大的灵性与智性的力量,具备批判现实的自觉性,表现出我们这个年代稀缺的勇气。好玩(即娱乐性)与勇气(即精神力量)兼备,表层与深层角力,寓言性与现实感同构,这是陈国峰三部剧作最有魅力之处,而这一切暗合了我对复杂性的偏好,使我深深沉溺。
苏妮娜,2004年研究生毕业,现就职于辽宁省文艺理论研究室,任《艺术广角》编辑已逾九年,主要从事当代文艺、文化现象观察和研究,发表相关文章五十余篇。2012年获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从表层看,这部剧作写了三个不同的故事:前市长、大富翁、老妓女对待上天堂或下地狱的不同态度、接引灵魂的天使和魔使对他们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三个故事加起来具有一种总括性,象征性地概括了人类的世俗图景,而三个故事中的每一个,又都是一次次起伏跌宕的意义崩溃过程。从深层次看,穿插于三个故事内部的一个隐形的故事——天使和魔使的身世揭秘和当下的困境——则是更为核心的故事链,三个表层故事和一个深层次故事最后交融在了一起,以递进式的解构,使天堂和上帝的虚伪形象不断崩溃,最后坍塌。这是一次总的崩溃,带有终结性的意味,清晰地表达了作者对所谓“天堂”的彻底否定。与此同时,正面的主题,关于人必须自我救赎的命题,在隐形故事不断浮出表层的过程中,在天堂和上帝形象不断陷落的过程中,逐步加强,最后突显。这部戏值得深度阅读,如果只浅浅读一遍,就只能停留在“好玩”或“痛快”的直觉印象上,须拿出智性和勇气跟着往里走,才会发现这滋味很独特也很值得,品味之后很有可能会上瘾。
一、反转的妙谛
这独特滋味是如何构成的呢?除了有趣,我对陈国峰创作的另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机智。他常让我感到智性的强大。说一部戏机智或复杂、深刻,就是说这部作品不论是在意义层次上,还是在情节演进上,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层次,只建立一种秩序,只遵循同一节奏;也就相当于说,它在不断地脱离常规,不断颠覆既定认识,总是在貌似浮现出结论的地方,完成新一轮的反转,把你以为十拿九稳的判断推翻重来。于是你会发现这里没有真正的结论和注定的答案,像是一个永远走不完的棋局。这既是吸引也是挑战。
就拿核心的一对人物天使和魔使来说,第一个反转便是出场:天使一登场便翅膀退化、羽毛脱落、神色萎靡,这时,魔使登场了。魔使器宇不凡,张扬而直率、佻跶而潇洒,语言连贯,妙语如珠;天使却一直张口结舌,呆若木鸡,完全是一副屌丝的形象。这便是第一个层次的颠覆,颠覆天堂华美而地狱阴暗、天使纯洁而魔使狰狞的常规印象。这第一个层次的反转直接指向了最终颠覆天堂的用意,但这个过程并非只有一个步骤,即反转之后还有反转。在剧情推进的同时,魔使和天使的强弱对比再次反转。天使与魔使这对兄弟,既论断他人的善恶,也在自我审视和自我剖白。魔使那张牙舞爪的外表被不断地解魅,剥到最后只剩下一个软弱无依的灵魂,天使也被曝出杀死魔使兄弟的罪恶,但,天使不仅没有从精神上被彻底摧毁,反而摆脱了障碍,口吃也不治而愈。一直到最后送走几个死魂灵之后,魔使却步于地狱的黑暗,天使却甘愿为了赎罪而代替魔使,大踏步地开始了自己的地狱之旅。两次反转,完成了否定之否定,结果是:天堂或地狱都呈现某种疲软,某种虚妄,天使和魔使的身份和自我定位都出现某种摇摆。于是,需要回答的是推翻原有的选择之后有没有新的选择?人能不能在天堂和地狱之外,依靠自己,选择新的出路?这是《天堂或地狱》在反转之后布置给我们的思考题。天使和魔使,再加上其他三个主要人物,没有一个是单极化的,而是每个都有内在的复杂性——在他们的终极时刻,每个人都有对于命运出乎意料的选择及反应,这就是反转。人物行为的反转背后,跟随着的是这样一种认识:绝对的好人或坏人并不存在,道德的绝对性评价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存在主义法则:人能不能通过选择来决定自身的存在,对既有命运做出承担。
不仅仅是从整体的情节和命运走向上,即便从细部看来,每一幕戏成立的内在合理性上看,这部戏也在不停地反转,从貌似常规的地方和约定俗成的观念中发现了悖论的存在,从而揭示一切坚不可摧和磅礴伟大的虚妄性。
《天堂或地狱》起始于“终极审判”,这是宗教假定的一种情景,是对于生命价值、个人品性做总结和清算的权威仪式。在生命终了时发生最后的审判,这意味着,有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始终在注视着我们,并且不厌其烦地把我们的善、恶之念,善、恶之行,像班主任批改作业那样一笔笔记录下来。不许抵赖,不许托词,巨细靡遗。
这部剧作从这里开始,幕启时登场的魔使与天使,就把生命垂危的人,或刚刚失去生命的灵魂——引入对现世的罪与善的追述、计算、辩解当中。前市长、大富翁、流浪老妓女,三个即将奔赴前路的灵魂,各自携带着对此生的怨怼、绝望和不甘。那一颗颗走过生命历程、辗转反侧的心灵在这里通通说出他们生前无处可说、无人肯听的衷肠,戏剧等于是从开头处就进入了一个小高潮。不过,善恶之举本身,在这里不断地被推翻,被质疑,在多重话语当中,你会发现所谓事实在慢慢融化——
前市长本是此地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临终时医院的医护们却无视他、怨恨他、报复他,趁他没断气就要摘除眼角膜。他说自己是秉公办事,
是实现制度的净化、打击潜规则的温床,但被触动利益的权贵和小民们却认为他权欲膨胀、玩忽职守、贪赃枉法。当然,“政客标榜崇高”,是世界上“最最滑稽无耻”的事,显然这位市长一直大言炎炎欺骗别人和自己,连忏悔本身也是自己编织的一重话语帷幕,但指责他的人显然也是出于自身的立场,而所谓公正客观地评价这位市长的标尺,根本是缺席的。在终结审判的时刻,按照常理推测,总该是对他一个盖棺论定的时刻到了,总该是由天使推出一个客观公允的标准来了,结果是,天使自己倒是一副命蹇时乖的倒霉样儿,也无非是来“打酱油”的。在第二部分中,天使终于说出“不作为”的潜台词是“上帝只需要赞美和信仰,不需要真相”,那么,何谈终极审判?任何一个法庭,哪怕是道德的心灵的法庭,都需要以事实为依据吧?可笑的是,地狱来的魔使在证明起人们的罪行时,能出示确凿无疑的事实:于是,终极审判时,魔使好比主控律师,他为了证明人心中的罪恶,有备而来,动不动列举来自地狱调查局的证供;而天使却不像是为了良心辩护的辩方律师,他倒像是陪审团,不去取证,似乎天堂的职能确如魔使所说,已经运转不灵。于是,我们发现,对品行的终极斟定和鉴别,既无法依赖于忏悔者的自白,又无法依赖于周边的证词,这里,依据真实的信仰已经悉数拆解。这里被反转的是真实本身。
我喜欢这种层峦叠嶂的反转,但我揣测,作者熟练地应用这种反转,不是在炫技,也不是为了迎合谁的喜好。尽管陈国峰有好几套笔墨,好几类创作,其间有极大的差异,但是也有种内在的统一性,那就是对复杂性的偏爱,在这种复杂的反转中他在完成一种测度,度量一下事物的内里和人的背后还有多少个层次的自相矛盾,这当中他品尝到一种创作者才能享受到的乐趣。这才是反转的用意。拆解是因为不信任别人的建构,但拆解本身是一种建构,至少是一个明确的指向,那就是对他所认可的真相的一种追问,一种质询,一种朝向可能性的自由奔跑。
二、颠覆的意义
一旦天堂所宣谕的“善”被虚化,“好人才能上天堂”的标杆和尺度也就立刻失效了。天堂又如何招募志愿者呢?只好依靠门槛的降低。于是,天堂为了录取者所设置的门槛,干脆绕过了罪行与善行的事实本身,只简化为临死前是否忏悔这一条。制度一简化,立刻被人钻了空子,“上天堂”作为荣誉和光环也立即暗淡,因此,即便是做了忏悔,市长,或是任何其他人,也不必为了标榜自己是好人而往天堂里钻。何况,按照剧中的逻辑,天堂在生活方面,也是个索然无味的地方,“欣赏音乐,观看歌舞,阅读《圣经》”——“得了,别自欺欺人啦!天堂根本就不适合你!”果然,魔使诱导市长去发现自己的本心,那心心念念的绝不是天堂的所谓高尚,而是在权力欲望所代表的世俗争斗中做赢家,唯有这样才能找到所谓活着的感觉和价值,于是市长带着那高尚的说辞和蠢动的权利欲望奔赴地狱而去。很显然,终极审判压根就是在场而缺席的,天使的情感表现干干巴巴,他像他代表的天堂一样,没展现出任何魅力和能力,也就失去了终极审判的权利,让本该一笔笔清理的善恶是非,又重新归为一笔糊涂账。不光是界定善恶的事实被反转,连天使和魔使的使命——终极审判,也从一开始的清晰渐渐变得模糊。反转指向着颠覆,颠覆的不仅是天使和魔使、天堂和地狱的常规形态、常规印象,更是背后貌似不可摧毁的稳定的价值、体系、结构,所谓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
人们相信终极审判的存在,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是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前提。任何一种宗教,如果不是对人的生命做出有说服力的总结,并对“来世”和“死后”的生命状态做出承诺,就无法实现对现世的影响,无法对红尘中沉沦的灵魂施行引导、教习、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终极审判是极其严肃而且重要的,尤其是在曾经笃信宗教的西方社会里——尽管这承诺的结果是不可证的,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天使和魔使,作为“审死官”同时到来,他们倾听死者的哀告和控诉,又不断地用语言敲打死者,一方面是考验他们选择天堂和地狱的心意,使用着貌似公正的标尺——那来自上帝或魔鬼的权杖;而另一方面又在催促或者迫使死者不断地挖掘自己一次次行为背后的心理真实,一次次推翻那些看起来是确凿无疑的善举或恶行,从而导致对方改弦更张——这又暴露了天使或魔鬼本身的立场游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剧作者力图向我们展示的人性深处的灰色地带,那善恶混淆、私欲与美德交错的一幅幅混沌图景。有意思的是,人的语言表达、人的行动立场、人的愿望动机,几者之间的不协调,构成对善恶标准的一种模糊,在观众心理中不断设疑,致使审判标准的一次次被解构。不仅好人上天堂,终于会成为一句空话,就连什么人才是好人,也受到敲打并最终粉碎。这种解构是全方位的。
最后摧毁这个审判标准的,是天堂准入制度本身的悖谬之处,解构天堂价值体系的,不是来自于地狱的魔使,而是来自于天使及其代表的上帝。剧中绝妙的讽刺,都是针对着天堂和上帝这位至尊,尤其是这个天堂的准入制度——忏悔条款及其解释。
这部剧对天堂准入的一套刻板仪式极尽讽刺。天使哥哥尽管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但在忏悔中却得到了天堂的接纳;魔使弟弟尽管被杀,却因为怀着对人类的极大仇恨而堕入地狱。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本心比行为更重要,这是天堂对死者接纳的规则,出于对人性本质的测量,而不以结果的对错而论。但是,显然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完全有空子可钻,这就是规则脆弱和荒诞的一面。这显然是对路德新教 “因信称义”原则的嘲讽。地狱对人的本质性欲望既是纵容也是解放,并且对恶做出无条件的承担,其灵活和有效,足以使魔使散发出人间精英的气质。与之相比,天堂对善行的召唤和垂询显然手续烦琐,且极为教条,发出类似官僚体制的腐臭气息。市长或是大富翁,都在不断地钻天堂律令的空子。在精通规则者眼中,经由信仰到达福地的承诺,已变成一场庸俗的交易,天堂无非是又一处高档会所,提供另一个世界的VIP服务,可以凭交换所得。
关于“天堂准入制度”,“最终解释权”归天堂,也就是归天堂代言人的天使。天使恰如魔使所讥刺的那样,状态并不好,对上帝钦点进入天堂的人,并没有格外上心,这无疑是失职,但是剧作者借魔使之口对天堂和上帝冷嘲热讽,倒是使人看清楚,天使无心行使的标准,倒像比天堂的条规制度更公允些。他一直精神萎靡、心事重重,岂不知他是对什么人该上天堂有准确的判断。经验的操作上反倒胜于教条,他行使那磕磕巴巴的“解释权”,便把一个他本来就无心招募的人拒之门外,而且理由足以把对方气得失去理智。
表层上看,剧作分三个部分,写了三个垂死、已死者,事实上交叉在三个故事当中的,是魔使和天使这一对兄弟的生死纠葛。这一对审死官之间的是非和选择,才是剧中的核心矛盾。魔使就灵魂的交易讨价还价的画面,最早在《浮士德》之前就已出现了。但是这一次,比魔鬼更鲜明的形象是纠结的天使。魔鬼的可爱之处在于对欲望的充分理解,魔鬼以及魔使,要比天使更理解“人”,理解人的欲望,并且从这里找突破口带人们到地狱去。问题就是向善和向好的力量也出自人的天性,但是对这种天性的体认却充满苦涩,否则天使不会是时下常被人讽刺的“屌丝”形象。剧作虽然沿用天使魔使的结构和模式,但是显然意在颠覆,天使代表了上帝,但他无心于拯救的角色。在他面前,更重要的任务不是度人,而是度己。如果身为天使尚且生活在内心的黑暗当中,那么天堂的实质性感召力又存于何处呢?没有天堂作为终极理想,一个灵魂又要投奔到哪里去呢?如果这部剧作的意义和价值仅仅是颠覆,那么所谓不断循环的反转就只是一场一般性的喜剧而已,关键就在于,剧作还要给灵魂一个出路,它有能力给出这个出路,构成一个关于起点的终点,给出了开放性,给出了一种动人的光亮。
三、把选择的权利交还给人
一个诱奸少女、得了前列腺炎和老年痴呆的上帝,一个时运不济内心纠结失手杀亲的天使,一个滑稽可笑的天堂准入制度,一个取消普通人的基本欲望却需要不停唱赞歌的虚伪文化,这一切都指向了天堂对人的终极召唤的失效:人们既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儿,也不知道去那到底有什么意思。天堂或地狱,作为非此即彼的选择,显然不能尽如人意,譬如,对于魔使和天使兄弟而言,二者都有待不下去的苦衷。于是,在熟练地设置继而调侃了二元模式之后,又开始了对模式的自反:二元之外,还有没有第三种选择,也是最理想的选择?
有的。选择的权利依然握在自我的手里。
这个故事的最终走向是,天使做出了最不可思议的选择,他不是为了向魔使认输而去了地狱,而是因为他要为自己担当,不仅是赎罪式的担当,也是为了挣脱天堂强加给他的束缚。道德,本是一种信念,却被转换为一种束缚,当“善”从发自内心的情感指向转化为宗教教义之后,当信仰成为制度、当道德成为律令,它其实已经站在人的对立面,从人的情感枝干上被剪掉了。因此,可以这么说,作为教旨、律令、秩序和制度的善,是被人为规定的,是不信任人的本性的。而真正的对善的信仰,是发源于人内心生长的意念,以及对这种意念的坚持。道德只有内化为情感,只有当人面对道德选择却浑然忘却了所谓道德,依照本心便合乎道德的时候,人才有可能把善作为一种信仰,而天堂就存在于人的善念之中;否则为了表现善而行善,所谓善举也无非是一种贿赂。
天使杀了自己的弟弟,尽管在真心忏悔的一刹那死去,由此进入了天堂,但却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这就指出了一个命题,救赎之所以不能借助外力,是因为不原谅和不放过的执念本身比天堂的制度更严格,它产生于人自身,产生于善的意愿和对灵魂拯救的意愿。宗教需要信仰,但是信仰却不一定只能皈依于宗教。人总要寻找一种把自己从现实痛苦中解脱出来的能力,相信有这种能力的存在,这就是信仰。这种信仰是指向人本身的。
三个故事当中,上帝所代表的高尚形象一层层被剥落,到最后一个故事,上帝其实一直怀着他本身都无法超脱的怨恨,才把苦难播撒给如同老妓女那样的无辜者,而我们被迫要面临这个问题:是否要把信仰交到这样的人手中?是否要信仰这样的上帝?上帝只是这剧中的一个角色,此番塑造的用意并不在于攻击宗教及神的教义。这部剧中天堂崩塌的过程,隐喻着近两个世纪,人们把自己的精神家园寄托在各种说辞和由之衍生的乌托邦世界之后,渐渐萌生的觉醒。既然天堂如此脆弱不堪,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之后,从神的怀抱挣脱之际,人们是否只能在不信和不解脱的苦海中挣扎沉沦?如果人不信自己,还要上天入地去为自己寻找新的权威、新的神迹么?如果说20世纪的人祸大于天灾,就在于——越痛苦,便越盲目地崇拜和信仰;而越是盲目地崇拜和信仰,痛苦就越加剧。一个凡人,选择了信,因为这是面对无常生命最好的精神选择,但如果他发现,他的信仰被利用,被用来制造恶,他的信仰转而成最坏的事,这岂不是人活在世上遭受的最大的欺骗?二战之后,德国哲人们围绕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一人类的罪行象征,做了许多深刻的精神反省,包括:第一,盲信导致集体的犯罪,不加理性审核的盲目信仰会造成极权,而极权导致集体的犯罪,就会使人类永远在炼狱中沉沦;第二、集体的犯罪导致集体的麻木,没有哪一个具体的人会感到罪在己身。而事实上,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罪。唯有以乌托邦理想编织的制度理念彻底崩塌,人们才能更好地反思作为个体的责任。回到《天堂或地狱》,犯过罪责的天使便是这样一个罪人形象的投射,他不以天堂的接纳而终止作为个体的反思。天使作为一个凡人犯下的罪恶,是因为内心的怨恨无法排解,在非理性状态下他选择了罪恶地爆发,瞬间爆发之后他醒悟过来,立刻处决了自己,并做了他的第一次忏悔,他的忏悔为天堂准入制度所接纳,因此他成了天使。这是一次针对恶行为的忏悔。而第二次的忏悔,也就是面对成为魔使的弟弟一次剖白心迹,则是针对恶的根源的忏悔,面对的是自己,指证的是本心中残余的罪孽,天使在这第二次忏悔之中获得了真正的解脱。第一次的忏悔,他一死摆脱了在世生活的苦,进了天堂,但却无法解决他的心结;第二次忏悔过后,他决定走出那个缺少精神能量的天堂,是因为他终于能面对世界坦承自己的罪恶,并决定承担自己,由此,才结束了灵魂的受苦。把自己从意念的地狱中拔出来,还是依靠人的自我反省。可见,人的救赎力量本来就在自身手中,相信这种力量同样是一种信仰,如果不能找到这种力量,即便身在天堂也如同炼狱;反之,便步入地狱也如在天堂。当天使走向地狱的时候,我终于从天使身上看到一种豁然一种明朗,那是生命本身的光亮。
四、带着魔性行走
我常常感觉陈国峰身上有某种魔使的特质,他的写作追求一种不断加速不停反转带来的激情,这是赛车手在赛场上的状态,不疯魔不成活,从激情和感性的角度来说,这是创作的引爆点,另一个方面,魔性意味着运用常人的智慧,便能拆穿一切话语所谕示所虚构的至高无上。这是一种反叛。这部剧作里,你一定能感到,他爱好揭穿那些磕磕巴巴难以自圆其说的炎炎大话,解构那些假借信仰、制度、伦理的名义却桎梏人性的东西。与此同时,他投给人本身的,也不是一味的宽容慈悲,而是他独有的一种金属般的眼光,或者说是天生反对派的眼力,他以之反复地逼视出人物内在的伪善、软弱、灰色的质地。陈国峰有一种“一个都不放过”的彻底性和纯粹性,对此我无以名之,只好泛泛地称为“魔性”。魔性的种种体现统一于对“自由”的执着。体现为不竭的激情、不停歇的探索和不设限的自觉。
如果用酒来打比方,陈国峰的这几部戏有着很醇的浓度,很高的烈度。密集的戏剧矛盾,意识与无意识的辩驳,善与恶的轮番表达,真实与虚妄的交错,以及情节的冲突往复,开开合合,对话蕴含的力量关系火花四溅或暗流涌动,人物心理的软弱、犹豫或强势反弹,等等,在他的戏里都以很高的频次、很快的节奏呈现出来。彷佛这些内容在表达出来之前,孵化在作家的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之时,就带着着很高的压强,而一旦表达出来,便形成了一个旋涡,把人送往一个不可知的中心去。这是很带劲很过瘾的体验。带劲和过瘾还因为这些戏剧的内核其实是未知的,夹带着我们的惶惑和荒谬感——作者就没打算带我们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正确结局那里去。这样的戏是有寓言性的,因为它浓缩了我们对世界的某种认识,带着某种似曾相识的面目,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上演,并会不断继续演下去。但这戏又不完全是寓言性的,因为寓言总是某一种经验的凝结,带着舍我其谁的正确性,而这几部戏剧却显然不提供对世界现成的判断,而宁可悬置一个具体情境中的最后判断——尤其是要排空寓言经常提供的道德判断。谁是精神病患者?无解,也许剧中二人都是,也许都不是;也许疯狂的是这个世界,而人的精神疾患只是对应世界的一种方式,甚至是一种自我保护。天使和魔使谁是无辜的,谁是有罪的,谁会完成对谁的救赎?凶手何以会上天堂,被杀者却在地狱,天堂或地狱,谁是最终的选择?这一切都没有现成的解释。当然,判断是有的,道德问题也是这剧作所关心的,只不过,它不规定唯一的答案。戏剧本来就不是用来解释生活的,它需要呈示的是一种探索,重要的是对终极思考不断逼近。这样的剧作富于某种幽暗深邃的魅力,也予人一种不断前行的力量。陈国峰的这三部剧作,有种稀缺性的品质,是逼人而来的一种锐利,这种力量我们久违了。但内容却不眼生,因为看似谈鬼说虫,或是谈遥远的异国,但内在仍是沉甸甸的现实关注,是对人的荒谬处境的大胆直视。那种站在现实对面大声发笑的勇气,是很多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所不具备的。这个年代的荒诞剧之一,就是:人们常常忍受着傅粉施朱的现实主义,尽管明知其内在的现实精神已经萎谢了。
有人指出陈国峰的这几部戏可以称为超现实主义。但我却觉得,其实不必以此冠名。事实上,是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太僵化了。我们缺少那种能力和意识,因此没有在精神现实的意义上去探索现实,也就不能实现各种各样的自由表达。而这正是陈国峰所做的。这不是超现实,这正是一种带着自由探索意味的写实。已被界定的现实主义常常意味着不能摆脱当下,暗示着人只能像匍匐的灌木一样紧紧抓住地面,不能御风而行,也不能在树梢跳舞,须严肃而明确地描述世界,并且始终带有完整的价值判断。与之相对的,便是不严肃和任性,是住在人类心里的顽童跑出来捣乱。拘泥于形式上的现实主义常常使我们忽略了内里。现实主义走到今天,我们必须追问:它所指称的现实本身到底是什么?它所张扬的现实精神,到底是怎样一种精神素质?正是因为人们总是离开现实性关注去理解现实主义,以至于现实主义经常被架空,经常被陈词滥调所代替,因此它被指责为虚伪,是现实的赝品。事实上对现实的深度关注不一定容纳在被称作现实主义的方式和风格中,真正可贵的是现实精神,它完全可以独立出来,放在别的形式当中。陈国峰这样一个积极入世关注现实的人,就常常会采用一种看起来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现实关注,由此创作了一系列这样的剧作。这个维度的创作袒露了他真实的心迹。荒谬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而那个理性清明井井有条的世界,毋宁说是出自我们的想象。所以看似荒诞的,反而最逼近真实。抵达这种现实,需要我们透过事物的表面,不断地向下挖,去寻找内在于社会现实中的人类的精神现实。人类每往前一步,对现实的内在精神性维度就越关注一些,而唯有试图突破内在的困境,艺术的创作才能获得价值感,才能征服真正关注自我内心处境的人。好的作品令人迷恋、欣羡、流连,就是因为它总能戳破生活的硬壳,不断击中深藏于心的自由和激情,给我们一种遥远天际的另类光明。
责任编辑 陈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