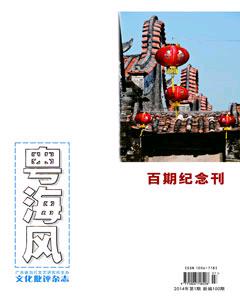人文关怀、文化自觉与批评尺度
庄伟杰
一
时令进入癸巳金秋,遥望南天,想起南国大地,想起岭南风光,想起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那片热土,似有一股金风徐徐拂来。沿着风的指向,令人仿佛看到珠江腾跃的浪花,南海抑扬顿挫的潮声,都在弹响富有强烈节奏的音符,无论是盎然得叫人荡气回肠,还是律动着暖流细浪,皆蕴含着无尽的意味。
作为一个走在文化苦旅上的游子,因为怀揣一份挥之不散的文学文化情结,此刻,我的内心似乎被一个十分形象而灵动的名字——“粤海风”所攫住。它作为一个自然意象,在思维的接合点,让我禁不住联想到那本以《粤海风》命名的文化批评杂志。当粤海的雄风、文化的气息在这里流淌或者凝聚,正如高架桥横空的走势,梦想的无限延伸,所有呈现的文字垒起的堤岸,逶迤成一道灿烂的人文风景,让一座南国都市的立体思维,显得更加开阔。
春秋代序,满园生机。欣闻自从1997年改版之后的《粤海风》,即将出满100期。如是屈指盘数,至今已走过了16个年头。作为它的一名忠实读者和受益者,我深知在一个谈“股”论“金”的时代,一本纯粹的文化批评杂志在文学走向边缘化,文学刊物处境窘迫、甚至吃力不讨好的现实境遇中,依然扎根于边缘地带,在沧桑岁月中坚守延展,在艰难与恬淡中自然生长,并逐渐地引起海内外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其影响力已从文化圈扩大到社会各界,让人感知到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气息和文化脉动。这本身就是一种能耐,一种气象,一段历史见证,一方文化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粤海风》这十数年的办刊实践,既为多元时代的文化现场发出清晰、理性、鲜活的声音发挥了先声作用,又驱使我们思考如何重新定位杂志与建立起批评尺度,提供了生动而有力的注释和启示意义。同时,也生发出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二
当我提笔想为《粤海风》百期纪念刊写点东西时,万千感慨一齐涌向心头,联翩浮想像一叶扁舟飘荡在浩茫的感受大海之中。毫不夸张地说,缘结《粤海风》,结交素未谋面的徐南铁主编,无疑的已构成为人生中一段值得格外动情和珍惜的记忆,凝成为一份富有诗意的美好情结……
往事并非如烟如梦。认真说来,与《粤海风》及其掌舵人徐南铁相交往,应是跨世纪之交的事情。那时,我像一只遍体鳞伤的“海龟(归)”爬上岸来,落满尘埃的灵魂,期冀重新涅槃和飞翔,驱使我依然走在路上,一边继续从事创作,一边把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展开探险——批评之旅。承蒙谢冕先生不弃,1999年秋季我荣幸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北大中文系做访问学者。就在那时,我从众多文学期刊中发现了《粤海风》杂志,它的丰富多样、它的办刊风格、它的文化品位、它的领异标新,在瞬间抓住了我的眼球。于是,我兴致盎然地把一篇题为《女性、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的评论,直接投寄给徐南铁先生。由于稿件是断想式的批评文字,能否发表还是未知数。料想不到,徐先生处理稿件之快令人惊讶。除了把拙文刊发于《粤海风》2000年第7-8期上,我还获得意外的礼遇,即从此获得该刊的长期赠阅。这对于一个刚刚转型从事文学批评写作的青年来说,不仅是一种奖掖,更是一份关照和鼓励。之后,我们便建立起友好而持续的往来。时至今日,我几乎每年都有批评文字在该刊“亮相”。可以说,我的文学(艺术)批评之旅是从这里起步的。
倡导以“文化的现象批评,现象的文化批评”为宗旨的《粤海风》,其影响因改版成功而渐渐引人关注。它不仅为当代批评家、学者提供了公开发声的平台,同时在张扬着一种写作精神,敞开一种自主而开阔的批评空间。于是,很多批评家的成长和崛起,往往与之构成一种特殊的关联。诚然,一本杂志的影响力的形成,同样离不开刊物主编的才情、智慧和人格魅力,尤其是地方性期刊。换句话说,一家刊物的命运往往紧系在主编身上。徐南铁和《粤海风》的关系,就是最生动的案例。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主编,要把一本刊物搞上去,必须具有三种姿态或情怀:一是热情和信念。这与其说在编辑一本刊物,毋宁说在守望自己内心的信念以及对文化的热情。否则,是很容易被外界的喧哗所搅扰的,更难以持之以恒地坚守。二是眼光和胆识。一本文化批评类杂志要在一个开放的大省扮演文化改革助动力的角色谈何容易,主编者必须具有过人的眼光、胸襟和气魄,如是方能吸引名家来稿又能从中发现新锐,把手中的刊物办成一份被批评家和读者普遍推崇的重要阵地而产生影响。三是自我牺牲精神。根据笔者自身的经历和体会(本人曾在澳洲担任一刊一报的社长兼总编8年有余),一家媒体的主编,不仅要敬业乐业,甘为她人作嫁衣裳,还要心无旁骛深扎进去,才有可能把刊物办好办出特色。自从接手《粤海风》之后,徐南铁付出的精力、心血和劳动是可想而知的。从我们的交往中,笔者方才发现,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精英,是一位兼具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书法家等多重身份的南国才子,曾在某个小圈子被誉为“羊城八支笔”。我读过他惠赠的长篇报告文学集及散文集《三十不惑,四十而立》,为他的文学才情所感动,为他的文字功力而拊掌。特别是《粤海风》每期的“卷首语”堪称一绝,我每期必读。卷首之文,多为短论,然虽短尤精,见解独到,精彩纷呈。或击中时弊,或畅所直言,或高屋建瓴,集中地表达了自己的编后心得与感想。我曾有感而发:“那里面大多是对于人生与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追诉与思索,是以一种开明的心境与姿态去张开其思想的一角天空,即理性思考、呼吁与诉求。”为此,记得我曾写信建议他把“卷首语”单独汇编成书。至于他那笔走龙蛇的一手好字,更是叫人喝彩。相信读者从《粤海风百期纪念刊约稿信》(见《粤海风》2013年第5期)中便可窥其一斑。首次在刊物上看到如此别致的邀约方式,令人耳目一新。观其书法,可谓赏心悦目。流动飘逸的线条,灵活自如的结体,布局有序的章法,摇曳多姿的笔致情韵,扑面而来的书卷气息……恕我斗胆妄评,然洵非溢美。话说回来,他本来完全可以在书文创作上走得更远获得更多硕果,仅仅因为长期担当《粤海风》主编等繁重工作,无形之中就得牺牲这方面的才华和精力,包括宝贵的时间。或许,这是一种宿命;或许,一个优秀主编的背后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三
一本批评类刊物的魅力,不一定是它的缤纷,更多的是来自于其中的冷静、沉稳、锐利和自信。
在这个大变化的消费时代,对于一本新改版的文化批评杂志,要持续坚守实属不易,更遑论要办出自己的风格特色,改变其生存格局。对此,徐南铁深有感触:“人文社科类期刊因为贴近意识形态,除了要考虑市场和受众之外,还不得不花许多精力去考虑说话的方式,把捏说话的分寸。这就是中国期刊市场的现状,它是读者的取向,市场的取向,更是社会的取向,是主流意识形成的取向。”(见《杂志的生存》,《粤海风》2013年第5期·卷首语)面对这种尴尬的现实境况,其中的甘苦得失局外人可能无法想象得到,但作为一刊之主,徐南铁是清醒的,也是明智的。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类刊物的确首当其冲面临着生存考验,也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展开运作和定位,并以此参与到当代人文精神的重建进程中。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在他看来,文化的传承与健康发展,尤为需要理论与批评的正本清源,才能展开公正、客观和有效的文化批评,从而构建起具有现实冲击力和历史穿越力的文化评判体系,驱动文化审美自觉地进行当代性的现代转型,并促使社会审美向高雅转化成为一种可能。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由传统人文精神向现代人文精神转型的三重转型所构成的巨大社会变迁中。社会各种杂陈纷然的文化艺术思潮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是自西方涌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谓崇尚非理性、解构真理和理想、追求游戏状态,已占有一定的文化市场;另一方面是以儒道释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在急遽的社会变革中仍存有根深蒂固的影响。置身于广东这片经济发达、百废俱兴的热土上,生活在这里的广阔人群该怎样应对,如何思想呢?或者说,面对这个大变动的时代,如何寻求以现代化追求为旨归的文化思潮,即尊重理性、个性和人格,崇尚民主与平等,倡导科学精神这一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已然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徐南铁似乎深谙其中三昧。作为一个经验丰富、颇具远见卓识的文化人,他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文化旨趣。他深知在这个充满功利的时代,尤其需要文化的熏陶,思想的滋润和美的纯化。
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尤其是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一些文化人精神的失落造成了片面追求物质、精神平庸和信仰缺失的现象,反映在文学艺术界则显现出浮躁不安。价值观念趋于多元,物质至上的社会心理,必然导致耽于娱乐的消费文化欲望。于是,社会秩序、文化秩序、心理秩序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难怪乎《西方正典》一书作者哈罗德·布鲁姆声称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并直言作为文学批评界的一员,自己遭遇到了最糟的时代。在这种历史境遇中,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抵挡不住物质的诱惑,精神大面积地撤退,众多的文学文化期刊也纷纷改弦易辙,甚至四面出击举办形形色色的创收活动、收取版面费等等,结果导致集体性的话语大滑坡,忘却了文学艺术的真知及其人文精神。身处其中,《粤海风》依然冷静、沉着,不愿媚俗跟风,并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从容应对。在办刊策略和定位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广开言路,注重现代人文精神的重建。从某种程度上看,作为一份文化批评杂志,《粤海风》的开明、坚守和通达,乃是广东精神的一种文化象征和小小缩影。而这与杂志掌舵者的知识结构、生命意识和文化精神是息息相关的。
四
一个时代理应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与艺术形式,建立自身特有的时代人文精神。而文化自觉对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未来,对于社会文明的进步至关重要。因为文化自觉是建立在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与自信心态。一本批评类杂志作为一个文化窗口,所传达的声音尽管有限,只要能在文化自觉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就可塑造成连接文化与受众、主流与民间相互动的载体。一旦文化批评场域扩展开来,其潜在的作用和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最匮乏的是什么呢?应是以更加开放的文化姿态,既倡扬科学理性又高扬现代文化精神。我们知道,自近现代历史以来,报纸、杂志曾经以自身充满人文气息的声音影响着中国的核心阶层。然而,当代文化刊物却出现了生存焦虑,常常遭遇被忽视被冷落的局面,明显的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的确令人深感无奈和困惑。加上许多文化人缺乏必要的道义、责任和担当意识,日益丧失了思想创新能力,于是在许多关键时刻,文化批评的声音疲软不堪乃至患上“失语症”。更多的人似乎很少真诚地正视和思考发生在我们周边的、正在形成的新的文化格局与文化情境。殊为难得的是,《粤海风》却能以它独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团结一批老中青文化批评家和学者,推出了诸多对社会历史文化与文学艺术具有深度思考且体现出探寻现代人文精神重建等具有问题意识的佳篇宏论,或者刊发了一些来自生活现场且有感而发的精彩时评,抑或抓住一些前沿文化话题和热点文化现象,展开深入而平等的对话,等等,从某种程度上,为当代文化期刊如何前行,为寻求新的文化理念和建构新的文化环境提供了一种参照。在社会转型大变革时期,或许这些声音和论说未必能直接产生什么实际效应,也未必能对于社会和文化方向起到什么引领的作用,却能以自己独有的品质,为更多有志于推动文化(批评)发展的人所记取所呼应。确切地说,《粤海风》的存在本身,已经体现出一种现代人文关怀。
著名人类文化学家费孝通生前曾给文化自觉提出一个坐标系——纵轴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个时间轴;横轴是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确定共存在的意义和对世界可能做出的贡献,这是一个空间轴。当代文化批评如能以此坐标系为参照向度,在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更为理想地找准自己的方位,相信当代文化批评写作(实践)的有效展开就能在文化大道上纵横驰骋,步步为营,渐入佳境。
五
成功改版之后并迈开步伐走向100期的《粤海风》杂志,为文化批评写作构筑了一个开放的发表平台,以及平等对话的姿态,已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回眸巡视,正是凭借自身的办刊策略和长期累积的编辑经验,它为当代文化的批评尺度,起码带来了几个方面的有益启示。
首先是文化批评要有客观性。即批评家应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根据事实或依据具体文本说话,或透过表象背后的真相揭示加以言说,而不是根据作者的身份职位或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言不由衷。其次是应有针对性。立足现实,关注当代,抓住现象,有的放矢,以理服人。看待当今的文化发展,最好站在一定的制高点,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着眼于当代文化的创新机制。这与尊重传统、尊重前人经验并不相悖。再者是需有前瞻性。面对当代各种文化现象,或面对某一个具体的批评对象时,能否把过去、现在、未来综合起来考察透视,以前瞻其发展前景为旨归,往往是批评家是否高明的分水岭。批评家的前瞻性应对所评论的对象,包括具体文化现象、艺术文化思潮的选择中表现出来。对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对象做出深入研究后,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思想见解和学术创见。优秀的评论家,应有常人所不具备的学术敏感,善于从纷纭的文化现象或文化艺术活动中,发现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普遍性的特质,并从文化、人文的角度出发予以观照。一言以蔽之,批评家的思维应该是超前的、独具慧眼的。复次是探索性。一个思想锐利的批评家,总是置身于当代文化的现场,以丰沛的文心和深湛的思考力量,观察、发现并善于提出问题,同时具有不同于一般的理解力和陈述力,既敏锐独立又充满探索意识,寻求一种自由境界,力求建立属于自身的主体精神。另外是导向性。人们的意见形诸文字,发表于各种媒体,都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形成导向,批评家的意见尤其如此。真正的读者总是期盼正确的导引以升华灵魂,深受启迪。或能激浊扬清,褒美贬丑,驱动当代文化艺术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报刊本身就是舆论导向的平台,自有其鲜明的编辑意向、文化定位和宗旨。如果被评论者用非正常手段换取了评论家的话语权,或换取了媒体的导向权,那么真正的文化批评就可能变成一场由外力导演的闹剧或丑剧,那将会是当代文化批评的不幸。但愿这只是个人的一种担忧。
以上拉拉杂杂、连篇累牍地说了些许肤浅的感想和不成熟的看法,说明笔者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如果有说到点子上的,自当庆幸或聊以慰藉;假如没有,却能得到走在文化之路上的同行方家的赐教指正,也将令我欢欣鼓舞。
一份刊物的定位和坚守,文化批评的兼通与批评尺度,这些因素的合力,只要形成一种人文精神气场,就有可能成为历史和这个时代的见证,也见证了自身的平稳发展,并意味着文化批评(写作)的可能性,自然的也将在不断探寻和加以完善的进程中指向美好,径直通往未来。
但愿《粤海风》越办越起色,风行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