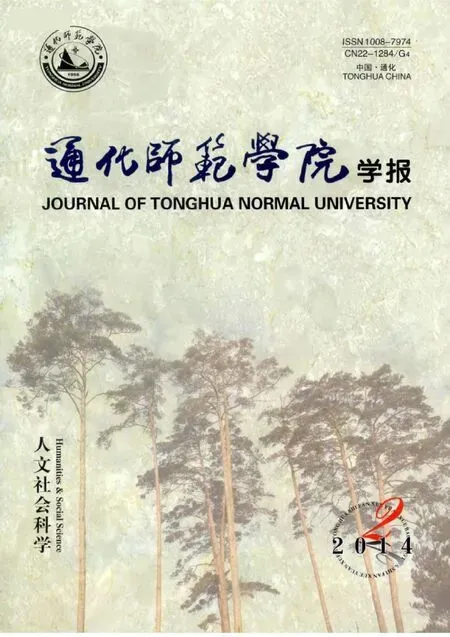论唐传奇中人鬼恋小说的母题演变及发展动因
赵 妍,杨 雪
(吉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了唐代,传奇可谓大放异彩。它前承六朝志怪,后启宋元话本,而与前朝小说相比,唐代传奇的笔法更为细腻精妙,故事情节更加丰富离奇,人物情感亦更加浓烈奔放,是中国古典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
唐代中期是唐传奇的繁荣时期,从作品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神怪、爱情、历史、侠义等题材。其中有些作品内容相互交叉,如神怪兼爱情类的题材就很多,人鬼恋故事即属其中。这类题材并非始于唐代,早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就以清晰的面貌和鲜明的个性完整地出现在的志怪小说中。而作为前朝志怪小说的继承和发展,唐传奇中人鬼恋小说的着眼点已从鬼神之“怪”转向人事之“奇”,通过描写人与鬼的婚恋来反映世俗爱情。
一、人鬼恋小说的题材类型
唐传奇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将近20篇。有学者将其分为以下几大类:一类是在魏晋志怪《列异传》中《谈生》、《辛守道》的情节结构模式基础上进行演绎。如《广异记》中的《张果女》、《王玄之》;第二类是古代冥婚风俗在作品中的升华。故事背景在女方死后展开,生前与该女子或相识或素昧平生的男子进人墓冢与女鬼相爱,终成“眷属”,并为封建家长所认可。第三类,展示男女主人公生前相恋,死后续缘的过程,情节曲折,情韵悠长,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生死之恋的浪漫小说。代表作品有《李章武》、《唐煊》和《华州参军》等;第四类小说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着力描写“现代”男子与古代女鬼之间的爱情,情节更加荒诞离奇,比之前三类,道教的精神在这类小说中有更明显的体现。如《崔炜》、《张云容》等。
二、人鬼恋的故事原型
“鬼”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为:“鬼,人所归为鬼。从儿,由象鬼头;从么,鬼阴气贼害,故从么。”灵魂永生的观念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早已根深蒂固,它是创作人鬼恋故事的灵感源泉。源于灵魂的永生观念,故在民间就诞生了冥婚这一独特婚姻形式的发生。
所谓冥婚就是为使生前未婚的亡魂在阴间也能过上夫妻生活而举行的婚礼。这种风俗由来已久。《周礼·地官·媒氏》中记载了有关条文“禁迁葬者,与婚殇者”,唐代孔颖达疏云:“迁葬谓成人鳏寡,生时非夫妇,死乃嫁之。嫁殇者,生年十九已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殇娶者,举女殇,男可知也。”但因冥婚耗费人力、物力且毫无意义,曾被禁止,但千百年来这种陋俗始终没有杜绝,即便在现代,冥婚仪式也是有迹可循的。因此可以说,这种风俗的盛行不衰正是一个个凄美的人鬼之恋故事源源不绝的现实基础。
三、唐传奇对人鬼恋故事的创新
唐传奇中人鬼相恋的小说比比皆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 《李章武传》、《华州参军》、《唐煊》、《崔炜》等。作品在情节上虽然是对志怪小说的继承,但还是有些创新的尝试值得我们注意。
1.由谈鬼色变到人情味十足
在六朝同类题材小说中,男女主角大都是在男方不知女方为鬼魂的情况下产生爱情的。但当男方得知爱人的真实身份后大部分却因恐惧而死,小说不自觉地就被笼罩上一丝恐怖的氛围。而到了唐代的传奇小说,女鬼们依旧保持娇好的形象外,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情味,她们对所爱恋的男子情真意重,至死不渝。如《李章武》中对女主人公王氏子妇的描写,“或竟日不食,终夜无寝”,因为李章武离开后,王氏思慕至切,不到二三年便忧伤而死了。而在她死后,对章武的爱恋却没有丝毫减弱,仍像生前那样柔情似水,美丽动人,只是来去倏忽。
“视衣服,乃主人子妇也。与昔见不异,但举止浮急,音调轻清耳。章武下床,迎拥携手,款若平生之欢。自云:‘在冥录以来,都忘亲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与狎昵,亦无他异。”[1]
得知王氏非人之后,章武并没有惧怕而死,而是急切等待他的爱人前来。打破了前朝鬼话小说的恐怖氛围。
“至五更,有人告可还。子妇泣下床,与章武连臂出门,仰望天汉,遂呜咽悲怨,却入室,自于裙带上解锦囊,囊中取一物以赠之。……款曲叙别讫,遂却赴西北隅。行数步,犹回顾拭泪。云:‘李郎无舍,念此泉下人。’复哽咽伫立,视天欲明,急趋至角,即不复见。 ”[1]
临别赠物,再现款款深情,女鬼情之真切,与世间女子无异。
2.由阴阳相隔到生死相随
这一时期的人鬼恋故事中,不论男女主人公以什么方式相遇,这些女鬼一概是美丽且深情,但这一场场“艳遇”到了最后往往却因最终人鬼殊途而不了了之。
在这些作品之中,《郑德楙》对故事结局的处理则有别于其它小说以男女永诀抑或复活团圆收场,那就是在艳遇过后,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未因为种种外界因素而断绝,相反,跟女鬼约定的时限一到,郑德楙竟坦然地安置好家中事务,第二天便“暴卒”了。这一结局让《郑德楙》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
值得一提还有作品《唐煊》。故事发展到最后虽然也是夫妻分别的悲剧结局,但临别留下一幅罗帕,送给丈夫作为留念,并告之四十年后能相见,这无疑给丈夫一线希望。不像王氏妇子与章武一别,有如石沉大海,永无会期,悲剧色彩更显浓烈。
四、人鬼恋小说发展的内外动因
人鬼恋小说在抒发作者的爱情理想、抨击封建礼教、肯定女性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努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类作品的层出不穷,除了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人们猎奇心理等复杂多样的原因外,人鬼恋母题本身的文体特色也是人鬼恋故事发展的重要动力。
首先,作品的超现实性符合文人的猎奇心理和创作需要。
“死亡并非生命的结束,它仅意味着生命形式的改变”,灵魂不灭的信仰“是处于所有进化阶段的人们中间普遍存在的一种信仰,可以当成一个毫无疑问的真理,很难说有哪一个野蛮人的部落完全没有这种信仰”。[2]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死的灵魂总是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奇幻、怪异、拥有神秘力量的“鬼”作为一种非现实的存在,却一直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纠缠不清,令人着迷而又畏惧。爱情和死亡作为人类文学永恒的主题本身已为人津津乐道,人鬼婚恋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绝对能给人们带来更加强烈的感官冲击。
另一方面,超现实性为作家更有效的表达真情实感涂上了一层特殊的保护色。在文风森严的封建时代,作者得以于严格的正统两性道德之外,假托无所不能的鬼魂将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爱情理想尽情抒发出来,为现实中受到重重阻碍和压迫的自由爱情观另辟蹊径。基于以上原因,鬼文学成为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惯用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
其次,社会风尚对人鬼恋故事创作起到了绝对的推动作用,并在其小说创作上打下时代的烙印。
唐朝结束了自三国以后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一统中国之后,社会安定,农、工商业都得到长足发展,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大城市为了满足各阶层娱乐生活的需求,民间的“说话”艺术应运而生。另外,随着佛教的兴盛,佛教徒也利用这种通俗的文艺形式演唱佛经故事以招徕听众、宣扬佛法,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大量变文,促进了“说话”艺术的发展。从民间到上层,“说话”受到了广泛的喜爱。
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所带来的局面就是,各阶级、阶层还有整个国家、民族都处在欣欣向荣的社会氛围中。“于是,远大的政治抱负,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潜心于诗艺的探求,向往着隐居求仙,以及丰富的生活情趣,放浪的酒色生涯,就构成了唐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阶层的社会风尚。”[3]在这种追逐风流的时风之下,人们对色欲的追求已无需在任何掩饰之下,许多作品因而都表现出了浓烈的青楼色彩,《王玄之》中“王试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 ”;《李章武传》中“数日,出行,于市北街见一妇人,甚美。因绐信云:“须州外与亲故知闻。”遂赁舍于美人之家。……乃悦而私焉。居月余日,所计用直三万余,子妇所供费倍之。既而两心克谐,情好弥切。”等等。唐代崇尚奢靡、放荡轻浮之风刺激了人们对性的幻想和心理诉求,无疑成为人鬼恋故事创作高峰的外部推动力。
总而言之,唐传奇中人鬼之恋小说对前朝志怪小说的刻板模式进行了质的突破,其中的人物形象也有了各自不同且鲜明的个性特色。对生死之恋的充分展开,对细节部分的精妙处理和细腻刻画的艺术手法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承前启后,堪称“绝代之奇”。
:
[1]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李志慧.中国古代文人风尚——唐时文苑遗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4]钟林斌.论唐传奇中的人鬼之恋小说[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2).
[5]伍微微.人鬼情未了——论唐传奇人鬼恋故事新变[J].名作欣赏,2011(11).
[6]伍微微.论唐传奇人神恋故事的人神平等性[J].湖北社会科学,2013(4).
[7]范治梅.悲欢人鬼恋 阴阳两世情——《聊斋》人鬼恋故事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1.
[8]俞佳琪.人鬼·艳遇·成仙——由郑德楙的去向谈唐传奇所反映的文人心态及人鬼婚恋故事的历史文化渊源[J].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