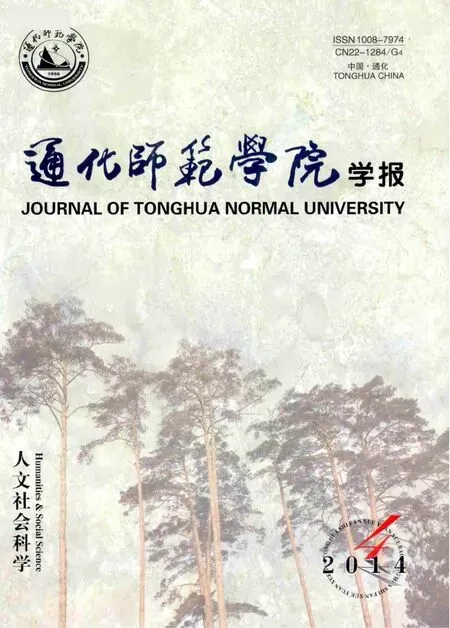中国七夕节与西方圣瓦伦丁节、阿多尼斯节文化习俗比较
汪保忠
(1.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2.平顶山学院,平顶山 467000)
中国七夕节与西方圣瓦伦丁节、阿多尼斯节文化习俗比较
汪保忠1,2
(1.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2.平顶山学院,平顶山 467000)
七夕因为牛郎织女传说的广泛流传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寄托着痴情男女的美好愿望。男女鹊桥相会,佳期不再,欢愉苦短,往往被一些民俗学者误会成中国的情人节,但其实并非西方情人节可比,七夕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因素。二者有不同的文化渊源,经过不同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过滤,考诸希腊神话,其阿多尼斯节却与七夕庶几近之。通过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比较与探寻,阐释了七夕与阿多尼斯节在文化习俗上的诸多相似之处以及与圣瓦伦丁节的显著差异。
七夕节;圣瓦伦丁节;阿多尼斯节;妇女节;情人节
牛郎织女传说是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与《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起在民间流传千年而广为人知。牛郎织女凄美的爱情故事传说,引起世世代代人们的同情,学者历来对此研究热情不减,大多认为牛郎织女传说是“孕育时间最久,产生时代最早,最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中华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征。”[1]也正因为流传久远,影响地域广泛,2008年1月被收入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传说中,牛郎织女被天河阻隔,每年七月七日鹊桥相会,这留给人世间无限遐想,因此才有七夕这个传统节日。风月无边,历代风骚之士多有吟咏,自《诗经》以来,以七夕为题的诗词歌赋不胜枚举。据考证,《全唐诗》有54位诗人82首诗歌,《全宋词》有62位诗人108首词作,均以七夕为歌吟对象。[2]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七夕与端午、中秋、春节、元宵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成为中华民俗的历史记忆。但是近年有民俗学者把七夕盲目比附2月14日西方情人节,在笔者看来是捕风捉影的,缺乏学理上的依据。
一、中国七夕渊源考
牛郎织女传说最早是源于星相的解释,即关于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这两个星座的来源作神话学解释。这个问题学界没有什么争议,论述基本一致。一般认为,牛郎织女传说起源于上古之世,大约在殷周之际就已经初步具有大概的故事轮廓。初民蒙昧,天真烂漫,多所幻想,学者多倾向于将此一时代,即《诗经》时代的牛郎织女划归为星宿神话。根据研究,最早记载牛郎织女传说的,是西周时期。《诗经·小雅·大东》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但是,《大东》是严肃整饬之诗,还不允许有闲情逸致来穿插浪漫的男女情爱,至少是隐约、含蓄、温情脉脉的优雅,过于浓烈、热情奔放不符合《诗经》编订者孔子的审美标准。后历经秦皇汉武,以至三国、魏晋南北朝,牛郎、织女这两个星座已经逐渐人格化为夫妇,而关于牛郎织女这两个星座的神话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传说。虽然民间文学研究者把神话与传说区分得很清楚,但实际上牛郎织女是神话还是传说严格来说,区分意义并不大。南北朝时代任昉的《述异记》里说:“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织紝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讲述的就是这个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
农历七月七日,最早成为双星节、双七节,自汉代起就成为七夕节、乞巧节。到了唐宋之际,又称为女儿节、少女节。至此,牛郎织女传说及七夕风俗,都发展得成熟且基本定型了。有学者认为,七夕就性质而言,应该是中国的女儿节。[3]68对此观点,笔者甚表赞同,七夕应该是女儿节而非情人节,随着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日趋完善,七夕节已成为普遍的节日。
七夕在千百年的流传中,女子乞巧是最主要的民俗活动。虽然作为经典爱情故事的李 (隆基)、杨(玉环)之爱,有一定说服力,“七夕乞巧,长生盟誓”在民间影响深远,涉及爱情主题,但是杨妃的目的仍然是“今乃七夕之期,陈设瓜果,特向天孙乞巧”。明代传奇《长生殿》里七夕之夜香案供奉的是“金盘种豆”等物品,杨妃的目的仍在于祈求子嗣。生育子嗣、延续生命是女性的使命,这与爱情是迥然有别的。因此,不能单纯把七夕比拟为西方的圣瓦伦丁节[4]166。
我们看看七夕的民俗流变。
晋葛洪 《西京杂记》卷一记载了汉代七夕风俗:“汉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5]386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言之凿凿,“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人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等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6]44唐代《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7]98两宋之际,周密《武林旧事》、吕希哲《岁时杂记》也多有记载。清代七夕风俗在日本文献《清俗纪闻》也历历在目:“七月七日称为巧日,在露台放置桌子,以点心鲜果七种、针七根、线七条向牵牛织女二星上供。幼女等于夜半拜星,并用线穿入上供之针,称为穿针乞巧”。[8]42民国文献《中华全国风俗志》也大致情节相似,“七夕,人家盛瓜果酒肴与庭中或楼台之上,谈牛女渡河事。妇女对月穿针,为之乞巧。或以小合盛蜘蛛,次早观其结网疏密,以为得巧者多寡。 ”[9]508
这些文献说明,自古至今,七夕之夜,人间女子希望天上的织女吃了人间女子的瓜果,自己能够像她一样智慧和灵巧,故称为“乞巧”。[10]97正如陈勤建先生所言:“文化生命基因是与有型物质的生物生命基因相异的独特生命元素:它虽然是无形的,却溶化在人的生命里,并不经意地流露在人们的言行中。”[11]66因此,我们不能简单把七夕因为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就等同于西方圣瓦伦丁节。探赜索隐,穷神知化,其实七夕内涵极其博大,远非瓦伦丁节那么简单。
二、西方圣瓦伦丁节及其风俗
我们知道,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圣经》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即所谓 “二希传统”。但是,基督教在非犹太教地区传教开始是受到极端排斥和抵制的。罗马历代君王多次对基督徒进行了极其血腥的清洗与迫害。只是到了公元313年,受到基督教徒支持才登上君主宝座的君士坦丁,在米兰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利西尼乌斯共同颁发了一个敕令,即著名的《米兰敕令》,才使得基督教在经受了250年的迫害之后,终于在罗马帝国获得了合法地位。而在这之前,做一名基督教徒是很危险的,而瓦伦丁就是早期的基督教徒之一。
公元270年,基督教还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因此,做一名基督教传教士并无中世纪的神圣地位与无限荣光。瓦伦丁在传教过程中,带头反对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而被罗马统治者关进监狱。虽然遭受牢狱之灾和肉体鞭挞之苦,在监狱中,瓦伦丁却治好了典狱长女儿双目失聪的眼疾,也得到这位女子的悉心关照与爱慕。但愈是这样,愈加使残暴的统治者惊恐不已,本来就惊恐于基督教传播扰乱民众的精神信仰,因此惨无人道地将瓦伦丁枭首示众。临刑前夕,即将付出生命代价的瓦伦丁给典狱长女儿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书简,诉诸生离死别之情。受刑当天,典狱长女儿无力扭转情人的悲惨结局,便在瓦伦丁墓前种上红色鲜花,以寄托自己无尽的哀思和依依难舍的深情。这一天为2月14日,从此,西方就把2月14日约定俗成地称之为情人节,即圣瓦伦丁节Valentine’s.Day。
从此,情人节开始在西方广为流传。但在不同时代,圣瓦伦丁节的习俗有所不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情人节习俗颇为独特:情人节这一天,青年男女将一株含苞待放的花枝移植于新鲜的花盆,花名的首字母必须与这对情人姓名的首字母吻合。几天后,如果并蒂花开,争奇斗艳,便是“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如果相背吐蕊,那就是“一朝天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了。今天的情人节,情人之间送玫瑰花、巧克力等礼物,互相表达爱慕之情已经使其成为大众化的节日,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普通民众也多参与到这个西方节日中来了。但是应该看到,西方节日富有宗教色彩,节日的文化内涵比较单一,普通大众只是借以点缀生活的平庸,增加情趣,再加上商业文化的炒作,遮蔽了原来节日文化的神圣光芒。
三、西方阿多尼斯节及近似七夕的理由分析
希腊神话中,阿多尼斯节是一个女性的节日,是西方女性为了纪念如花似玉的美男子,植物神阿多尼斯Adonis而举办的。阿多尼斯是希腊神话中传说的美少年,于树身爆裂中诞生。因他长得精致俊俏,风姿绰约,宛如天使,一天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驾着天鹅车来到阿多尼斯身边向他倾诉相思爱慕之情。
阿多尼斯酷爱打猎,每天都和阿佛洛狄忒在苍翠欲滴、如诗如画的山林里狩猎,在泉水淙淙的溪边休息,他们漫游四方,过着神仙眷侣的逍遥生活。一天,女神预感到要大祸临头,她极力劝说阿多尼斯不要去打猎,但他执意要去,结果被野猪咬伤并致死。“也许是被嫉妒的阿瑞斯杀死,阿瑞斯变作野猪模样伺机杀死了他的情敌。”[12]475爱神本与战神阿瑞斯情投意合,现在移情别恋,当然可能招致战神的报复而引来杀身之祸。失去阿多尼斯的爱神异常悲痛,她怕尸体在灼热的阳光下暴晒,损坏阿多尼斯的形象,就将尸体化成一朵鲜红的海葵。强烈的伤心之痛使爱神整天对着海葵流泪,此举感动了冥王哈得斯,允许已入冥土的阿多尼斯在每年中有6个月回到大地与爱神欢会。后来阿多尼斯成了植物和美之神,每年死而复生,永远年轻,青春永驻,容颜不老。[13]50
在古希腊,每年春季举行阿多尼斯节。在游人如织、举国狂欢的节日里,男女青年格外兴奋,春情荡漾,野外欢聚,纵酒作歌。人们在节日的第一天无比伤心地哀悼他的逝去,第二天便欢呼庆祝他的复活重生,抬起阿多尼斯和阿佛洛狄忒的神像游走四方,迷狂,放浪形骸。“人们用清水洗净这位已故神祗的雕像,涂上香膏,裹以红袍,然后对着雕像诵唱挽歌,雕像前香烟缭绕,似乎要刺激他的休眠的知觉从死亡的长眠中苏醒过来。”[12]474在叙利亚,“女孩子们年复一年地悲悼他的死亡,这时属于他的花朵,红色的秋牡丹 (传说秋牡丹的颜色由阿多尼斯的鲜血染红)在黎巴嫩的杉树中开着花,红红的河水流入大海,每当海风拂岸的时候,河水沿着青蓝的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像一根蜿蜒的深红条带。 ”[14]318
在纪念阿多尼斯时,“男女青年到树林里去,砍一棵小因果树或一根因果树枝。他们胜利地把它背回家来,又跳舞、又唱歌、又打鼓,把它种在村里广场的当中,并奉献祭品;第二天早上,男女青年手挽着手,围着因果树站成一个大圆圈,跳舞,树上装点着一些彩色的布条和谷草编的假手镯假手链。”[12]496我们比较一下中国七夕,他们在很多方面有相似的风俗。周密《武林旧事》记载:“七夕节物,多尚果食。……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饾饤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小儿女多衣荷叶……”。至于阿多尼斯节时希腊人在屋顶凉台上布置的阿多尼斯花园,自然是乞求植物神阿多尼斯保佑植物生长。弗雷泽在《金枝》中这样描述,“把种子种在潮湿的沙地上,叶子发芽时露出一种淡黄色或樱草色。到了节日那天,女孩拔出大麦苗,放在篮子里,带到广场上去,毕恭毕敬地匍匐在地把它放在卡马树面前。”[12]497中国七夕也有“种生”的习俗,“种生”又称之“生花盆”。宋代人吕希哲《岁时杂记》记载可为其佐证:“京师每前七夕十日,以水渍绿豆或豌豆,日一二回易水,牙渐长至五、六寸许,其苗能自立,则置小盆中。至乞巧,可长尺许,谓之生花盆儿。”东西方女子节情节如此相似,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巧合,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精神的“遥契”。
四、七夕不同于圣瓦伦丁节的原因分析
笔者考诸文献,结合民俗,觉得有以下理由:(一)风俗及内涵不同。圣瓦伦丁节为送人玫瑰、谈情说爱之时,并非夫妻久别重逢。七夕在中国民间是乞巧,女子希望心灵手巧。客观的讲,牛郎织女传说只是凄美感人,并不是人们世俗观念里期盼的完美爱情。银河阻隔,男女遥遥相见不得亲,引起人们同情是正常的,如果是世俗爱情的长相厮守,可能得不到如许响应。七夕最早与爱情并无关系,七月入秋,繁华落尽,万物萧条,“无端落木萧萧下”,是伤感哀愁的季节。七夕与西方圣瓦伦丁节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有很大区别。七夕节本来是未婚女子乞巧,男性不参与其中。圣瓦伦丁节未婚、已婚均可参与其中,男性、女性也不加限制。(二)节庆活动不同,人文关怀差异巨大。圣瓦伦丁节使万物复苏,青年男女尽情满足自己的精神与情感需要,彰显西方个人主义传统。有宋代“上元日”时欧阳修“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旖旎情致。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繁华的开封,“青楼画阁”、“绣户珠帘”,处处是“柳陌花衢”、“茶坊酒肆”。或者如暮春三月,也就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过的节日“三月三”,那是风情摇曳的日子。“江南草长,群莺乱飞”,青年男女相约郊游以致两情相悦,似乎也情有可原。但七夕时值瓜果成熟之时,源于神话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缺少娱乐色彩。(三)文化传统不同。七夕是中国传统文化农耕文明的反映,男耕女织,躬守田园。七夕风俗是一种活态民间文化,古代中国本来不具备情人节的伦理基础,男女授受不亲是儒家先圣的教化大义。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人文主义的传统,提倡人性。即使是神,也是“神人同形同性”,也像人一样具有爱恨情仇。孔子评论《诗经》“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汉代《毛诗序》对《诗经》里面《关雎》之类的爱情,也作了符合儒家经典的阐释,后代一直奉为圭臬。东西方民族文化的根基不同,不必强行攀比。七夕不是苗、瑶、布依等热情奔放的少数民族节日,是汉民族的文化传统节日,尽管寄寓美好,但也不是情人相会。(四)伦理与世俗规范不同。情人节西方人送玫瑰花,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情人节,但情人之间有送别互赠礼物,据《诗经·郑风·溱洧》记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以芍药”。至于“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江淹《别赋》优美如斯:“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这都是可靠的文献,但出于中国正统文化的压制,在中国古代谈情说爱是非常奢侈的事情,诗庄词媚,士大夫的个人情调只是在低俗的词曲里唱唱而已,比如欧阳修、柳永等诗词名家均可作如是观。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因牛郎织女而成的七夕节,不可盲目比附为中国的圣瓦伦丁节(情人节),实际上是中国的阿多尼斯节(女子节)。陶立璠先生在为赵逵夫 《主流与分流——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传播与分化研究》所作的序中也说过大致类似的话。七夕节是传统民俗的延续,但将牛女传说视为纯爱情故事,将七夕节定位为中国的情人节,这是极其荒谬的,是对文化遗产的蔑视,也是对牛女传说和七夕文化产生与传播历史的无知。
[1]赵逵夫.先周历史与牵牛传说[J].人文杂志,2009(1).
[2]张玉璞,曹瑞娟.“七夕”题材诗歌源流考[J].聊城大学学报,2005(1).
[3]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清]洪昇.[日]竹村则行,康保成笺注.长生殿笺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5]武文.中国民俗学古典文献辑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6][梁]宗懔.荆楚岁时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
[7][五代]王裕仁等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日]中川忠英编,方克等译.清俗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2006.
[9]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
[10]胡怀琛.民国文存·中国寓言与神话[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11]陈勤建.文艺民俗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
[12][英]弗雷泽,徐育新等译.金枝[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13][韩]金淑姬.世界50大神话[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14][英]弗雷泽,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金枝[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章永林)
G04
A
1008—7974(2014)04—0051—04
2014-05-19
汪保忠(1969-)河南信阳人,在读博士,平顶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2014-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编号:Z201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