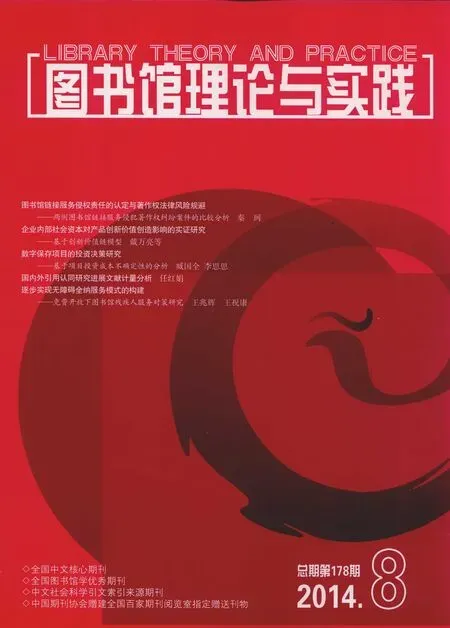图书馆链接服务侵权责任的认定与著作权法律风险规避——两例图书馆链接服务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比较分析
●秦 珂(新乡学院 图书馆,河南 新乡 453003)
“链接”是互联网的灵魂,链接服务是网络环境中图书馆最重要的服务方式之一。然而,链接服务给图书馆“连”来了“官司”,“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诉重庆涪陵区图书馆侵犯著作权纠纷案”[1](案例一)和“北京优朋普乐科技有限公司诉广东肇庆市图书馆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2](案例二)就是由于图书馆提供链接服务引发的两起著名的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两起典型案件中的图书馆都向读者提供了链接服务,但是,却承担了大相径庭的法律后果,其中原委有必要从图书馆利用著作权的具体行为性质,法理和立法以及法官对法律法规的认知与掌握能力、司法经验和审判倾向等角度进行解读,而图书馆管理著作权的得失同样值得总结和反思。
1 图书馆链接服务典型侵权纠纷案件及其影响
1.1 案例一的审理和判决概述
2007年4月17日,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简称“三面向公司”)认为涪陵图书馆未经其许可链接传播了江西新余电信网站中的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也未支付报酬,在向涪陵图书馆发出要求支付作品许可使用费通知书的同时,在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图书馆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涪陵图书馆在接到通知后随即断开了链接,并向重庆涪陵区公证处申请对链接行为进行公证。一审法院认为,涪陵图书馆是公益性文化机构,链接的目的是发挥知识导航的作用,而且对涉案作品的使用并非在自己的网站中直接占有、存储文章内容,提供的仅仅是狭义的链接服务,不是内容的直接登载者。法院还认为,涪陵图书馆不知道被链接网站内容存在侵权问题,无隐瞒被链接网站的网址和网络域名,主观上无使读者产生误认的故意。涪陵图书馆无赢利行为,在接到通知后断开了链接。法院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图书馆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二审法院认为,涪陵图书馆提供的是“深度链接”,未得到原告许可直接通过网络链接涉案作品,向网络用户提供内容服务,未支付报酬,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改判图书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2 案例二的审理和判决概述
2009年底,北京优朋普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优朋公司”)、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网乐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向广东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联合诉讼,状告“肇庆数字影院”网站的主办单位肇庆市文广新局和承办单位肇庆市图书馆提供链接服务侵犯了其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010年1月10日,肇庆市图书馆在收到法院开庭传票后向肇庆市震东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并在公证下断开了链接。一审法院对案件审理后根据《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认定图书馆等的行为不构成侵权,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不服,单独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0年12月1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中的优朋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诉,但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
1.3 案件的社会影响与学术争论
“案例一”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提供链接服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第一个案件,具有里程碑价值。“案例二”耗时两年,历经中、高和最高三级法院审理才“一锤定音”。图书馆虽然胜诉,但是作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成果的“肇庆数字影院”被无限期关闭,其他许多图书馆在得知肇庆市图书馆被起诉后也纷纷停止了相关的服务。所以,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诉讼”。[3]然而学术争论却随着法锤的落下而发酵,如有学者认为,“案例一”中二审法院对涪陵图书馆直接侵权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判定,不合理地加重了图书馆的法律责任。[4]相反,有学者却对“案例一”的终审判决结果表示赞同。[5]又比如,有学者认为在“案例二”中,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肇庆市图书馆链接行为已经不属于中立的信息定位服务。[6]著作权问题是技术变革中图书馆终究绕不过去的坎,既然权利纠纷甚至侵权诉讼不可能完全避免,那么“因噎废食”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措施。图书馆努力掌握法律规范,科学管理与合法利用著作权,学会保护自己才是根本的办法。
2 链接服务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结果比较
2.1 链接服务的法律性质与侵权类型
(1)链接服务的法律性质。国外法律中的“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理论对我国著作权侵权责任的立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也被吸纳。传统理论认为,网络环境中“直接侵权”的法律性质是未经许可行使他人专有权利而又无法定免责理由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在“案例一”中,一审法院认定图书馆提供的仅是狭义的链接服务,显然不认为图书馆的行为构成信息网络传播。二审法院认为,图书馆直接通过网络链接使用涉案作品,向网络用户提供内容服务,其实质就是对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肯定。在“案例二”中,二审法院指出,原告认为图书馆向用户提供了内容服务的诉求缺乏法律依据,也是对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否定。虽然不排除图书馆把链接来的信息向用户“再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在提供单纯的链接服务中,图书馆对用户获取信息只起被动引导作用,未直接把作品放在信息网络中传播。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有不同的理解,《最高法规定》已经明确把“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区分成“作品提供行为”与“其他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单纯的链接服务属于后者调整的范畴。
(2)链接服务的侵权类型。对“普通链接”法律性质和侵权责任的认定一般没有异议,但是对“深层链接”是否可以构成直接侵权的问题却存在着认识分歧和不同的案例,主要是“用户感知标准”与“服务器标准”之争。“用户感知标准”指只要用户在点击链接时能感觉到是链接服务提供者在提供作品,就构成直接侵权。在“案例一”中,一审法院认定图书馆的行为构成侵权,这是间接侵权,因为适用的免责规定是《条例》第二十三条。法院之所以没有用“间接侵权”的表述,概因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没有“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的划分。[4]二审法院认定图书馆的行为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获得报酬权,则是采用“用户感知标准”判断图书馆构成直接侵权的典型例子,因为适用的法律是《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服务器标准”指只有将作品上传到向公众开放的服务器中的行为,才构成直接侵权。[7]在“案例二”中,原告认为涉案作品的内容存储在图书馆的网站上,意思就是强调图书馆的行为符合“服务器标准”,构成直接侵权。然而,法院认为图书馆没有对涉案作品进行存储或开展上传下载服务,不构成直接侵权,即认为图书馆的行为不符合“服务器标准”。目前,提供链接服务(包括提供深度链接)不可能构成“直接侵权”的结论已在国际上达成广泛共识。[8]我国《条例》第二十三条、《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用语也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9]
2.2 图书馆在链接服务中过错的判定
(1)“红旗标准”的适用。链接服务能够为直接侵权提供实质性帮助,所以可能构成间接侵权。“主观过错”是间接侵权的最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包括“明知”过错和“应知”过错两种情况。链接服务提供者是否具有过错通常用“红旗标准”进行判断,即当被链接内容足以反映出侵权特征,凡是“理性人”都能够对像“红旗一样飘扬”的侵权事实作出判断时,链接服务提供者不能予以链接,或者采取“驼鸟政策”,视而不见,继续链接。《条例》第二十三条、《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对“红旗标准”都有体现。《最高法规定》第八条规定,应当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认定其承担的侵权责任,包括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红旗标准”不赋予链接服务提供者承担对被链接内容合法性的审查义务。在“案例一”中,一审法院认定图书馆“不知道”被链接内容侵权,二审法院却认为图书馆提供“深度链接”而未尽到审查义务构成“应知”侵权。这与《条例》没有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做出明确规定相关。在“案例二”中,针对原告认为图书馆未尽到足够的审查义务,构成“明知”或者“应知”侵权的指控,二审法院指出网络具有互联性、开放性,信息内容庞杂,数量巨大,要求图书馆对链接信息是否存在权利瑕疵先行作出判断和筛选是不客观的,不存在图书馆“明知”被链接内容侵权还提供链接的事实。《最高法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审查的,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
(2)“避风港标准”的适用。“避风港标准”包括“通知”和“删除”两个部分,又称“通知+删除”规则,是指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著作权人发出的侵权通知后应立即采取措施断开与侵权内容的链接,从而进入“避风港”得到免责。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条例》对“避风港标准”的规定较为完善(其中第二十三条对链接问题有专门规定),《最高法规定》第十三条已经把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按照要求执行了“通知+删除”规则作为判断其“明知”过错的标准之一。“案例一”、“案例二”中,图书馆都较好地执行了“通知+删除”规则,但是在“案例一”的二审中,法院对图书馆执行“通知+删除”规则的事实未予认定,不能不说是一种欠缺。就“红旗标准”与“避风港标准”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一种例外,但是没有“红旗”,才是“避风港标准”适用的消极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在适用“避风港标准”之前首先要考虑是否具有“红旗”,如果“红旗”已经高高飘扬,那就没有必要适用所谓的“避风港标准”。[10]在“案例一”中,二审法院之所以对图书馆没有适用“避风港标准”免责,或许就是认为图书馆提供“深度链接”时“应当知道”侵权的事实像“红旗一样已经在飘”而不再适用这项标准。在“案例二”中,原告利用《条例》第二十三条“但书部分”的规定认为图书馆的行为构成“明知”或“应知”侵权,但是由于未能提供充分的事实根据,诉求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
3 图书馆防范和规避著作权法律风险措施的比较
3.1 措施的相同点
(1)没有直接获取经济利益。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有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情况,那么将使相关的责任认定原则、机制发生改变。[11]在“案例一”、“案例二”中,图书馆都没有从链接服务中获得任何经济利益,这是正确的做法,也得到了法院的肯定。然而,在“案例一”中,二审法院在认定“图书馆是公益性机构,未从链接服务中牟利”的情况下,仍然判决图书馆承担民事责任,值得反思。究其原因在于我国《著作权法》未设置公益性图书馆“善意”侵权免于赔偿责任的条款,在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上,图书馆与一般主体毫无二致。[12]这说明,图书馆由于其公益主体性质而在著作权法体系中享有的其他作品传播者不具备的“特权”并不能成为其侵犯著作权的免责牌。至于什么是“直接获取经济利益”,《条例》、《侵权责任法》等都没有明确规定,从对《最高法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收益和侵权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鉴于此,图书馆出于开展和维持单纯的链接服务用于弥补运行成本的收费是被允许的,只要不把被链接的“特定的”侵权内容当成获得经济利益的工具。《最高法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从网络用户提供的作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应被认定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因此,图书馆在网络信息服务中收费要慎之又慎。
(2)对链接不施加人工干预。链接技术本身具有中立性,如果链接服务提供者主动对被链接信息进行分类、编辑、整合,设置各种栏目、榜单等,则可能认定其接触了侵权内容,构成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提供链接。在“案例一”中,图书馆提供“文学作品目录链接”并非施加了人工干预措施,链接过程由软件自动完成。在“案例二”中,原告认为图书馆网站设置了专门的电影频道、电视剧频道、动漫频道、综艺频道及其排行榜,存在主观过错。然而二审法院却认为图书馆网站上的分类与索引都是软件自带的分类,图书馆没有主动设置与修改分类,没有对视频进行编辑,主观上没有侵权的故意。《最高法规定》第十条已经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热播影视作品等以设置榜单、目录、索引、描述性段落、内容简介的,应认定其“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另外,即使链接是自动完成的,但是如果链接服务提供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被链接内容侵权而继续链接,就可能构成侵权。在“案例二”中,原告认为图书馆网站链接的内容“不是处于热播的影片就是经典影片”(即认为侵权的“红旗”明显在飘扬,而图书馆却视而不见),但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没有涉及此问题。
(3)履行删除侵权内容义务。在“案例一”、“案例二”中,图书馆都在接到著作权人的通知或者法院传票后断开了链接,较好地履行了删除义务。但从图书馆管理著作权的实践看,还有一些法律界限需要澄清。其一,《最高法规定》已将《条例》对通知的“书面”形式扩大到“电子邮件”等形式。其二,对删除义务的履行应当是积极的、主动的,对于像“红旗”一样飘扬的侵权行为,图书馆要主动采取断链措施,不能坐等著作权人的通知而后删除。其三,“通知”不是“明知”侵权的唯一途径。在“案例二”中,二审法院确立了“无通知即无明知,无明知即无责任”的原则,实际上,“通知”只是认定明知状态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13]图书馆不要把无“通知”当成不主动履行删除义务的借口。其四,对于不符合《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法定形式的“不合格”通知,只要足以准确定位侵权信息就具有法律效力,图书馆就要积极履行删除义务。其五,对于“及时”删除的合理期限,《条例》没有明确,《最高法规定》第十四条只提出了原则性标准。北京市版权局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指导意见(试行)》第九条规定为“24小时”,如果在此期间内不能删除侵权内容,应书面告知著作权人。
3.2 措施的不同点
(1)明确地告知信息的来源。“信息来源标识”的目的是避免网络用户产生疑惑,以为作品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也利于著作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联系,明确追责对象,降低维权成本。“信息来源标识”是《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设置的免责条件之一,然而第二十三条对链接服务的免责规定中并没有这种要求,这只能说法院不会因为链接服务提供者没有标识信息来源,就认定其构成侵权甚至判定其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否标识了信息来源在案件审理中却会成为判断其过错的因素之一。如“案例一”中,虽然图书馆其网页上没有清晰标明信息来源,但是一审法院仍然认为,图书馆未隐瞒被链接网站的网址和域名,主观上无使读者产生误认的故意,读者不会误认为是在图书馆网站上阅读该作品。对此,二审法院却有相反的认识,指出图书馆提供“深度链接”服务,使读者不一定知道图书馆的网站同其他网站建立了链接,使读者误认为作品由图书馆提供。在“案例二”中,图书馆不仅在网站上标明了信息来源于第三方网站,而且指出了设置链接的目的,提供了联系方式,承诺了删除侵权内容的期限。这种做法对一审、二审法院作出有利于图书馆的事实判断起到了作用。
(2)收集和保全相关的证据。当著作权人指控图书馆侵犯其权益时,图书馆必须根据其诉因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抗辩主张的事实成立,如果举证不能,则只能认定其行为构成侵权。在“案例一”中,公证保全的证据尽管证明了图书馆提供的是链接服务,但是却没有为图书馆提出的“不提供内容服务”的主张提供有力支持。在“案例二”中,图书馆的证据保全工作相对周密,针对原告的诉求前后两次申请公证保全证据,尤其是这些证据为图书馆关于“未从事存储和上传下载服务,只是链接服务”的抗辩主张提供了充分支持,成为赢得胜诉的关键证据。《最高法规定》第六条已明确规定,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作品,但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网络服务,且无过错的,不应认定为侵权。网络证据具有易变性、易逝性的特征,图书馆在通过公证、诉讼等途径申请证据保全的同时,要自行开展证据保全工作,以克服公证保全、诉讼保全存在时滞的弊端,也为公证保全、诉讼保全的证据提供其他相关的佐证。
(3)采取低风险的链接模式。一般认为,提供“深度链接”服务的法律风险高于“普通链接”。“深度链接”将用户直接引导到具体内容所在的页面,会使人感觉到设链者的目的并非是为用户自己获得作品提供向导,而是直接提供内容服务,更容易察觉侵权事实的存在,更有机会和能力判断侵权行为,因此提供“深度链接”者往往被赋予相对高的合理注意义务。如针对“案例一”二审的判决,有学者认为其积极意义在于对提供普通链接服务和深度链接服务者的注意义务进行了明确区分。[5]在“案例二”中,点击图书馆网站中的作品链接,可以清晰地表明视频来源于优酷、土豆、六房间、qvod等第三方网站,而非直接链接到被链网站的分页面,这是一种低风险的普通链接。《最高法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应把网络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以及应当具备的信息管理能力,作为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侵权的因素。图书馆提供数字信息服务(不仅限于链接服务),应对技术的法律风险性开展评估,合理选择实现模式。
[1]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渝高法民终字第 146 号 [EB/OL].[2012-11-21].http://ipr.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sfwsphp?id=23096.
[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粤高法民终字第 347号 [EB/OL].[2013-05-03].http://ipr.court.gov.cn/gd/zzqhljq/201012/t20101230.html.
[3]刘婵.一公共图书馆惹近两年版权纠纷[EB/OL].[2013-05-03].http://culture.people.com.cn/h/2011/1216/c226948.html.
[4]韦景竹.图书馆工作中的版权侵权责任分析与启示——从涪陵图书馆链接侵权案谈起[J].图书情报工作,2010(1):54-57,138.
[5]黑小兵.网络链接侵权法律问题研究[J].科技与法律,2011(4):68-73.
[6]梁志文.我国法上的避风港规则:利益失衡与立法完善[J].电子知识产权,2011(9):33-40.
[7]祝建军.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判断[J].中国版权,2010(1):48-50,53.
[8]王迁.提供链接与帮助侵权[J].中国发明与专利,2007(7):14-15.
[9]曹阳.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分析——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主要对象[J].知识产权,2012(11):24-27.
[10]许明春.“在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全文 [EB/OL].[2012-08-07].http://blog.sina.com.cn/s/blog491fe2410100gmj7.html.
[11]周应江,谢冠斌.论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的版权侵权责任[J].科技与法律,2009(3):72-77.
[12]王清,陈凌云.中美版权法之公益图书馆豁免制度比较[J].图书馆杂志,2008(9):2-5.
[13]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