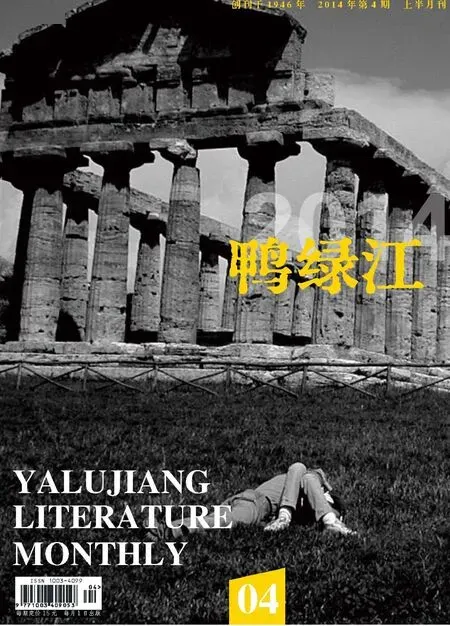蚁穴
尹守国
蚁穴
YIXUE
尹守国

老伍坐在一块石头上,眼睛盯着对面的山坡,像是入了迷似的。他的脚下,横七竖八地扔着十几个烟头,其中的一个还冒着缕缕白烟。
从早上五点多,老伍就开始坐在这儿。烟叼在嘴上,任其在风中自行燃烧。有时候换了风向,丝丝青烟溜进眼里,呛得他不得不使劲地眨巴几下,把泪水挤回去。直到感觉烟头有些烤到嘴唇了,才呸的一声吐掉,顺便挪动一下早就被石头硌得疼痛的屁股,改换一下坐姿。
对面山上的松树,显然是在同一时间植上去的,都是一样高的个头,齐刷刷的。山坡呈梯田状,树便显得很有层次,前边的树冠正好遮挡住后边的树干及树下的一切。从老伍这个角度看,便是一片翠绿,像从山顶铺下来一块绿地毯。
有烟雾从树林中升腾起来,与山间的霭气融成一团,缥缥缈缈,笼罩在山顶上。老伍知道,这是有人来看他们的亲人了。
对面的山坡是这个县城的公墓。那些被松树遮挡住的地方,埋葬着成千上万个原来行走在这个城市的人们。其中就包括老伍的前妻郝凤霞。他也是来看他的亲人的。
算起来,老伍已经有四年没来过这里了。这些年,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在逢年过节之前,打电话给伍帅,让儿子来这里祭奠一下,给郝凤霞送点纸钱。而每次打电话时,还得背着杜亚娟。他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到他与杜亚娟的情感。或者说,因为郝凤霞的离去,老伍更加珍视与杜亚娟的这份爱情了。

尹守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中青年作家班学员。已在《中国作家》《芙蓉》《清明》《山花》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一百多万字。有中短篇小说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转载并收入年度选本。出版有小说集《动荤》等,曾获第六届辽宁文学奖。
在与杜亚娟恋爱的那段时间里,老伍还能时不时地想起郝凤霞来。他是拿郝凤霞来衡量杜亚娟时想到的。此时的郝凤霞,已经不再是老伍的妻子,而是他评价妻子的一个参照物。
老伍跟郝凤霞是一个村子的,两家子前后院。两家大人处得非常好,两个孩子从打会爬那会儿起,就被大人放在一个炕上玩。郝凤霞比老伍小四个多月,她一直管老伍叫小哥哥。他们一起上学,一起写作业,算是真正的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高中毕业后,又都没考上大学,便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因为太熟悉了,以至于他们没经历恋爱的过程就睡到了一个被窝里。直到郝凤霞怀上伍帅,两家大人才匆匆地给他们办了个婚礼。
在他们共同生活的二十年零四个半月里,老伍对郝凤霞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也是非常满意的。郝凤霞这个人,没有啥突出的优点,但也找不出任何缺点。从嫁给老伍的那天起,她就是老伍的管家兼用人。郝凤霞没有工作,她的全部工作就是满足老伍的一切需求。比如老伍晚上下班,本来家里的饭做好了,但老伍说要吃饺子,郝凤霞就把做好的饭推到一边,去院子里割菜,重做。那时老伍还只是个大队会计,但在郝凤霞眼里,却享受着县长级别的待遇。
郝凤霞倒不是怕男人的那种类型,用她婆婆的话说,是她太惯着老伍了。这种因疼爱而产生的信任,不单单表现在支持老伍的正常工作上,也表现在支持老伍因工作而产生的不正常的活动,包括老伍陪领导打麻将、上歌厅。当好心人把老伍的这些行动告诉给郝凤霞时,她总是满不在乎地说,我知道,是我让的。好心人劝她多长个心眼,多留点心。郝凤霞有些气愤地说,我们俩是孪生的,别说他做啥,就是他想啥,我都能感觉到。
郝凤霞就这样铁了心地跟着老伍一路走下来,目睹丈夫由一个临时工转成国家公务员,由一个办事员爬到工业办主任,再到副乡长、乡长的全过程。就在老伍一路飞黄腾达、春风得意之际,她终于无法担当工业局局长夫人的名分,在切除子宫之后,还是死于宫颈癌上。
杜亚娟是在郝凤霞去世四个月后跟老伍认识的。她原来是这个县食品加工厂门市部的一名售货员。十多年前,这个厂子破产,她也跟着失业了。但这并没影响到杜亚娟的生活,反而让她过得更加自在起来。每天除了接送孩子和收拾利索那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家外,其余的时间都泡在麻将桌上或美容院里。别人是越活越老相,而她却越活越年轻,脸上连一个皱纹都没有。一个下岗工人,能过着如此富足舒坦的日子,这得益于她的丈夫刘贵成。
跟杜亚娟结婚的第三年,刘贵成就升任为钢管厂的财务科长了。那是一个有着上亿元固定资产和几千名职工的大厂,也是这个县家喻户晓的知名企业。在这样的一个单位管钱,随便用手指甲划拉两下,回到家里剜出来,都是硬邦邦的真东西。何况他伙同厂长一起大把大把地往怀里揣呢!在行迹败露后,为了保护厂长或迫于压力,在某天晚上,刘贵成竟然拎着一桶汽油去了单位,烧掉所有账目,然后跳楼自杀了。
当时老伍刚当上局长不到半年。而这个钢管厂,又是他这个局的下属企业。从刘贵成出事的那天起,老伍一直参与处理此事。也是那个时候,他开始认识杜亚娟的。老伍对杜亚娟的好感,不仅来自她那漂亮的外表,更多的是源于她对刘贵成的情义。在刘贵成出事的当天,杜亚娟先后哭得昏死过去五次。这是老伍亲眼目睹的。当时他就想,一个男人,有这么钟情的女人疼爱着,不好好地活着,实在是太可惜了,也太可恨了。在处理善后问题时,老伍对杜亚娟母女也格外关照,能为她们开脱的,都开脱了;该为她们争取的,也都尽心尽力。老伍所以产生这份情感,与郝凤霞的刚刚离去有关。他与杜亚娟有点像毛泽东诗词里说的“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感觉。
处理完刘贵成的事后,虽然一年多没跟杜亚娟接触,但老伍不止一次地想到她。特别是老伍在思念郝凤霞时,杜亚娟总时不时地出现在郝凤霞身后。有一次在酒桌上闲聊,有人又提到刘贵成,老伍便问谁知道杜亚娟现在的情况?办公室主任老王说他跟杜亚娟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们早先就认识,还多少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这之后,老伍就对老王格外亲近。有时话里话外的自然不自然地提到杜亚娟。老王当了二十多年的办公室主任,能琢磨不出领导的意图吗?在老王这根火柴的点燃下,老伍和杜亚娟这两堆存放已久的干柴,忽地一下就腾起爱的火焰。
老伍与杜亚娟确定恋爱关系时,伍帅在省城念大学。伍帅虽然不反对父亲给他找个后妈,但反对父亲给他找的这个后妈是杜亚娟。在第一次见过杜亚娟之后,他一脸顾虑地对老伍说,爸,你对我杜姨了解吗?老伍点点头,说我们都认识两年多了。伍帅又问,你不觉得她太年轻吗?老伍嘿嘿地笑着,走到儿子的身边,拍着儿子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也是个男人,以后你就知道了,女人年轻点,不是坏事。伍帅还想说点什么,但看到父亲没心思听,只好嘎巴几下嘴,换成一句“那就祝你幸福”的话。
那时老伍虽然还没跟杜亚娟正式结婚,但他们已有了夫妻之实。他们幽会的地点是在杜亚娟的家里,老伍已经习惯于那间宽敞的卧室和那张柔软的大床。在这张床上,他更有激情,有一种鸠占鹊巢的感觉。老伍甚至想等结婚时,自己干脆倒插门算了。
可还没等走到结婚这步的某一天早上,老伍还在睡梦中,杜亚娟突然打来电话。老伍听见那边嘤嘤的哭声,急着问怎么了?杜亚娟非但不回答,且哭得越来越激烈了。老伍忙三跌四地穿上衣服,出门打个车就奔过来。老伍敲门时,是杜亚娟的女儿小芮把门打开的。老伍只跟孩子点点头,连拖鞋都没顾得换,就跑进卧室里。
看到杜亚娟正围着被子坐在床上,头发蓬乱,还有些瑟瑟发抖的样子,老伍又问她怎么了?杜亚娟还是哭而不答,眼睛盯着站在门口的小芮。老伍给小芮几十块钱,让她自己下楼吃饭,然后打车上学。
打发走小芮,老伍坐到杜亚娟的面前,把她搂在怀里,连拍带哄好半天,杜亚娟才缓过神来。老伍再次问起时,杜亚娟说她梦到刘贵成回来了,进屋不由分说,双手掐住她的脖子。她不停地挣扎,把床单都蹬撕了。要不是小芮醒得早,跑过来招呼她,真就被掐死了。她还说,这个梦做得特别奇怪,醒了之后,脖子还疼着,呼吸感觉都很困难,像真的一样。
这种事,老伍从来不往心里去。他认为是他们频繁接触,杜亚娟可能也和他经常想起郝凤霞一样,又想起刘贵成来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很正常。但老伍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床单,虽然没有撕破,但皱巴巴的卷成一团,像根绳子,有一半已经搭拉到床下边去了。很显然,杜亚娟不是在撒谎,确实被折磨得够呛。
老伍只见过刘贵成一次,还是在他摔死的现场。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刘贵成的那双眼睛,瞪得和铃铛似的,还往外冒冒着。老伍一想到那个场景,也有些头皮发炸。过了老半天,神色才算稳定下来。他强装镇定地安慰杜亚娟一会儿,终于哄得杜亚娟不再发抖。他帮杜亚娟穿好衣服,又到楼下的小吃部买来早餐,哄着杜亚娟吃下三个包子,杜亚娟的神情才算恢复正常。
第二天中午,老伍再去杜亚娟的家时,见杜亚娟仍然神情忧郁。她说一个人在屋里待着,总觉得身后有动静。老伍哄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把杜亚娟哄上床。杜亚娟扯个枕巾蒙在脸上,双手紧张地抱着老伍,说她不敢睁眼睛,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们。老伍虽然没在意,但终归影响到情绪,草草地打了几个把式,就收场了。他感觉这已经不是在做爱,而是在奸尸。尽管老伍临行前,看到杜亚娟一脸的歉意,但他发恨再也不上这儿来了。
虽然是不到杜亚娟家里去了,但老伍不能不与杜亚娟幽会。自打那根神经被杜亚娟唤醒后,他便把这事看成饭菜,恨不得每天吃三顿。老伍把他和郝凤霞用过的被褥都存放起来,又买套新的铺上,把作战的阵地换到他家。这招还真管用,杜亚娟立即恢复了原来的激情。
来过老伍家几次之后,杜亚娟便以女主人的姿态,对房间进行改造。老伍两口子原来住的那间大卧室,被安了个门,改成两个小卧室,分给伍帅和小芮各一间。杜亚娟和老伍搬到伍帅原来的房间里去了。老伍原来的那张双人床,被改头换面,成了伍帅的单人床。杜亚娟又新买了一张和她家一样的双人床。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征得老伍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产生的费用,也是老伍提供的。
在去杜亚娟家的那段日子里,老伍并没急于结婚。他觉得这样挺好的,又方便又自由。可杜亚娟搬到他家之后,黑天白天住在这儿,不结婚便不行了。他毕竟是局长,让邻居传出去,好说不好听。
把结婚的日子选定在五月一日,老伍更多的是基于对儿子的考虑,他是希望伍帅能回来参加他的婚礼。老伍提前二十天就跟儿子打招呼,伍帅当时也答应了。可在结婚的头一天,儿子打来电话,说没买到车票。老伍虽然心里有些不痛快,也没好表露出来。以前伍帅回家挺勤的,从打老伍结婚后,他很少回来了。即使是回来了,也很少待在家里,总是去他舅舅家,去他姨家,或同学家。
其实伍帅在家时,也很少跟杜亚娟说话。偶尔赶上老伍在跟前,管杜亚娟叫妈时,总是红着个脸,像个大姑娘似的。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管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叫妈,是有点张不开嘴,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从结婚的那天起,小芮便改口管老伍叫爸了,这也就逼着伍帅必须管杜亚娟叫妈。
老伍挺喜欢小芮的,喜欢得能让那些不知底细的人看不出这个孩子不是他的。他们三口人出出入入时,都是站成横排。有时是杜亚娟拉着小芮的一只手,老伍拉着小芮的另一只手。更多的是杜亚娟挎着老伍的一只胳膊,老伍拉着小芮的一只手。只有伍帅回来时,他们才改成竖排。老伍走在最前头,杜亚娟其次,之后是小芮,伍帅跟在小芮的后边。四口人在一起,别人很难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三口人时,也就是伍帅不在跟前,他们绝对是一家人。
正式结婚后,老伍与杜亚娟便和所有的家庭一样,开始过正常的日子。这时,杜亚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杜亚娟,而是老伍的妻子,局长的夫人。或者说是郝凤霞的继承人,她是要履行一个妻子的义务的。
与郝凤霞相比,杜亚娟的缺点很多。她不太会操持家务,饭也做得稀里糊涂,但这对老伍的影响并不大。这时的老伍,每天总有饭局,已经很少回家吃饭了。在家里吃的时候,基本都是早餐。不是买现成的油条豆腐脑,就是小米粥煮鸡蛋。这样的饭食,谁来打理,结果都是相同的。

杜亚娟不会洗衣服,但这并不影响老伍穿着的整洁。城里有干洗店,杜亚娟把衣服送到那里去。老伍在第一次穿上干洗过的衣服之后,就明确地指示过,以后就不要在家里洗了。
杜亚娟还很任性,啥事都得让老伍听她的,老伍也很欣然地接受着。他是这样认为的,人家比你小十多岁,自然是要耍点小孩子脾气。老伍把这理解成情调,这也是他在郝凤霞身上这些年没获得过的。特别是杜亚娟在床上的激情,让老伍的青春又激活一次。杜亚娟有什么要求,总在床上提出来,在老伍即将进入状态之前提出来,这让老伍想不答应都难。
总之,自从有了杜亚娟之后,老伍对郝凤霞开始不满意了。老伍觉得跟郝凤霞过的那段日子,生活是暗淡无光的。渐渐地,郝凤霞淡出了老伍的生活。
住进老伍家里不久,杜亚娟便把她的那套房子租给她妹妹住了,每个月象征性地收三百块钱的房费。杜亚娟说把房租给小芮当零花钱,老伍也欣然同意。他觉得房子是小芮的爸爸留下来的,收的钱当然应该给人家的女儿。
在家里待了两个多月,杜亚娟竟然不愿意在家里待着了。她跟老伍说,要自力更生来养活自己。老伍虽然嘴上说不用你操心,我能养活你们娘俩,但心里并不反对。老伍的那份工资,每个月有一半得寄给伍帅。这段时间,家里的支出总是捉襟见肘,老伍不得不向单位的钱伸手。虽然从单位揩取的数额不大,但他意识到这是个危险的开始。特别是搂着杜亚娟的时候,总想到刘贵成的结局。当杜亚娟第二次提起这件事时,老伍欣然应允,说你想干点啥?我帮你张罗。
杜亚娟当时也是才有想法,还没有具体的目标。但看到老伍没反对,接下来便紧锣密鼓地考察项目。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她依偎在老伍的怀里说,今天她去干洗店取衣服,发现开干洗店这个项目不错。人们的服装越来越高档,在家里没法洗;而人们的工作越来越忙,也没时间洗了。老伍考虑一会儿,也觉得这个项目可行,投资又不是十分大,也有市场发展空间,便同意了。
从打单独支门子过日子那天起,老伍就没问过家里的存款情况。反正他穿的用的,郝凤霞都给准备到那儿。就连给上级领导送礼,郝凤霞都把钱装到信封袋子中,他只要掏出来递过去就算完事。直到郝凤霞得了病,他才经手家里的钱。等把郝凤霞发送完毕,家里的存折上,就剩四万多块钱了。
这两年,老伍的工资正好够他和伍帅的花费。也就是说,从打郝凤霞去世,他就没往存折上存过钱。在商量这件事时,老伍提到过自己手里只有四万块钱。当时杜亚娟不信,老伍就把存折拿出来给杜亚娟看。那个存折上满满的全是数字,最早存入的那笔,还是十五年前。杜亚娟显得很为难地问那怎么办?连租房子带买设备得八万多呢。老伍本来是想问问杜亚娟手里有没有钱,可转念一想,自己开着一份工资都没攒下钱,一个女人领着孩子过日子,哪儿还有钱可攒!老伍便立即改口说,不用你管,我想办法。当天他打个欠条,从单位财务借了四万块钱。他告诉财务科长,每个月扣他一半的工资,直到还清为止。老伍把这四万块钱的现金和那个存折一起交给杜亚娟时,还嘱咐一句:要是不够的话,我再想法。
没用几天,在振兴街上,丽娟干洗店开业了。
干洗店用的是杜亚娟妹妹的名字,注册法人当然也是杜丽娟了。在跟老伍商量这件事时,杜亚娟说丽娟两口子都是下岗工人,能享受些优惠政策;更主要的是为了避嫌。那阵子市里有文件,不许领导干部的家属从事商业经营。对于这个方案,老伍不单同意,还有些心存感激,觉得杜亚娟考虑问题确实比郝凤霞周到细致。这要是放在郝凤霞身上,她才不会想这么多呢。
杜丽娟两口子没有固定工作,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店里的员工。这个店也就变成杜亚娟她们一家人的大本营。从开业的那天起,他们中午就在店里开伙做饭。两家的孩子放学后,也都来这里吃饭。当然老伍是不来的,他基本每天中午都有饭局。就算偶尔没有饭局,单位食堂的伙食也是比家里好,最起码厨师的手艺比杜亚娟好。
单位食堂晚上不开伙,在没有饭局的情况下,老伍就得回家吃饭。可是杜亚娟晚上得下班这段高峰过后才能关门。就算没有送衣服的,还有取衣服的。干洗这个行业就是这样,衣服没取走之前,你的责任还不算完成。顾客专门来取衣服,要是赶上没开门,让顾客跑了空,惹得人家不痛快,也是影响生意的。
开始那段时间,老伍回到家里,还和往常一样,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这并不是说老伍有多懒,是他真不会做饭。从打跟郝凤霞结婚,且别说做饭,就连盛饭都很少用他。对于老伍不会做饭的事,杜亚娟是知道的。所以她看到老伍在沙发上躺着,也不说什么,就赶紧下厨房做饭。尽管紧忙活,等吃到嘴时,一般都得晚上八九点钟。老伍早就饿得饥肠辘辘,看到小芮坐在身边吃小食品,老伍在边上馋得直吧嗒嘴。
以前吃完饭,小芮在家写作业,老伍两口子还能出去到公园溜达一会儿。现在可好,等吃完饭,已经是夜深人静。此时走到大街上,已经不再是散步,好像是夜游。两个人怕影响小芮学习,又不敢在客厅里看电视,只好去卧室。看到杜亚娟满脸疲惫地躺在床上,老伍也失去了原来的激情。
这种日子过不到两个月,老伍实在受不住了,开始想对策。最初老伍是叫外卖,可叫了十几次,不得不停下来。饭菜要得过于简单,饭店不乐意给送;要多了,也实在吃不起。最后没办法,老伍只好亲自下厨做饭。
开始的几顿,老伍学着煮挂面。虽然也算一顿饭,也得到杜亚娟的表扬,但吃得清汤寡水的,完全是在糊弄。有一天老伍心血来潮,打电话把食堂的大师傅叫到办公室,让他教自己炒菜。大师傅还真上心,教了老伍半天,还是不放心,又把主料、配料、用量、做法都写到纸上。老伍下班后,拿着那张纸去市场买菜,回来后按着程序一点点地进行。等杜亚娟领着小芮回来时,两个菜已经摆在桌子上。
下班后,杜亚娟看到桌上的菜,以为又是叫的外卖,坐下来就吃。老伍边吃边观察杜亚娟娘俩的表情,见她们没有异常反应,就试着问今天的菜好吃吗?那娘俩都回答说好吃,这让老伍受到极大的鼓励。他自豪地说,这是他做的。杜亚娟娘俩都不信,老伍便领着她们去厨房查看现场。等杜亚娟确信后,激动得竟然当着孩子的面,奖励老伍一个很热烈的吻。当然,那天晚上也让老伍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澎湃。
尝到美食带来的甜头,老伍开始迷恋上厨房。在没事时,他就把食堂的大师傅叫到办公室来,请教各种菜肴的做法。学会一招,就迫不及待地回家展示,不单吃得杜亚娟心花怒放,还时不时地把杜丽娟一家三口领到家里来品尝。在得到一致的表扬后,老伍的信心和干劲十足。他不单单晚上下厨,就连早上也起来露一手。
家里原来都是杜亚娟买菜,现在也变成老伍。杜亚娟买菜用的是干洗店挣来的钱,老伍买菜自然就得用他的工资。他是不好意思跟杜亚娟伸手要钱的。杜亚娟虽然也在月底向老伍汇报干洗店的收入和支出情况,但基本都是在被窝里。老伍只要是躺到床上,心思便沉浸在杜亚娟身体给他带来的愉悦上,对杜亚娟的话并不怎么上心。就算是认真去听,也是在听杜亚娟的声音,至于她所说的内容,一听一过也就算了。特别在对待钱的问题上,老伍天生就是个弱智。
其实除了伍帅的费用,老伍也没什么可花钱的地方。有一些花费,像抽烟什么的,也都变相地从单位报销了。虽然老伍原来的那个存折还在,杜亚娟却没往上边存过一分钱。杜亚娟说她又开了个户头,店里的收入都在那个存折上。老伍仍然没往心里去,觉得反正都是家里的钱,放在左兜里与放在右兜里也没区别。
这年秋天,毕业后的伍帅在省城找到工作,老伍的心情更放松了。他这个年纪,仕途上也没有再往上走的空间了,便把整个精力都投入到家庭生活中。此时的老伍,厨艺已经非同一般了。跟那些厨师在一起,不再是请教,而是交流。他去饭店吃饭,发现哪个菜做得好,也把人家厨师叫过来,让人家教教他;发现哪个菜做得不对味,便把老板叫过来,评点一番。那些和他一起出去吃饭的人,都开始称他为美食家。
老伍越发成熟的技术和对厨艺的迷恋,让他再也吃不下去杜亚娟做的饭菜了。就算是杜亚娟不忙不累时,老伍也不再用她下厨,嫌她做的饭菜不好吃。两人的角色无形中进行一次大转换。老伍在做饭时,看到杜亚娟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便想起郝凤霞来,觉得对她有一份愧疚。郝凤霞这一生,包括坐月子在内,都没吃过老伍亲自做过的一顿小米粥。但老伍的这种感觉每次刚刚升起,立即就会被杜亚娟母女那种欢声笑语所覆盖了。
五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老伍早上拟好一个菜单,对杜亚娟说,前段时间你们辛苦了,现在到了淡季,也不忙了,中午把丽娟她们一家叫来,我好好犒劳犒劳你们。杜亚娟接过菜单看了一眼,说这段时间咋还跟山药干上了,大热天的,再吃那东西,上火。老伍回头扫了一眼小芮的房门,往前凑了凑,小声地说,这山药与以往的不同,是老刘出差在焦作买回来的。据说这东西,男的吃了,女的受不了;女的吃了,男的受不了。杜亚娟也向小芮的房门口看了一眼,嬉笑着问,那要是两个人都吃了呢?老伍呵呵地笑着说,你听过这个说法啊?杜亚娟摇了摇头,说没有啊,你做了,我们不都得吃吗?老伍往前凑了凑,趴到杜亚娟的耳边小声地说,要是两个人都吃了,那床受不了呗。杜亚娟略带娇羞地推了老伍一把,说去你的吧。老不正经。可转过身后,又一本正经地说,那就做拔丝山药吧。我爱吃拔丝的。老伍也面呈微笑,眼神中充满着暧昧,连连点头。
快到十二点时,除了那个拔丝山药,其他的菜都做好了。老伍往杜亚娟手机上打电话,想问她们几点到家,好根据时间做最后的这个菜。电话打通后半天没人接,老伍也没在意。他想杜亚娟一定是忙着答对顾客,没时间接。以前这种情况也有,只需一会儿的空,杜亚娟就拨过来了。可老伍又等有十分钟,电话也没动静。他只好再拨,电话提示正在通话中。老伍又等一会儿,再拨过去,那边还在通话。这让老伍有了一丝担心,也有一丝不高兴。他正想往杜丽娟的手机上打电话,听到门口有敲门声。老伍那一丝火气立即消融了。心想,怪不得不接电话,敢情是快到家了。
打开房门,老伍见小芮背着书包站在门口。小芮从五岁就开始学钢琴和舞蹈,到了周末,比上学时还忙。还没等老伍说话,小芮便满脸不高兴地问,老爸,我妈他们都回来了?老伍说没有啊!小芮走进屋,边换拖鞋边愤愤地说,他们都关门了。没等我。小芮学琴的地方离干洗店不远,以往她放学都是先到干洗店,再跟杜亚娟一起回来。打干洗店开业那天起,就一直这样子。
老伍没带上门,边往厨房走边安慰小芮,说她们也许是买东西去了,马上就能回来。他也开始再次点燃炉灶,做最后的那道菜。等老伍把拔丝山药做好后,仍然不见杜亚娟他们回来。老伍又去打电话。这回打通了。老伍问杜亚娟在哪儿呢?杜亚娟说她跟丽娟去市里,中午就不回去吃饭了。老伍问她们干啥去了?杜亚娟吱唔两声,说没啥事,去买衣服。杜亚娟说完立即把电话挂了。老伍从电话里听见那边应该有好多人,乱糟糟的,好像还有人在叫骂。他又按了重拨键,传来一个和杜亚娟很像的声音: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拿着听筒呆立一会儿,老伍看见小芮在扒着门口看他,就勉强地笑了笑说,你妈和你老姨去市里买衣服了,得晚上才回来,咱们俩吃饭吧。小芮又噘起小嘴嘟囔几句,便向饭厅跑去。老伍坐到饭桌前,看着一桌子的菜,觉得就他们俩吃,有些可惜,便告诉小芮说,去给你老姨夫打个电话,让他领着孩子过来吧。不一会儿的工夫,小芮跑回来,说她老姨夫都吃完饭了。老伍本来是准备了酒的,想好好地喝两口,但这个情形,也没有喝酒的兴致了。
黑天时,杜亚娟打来电话,说她在车上,一会儿就到家了。老伍赶忙把中午的饭菜放到微波炉里热好,摆在桌子上。杜亚娟是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家门的,进屋后冲老伍勉强地笑了笑,便去了卧室。老伍也跟到卧室,见杜亚娟脸色苍白,眼睛布满血丝,便关切地问怎么了?杜亚娟仍然勉强地笑着说,没怎么,就是有点累。老伍扫一眼杜亚娟的挎包,见那包瘦瘦的,便又问,没买衣服?杜亚娟愣一下神,半天才反应过来,说没有相中的。老伍明知道杜亚娟在搪塞,她根本就没去买衣服,但他也不好再追问,就招呼她出来吃饭。老伍觉得杜亚娟现在没跟他说实话,是没到说的时候,等上了床,一定会说的。
可他们上床后,杜亚娟只是简单地问了两句小芮今天的情况,就把床头的台灯关了。按照以往形成的习惯,这个台灯相当于十字路口的信号,关灯所传递的意思就是睡觉。
躺了大约半个小时,老伍也没有一丝睡意。他从杜亚娟的呼吸声中,知道她也没睡着。老伍突然被积攒在胸中的一股气愤掀了起来,像睡毛楞一样,搭在他身上的那条毛毯也被吹落到地下了。他觉得胸口被一块大石头压着,喘不出气来,如果再不坐起来,就会窒息的。
老伍的这个举动,吓得杜亚娟也从床上弹起来。杜亚娟已经感觉到老伍的情绪,往前扑了一下,抬手搂住老伍的脖子,身体也顺势倒在他的怀里。她先是用脸在老伍的胸前蹭了两下,才柔软地说,我知道你想问啥。但你得答应我,听了不急眼,我再跟你说。老伍本来是一肚子气的,让杜亚娟这么一搂一蹭的,气便消了一半。他抬手抚摸着杜亚娟的头发,略带焦急地说,我答应,快说吧。

杜亚娟又往前挪了挪身子,往后一扑,便把老伍放倒在床上。她上身趴在老伍的胸前,用带着自责的口气说,老伍,我惹大祸了。老伍知道杜亚娟好大惊小怪的,有一次她往下换床单,把老伍放的手机裹到床单中扔到洗衣机里。她在跟老伍汇报时,也是这神情,这口气,这句话。老伍在心里想,这次大不了又是一部手机的事!他拍了拍杜亚娟的后背,略带鼓励地说,没事的,天塌下来,本局长给你顶着。杜亚娟还是半天没吱声。老伍刚想催促,却感觉到胸前凉凉的,湿乎乎的,这才意识到杜亚娟哭了。老伍被杜亚娟这个举动吓了一跳,觉得事情可能比他预想的严重。他试图坐起来,但身体被杜亚娟压着,努力两次,只好放弃。
虽然没哭出声来,但杜亚娟说话却是带着哭腔。她说刘贵成走之前,给她留下一笔钱。她觉得这钱放在手里也没用,就参股买了蚂蚁养殖场,想增加点收入。没想到那个收购蚂蚁的蚁神酒公司破产了。她投入的那些钱,都打了水漂。她上午才知道消息,她们去找市政府去了。
对于养蚂蚁的事,老伍知道一点儿。前两年还有朋友动员过他呢!当时他就觉得这事玄乎,没上心。他问杜亚娟投入多少?杜亚娟模棱两可地说没多少,我还能有多少!老伍也没再追问,觉得顶多也就是三万两万的。因为刘贵成出事后,他所有的账户都被查封了,家里也被搜查,总计追回赃款一百多万呢。就算还有漏网的,也都是些小鱼虾米。再说了,这钱既然是刘贵成留下的,自己也没权过问和指责。
事情虽然说开了,但老伍心里头仍然疙疙瘩瘩的,有一种被欺瞒的感觉。他耐着性子安慰杜亚娟两句,便以胳膊被杜亚娟给压麻了为借口,从杜亚娟的身底下挣脱出来,把身子挪到床边上。杜亚娟也识趣地翻到床的另一边,两个人背对着背,一夜无言。
第二天上午,老伍给他那个养蚂蚁的朋友打了个电话。本来是想问问他损失多少,那朋友却笑着说,我那点玩意儿,跟你家嫂子比,算个屁啊。老伍便问杜亚娟投入多少。那个朋友反问,多少你还不知道?老伍说真不知道。那个朋友说,我损失四万,她是我的十倍还多呢。
老伍听后吓得瘫坐在椅子上。他所震惊的不是钱的数量,而是杜亚娟的城府和心计。他连续抽了两支烟,才缓过神来。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企盼这一切都是他们结婚之前的事。可他托人核查了一下,杜亚娟的最后一笔五万元的投资,居然是干洗店开业半个月后产生的。
整整一个下午,老伍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房门反锁着。有电话打进来,他不接;有人敲门,他也不吱声。到晚上下班前,他用手机给杜亚娟发了个短信,说他出差了,得过几天才回来。办公室的人都走光后,他才离开单位。他在人民路东段找了一家偏僻的小吃部,要了两个菜,喝了一杯白酒。天黑下来,他又到附近的如家宾馆开个房间。
这是老伍再婚以来,第一次夜不归宿。他本来是想消消火,调整下情绪,或者想想怎么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可越想事情越多,思绪越乱。从杜亚娟做噩梦到干洗店开业,一件件一幕幕都涌上心头,让老伍不由得脊梁沟里嗖嗖地冒着凉气。他几乎是彻夜未眠,打了两次盹,都被噩梦惊醒。
早上不到五点,老伍就从宾馆出来了。路过一家早点铺,他感觉有点饿,就在犹豫是否进去吃点早点的时候,他忽然看见街边的皇朝宾馆门口走出来一男一女,那女的竟然是杜亚娟。杜亚娟和那个陌生男人靠在一起走着,既默契又缠绵,那神情明显是共度一宿之后刚刚退房出来。
老伍不认识那个男人。他也不知道杜亚娟和他是什么关系,认识了多久,是在杜亚娟与他前夫结婚时认识的还是与自己结婚后认识的。老伍感觉太累了,他没有力气走上前去一问究竟。
老伍转过身,包子也没买,他决定去看看郝凤霞,看看那个对自己一心一意的人。
可是到了山上,老伍最终还是没敢走到郝凤霞的墓前,只是在山坡对面坐着。上午十点多,他把烟盒里最后一支烟点着,感觉到脖子后有点痒。他用手摸了一下,一只蚂蚁被他捻死了。他望着手中的死蚂蚁,刚刚消下去的气又冲上来。他发现脚下不远处有个蚁穴,有蚂蚁出出进进的。老伍凑过去,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开始挖起来,边挖边呵呵地笑着,声音越来越大。
责任编辑 晓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