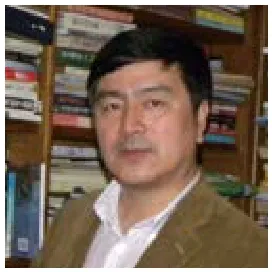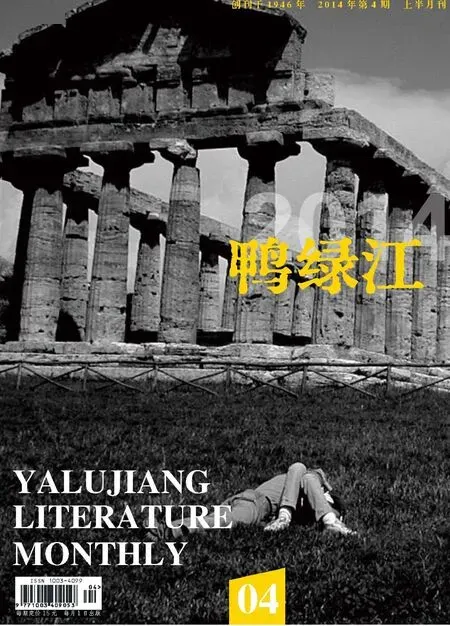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和眷恋
——简谈陈忠实的手札
文/张瑞田 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
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和眷恋——简谈陈忠实的手札
DUICHUANTONGWENHUADE JIYIHEJUANLIAN
文/张瑞田 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
手札的其他称谓也是形象可感的,以写作材料的不同,派生出简、札、牒等;又以授信方的不同,分化出笺、启、状、教、移、表等。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尔雅》:‘简谓之毕。’《说文》:‘简,牒也;牒,札也。’又谓之牍,《史记·匈奴传》:‘汉以尺一牍。’注:木简也。今云尺牍,便文尔。’《中庸疏》:‘简、牒,毕同物而异名。’”
欧阳修在《与陈员外书》中,对手札的称谓和功能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古之书具,惟有铅刀、竹木。而削札为刺,止于达名姓;寓书于简,止于舒心意、为问候。唯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长吏或自以意晓其下以戒以饬者,则曰教;下吏以私自达于其属长而有所候问请谢者,则曰笺、记、书、启。”
手札中的长幼尊卑,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仪密切相关,是一以贯之的文化生态。民国后,这种延续两千年的文化生态被时代的云烟改变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汉语为主体的现代书信。毕竟有着深刻的历史烙印,即使再强大的现代汉语,也无法抹去我们对传统手札的温情记忆。今天,我们写手札,依旧脱不开往日的习惯。
陈忠实致杨匡满的手札,就是一通具有传统遗韵的现代书信。陈忠实以现代汉语行文,但自右至左,竖式八行,毛笔书写,古韵古风犹存——“匡满兄:您好。终于可以给您送上一篇稿件了。说来惭愧,在《中国作家》创刊多年里,竟是第一次投稿。这篇短篇写得稍长了点,大约接近一万七千字,自去年开始重写短篇以来,这是最长的一篇。我去年以来写的这些短篇,都是写当下正在进行着的生活的,现实令人感动的东西太难摆脱了,也许可以作为生活发展的屐痕存下,粗糙一点我都不顾及了。短篇小说如何写,是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各人按各人的理解去写而已。我也不用留恋80年代关于短篇的写作,寻求新的表现形式,效果如何,有待您夺定。贵刊赵虹坚持向我约稿,您可告知,我已践约。接到稿子时,请电话告知,以释邮路之念。祝刊物更富生气和影响。祝您快乐安健。忠实二〇〇二年三月八日于原下。”
陈忠实给《中国作家》杂志寄稿,致函杨匡满,陈述寄稿的背景,简略表明了自己对当代短篇小说的认识和自己的写作状态。应该说,这通手札,对于了解陈忠实的文学写作是有帮助的。只是此文不是探究陈忠实的文学作品,因此,就不在此域饶舌。
拜观陈忠实的书法,容易想起白嘉轩。在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里,我们对陈忠实渊深的历史文化修养所折服。小说中的人物,均具有中国文化的人格特征,婉曲、幽深、凄美、壮观。白嘉轩既是一位明大理、晓善恶的士绅,也颇像一位诗书浸泡的文人。
显然,陈忠实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是依靠毛笔进行文化启蒙的。尽管陈忠实的字里行间,不见书法家的刻意为之,但谨严的草法,流畅的用笔,依然让人感受到旧时文人的书法积淀。当代著名作家,具有书法家自觉意识的人不少,比如李凖、周而复、姚雪垠、马识途、刘征等,相比较而言,陈忠实是依靠童年与少年时期的毛笔训练,进行当下的“书法书写”的。不讲求规矩,不注重形式,也不迎合当下的需求,仅以自己的毛笔,抒发情感,判断现实,理解文学,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顽强记忆和真情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