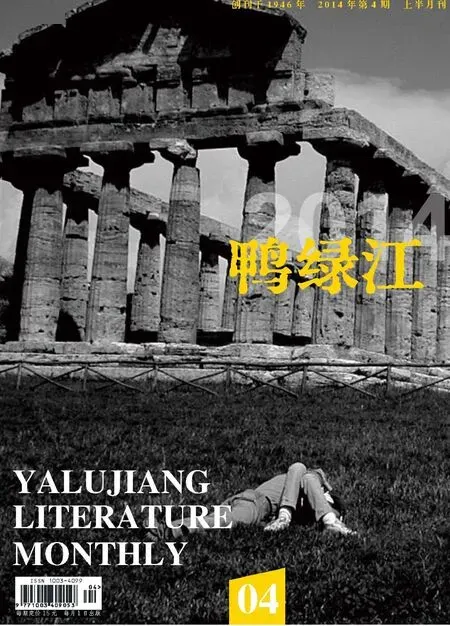揭皮
安 勇
小说
揭皮
JIEPI
安 勇

在我们八间房,说到城,指的必是百里外的新市。两个人相遇,说声进城,彼此都心领神会,没谁会听到别处去,也没谁会走到别处去。最近这几年,村上好多人到城里讨生活。他们说的是发展。有发展成力工、瓦工、油漆工的,有发展成卖菜、卖水果、蹬倒骑驴的,有发展成小区保安酒店门童的,个别的女孩子也有把自己发展到洗浴中心和歌厅里去的……甭管怎么发展吧,人家都是乐呵呵来城里挣钞票的,只有袁福不一样,他没想过要进城发展,是被逼得没办法,才离开了八间房。

安 勇,1971年生,毕业于地质学校,中国作协会员,现居锦州。近年来有小说发表在《山花》《天涯》《文学界》等刊物,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
事情说起来也很简单,袁福是和袁世发起了纷争。袁福是个守旧的人,把香火看得很重要,第一个孩子是丫头,他就鼓励老婆努努力,争取生个儿子出来。袁福老婆名叫陈凤珍,和袁福同岁,也已经四十出头的年纪,但她决心很大,一努力,还真就怀上了。不过,可能是努力程度还不够,几个月前临盆,生下的又是一个女孩子。虽然没能如愿生儿子,但把两个女儿抱在怀里,袁福同样乐得嘴咧到耳朵根子上。家里添了人口,就涉及要地的事。袁福就去给支书袁世发拜年。袁福叫袁世发叔,虽然不在同一支上,但一笔写不出两个袁字,正赶上过年,先拜年后要地,也顺理成章。袁福到袁世发家去了几次,从初一到初四,一直没找到袁世发,初五傍晚,却在家门口的当街上走了个顶头碰。袁福拜了年,就把要地的事情说了。
袁世发受了他的礼,把脑袋摇成拨浪鼓,地早没了,头些年包产到户时,就把地分光了。
袁福不太擅长说话,他的话来得总是有点慢,就好比同样都是水管子,人家只有十几公分长,水龙头一打开,水哗哗就下来了;他的水管子却有十几米长,水龙头拧开好一会儿,水才不慌不忙地流出来。好半天,袁福才想起一句话,叔,咱村还有点机动地吧?
袁世发横他一眼,你听谁说有机动地?我都不知道的事,你咋知道的?
袁世发平时有些霸道,喝了酒更甚些,这天傍晚他就喝了酒,喝得还不少,一张嘴,酒气就撞进袁福鼻子里。袁世发打个酒嗝,狠狠冲地上吐口唾沫,又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没了就是没了,操他娘的,谁敢和镇政府装×?
袁福想了想,不太确定对方骂的是不是自己,但他觉得是的可能性很大,心里就有些不高兴,俺娘死好多年了,你折腾她干啥呢?但袁福也没打算发脾气,他是个老实人,从小到大也没和谁起过纷争。他赔着笑脸,身体转半圈,抬手往村外指,叔,涝河上不就有机动地?
涝河上是一块地的名字,在村庄西北方向,前面临水,背后靠山。袁福指的时候,火红的夕阳正翻过矮墙照过来,刺得他有些睁不开眼睛。他就眯缝着眼睛把胳膊伸了出去。没承想,手指头捅到一个肉乎乎滑腻腻的东西,好像是只蛤蟆。袁福心里纳闷儿,半空中咋会有蛤蟆?但随后他就搞清楚了,不知咋弄的,他戳到了袁世发的鼻子上。
袁福琢磨说几句道歉的话,袁世发已经急眼了,一把推到他胸脯上,你他娘的往哪儿指?
袁福往后退两步,话这时候才流出来,叔,俺不是故意的,没指准,才碰到你鼻子。
袁世发又推他一把,你他娘要是指准了,就把老子眼珠子捅瞎了。
袁福又往后退两步。袁世发追上来,薅住袁福脖领子,兜屁股又一脚。袁福被踢得往前一蹿,棉袄上两颗纽扣绷掉了,像子弹似的飞出去。就是这样,袁福也没打算发火,他性子过于绵软,村里人提起他时就会说,三扁担压不出个瘪屁来。袁福在心里开解自己,当叔的打侄子几下,也在情理之中。但接下去,袁世发说出的一句话,却让他动了真气。
袁世发指着他鼻子说,要真是个小子也就罢了,生个丫头片子,你还要啥地要地?
袁福最受不了别人说他生不出小子,叔,你这是咋说话呢?要地和生丫头生小子有啥关系?你共产党的干部,咋也搞重男轻女这一套?
袁世发又推他一把,生得出,你生个给我看看,瞅你没囊没气的样,就是个生丫头的货。
一股血从脚底冲上来,撞得袁福昏头涨脑,脑袋里就剩下一句话: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他腰一弓,一头撞在袁世发肚子上,叔,你欺人太甚了。
袁世发向后退出十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袁福立马就后了悔,惹毛了袁世发,地就更难要。他紧跑几步上去扶,叔,俺不是成心故意的,快起来,大冬天的地下凉。
袁世发不起来,咧着大嘴,边唉哟,边骂袁福,你个狗操的,下手真狠啊,打伤了老子,有你好果子吃。袁世发从怀里摸出手机,手哆嗦着拨号码,你小子等着瞧,我让大盖帽抓你去蹲笆篱子。
袁福开始以为,袁世发是故意吓唬自己,一个屁股墩儿咋能伤到人?见袁世发一直不起来,脸色惨白,冷汗直流,才知道放屁扭腰——寸劲了,袁世发还真受了伤。袁福急得直搓手,不知咋办好,嘴上说,面汤热,孩子闹,谁难受,谁知道!这句话是袁福的口头语,不知不觉就会说出来,有时候能用对地方,有时候用不对地方。
你个兔崽子,还说风凉话?袁世发骂。
陈凤珍抱着二丫头从院里跑出来,用肩膀扛袁福,当家的,你傻站着干啥,还不快跑?
袁福搓着手转一圈,俺往哪儿跑?
往城里跑。陈凤珍说着又推他。
袁福又转一圈,俺跑了,你和孩子咋办?
你跑了就行,不用管俺们。
袁福就跑了,刚跑两步又折回来,二丫她妈,今天是初五,犯忌讳,不能出远门啊!
陈凤珍使劲推他一把,咋也比蹲笆篱子强!
袁世发坐在地上,伸手抓袁福脚脖子,你小子有种就别跑。袁福一抬腿,脚躲过去了,鞋没躲过去,一只鞋被袁世发捞到手里。
袁福掩着怀,光着一只脚,先坐汽车后坐火车,半夜三更进了城。想起二爷在城里,就投奔过去。二爷是袁福的亲二爷,没儿没女,没家没业,一直在城里捡垃圾为生。二爷说,既来之,则安之,我正要回老家收拾房子,你就在这住下吧!白胡子冲着门口撅两下,又说,钩子、袋子都在那放着呢,你明天就开工,城里的垃圾没有主,谁捡到就是谁的。
第二天,袁二爷又交代一番,回了八间房。袁福就干起了捡垃圾的营生。
……
那天晚上,袁福遇到那个贵人时,已经接近十一点钟。通常情况下,袁福都是晚上十点以后出门,那时候街道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人影子,宽广的大马路就成了袁福的天地。他胳肢窝里夹着抓钩子,手上拖着蛇皮口袋,从一个垃圾箱转移到另一个垃圾箱。刚到城里时,他没太摸清门路,挣钱的心又太切,常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垃圾箱翻得底朝天,惹得人家捂住鼻子骂。挨了几次骂,袁福就长了记性,调整了工作时间。晚上十点钟以后,城里人和垃圾都各就各位,该回家的回家,该进箱的进箱,怎么折腾全凭袁福说了算。反正有路灯照亮,也不会漏过什么好东西。
贵人上前打招呼时,袁福正埋头在垃圾箱里,边翻捡边想心事。元宵节那天,袁福给家里打了电话。陈凤珍一听他的声音就哭了,当家的,咱这回摊上大事了。那个屁股墩儿不起眼,把袁世发的骨头盆子摔裂了,在医院住了六七天,现在走路还直拉胯,大盖帽来过家里两次了,逼俺把你交出来。袁福叹口气,这可咋办好呢?陈凤珍说,你就在外面躲着吧,俺不叫,就别回来。
袁福摇头叹气时,贵人喊了声师傅。贵人是袁福心里的称呼,人家从没拿自己当贵人,一直要求袁福叫他老关。老关喊了几声,见袁福没反应,就伸手拍他肩膀。袁福吓得一哆嗦,抓钩子扔进垃圾箱里。回头见身后站着一个胖男人,双手托着肚子,背头亮得像牛舔的,眼睛上罩着副蛤蟆镜。
师傅,我想请你帮个忙。老关说。
袁福没敢动窝,低下脑袋,看守住自己的两条腿,腿抖得很厉害,眼看就要从裤筒里逃出去。刚来那天二爷就说过,在城里混日子要小心谨慎,指不定啥时就兴许惹了哪位爷。袁福攒了好一会儿力气问,你想让俺帮啥忙?
我想请你清理小广告。老关说。
俺得捡垃圾,没有闲工夫。袁福腰弯着,话说得小心翼翼。
我不让你白干,付给你报酬。你看这样行不行,每清理一张,给你一元钱?
袁福有些发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要是这么算起来,满街的小广告得值多少钱?
你说话当真,不是拿俺寻开心?
老关呵呵笑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钱递过来,当然是真的,这钱你先拿着,就当是订金。
袁福瞄一眼,是张一百元的大票子,搓搓手没敢接,还是先干活儿后拿钱,俺心里踏实。
老关硬把钱塞进他怀里,让你拿你就拿着,到时候多退少补。
袁福又谦虚一下,就把钱接了过来,钱揣进口袋里时,他发现自己满手掌都是汗。
师傅你跟我过来一下,我告诉你清理啥样的小广告。老关把袁福带到一根水泥电杆下,回头问,师傅你识字吧?袁福初中毕业,可以说识字,但偶尔捡到一张报纸,上面也常有不认识的字,袁福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脸憋得通红,低头搓手不说话。
识不识字都没关系,老关指着电杆上一张巴掌大的纸说,你记住这张纸的样子就行了。
老关说的纸夹杂在五颜六色的小广告中间,上面是祖传老中医专治牛皮癣,下面是性病淋病尖锐湿疣,左面是红娘征婚,右面是招聘男公关。那张纸有巴掌大,白地上用墨笔写着黑字,看上去很普通,半点都不像值一元钱的样子。袁福又仔细看了看,最上面写着一行大字,其中有个字,袁福只认识左半边。袁福就悄悄在心里念一遍:大贪官王每金。
师傅你记住了吧?老关问。袁福点点头说记住了,眨巴几下眼睛又说,别叫俺师傅行吗?俺们那疙瘩,打铁剃头的才叫师傅。俺叫袁福,幸福的福。
老关说,那以后我就叫你袁福。袁福,别的广告你不用管,就专门清理这样的,一张一元钱,有一张算一张。三天后吧,还是这个时间,咱们在这里见,一手交广告,一手付钱。
老关伸出手,袁福也伸出手,忽然想起手上有汗,赶紧又收回来,在裤子上蹭了蹭。老关的手厚实绵软又温暖,让袁福觉得分外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握到过。究竟在哪里握的,袁福却没想起来。老关已经走了,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角上。
袁福拖着蛇皮口袋向前走几步,突然停下来,使劲掐一把自己的大腿,疼得直咧嘴,这才知道不是做梦,他真在垃圾箱旁边捡到一个好差使。这笔账是秃脑瓜上的虱子——明摆着,一张巴掌大的纸片一块钱,十张就是十块钱,一百张就能换回一张红彤彤的主席票,在八间房土里刨食苦一年,能刨到几张这样的钱?袁福迈步又向前走,走着走着就呵呵地笑出了声。他想起了老关的手。他突然明白,老关的手为什么让他感觉熟悉了,原来握上去非常像摸陈凤珍的屁股。
第二天一早,袁福去了一趟住处附近的日杂商店,买回两把铁戗子,就正式上了岗。那种铁戗子本来是油工的工具,前面是半拃宽三角形状的薄铁片,后面装着光滑的木头柄。袁福把铁戗子拿起来,在空气中铲了几下,似乎就看见一张又一张的一元钱像雪花一样从面前落下来。
但真正开始干起来,袁福才发现,这钱挣得没有想得那么容易。那种值钱的小广告倒并不难找,它们很有规律地分布在街道边的电线杆上,像一张张笑脸似的,向袁福发出邀请。北边到六纬路,南边到七纬路,西边到四经街,东边到五经街,刚好围成一个方块形。袁福还发现,它们没有过马路的习惯,都规规矩矩地在街道右侧等着他。但要把它们完整地铲下来去换钱,却比登天还要难。在六纬路和五经街的交叉口,袁福第一次把铁戗子铲向“大贪官王每金”时,就遇到了严峻的考验。他发现,那种值钱的纸片是用胶水粘到电线杆上的,而不是用糨糊。糨糊这东西黏度有限,时间也不持久,而且非常黏稠,不利于涂抹。用糨糊粘贴时,人们往往都是在纸片四角抹一点,顶多在中间再加固一下。风一吹,糨糊干了,纸片就卷曲起来,自己把自己揭了下来。胶水则不然,胶水黏度大,而且容易涂抹,一贴上去,就粘得牢牢的,越干越结实。如果是粘在水泥电杆上,就会尤其结实。纸片好像已经长到了电杆上,变成了电杆的皮肤,不管袁福的铲子如何变换角度,还是连一道缝隙都撬不开。袁福心里一着急,手上加大了力度,结果,纸片倒是铲下来了,但已经变成了一堆碎沫,根本不能拿着去换钱了。这么说吧,袁福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从六纬和五经的交叉口出发,顺时针转了一圈,又回到这个交叉口上,一共遇到了五十五张值钱的纸片,但最后只铲下了五张完整的,外加八张半截的,剩下的都变成了一堆纸屑。
袁福不敢算账,一算就难过得要哭,但又板不住在心里算个不停。两笔账就像上牙和下牙,中间隔着的黑洞洞的大嘴巴里,盛着的都是他的悲伤。本来呢,一张纸一元钱,五十五张就是五十五元。但现在呢,只有五元钱,八张半截的,还不知道人家怎么给,要是两张顶一张,那就又能得四元,两下加一起,一共是九元钱。眼见着五十五元变成了九元,谁心里好受得了呢?袁福觉着自己真是败家子,眼睁睁就把钱铲成了一堆碎末,用八间房人的话说,这不是拿钱砸鸭子脑袋吗?
他难过了整整一个下午,算一遍账,就叹上一口气,叹完气,就自言自语说一句:面汤热,孩子闹,谁难受,谁知道!傍晚吃过饭后,袁福就慢慢想通了。他是个信命的人,他觉得啥事都有个因和果,去年你丢了一只鸡,今年补给你一只鹅,是吃了亏,还是占了便宜,老天爷的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谁也别想偷奸耍滑,多吃多占。是你的,到时候自然就给你了,不是你的,咋争咋抢也没有用。就拿眼前的事情说吧,老天爷给他一个好差事,必是有啥原因的,老天爷把给出的东西又收回去一部分,也必是有啥原因的。老天爷有他自己的想法,凡人咋猜得透呢?这么一想,袁福就不再难过了,吃过饭就去路边看热闹。几个钢厂退休的老头每天傍晚都借着路灯下象棋。袁福看了会儿下棋,回到屋里睡一觉,睁开眼睛时,就又到了每天出门捡垃圾的时间,袁福拿起抓钩子,拖着口袋出了门。

值钱的纸片已经铲光了,第二天上午,袁福就没有再出门,而是留在了住处。袁福住的地方名叫西游记宫。围墙圈起来的院子里,竖着几座圆形的大房子。袁福听下棋的老头们说过,这里原本要建成一个游乐场,但不知为什么,却一直也没有竣工,当然也就没有营业过。袁福住的房子在西墙边,是搞建筑时临时搭起来的一座简易房,一面靠墙,另外三面垒着单层砖,房顶遮着石棉瓦。房子里通了自来水,但没有电,晚上照明就只能点蜡烛。
袁福捡回的东西,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进行分门别类。袁福在住处前面的空地上支开摊子,废纸放在一起,矿泉水瓶放在一起,纸壳放在一起,破铜烂铁放在一起……手头的活计干完了,袁福就坐在门前的石礅上,随手从怀里摸出一张值钱的纸片看。纸上的字有一些袁福不认识,但连猜带蒙他也弄懂了大概意思。纸上说,那个叫王每金的人是个当官的,他干了好多坏事:乱搞女人、随便拿人家钱、对有意见的人打击报复等等。袁福放下纸片,使劲想了想,到底也没想清楚王每金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拿他自己举例,有一个陈凤珍就知足了,弄那么多女人咋养得起呢?钱这东西,多有多花,少有少花,没有就不花,干啥偏要去拿别人的?袁福想得脑袋疼,肚子里咕咕叫,就把纸片收起来,起身去做饭。

作者书房
中午吃过饭,袁福把整理好的东西放在一架手推车上,去了废品收购站。收购站在二经街上,把东西换成钞票后,袁福就推着空车慢悠悠地向回走。走到四经街和七纬路的交叉口时,袁福无意间向路边看了一眼,忽然发现一根电线杆上又出现了那种值钱的小广告。纸片还是巴掌大的白纸,只是手写的毛笔字变成了打印字,标题还是同样的“大贪官王每金”。袁福心里一阵窃喜,看来老天爷果然自有主张,知道他损失了一笔钱,就又想办法给他补上了。
把推车送回住处,袁福就拿着铁戗子上了街。这次他从七纬和五经的交叉口出发,沿着街边逆时针前进。那种值钱的小广告,还是贴在电线杆上,有一些干脆就贴在原来的位置上。到傍晚时分,袁福又回到七纬和五经的交叉口上。他发现,和上次一样,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五张纸片。但不同的是,对方大概为了预防被人铲掉,在纸片背面涂抹了更多的胶水。每张纸粘得都很结实,尽管他一直加着小心,但这次,只铲到三张完整的、六张半截的,剩下的都铲成了碎片。这一次,袁福没费什么力气就想通了,虽然挣得比上次还少,但没准老天爷还有别的打算呢!就着中午剩下的半块豆腐,吃下两个馒头,袁福就到街边上去看下棋。袁福不懂棋,勉强知道马走日象走田小卒一去不回还,但他喜欢凑热闹,看着人家下得热火朝天,他就在心里跟着高兴。
今晚几个老头却没有下棋,他们正在说钢厂改制的事。钢厂袁福知道,它就在他铲小广告的那个方块里,很威风的一座大铁门,上面挂着通红的大牌子,但“改制”是什么东西,袁福却摸不清头脑。他竖起耳朵,使劲听了一会儿,从人家话缝里听出点意思来,好像有一个名叫冯材的人收了好处,要把钢厂便宜卖掉。袁福搞不清楚这件事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在心里替钢厂的职工着急了,他想,如果有人把八间房卖掉,他和陈凤珍、大丫、二丫就没地方住了。袁福暗自想,出了这样的事,咋就没有人管一管呢?好像是为了回答他的疑问,一个瘦老头摇头叹气说,这事难弄啊,冯材敢这么整,还不是上面有人罩着?一个胖老头抢过话头,晃着拳头说,我看咱就得动这个。袁福看见胖老头的拳头大得吓人,他想起以前听村里的学生说过,一个人的拳头有多大,心脏就有多大,他似乎就看见一颗巨大的心脏在胖老头的腔子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第二天上午,袁福多跑了一趟废品收购站。头一天晚上,他在七经街的一个垃圾箱里捡到了两块王八铁,这一片离钢厂近,不时就能捡到钢和铁。王八铁有脸盆大小,分量重得很,装进车里不好掌握平衡,袁福就单独装了一车。不管是在村子里,还是到了城里,袁福都不怕花力气,他一直记着爹说过的一句话:力气这东西越用越长,不用就白瞎了。袁福推着车走到五经街和六纬路的交叉口时,车前轮压上了一小片薄冰,袁福的车失去了平衡,像一只喝多了酒的老母鸡,挓挲着翅膀摇摇晃晃向前冲。袁福好不容易把车稳住,脑门上已经钻出一层白毛汗。他把手推车支在马路牙子上,抬手把汗水抹掉,无意间向旁边瞥了一眼,看见几步外的一根电线杆上又出现了那种值钱的小广告。袁福想,看来老天爷心里真有一杆秤,知道他吃了亏,就一次又一次找补。袁福推着车向前面走,眼睛不时向街边扫一下,他发现每一根电线杆上又都长出了那种小广告。
卖掉王八铁回来,袁福就拿着铁戗子,兴冲冲地上了街。新长出来的小广告还是巴掌大小,标题也一样写着“大贪官王每金”,数量也一样是五十五份,不过内容略有些变化,后面增加了一条,说王每金收受钢厂厂长冯材的贿赂。袁福读完这段话后,眼前就晃动着一个巨大的拳头,那是胖老头的拳头。
老关很讲信用,当天晚上,差不多又是上次那个时间,准时出现在了垃圾箱旁边。
袁福从怀里掏出一沓纸,分别握在两只手里,一五一十地讲了铲除小广告的经过。
袁福把右手伸出去说,你老数一数,三次加一起,一共是十张整的。又把左手伸出去,还有二十张半截的,你老看着给。
老关呵呵笑几声,摆摆手,用不着数,怪我考虑不周,这种计费方式不太合理,小广告本来就不好往下揭,你前后清理了三次,每次五十五张,加一起就是一百六十五张。老关掏出钱包,抽出两张钞票递过来,这是给你的报酬。
袁福瞄一眼,见两张都是百元的大票子,两条腿就止不住开始打哆嗦,心跳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世界上咋会有这样的好事呢?就跟变戏法似的,十几块钱眨眼就变成了二百块钱。袁福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把手藏在身后,低下脑袋往后退两步。老关追上来,硬把钱塞进他怀里,收下,收下,这是你应得的。
袁福勉强收了,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一沓零票子,往手指上吐口唾沫,一张张捻着数,俺还得找你三十五呢!
老关摆摆手,不用找了,天气怪冷的,多出的那点钱你买杯酒喝,驱驱寒气。天气果然很冷,老关的嘴巴边扯出一团白气,好像是一把白胡子。袁福忽然想起那一百元订金,赶忙掏出一张钱要还给老关。
老关说不用还了,袁福,你考虑考虑,看这样好不好,以后咱们按日工资结算,只要你把那种小广告清除掉,有一天算一天,一天我付给你一百块钱。按日工资算,三天刚好是三百块钱。
袁福用不着考虑,直接就点头同意了,不用按件计酬,他就可以想怎么铲就怎么铲了。
老关临走又和袁福握了手,说在城里有什么难处只管开口。袁福又一次想起了陈凤珍的屁股。第二天上午,袁福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扔进一枚硬币,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他告诉陈凤珍,自己找到了一个揭皮的好差使,三天就挣到了三百块钱。揭皮是袁福临时想到的一个词,他觉得用这个词说自己干的事很贴切。陈凤珍高兴了一小会儿,很快又满腹忧虑地叮嘱袁福,这阵子出来进去要小心,袁世发还没过劲,这两天正嚷嚷着要带大盖帽进城抓人。袁福在电话亭里转一圈,闪着银光的电话线缠到了脖子上,这可咋整呢?要不咱花钱消灾,给袁世发上点供?陈凤珍说呸,错的又不是咱们,有钱花给大丫和二丫,还能听见她俩喊咱一声爹妈,花给袁世发算怎么回事?陈凤珍一向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大事小情袁福都听她的。
那些写着“大贪官王每金”的小广告长势喜人,就像袁福家后园子的韭菜,割掉一茬又长出一茬。它们还有些像某种神奇的皮肤,揭掉一层,就会又长出一层。袁福需要做的就是不断收割和揭皮。袁福形成了新的生活规律,每天早起上街清除小广告,下午把捡回的垃圾整理好,推到废品收购站,晚上如常上街捡垃圾。盯着一根根电线杆看得时间长了,袁福慢慢发现,城里的小广告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治病的、招聘应聘的、办假文凭假证件的、出租出售房屋的、卖猫卖狗的……有一天,袁福竟然看到一张绿色的纸上写着“自卖为奴”几个字。袁福看得最多的一个小广告,只写着三个字:包小姐,下面是一串手机号码。袁福心里纳闷儿,这个姓包的女人在搞啥名堂呢,干啥到处留自己的号码呢?
当然了,这些小广告和他袁福都没啥关系,他需要收拾的只有写着“大贪官王每金”的那种纸片。袁福嘴上笨,但心里不笨,没干几天,他就找到了窍门。每次上街他都随身带一把塑料喷水壶,找到那种纸片后,哧哧喷几下,等个半袋烟工夫,纸就变软了,铁戗子再上去铲,就易如反掌了。
有一天早晨,袁福无意中发现,写着“大贪官王每金”的纸片不再规规矩矩待在方块里了,它们过了马路,跑到了街道对面的电线杆上。袁福手里拿着铁戗子,追着它们也过了马路。这时候,袁福才搞明白,原来这些纸片不是过马路就完事了,而是像河水似的沿着街道向四面八方流淌漫延。向北,它们漫过六纬路,淹没了五纬路;向南,它们流过七纬路,漫延到八纬路;向西,它们越过四经街,占领了三经街;向东,它们突破五经街,跑上了六经街。袁福从早晨干到晚上,铲得胳膊酸疼,才总算把那些纸片都收拾掉。向回走的一路上,袁福就在心里想,贴纸片的是些什么人呢?他上半夜捡垃圾时,没见有人往电线杆上贴纸片,这些东西必是后半夜贴上去的,这么多纸片要贴好长时间啊,恐怕一宿都睡不上觉了,这些人何苦要这么干呢?
袁福边想边走,远远看到那几座高高的圆房子时,忽然发现有三个人正站在西游记宫大门口。两个头上戴着大盖帽,另一个又矮又胖,正是袁世发。袁福赶紧一闪身,躲到路边一棵柳树后,两条腿抖得像通了电,心跳到嗓子眼。袁世发真没放过他啊,已经带人追进城里来了,从今往后,他袁福很难再过消停日子了。袁福在那棵柳树后面一直藏到天黑,直到看见袁世发他们从另一条路离开,才心惊胆战回到住处。
当天晚上见到老关,袁福收了报酬,就把小广告蔓延的情况说了。袁福有些担心地说,这事儿,俺觉着有点不太妙啊!他是替老关担心,袁福觉得老关和王每金必是有些关系的,没准老关就是王每金也说不定,所以才会花钱雇人清理这些小广告。
老关听了他的话,抬手摸一把油亮的背头,呵呵笑几声,很随意地说出了两个字——刁民。袁福想了想,觉得老关说的不是自己,就点头哈腰地附和说,刁民,真是刁民。老关又呵呵笑两声喊袁福,你看这样行不行,小广告增加了一倍,你的工资也长一倍,每天给你二百好了。袁福吓得差点尿裤子,一天挣二百块钱,他连做梦都梦不到啊!他想着推辞几句,但老关已经抻出几张钞票递过来,这次就按二百算。
老关临走时,照例和袁福握手,问他在城里有没有什么难处。袁福犹豫一下,就把袁世发带两个大盖帽来抓自己的事情说了。老关听完显得很气愤,连着说了两句简直是无法无天,又详细问了八间房所在的县和镇,最后说,袁福,这事你不用怕,只管放心住在城里,以后不会再有人来找你麻烦。袁福虽然点头答应着,但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你一个城里的老关,咋能管到乡下去?
袁福的工作区从小方块变成了大方块。他觉得,有人正在暗中和他比赛,就像早年间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每人拿一条垄,你追我赶,各不相让,他铲得越快,对方就贴得越快,他铲得越多,对方就贴得越多。袁福的铁戗子磨薄了,刃口闪闪放光,好像成了一把刀。他铲小广告的技艺也越来越高超,先用喷壶哧哧两下,从下往上两铲子,从右向左再来两铲子,纸片就从电线杆上消失了踪影。袁福干得得心应手,轻松自在,手上做着活,眼睛还不耽误看街上的热闹。有一天上午,袁福就在街上看到一个大热闹。他铲到五纬路上时,看见钢厂前面的广场上黑压压地聚了好多人。这些人把拳头往天上捣,嘴里大声喊着口号。袁福侧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发现他们喊的是:还我工厂、还我工作、还我工资。袁福听了一会儿,看了一会儿,眼前那根电线杆上的小广告铲掉了,他就迈步向下一根电杆走,边走边想,有事说事,这么胡闹有啥用呢?

作者手边书
需要清理的那种小广告还在不停向四面八方漫延,向北到了二纬路,向南过了十三纬路,向西最远已经到了废品收购站所在的二经街,向东也到了十经街。袁福已经顾不上再捡垃圾了,每天起早贪黑铲除那些“大贪官王每金”。袁福觉得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了,看这架势,暗中和他比赛的绝对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很可能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老关却仍然毫不在意,依旧笑呵呵地说刁民,这期间他又给袁福加了一次钱,把报酬从二百涨到了三百。钱虽然越挣越多,但袁福的心里却越来越发慌,就好像随时都要发生什么事情似的。有一天下午,袁福给老婆陈凤珍打了电话。以往他心里没底时,都是向陈凤珍讨主意,在袁福看来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往往陈凤珍三句五句话就解决了。但这次,没等袁福说出心里的烦恼,陈凤珍就说要把电话给袁世发。袁福吓了一跳,正想把电话挂掉,陈凤珍又说,叔来咱家守好几天了,就为了和你说几句话。
听筒里传来袁世发的声音,低三下四喊福子。袁世发说,福子,你只管放心,叔骨头盆子摔裂这篇从今往后就算掀过去了,谁要是再往回翻,就是大姑娘养的。袁福心里糊涂,搞不清袁世发抽的哪根筋。袁世发又接着说,二丫头的地呢,是真没有了,涝河上那块地一年前就让镇政府要去了,听人说镇政府是给县里要的,说是要盖啥别墅。究竟啥时候盖,盖成啥样子,咱就弄不清楚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是真有地,小舅子才不给咱二丫头分呢!
袁福嗯啊地应着,心里越来越糊涂,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袁世发可啥时候这么和自己说过话啊!袁世发又喊一声福子说,想不到你那么有办法,刚到城里没几天,就结识了大人物。袁福这才想到了老关,看来人家真拿他的事当事办了。袁世发咳嗽一声又说,福子,啥时候得了空,就回咱八间房看看,你走这么长时间,大家伙都怪想的。
放下电话,袁福在心里算了算,从打初五出来到现在,一晃也有二十多天了,真该回去一趟了。但袁福只是这么想一下而已,他也明知道自己脱不开身,那些写着“大贪官王每金”的小广告,还在不断沿着新市的各条街道扩散,如今差不多已经占据了铁道北的小半座城市,并且有越过铁路向另外半边传播的趋势。贴广告的人知道有人和他们对着干,除了不断扩大范围之外,还想出了一些新花样,有一天早晨,袁福看见电线杆上出现了用红油漆写着的“大贪官王每金”。袁福把这个情况向老关做了汇报。老关像过去一样,胸有成竹地呵呵笑两声,说这些刁民还真有鬼点子,拍拍袁福肩膀又说,回头你买点石灰粉,他用红的,咱就使白的,刷子一抹就盖上了。
袁福是三天后的夜里挨打的。当时,他正站在七纬路和三经街交叉口的一根电线杆底下,用刷子蘸石灰水涂抹红油漆写的“大贪官王每金”。那些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呼啦一下就把他围住了,等袁福察觉情况不妙,脑袋已经被套上一只破布袋,眼前顿时一片漆黑,脚底下挨了一绊子,扑通一声就倒在了地上,棍棒和拳脚不分脑袋屁股地落下来。他听见有人边打边喊他狗腿子,不知咋的,袁福想起了胖老头巨大的拳头。袁福正想仔细听听,脑袋上突然挨了一下,随后就昏了过去。袁福醒过来时,发觉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眼前一片黑,他以为眼睛被打坏了,用手一划拉,才知道脑袋上还套着口袋。袁福把口袋摘下来,发现左脸颊一片黏糊糊的潮湿,抬手一摸,抓到满手掌的血。袁福知道自己的脑袋被打坏了。袁福想站起来,挣扎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左腿吃不上劲,一动就钻心地疼。袁福就知道,自己的腿也被打坏了。袁福没有喊救命,他脑袋里一直转腾着一句话,他就把这句话说了出来:面汤热,孩子闹,谁难受,谁知道啊!在街头躺了一个多时辰,袁福才看到一个拖着蛇皮口袋的同行走过来,央求对方把自己送到医院去。
袁福在医院躺了一周,才总算能拄着拐杖下地活动了。这些日子里,袁福心里一直在想着两件事:打他的必是贴小广告的人,见到老关他要好好告一状,让老关收拾收拾那些刁民;另外呢,城里的医院贵得像抢劫,住了这一次院,从老关那里挣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他要加倍努力,争取把钱再挣回来。
回到住处第二天,袁福就拄着拐杖上了街。这些日子没有清理,写着“大贪官王每金”的小广告已经泛滥成灾,一根电线杆上往往就有两三张。袁福二话不说,使喷壶喷几下,抄起铁戗子就干起来。袁福整整忙了一天加大半夜,看看快到了以往和老关见面的时间,就又回到老地方等老关。这一晚,老关一直没有来。袁福也没多想,第二天晚上又接着等。一连等了十天晚上,老关仍然没有照面。袁福开始感觉不对劲了,以往老关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不露面的。但袁福转念一想,老关不是平民百姓,保不齐就许有啥事绊住脱不开身呢!袁福就继续等。
那些需要清理的小广告渐渐都被收拾干净,而且没有再长出来,没有什么事情做,袁福就又开始每晚捡垃圾。有一天晚上,袁福正埋头在垃圾箱里,突然听到城里响起了鞭炮声。开始只是在钢厂所在的小方块里面炸响,很快就蔓延到周围,最后整座城市都响起了鞭炮声。袁福停下手,四下里看了看,摇摇头,在心里说,城里人真是败家子,不年不节的放哪门子鞭炮呢?
袁福的腿已经彻底好了,扔掉拐杖也能行走自如,但老关却一直没再露面。这件事,袁福慢慢也想通了,世事不就是这样吗?本来不该是自己的,咋争咋抢也没用,老天爷给了他一笔财,又变着法子拿了回去,里外里,他既未多,也未少,没吃亏,也没占便宜,这不就结了吗?
不久后的一天上午,西游记宫门外开来了两辆张牙舞爪的大铲车。袁福打听了一个老头才知道,城里正在搞形象工程,首先整治烂尾建筑,能继续建的继续建,不能建的就干脆拆掉。袁福问啥叫形象工程?老头说,就是树立领导的形象呗,新官上任三把火,不搞出点名堂来那还能行?袁福前脚把自己的东西搬出来,铲车的大爪子后脚就落下来,轰隆一声就抓倒了那座简易房。袁福看着废墟上腾起的烟尘想了想,就决定回八间房。
袁福先坐火车后坐汽车,在傍晚时分进了村。一晃两个多月没回来,看哪儿都觉得亲。袁福正往前走着,听到身后有人喊福子。他回过头,见袁世发满脸堆着笑,站在自己身后。
袁世发问他是啥时候回来的?袁福随便应付几句,就想赶紧回家去,虽然袁世发说过去那篇已经翻过去了,但见到他袁福还是觉得不自在。袁世发却不放他走,拉住袁福的袖子把嘴巴凑到袁福脸边说,福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二丫的地有着落了。我刚整明白,涝河上那块地县里也不是自己要的,而是给城里要的,城里的一个大官要修别墅,相中了咱那块地,现在那个大官倒台了,咱的地就跟着解放了。袁福嘴上应着,那敢情好,那敢情好,心里却想起了小广告上的“大贪官王每金”,当然还有那个总是呵呵笑着说“刁民”的老关。
袁福正想着,袁世发又说,福子,你在城里结识了大人物,回头再进城,帮咱村说句话行不行?往镇上去的那条路早就该修修了。
袁福没把袁世发的话听进耳朵里,他脑袋里正像风车似的呼呼地转动着一句话:面汤热,孩子闹,谁难受,谁知道啊!
责任编辑 晓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