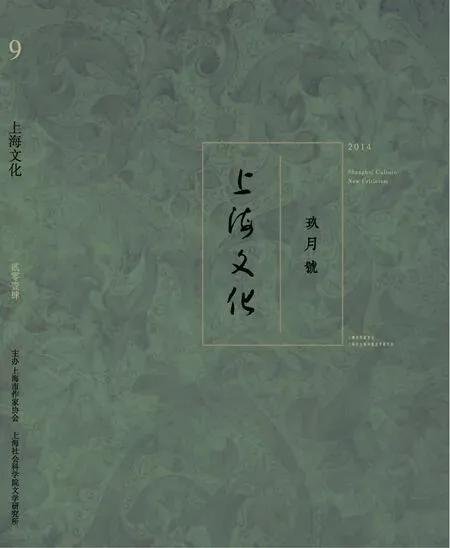那些与情欲缱绻一处的审美
吕永林
那些与情欲缱绻一处的审美
吕永林
陈清扬的裸体美极了。
多少年后又一次翻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才发现,以往无论作者读者,都中了一种叫作审美的毒而不自反——非但不自反,简直是义无反顾。个中原因或许在于,此毒之于我们,犹如纳博柯夫笔下的“洛丽塔”之于“亨伯特”,是令红尘颠倒的腰胯之火,是生命之光,是罪孽,是灵魂,它从来就渗透在创造者的字里行间,解构者的文本深处,反抗者的有意无意之中。近十多年来,“王小波门下走狗”众多,《黄金时代》也一度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然而至今未见有谁提起,王小波对陈清扬之“美”的配置,既是解药,也是毒,且一直贯穿于作家本人所宣扬的“三大基本假设”之内。尽管在“第二个假设”中,王小波尝作如是自白:“我很喜欢女孩子,不管她漂亮不漂亮。”然而小说的实情却是: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面,女主人公“X海鹰”虽然长相一般,身材却棒,而“姓颜色的大学生”则十足是一位美女,至于《寻找无双》里的“无双”(成长蜕变后的)和《红拂夜奔》里的“红拂”,也都是漂亮女子。
种种与情欲相关的审美冲动和种种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一同生产出对我们每个人的细密编织,并建立起一种无比甜蜜而阴险的“审美的暴政”
如果单就异性审美这一片面的话题而论,我认为,王小波的《怀疑三部曲》可谓并无多少怀疑意识与批判精神。相比之下,《我的阴阳两界》倒是先锋得多,在这篇小说中,“王二”对“小孙”之“好”的重视实实在在地穿透了他对“小孙”之“美”的重视,而这恰恰是一个连《黄金时代》里的“伟大友谊”都未能彻底完成的壮举。在《我的阴阳两界》中,“审美”的旨趣不再像在别的小说中那样,总是拥有一种秘而不宣的霸权,而是让位于一种可名之为“审好”的叙事冲动和伦理需要。“我觉得她是好的,这世界上好的东西不多,我情愿为之牺牲性命。”这是一句与众不同的情话,“王二”这句情话的根本所在,可用另一个句子来挑明:“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觉得她是自己人,她也觉得我是自己人。”所谓“自己人”,其根本就在于“李先生”所说的“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对无聊的问题是否充耳不闻”。当然,“小孙”长得也不赖:“她梳了个齐耳短发,长得白白净净,还是蛮漂亮的。”尽管如此,在《我的阴阳两界》的绝大部分文字中,“小孙”之“好”依然构成了她的首要特征,而“王二”对小孙之“好”的喜欢和渴望也似乎越出于他对小孙之“美”的喜欢和渴望之上。
令人遗憾的是,小说收尾之前,这种“审好”的强度却在不断减弱,并且最终,在一场未被言明的“美好之争”当中,王小波还是选择了一条既“美”又“好”的理想化叙事。即把“美”和“好”捆绑一处(二位一体),从而避开了在“美”和“好”的冲突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发表于1950年代的作品,如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和宗璞的《红豆》等,反倒显得更加富有某种直面“惨淡”的味道,虽然它们各自所提供的解决之道也并不十分高妙。如今回头去看,《在悬崖上》等社会主义“爱情故事”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对于人类文明史上持存久远的“美好之争”,朝向社会主义革命总体性的压抑与升华非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反而最终成为审美性情欲在1980年代迅猛登台的直接动因之一。而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留给我们的历史后果在于:许多时候,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大家都不得不去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种种与情欲相关的审美冲动和种种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一同生产出对我们每个人的细密编织,并建立起一种无比甜蜜而阴险的“审美的暴政”。毫无疑问,包括《黄金时代》在内的诸多王小波作品,也已然被嵌入到这一历史性的脉络之中。
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
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
你说要汽车你说要洋房
我不能偷也不能抢
我只有一张吱吱嘎嘎响的床
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
我的舌头就是那美味佳肴任你品尝
我有一个新的故事要对你讲
孙悟空扔掉了金箍棒远渡重洋
沙和尚驾着船要把鱼打个精光
猪八戒回到了高老庄身边是按摩女郎
唐三藏咬着那方便面来到了大街上给人家看个吉祥
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
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
你说这个故事不是香肠
我知道这个夕阳也披不到你的身上
我不能偷也不能抢
我不能偷也不能抢
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
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你钻进了汽车你住进了洋房
你抱着娃娃我还把你想
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
不用说,在对当前社会分配形式及其意识形态宣泄不满的意义上,何勇这首《姑娘漂亮》无疑是一首令人侧耳的抗拒者之歌;但是,在维护和传承审美之毒的维度上,《姑娘漂亮》却又是一首服从者之歌,因为它所迸发的不是反抗,而是一如继往的沉溺与失败。无论有意无意以及承认与否,在漫长的与情欲相关的审美道路上,众人似乎更愿意同中年叶芝逆向而行。
不知自何时起,审美这桩充满风险且浸透着人类社会等级制气息的事业,被所谓智识阶级大张旗鼓地擎举起来,并将其导入各级各类的教育体系当中四处播散,风气弥漫之深之远,从一本本我们打小诵读的语文课本可见一斑。对此,广大文艺工作者似乎抱着一种天然的乐观态度,认定审美可使人向善、求好、得自由,是启蒙的利器,治病的良药。有论者甚至称: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审美,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幼儿期是人的审美敏感期,审美教育也理应从娃娃抓起。对此,我常常感到疑虑,尤其是在与情欲相关的审美领域。
朋友Z君几年前曾跟我讲起他的宝贝儿子,说小家伙脸蛋长得很肉,肥嘟嘟的,有位邻家小姑娘,比Z君儿子大不了几个月,每回在小区里相遇,都会扑过来在弟弟脸蛋上“啃”上几口,可见小朋友皮肤之嫩之好,以及何等讨人喜爱。Z君之乐,在于幸福的夸赞与回味,同时也是一说了之,无甚深意。然而这件趣闻我却至今不能忘怀——我始终不明白,对一个两三岁大的小女孩而言,Z君儿子的幼嫩肌肤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也时常记起齐泽克讲过的一桩乐事。他说在他儿子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子俩一起经过一个报亭,亭子上贴着一张很大的海报,上面画了个一丝不挂的美女,双腿跨在哈雷摩托车上。于是儿子喊道:“快看,多棒啊!”然而他注意的并不是那个女人,而是哈雷摩托车!齐泽克讲起此事的本意是要交待1980年代斯洛文尼亚(属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的时代境况,他调侃说,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在社会主义的最后十年过得最好,除了拥有国家资助的食物、住房、工资、文化,人们还享受着可以抱怨政府的乐趣。“有三年时间,是绝对的自由自在,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规章条例来管理赤裸裸的色情文化,当时到处都是报亭,它们都贴着非常具有色情味儿的海报……那是我们的失乐园。”不过对于齐氏所讲的这桩乐事,我倒格外看重“儿子”对裸体美女的不敏感这一偶然枝杈出来的细节。与之对称的,自然是“父亲”对裸体美女的敏感,以及在成人世界,情欲和审美的诸多纠缠——情欲本就熬人,奈何又加审美。就“父亲”而言,色情文化的解禁一时间提供了某种情欲释放的渠道和审美的自由,但“父亲”也必须承受成人世界对另一种自由的失去,这就是“儿子”对性感女郎这一情欲审美对象的不敏感。那是一份独属于黄口小儿的灵肉自由,是冥顽未化者的“伊甸园”和“审美节日”。
然而黄口小儿终须长大,“伊甸园”也终将失去。《蜀山剑侠传》里的“苦孩儿”司徒平,本是铁了心求仙求道,不想造化弄人,硬是将他卷到紫玲谷去同秦紫玲、秦寒萼姊妹相会,秦氏姊妹乃天狐宝相夫人之女,“俱都生得秾纤合度,容光照人”,司徒平一见到这两位“云裳雾鬓,容华绝代”的少女,立时惊为天人,“不知不觉间起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从此之后,一切看似前因注定,实则司徒平自投罗网,误了飞仙大业,最终只能与秦寒萼双宿双栖,永久滞留凡间。小说中,司徒平一出场就已经是少年郎,尽管他“平时人极端正,向来不曾爱过女色”,明眼人都知道,这只能算作一种涉险者的自我压抑与自我克制,绝非稚子天真式的浑然不觉。而在峨眉修仙人的观念里面,司徒平上演的这场与情欲相干的审美活动,无疑是一场要命的“劫”。但自古以来,那些飞蛾扑火、向劫而奔的人,每每不在少数,只是如司徒平这般运气的,倒是少数,难怪网上有读者会酸溜溜地将司徒平的“艳福”概括为“屌丝男逆袭白富美”。
我读研究生时,同宿舍有位理工男S君,人极幽默,学识也高,又有才情,并且勤劳,我们于是赠他一个雅号——“小蜜蜂”。每晚临睡前,“小蜜蜂”总要哼几句王菲的歌,其中我们听过遍数最多的是: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如影随形
无声又无息
出没在心底
转眼吞没我在寂默里
我无力抗拒
特别是夜里喔
想你到无法呼吸
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
“小蜜蜂”也喜欢在下午四五点钟的学校操场上跑步,除了锻炼身体,他还希望能逢着一只美丽的“小天鹅”,一只独属于他的“小天鹅”。作为“小蜜蜂”的好哥们,我们几个都知道,这梦想同王菲的歌一起,扭成他心头蜜甜而忧伤的结。
倘若我们的追究就此打住,那么“小蜜蜂”的“小天鹅”之梦带给大家的,就是一抹简单、快乐的记忆,而司徒平虽然错过了修仙正道,本质上却可归于“两善择其一”而居的“幸福分配”范畴。不幸的是,在更为辽阔的现实之内,此种与情欲相关的审美之旅却常常会引为人生长久的苦痛与焦灼。其中颇为激进的呈现,除了何勇的《姑娘漂亮》,还可见于朱文的小说《我爱美元》——女友留给“我”的时间只是“廉价”的白天,而非作为“黄金时间”的夜晚;“我”能给“父亲”的,则是“廉价”的或者价位稍高一点的妓女。虽然“我”是多么渴望让自己、让“父亲”拥有一种阳光灿烂的“性”,问题是,对于无数的穷人而言,与此相干的审美教育所生产出来的幸福允诺多半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所谓审美自由,其所馈赠的往往不是欢乐,而是烦恼和苦难,跟其他所有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一样,人类审美资源的分配体系也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等级制。人们的审美行动既朝向幸福分配,也朝向苦恼分配或苦难分配,关键就看一个人在等级化的分配体系里面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了。
无论文本内外,我们都能看到,所谓的“美”和“审美”是如此广泛而深刻地镶嵌于社会等级制度之中——衣食品调、居住档次、出行方式、劳动分工与社会地位、阶层化的人口分布与空间区隔——人类的社会等级制是何等地乐于征用审美等级制这一人文装备,而审美等级制又是何等有效地巩固着社会等级制。尤为可怖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还在自己奋力追逐某些美或审美对象的同时,有意无意之间不停以自身为媒,欣欣然效力于某些美的特权及其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
如果你是长得好看的话,在公车地铁上睡着了,头靠在旁边人的肩上,旁边的人会一直陪着你直到醒来。你要是长的丑的话,头一旦靠在旁边的人肩上,他会立即拍醒你,并温馨提醒你保管好财物。
以上这段文字之初衷,本不在宣扬“美”,而是善意地提醒“丑”,然而无形之中,其对于“美”的特权,却是无条件的投降与服从,同时对“丑”造成变相的杀戮,因而看似悲情,终归无情。事实上,我们身边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或隐或显的杀伐行动,其传播渠道和范围有时十分广大,如知名膨化食品“薯愿”的电视与网络广告——几位美女吃着刚烤出的薯片,有说有笑,且大秀窈窕身姿,一脸满足之情。此时一位胖姑娘从旁边探出半个身子,羡慕地看着她们,满怀向往地说:“我也要薯愿。”此广告问世已有数年,且几度推出新的版本,但无论怎样出新,里面那个被蓄意丑角化(甚至是卑贱化)的胖姑娘形象却无一例外地保留下来。迄今为止,只听说该产品因外包装宣称“百分之一百不含反式脂肪”而涉及虚假广告,相应公司已受到工商部门的处罚,却未见有任何媒体或个人从审美等级制及其所生产的社会压迫角度对该广告提出置疑。因此可想而知,只要这一广告多流传一天,其所携带的审美压迫与歧视就会多播种一天,而看过该广告视频的观众对所谓“不美”的自我意识或社会歧视就会多滋生一天。
跟其他所有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一样,人类审美资源的分配体系也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等级制
我们的文学一直在生产、强化着美的特权,从“风”、“骚”传统到“四大名著”,从“五四”新文艺再到“后革命”叙事,莫不如是。在这个不停膜拜美且不断赋予美特权的文化历险中,《卫风·硕人》、《洛神赋》等无疑是典范之作,而《金瓶梅》、《红楼梦》等则更是居功甚伟,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也最多不过在英雄、好汉、取经人跟“美”(不分性别、物种、品类)之间下了几局暧昧不明的和棋。“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夫子的慨叹千古流传,却于事无补。一路而下,在中国文艺的疆域之内,或许只有“延安时期”和“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创作取得过短暂而局部的“想象性”胜利——社会主义伦理意义上的“好”实现了对部分“美的特权”的反动与超越。其中代表,除了《我们夫妇之间》、《红豆》、《千万不要忘记》等文学作品,还有《上海姑娘》、《五朵金花》等电影,以及诸多关于新中国的宣传画和新年画。
在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中,知识分子出身的“我”一进北京城,就开始感到贫农出身的妻子的种种不美:
同样是灰布“列宁装”,旁的女同志们穿上了,就另一个样儿:八角帽往后脑瓜上一盖,额前露出蓬松的散发,腰带一束,走起路来两脚成一条直线,就显得那么洒脱而自然……而她呢,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沿直挨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播一摆,土气十足……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她也不认输!我对她的一切的规劝和批评,完全是耳边风……
如若放在今天,多数写作者可能要么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难题,从而考虑制造一出惨剧,要么选择让女主人公成功实现由外而内的审美化改造,从而去生产一出喜剧,因为在今天通行的相关意识形态里面,人的外在美已然演化为一种宰治性的力量。但是在1949-1950年,萧也牧的选择是让“我的妻”之内在美上升为第一性的东西,在小说最后我们看到:
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仿佛回复到了我们过去初恋时的,那些幸福的时光。
在更加严格的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将此处的“内在美”这一依然属于美学范畴的词语置换为“好”这一更多朝向伦理学范畴的词语,并以此呼应前面所提到的一个重要命题——人类文明史上的“美好之争”。在1950、19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姚文元的《照相馆里出美学》、《论生活中的美与丑》诸文曾多次谈及这个我们名之为“好”的问题,但是对于他本人所描述的“清晨出来,一群红领巾笑着闹着从街上走过,精神焕发的青年人、老年人在公园里做早操、打拳,托儿所的阿姨满面笑容地迎接着妈妈和孩子,拿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工人、学生在出神地看着、沉思着”等形象,姚文元却仍旧用“劳动人民的美”和“共产主义的美学理想”来加以界定和统摄。在我看来,姚文元所表述的这些“美的形象”其根本所在乃是“美好之争”中的“好”,而不是“美”,也就是说,姚文元当时带入那场“美学大讨论”的,实际上已经不是美学与美学之争或审美与审美之争,而是“审美”与“审好”之争,是“美”“好”之争,可惜姚文元本人对此并无概念上的自觉意识和把握。
此处所谓的“好”并不排斥美,但是能够超越美,它的最终指向是人类追求群体性自由和解放这一“更高的原则”——在这个“更高的原则”之内,“美而且好”自然最好,但如果美而不好,则宁愿舍美而取好。当然,对于生来就已遭受生物遗传和社会教化之双重制约与围困的众人而言,这个实在太难。但是“好”从来都是难的,何况是如此之“好”——这个“好”的源头不是客观实在,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是个体或群体的自由意志;它的目标则是社会正义的现实化和普遍化,是由个人的、群体的主观努力而创造的社会现实和“第二自然”。
今天有很多人会认为,那时无论是与此相关的文艺创作,还是政治宣传,所呈现的那种比“美”更大的“好”皆属“虚构”,而非“事实”,乃与人性的本然相悖,是终究无效的历史瞬间之物。对此,我们可以用海德格尔在1937-1938年冬季讲座中说过的一句话予以回应:“保守,终将陷于历史的泥沼;只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达到历史的深度。革命并不是颠覆和破坏,而是一种起义,重新创造习俗,重新构造起源。因为源头并不属于开始,对起源的重构,决不是对更早出现的东西的拙劣模仿;重新创造的起源,完全是另外一个了。”我们还可以用蔡翔在讨论1949-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时的一句自白进行回应:“我的考察目的更多的在于这一时段的文学究竟提供了哪些想象,包括这些想象构成的观念形态。实际上,我更在乎的,或者说我认为文学主要提供的,恰恰在于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既是理论的,也是情感的,而我们总是根据某种观念来塑造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在这一意义上,文学总是‘有用’的。”须知,人之所以为人,根本就在人能够对其“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进行反动与超越,而许许多多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留给当代世界的可贵遗产之一,正是它们对这一“反动与超越”的叙述和想象——这些叙述和想象皆“事关未来的正义”。
纵观人类缤纷万象的等级化制度,几乎全部安装着三个核心部件——权、钱、美。当此三种部件被众人用以维护旧有等级结构或生产新的等级结构之时,“权”往往表现得最残暴,“钱”则最荒淫,而“美”最阴险。因此,这个世界如果真的能够创造和生成一种社会主义的好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种成功祛除了“权”和“钱”的社会支配性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成功祛除了“美”的社会支配性的生活方式。不妙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历史实践本身却既未能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成功祛除“权”和“钱”的社会支配地位,亦未能在精神分析学的层面成功祛除“美”的社会支配地位。因此无论是从“革命时代”的现实化程度来看,还是从“后革命时代”话语竞争力来看,众多社会主义文学作品对于能够超越“美”的“好”的想象也的的确确是“失败”了——它们最终未能在社会主义的生活内部“重新创造习俗,重新构造起源”。
如果说,“社会主义前三十年”在政治和经济层面虽然遭遇了种种失败,但经文革一役,它至少还在一定程度上勾起了中国人对于“权力垄断”的抗争意识,那么,在培养民众对“美的特权”的警惕和抗拒意识方面,却仍是收效甚微。追究起来,社会主义实践本身未能带给众人以普遍的“好”的生活无疑是极深的病根,无所栖居、无以销魂的“虚无”的人民从肉体到精神都更容易被“美”所召唤和吸引,关于这点,《锦灰堆与蔷薇花》可谓提供了一个极佳案例:
回到那个阳光刺眼的下午,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就在那个下午,我已发现新大陆。在那墙角的垃圾堆中,我看到了一个叫蝴蝶的女人,以及一个叫王人美的女人……这两个女人的美貌让我感到了心跳,简直不可思议,躺在锦灰堆里的女人……但只要翻开那堆肮脏的垃圾、发霉的杂志,这两个旧时女人依然光彩照人,呼之欲出,如夹在书中的蔷薇花瓣,它散发出幽香,她们似乎来自另一个国度。
“权”往往表现得最残暴,“钱”则最荒淫,而“美”最阴险
孔夫子所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之人性本然无疑也是重大因素,自有文明以来,人类对自身生物遗传的任何一种改写皆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从文学想象与叙述维度来看,当时许多作家所选择的某种共同的叙事路径也让人心生不满。例如,在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开篇,作者就为男主人公林震安排了一位“漂亮”的女主角赵慧文:
三月,天空中纷洒着似雨似雪的东西。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传达室的工人、复员荣军老吕微跛着脚走出,问明了那年轻人的来历后,连忙帮他搬下微湿的行李,又去把组织部的秘书赵慧文叫出来。赵慧文紧握着年轻人的两只手说:“我们等你好久了。”这个叫林震的年轻人,在小学教师支部的时候就与赵慧文认识。她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只是下眼皮上有着因疲倦而现出来的青色。她带林震到男宿舍,把行李放好、解开,把湿了的毡子晾上,再铺被褥。在她料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撩一撩自己的头发,正像那些能干而漂亮的女同志们一样。
对于这种近乎于1920-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之“革命加恋爱”的叙事路径,我们在此可将之界定为“好而且美”的社会主义理想化叙事。共产党人也爱美,社会主义“新人”也爱美,这都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导致人类文明史上的“美好之争”长久存在的原因恰恰就在于“好而且美”或“美而且好”的资源极度匮乏,这一匮乏并不会随着哪一种新共同体想象和实践的绽放而有丝毫缓解,因此,它也注定是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的超级难题。很显然,王蒙在创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对此并未有什么明确的问题意识和艺术考量。
再来看一处出现在曲波的《林海雪原》中的文本细节:
少剑波冒着越下越大的雪朵,走来这里,一进门,看见白茹正在酣睡,屋子暖暖的,白茹的脸是那样地红,闭阖着的眼缝下,睫毛显得格外长……她那美丽的脸腮更加润细,偶尔吮一吮红红的小嘴唇,腮上的酒窝微动中更加美丽。她在睡中也是满面笑容,她睡得是那样的幸福和安静。两只净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伸在炕沿上。
少剑波的心忽地一热,马上退了出来,脑子里的思欲顿时被这个美丽的小女兵所占领。二十三岁的少剑波还是第一次这样细致地思索着一个女孩子,而且此刻他对她的思索是什么力量也打不断似的。
以上文字,里面尽管有“她在睡中也是满面笑容,她睡得是那样的幸福和安静”这样的句子在暗示“好”(革命伦理)的主导地位,但是像“两只净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伸在炕沿上”这样的描写却使“美”可以随时随刻逸出“好”的领土之外,进而形成某种自足性,而后面的“此刻他对她的思索是什么力量也打不断似的”心理描写,则更是对“美”的这种自足性的强化。倘若再说得粗暴些,任何一件作品,当它对“美好之争”这一难题的自觉意识未曾得到有效呈现之时,其对“美”的表现就很容易在无形间造成一种毋庸置疑的“美”的独立性,而其叙事者对“美”的倚重也就很可能变成一种对“美”的无意识的供奉。因此,就算这种“好而且美”的理想化叙事在客观上也是一种对于“美好之争”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也是饱含风险。其唯一切实可贵之处,便是“美”的身边始终有个“好”在。
而当“美”越过“好”,越过善与恶的冲突,进而成为天然合法之物,乃至成为某种绝对目的,成为众人的宗教和神话之时,我们就在时间上皈依了1980年代。
①王小波:《〈怀疑三部曲〉总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②这三部小说分别对应于王小波所作“三大基本假设”中的“性爱”、“智慧”和“有趣”之维。
③可参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章《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中的相关讨论。
④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而言,在进入各种语文教材的众多作家当中,大概只有卡夫卡、鲁迅等极少数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对审美的等级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警惕。
⑤《荒诞不经的顽童齐泽克》,杜然编译,《经济观察报》,2004年10月27日。
⑥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第78回。
⑦见网络流行文本《这样密集的负能量段子,看起来实在是太爽了!》,作者未详。
⑧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或《论语·子罕第九》。
⑨人的内在美降格为外在美的附属,目的是为之服务、与之相配。
⑩见《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四集(《文艺报》编辑部编,作家出版社,1959年)和第六集(《新建设》编辑部编,作家出版社,1964年)。
(11)转引自陆兴华博客文章:《生态关怀导向全球文化大革命》,详见:http://hi.baidu.com/ lu060520/item/a7727d8681f64edfd0f8cd66。
(12)蔡翔:《事关未来的正义——“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上海文化》2010年第1期。
(13)我认为,这也正是人能够创造宗教而动物不能、人能够在其最幸福的时刻自杀而动物不能的原因所在。
(14)“钱”的问题暂且存而不论。
(15)吴亮:《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16)不分性别、物种、品类。
(17)多少年后,爱智如王小波者,也同样过于轻巧地避开了这一难题。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