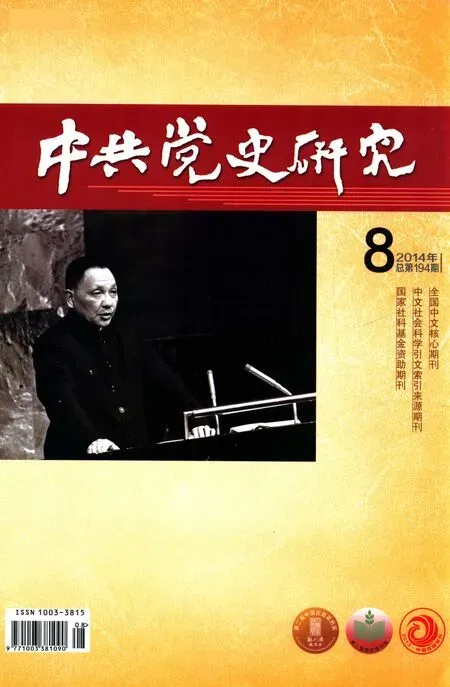新世纪国外邓小平研究特点分析*
成 龙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绩效更为显著,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更多的国外学者、人士加入到研究邓小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列,把邓小平研究再度推向高潮,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一、研究视野更加广阔,系统性、深刻性在增强
受历史条件和研究者认识水平的限制,上世纪的国外邓小平研究,还主要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具体政策及事件的描述性研究, “就事论事”的味道比较浓,视野相对狭小,理论性不强,系统而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并不多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外交流的扩大,国外学者、人士有更多便利条件展开深入研究,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更加注意挖掘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大大加强。
(一)从中外改革结果的对比中研究邓小平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成为一种世界性浪潮,既有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等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有里根、撒切尔等人领导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改革的绩效如何,孰优孰劣,在当时并不十分清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衰退,中国改革的效果日渐突出,一枝独秀,令世人刮目相看。追根溯源,这一切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密切相关。国外学者、人士纷纷回顾中国和其他国家改革的进程,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展开新的研究。意大利全球著名的财经专家洛丽塔·纳波利奥尼 (Loretta Napoleoni)的专著《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通过对全球改革,特别是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与里根、撒切尔领导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异同的比较,说明“中国模式成为最大赢家”“亚当·斯密为什么打不赢马克思”的道理。美国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沈大伟 (David L.Shambaugh)所写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通过对全球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苏改革背景、过程及其结果的详尽比较,以更为具体的事实说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改革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英国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所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其副标题是“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认为“现代性模式绝非只有一种,事实上有很多种”。他说:“西方希望总体上按照自身的标准——有时甚至是唯一标准——评估中国,尽管可以理解,但这是一种错误做法。”①〔英〕马丁·雅克著,张莉、刘曲译:《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30—331页。要求中国紧跟西方的脚步,拿这种思路来理解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这完全是一种幻觉”。此外,郑永年的《全球化与中国的国家转型》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宜兰·阿龙 (Ilan Alon)等的《中国治理:全球化与政治转型》 (Palgrave Macmillan,2009)、夏连特拉·D.夏尔马(Shalendra D.Sharma)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和印度》(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也都具有从全球改革视野研究邓小平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
(二)从以往研究的反思中研究邓小平
近年来,很多国外学者开始反思以往的研究,从思想的清理和批判中推进邓小平研究。由美国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高义 (Ezra F.Vogel)教授所写的《邓小平时代》,全书共计64.3万字,为完成这部巨著,作者先后查阅了中外与邓小平相关的档案和文献,拜访了邓小平的家人和好友,还前往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地,同与邓小平打过交道的中外政界要人及学术名家交谈,并对以往的中外文献展开辨析,以更为全面的资料反映了邓小平作为“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的形象,深入挖掘“邓小平时代”的开创过程及其特征。傅高义本人指出:尽管邓小平生前一再告诫写作者不要吹捧他,但在官方或半官方的历史写作中,褒扬英雄、贬抑他人的传统在中国依然流行。“在试图理解邓小平和他的时代的过程中,我阅读了赞扬他、批评他或者努力以学者的方式方法做研究的人所写的著作。”②〔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 《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viii页。这的确是作者力求客观的真情流露。大卫·兰普顿 (David Lampton)在《一脉相承的领导者:治理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一书的“导论”中指出: “在558次与中国领导者的会谈、案例研究、不可胜数的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剖析了自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向权力舞台以来中国极其特殊的发展过程,审视了中国国内政治、对外关系、自然的和人为灾害、军民关系以及中国人的谈判方式。”③David M.Lampton,Following the Leader:Ruling China,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p.1.这反映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基础和实证考察的功夫。其他学者如沈大伟、德里克、傅士卓、季塔连科等,也都与中国学术界、政界有着广泛的交流,他们多次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以旁观者的身份直陈自己的看法,反映出不断靠近客观、全面的学术追求。
平心而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人士所写的邓小平的传记并不少,如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所写的《邓小平》 (解放军出版社,1988)、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大卫·古德曼 (David S.G.Goodman)的《邓小平政治评传》(Routledge,1994)、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 (Richard Evans)的《邓小平传》 (Hamish Hamiltion,1994)、美国本杰明·扬 (Bengjamim Yang)的《邓小平政治评传》 (M.E.Sharpe,1997)等,尽管各有特色,从不同视角反映了邓小平的人生经历,但与傅高义、傅士卓、沈大伟等人的新作相比,其扎实性、厚重感已无法企及。
(三)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演变中研究邓小平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学者、人士更多地将邓小平置于中国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之中,从历史的比较中研究邓小平。由乔纳森·昂哥 (Jonathan Unger)主编的《中国政治的本质:从毛泽东到江泽民》 (M.E.Sharpe,2002)一书,共分两个部分,反映了中国政治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所实现的重大转型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承上启下的历史人物的作用。由傅士卓 (Joseph Fewsmith)主编的《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中国:从邓小平到胡锦涛》(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系统阐述了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的谈话、在中国再次掀起改革浪潮,以及江泽民和胡锦涛在邓小平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改革、深入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大卫·兰普顿的《一脉相承的领导者:治理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从国家治理体系视角论述了当代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脉相承的转变过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国外学者发表了一批专题论文和论著,如美国历史学家德里克 (Arif Dirlik)的《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法国经济学家让-克洛德·德洛奈 (Jean-Claude Delaunay)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法国著名左翼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 (Tony Andréani)的《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必然终结?》(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主编的《中国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等,从历史的视角重新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他们上世纪的研究相比,其思想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高度评价“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四)从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中研究邓小平
由邓小平开辟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未来前景如何?它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世纪之交,国外学者、人士都在思考这一问题。詹姆斯·凯基 (James Kynge)的《中国震撼世界:巨人的崛起与忧患的未来——及对美国的挑战》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6)、W.约翰·霍夫曼 (W.John Hoffmann)的《未来中国——世界最充满活力的地区》(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柏思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和贺尔林 (Bertel Heurlin)主编的《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位置:国际、地区和国内挑战》(RoutledgeCurzon,2002)、拉鲁·伊斯拉姆 (Nazrul Islam)主编的《中国复兴:问题及其未来》 (Palgrave Macmillan,2009)、赫伯特·S.叶 (Herbert S.Yee)主编的《中国的崛起:威胁还是机遇》(Routledge,2010)、威廉·A.卡拉汉 (William A.Callahan)的《中国梦:未来20种可能前景》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万明 (Wan Ming)的《中国模式与全球政治经济》 (Taylor and Francis,2014)等,都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一方面,国外学者、人士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驳斥“中国崩溃论”。W.约翰·霍夫曼指出:自80年代早期改革以来,有关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已有好多次,出现了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崩溃论”。尽管近来中国宏观经济改革的很多计划引起争议,但却没有哪个问题会导致中国崩溃。中国的适应能力以及影响变化的能力是无法估量的。①W.John Hoffmann,China into the Future: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0.另一方面,国外学者也表达了对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担忧,包括水资源问题、空气问题、土壤问题、能源问题、交通运输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腐败问题等。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教授华金·贝尔特兰·安托林认为,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已经达到了与30年前有天壤之别的新高度。但革命的年轻时代已经远去,成熟期的财富造成了不公正和腐败,现在迫切需要收复信心和重新平衡分配财富。①《革命与改革:新中国的六十华诞》,中国政策观察网 (西班牙)2009年9月6日,转引自中华网2009年9 月 9 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9-09/09/content_18494140.htm。
二、研究问题更加集中,充分肯定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上世纪的国外邓小平研究,虽然也有人很早就注意并使用了“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的概念。如早在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就发文指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②《世界风云人物邓小平》,《时代周刊》(美国)1979年第1期,转引自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页。。又如戴维·W.张 (David Wen-Wei Chang)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 (Palgrave Macmillan,1989)一书认为,中国正在搞的是一种“混合模式”。但总体来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尚未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概念。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发表《北京共识》以来,几乎所有的国外邓小平研究都与“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相联系,对邓小平历史贡献的评价,也是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框架下加以展开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超越资本主义视界的前景”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绝大多数国外学者、人士充分肯定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高度评价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 (John Naisbitt)明确指出:尽管中国在经济上拥抱“黑猫白猫”,尽管实施了改革开放,但是中国政治“猫”的“颜色”从未改变,西方式的民主也从未在中国兴起。“中国并不是一个慢慢脱去一层层共产主义外衣,悄悄滑入西方国家所准备好的资本主义外套的国家。”③〔美〕约翰·奈斯比特、 〔德〕多丽丝·奈斯比特著,魏平译:《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第4页。法国汉学家魏柳南 (Lionel Vairon)指出: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针对“文化大革命”追随者的极左意识形态以及新“封建主义”的批评声此起彼伏,但邓小平及其支持者们仍掌控着局势。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政,苏联政治风云突变,1991年苏联解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从而清醒地认识到,片面、僵化地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行不通。④〔法〕魏柳南著,王宝泉、叶寅晶译: 《中国的威胁?》,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德里克指出:“中国的领导人从未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奉”,与以往相比,“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似乎更加清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遗产,是“毛泽东未竟事业的延续”,这种社会主义具有“超越资本主义视界的前景”,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为资本主义寻找一种替代的持久冲动”。即使在中国的经济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之后,这种替代仍然具有生命力。⑤〔美〕德里克著,吕增奎译:《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美国美中友协主席大卫·W.尤因针对所谓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论”指出:设想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变相维护”,中共正在“努力将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失败后,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渡过了其最黑暗的时期。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如果它得到巩固)将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人类在21世纪最好、最切实的希望”⑥〔美〕大卫·W.尤因著,周艳辉译:《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争论》,《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2期。。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天儿慧 (Satoshi Amako)针对邓小平理论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指出:“邓小平确实从三个意义上超越了毛泽东。一是毛泽东相对拘泥于‘社会主义’说法,强调过度贫困,明确阐明‘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从正面肯定了追求‘富裕’。并且提出,不论好坏都要解放人们的‘欲望’,大大促进社会的活性化发展。二是把中国从割离于国际社会、自我封锁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增强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第三,与毛泽东的个人化领导方式不同,邓小平至少从形式上实行了‘众意达成’,并为后继者主动让路,做到逐渐改变个人化领导。”①〔日〕天儿慧著,范力译: 《日本人眼里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二)邓小平的改革哲学及战略完全不同于“华盛顿共识”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这是新世纪以来国外学者特别关注的带有神秘色彩的问题。雷默认为,“北京共识”与邓小平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变化如此之快,以致没有多少人,甚至本国人都赶不上形势的社会的产物,它也是由这样一个社会决定的。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②〔美〕乔舒亚·库珀·雷默: 《北京共识》,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7页。。奈斯比特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制定的共同目标”③〔美〕约翰·奈斯比特、 〔德〕多丽丝·奈斯比特著,魏平译:《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第1页。。中国的新社会依赖于“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洛丽塔·纳波利奥尼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一是源于能够调动民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而里根、撒切尔政府则在改革中远离民众、排斥非政府组织。二是西方人与邓小平的哲学和指导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相距甚远。如果说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们都被汹涌的洪水卷走了。三是邓小平当初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改造的目的在于改革体制、挽救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但里根与撒切尔“只是拆毁旧体系,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整体的建设计划”。④〔意〕洛丽塔·纳波利奥尼著,孙豫宁译:《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95、205、206页。
印度经济学家阿嘎瓦拉 (Ramgopal Agarwala)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源于邓小平时代领导人所采取的改革哲学和战略。就改革哲学而言,主要有两点:一是借鉴外部经验,但拒绝“华盛顿教义”;二是让“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同时进行的方式生机勃勃。就改革战略而言,中国独特的改革战略主要可以分成五类:采取渐进的方式方法避免“休克疗法”;根据现实情况仔细安排改革的步骤;通过过渡阶段而逐步适应改革,尽量减少社会成本;通过竞争而不是改变所有权来提高经济效率;重视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⑤〔印〕阿嘎瓦拉著,陶治国译:《中国的崛起:威胁还是机遇?》,山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59、62、63页。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波波夫 (Vladimir Popov)认为,1979年之后,中国之所以能实现良好运转,主要原因包括:首先,中国改革完全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一揽子政策——中国循序渐进而不是立即取消价格管制,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实施有力的产业政策和高外汇储备下的低估汇率政策;其次,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领导中国期间的成就——强大的国家制度体系、高效的政府、改善的基础设施和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等,为1979年之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再次,与苏联“休克疗法”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不同,中国渐进改革方式没有毁坏前述的所有成就;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至1949年短暂的西化尝试夭折之后,至今从未真正脱离得以使其保持低度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整体主义制度⑥〔俄〕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广阔视野下中国与俄罗斯的转型比较》,王新颖主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38页。。
沈大伟强调中共学习和自我调适机制的作用,指出:自19世纪70年代“自强运动”以来的100多年里,中国一直是一种“拿来主义”文化,即从世界其他国家寻找合适的模式和思想,引进并嫁接到本土的文化根茎上,创造出一种“兼收并蓄型国家”。中共发现它必须处在一个永恒的循环中: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在这个循环中,每一次改革都会带来某些后果 (有些是预料之中,有些则是意料之外),接下来又导致高速和进一步的改革。对中共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①〔美〕沈大伟著,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7、5页。百年来主要是传播和吸收西方优秀文明成果,谓之“拿来主义”显然是简单化了。
(三)中国的持续发展“改变了全球发展理念”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还是威胁了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外学者、人士充分肯定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的贡献。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罗斯·加诺特回顾中国自邓小平以来持续发展的经验,认为中国发展“改变了全球发展理念”。中国的成功大大促进了可持续的、快速的、国际化的现代经济发展。“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大量的经验教训来取得好的成果。”②〔澳〕罗斯·加诺特:《中国30年改革与经济发展经验》,王新颖主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第83—86页。季塔连科指出:20世纪,在最深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战略退却的条件下,中共承担了根据时代要求和新历史机遇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邓小平提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预防了社会主义被挤出历史舞台,对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模式提供了社会主义的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印度以及一系列发展中国家一起,为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各种文明的建设性对话积极行动,促进了另一种立场的确立,以替代在全盘西化进程中文明冲突的方针,以多极多色的世界来替代单极世界。③〔俄〕季塔连科:《论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远东问题》(俄罗斯)2004年第5期。
德里克认为,正是邓小平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当今“全球工厂”的战略中心,生产出全球消费的商品,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还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经济发展造就了一个活跃于中国和世界的新企业家阶层;中国社会不再只是欧美文化和产品的接收者,而是全球新奇商品的消费者和文化产品的出口大国。④〔美〕德里克著,吕增奎译:《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世界银行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哈拉斯认为:“中国的成功将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所助益,而不是造成伤害。”中国每年4000亿美元的进口额中有45%来自发展中国家,而进口贸易额在2003年又增加了550亿美元。中国对基础商品的需求十分强烈,从而抬高了粮食作物和铝、钢、铜、棉花、橡胶等工业原材料的价格。对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靠这些产品的收入谋生的农民来说,全球性的价格飙升来得正是时候,它扭转了几十年来价格不断下跌的局面。⑤Homi Kharas,“Lifting All Boats:Why China’s Great Leap is Good for the World’s Poor”,Foreign Policy,January-February,2005.
马丁·雅克指出,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实施的是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战略。崛起为世界主要大国的中国将提供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和范例。它“包含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后殖民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共产党政权、高度成熟的治国方略、儒家传统”。⑥〔英〕马丁·雅克著,张莉、刘曲译:《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第315页。“中国的崛起将意味着她的历史、文化、语言、价值、机制和企业将会逐渐影响全世界。如果说自1978年以来,世界带给中国的改变为要大大多于中国带给世界的改变,那么这种进程将很快发生逆转——中国带给世界的改变将远远多于世界带给中国的改变。”⑦〔英〕马丁·雅克著,张莉、刘曲译:《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第XXV页。克里斯托夫·A.麦克那尼指出:“中国的崛起无疑是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事件之一。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巨大成功,它与其他政治经济体的相互影响,将形成全球性的价值、制度和政策,因而重建国际政治经济。”①Christopher A.McNally,“Sino-Capitalism:China’s Reemerg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World Politics,Vol.64,No.4,October,2012.
(四)邓小平“完成了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
国外学者、人士回顾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遭受巨大痛苦的历史,高度评价邓小平为实现民族复兴作出的贡献。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②〔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第641页。。魏柳南指出,在近代以来的一个世纪中,中国人民曾寄望于孙中山一度构想的社会,但“民主革命之父”转化中国的愿望在顽固派的抵制下破灭了。之后迎来了毛泽东,他是一位毫不妥协且纯粹的革命家,但其在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制度过分强调集中,缺乏民主。“直到邓小平时期中国才迎来理性和实事求是主义的大获全胜,邓小平无疑是中国人自19世纪以来就苦苦等待的救世主。”③〔法〕魏柳南著,王宝泉、叶寅晶译:《中国的威胁?》,第11页。
曾任德国驻华大使的康拉德·赛茨 (Konrad Seitz)指出:“邓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使占人类1/4的人发生了巨大变化。拿破仑的预言在多次失败后好像就要成为现实:‘如果中国这头睡狮醒来的话,大地将颤抖’。”④〔德〕康拉德·赛茨著,许文敏、李卡宁译:《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191页。基辛格高度评价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邓小平南方视察几乎产生了神话般的意义,他的讲话成了中国后来20年政治经济政策的蓝本。甚至今天,中国的广告牌上还展示着邓小平南方视察时的形象和话语,包括他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⑤〔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 《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433页。俄罗斯A.B.维 诺 格 拉 多 夫 (Владимир Αлексеевич Виноградов)认为,中国模式是 “中国文明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功绩在于,它使由外界影响和革命活动带来的现代与传统二者之间的冲突转向统一。“此次改革第一次成功地突破了文明传统的框架,承认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传统文化背景下,首先在经济领域,允许个人发挥主动性。”⑥〔俄〕A.B.维诺格拉多夫: 《中国文明发展的新阶段:起源与超越》,王新颖主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第55页。
三、思维方式更为理性,挑战问题依然尖锐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深入,国外学者、人士在思维方式上有了较大转变,表现出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深刻认同。然而,某些已于上世纪提出并反复争论的问题,依然是争论的焦点。
(一)新自由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策略,国外就有人提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论调,认为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措施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必然要为资本主义所取代。近年来,虽然有更多的人开始认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但仍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成功完全是因为采取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策略。如戈登·瑞丁 (Gordon Redding)和迈克尔·A.韦奇(Michael A.Witt)所著《中国资本主义的未来:选择与机遇》(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一书,承认中国模式是“另一个奇迹”,但作者的所有论述是以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为前提。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在台湾出版了一本题为《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八旗文化出版公司,2010)的著作。他说:“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经验恰恰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国经验的支持。”①《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对话陈志武》,《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8期。同样地,斯蒂格利茨 (Joseph E.Stiglitz)等人把中国视为新自由主义成功的典范。尼克尔斯·拉迪 (Nicholas Lardy)对新自由主义适用于中国的这一核心原则作了概括。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强劲势头,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多年来经济改革积累的功效。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现在已经似乎决定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样重要的是,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竞争,不仅在制造业,而且在建筑业和服务业方面也是如此。“市场决定物价的深入开展以及竞争性的市场对资源的分配效率方面有了改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示范国——中国的形象,至少目前是如此”。②〔美〕马丁·哈特-兰兹伯格、保罗·伯克特著,庄俊举编译:《解读中国模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2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姓“社”还是姓“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曾经针对人们的议论,从多个视角进行了论述,反复强调市场与计划都是手段,本质上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邓小平的论述,打开了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视界。但在国外邓小平研究中,姓“资”姓“社”的争论并未停止。关键在于,坚持这种观点的人,依然受教条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把计划和公有化程度的大小作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借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挫折和失误,把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历史不可超越的唯一选择,以当今资本主义的繁荣掩盖资本主义曾经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掩盖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存在的压迫、剥削和不平等;未能看到新自由主义的推行给世界造成的经济社会危机;未能看到中国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一面,把中国借鉴资本主义等同于全盘照搬资本主义。
(二)实用主义还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上世纪80年代,国外就有人认为,邓小平所讲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三个有利于论”“实事求是论”,都是实用主义“有用就是真理”“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的另一种说法,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表现。进入新世纪以来,海贝勒、基辛格等人仍然坚持这种观点。海贝勒认为,中共的领导体制在经历了“转型”“巩固”两个阶段后,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 “意识形态已逐渐被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用主义所取代”④〔德〕海贝勒:《中国是否可视为一种发展模式?》,俞可平等主编: 《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基辛格也认为,邓小平的主要手法就是把“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到“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高度,利用毛泽东正统思想理论中的只言片语,放弃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照邓小平的说法,毛泽东是位实用主义者。”⑤〔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 《论中国》,第327页。言下之意,邓小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篡改和利用毛泽东的思想。实际上,国外所谓邓小平的“实用主义”,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认为相对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而言,邓小平理论变得更加务实、灵活,更加强调通过试验和探索寻求制度和政策的合理性。如巴里·诺顿所说:“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谨慎和实用主义的特征。灵活性和试验性的方法同‘渐进主义’结合起来,这通常通过援引一句中国的俗语—— ‘摸着石头过河’——反映出来。”⑥Barry Naughton,“Singularity and Replicability in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China Analysis,January,2009.洛丽塔·纳波利奥尼指出,在邓小平上台之后,“对意识形态的超越使实用主义的精神在中国人心中得到了重生,为中国实现伟大的一跃而奠定了基础……实用主义的回归使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对市场的重要性有了清醒的认识。但是无论怎样,中国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厨师还是那厨师,只是在尝试新菜”①〔意〕洛丽塔·纳波利奥尼著,孙豫宁译:《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第66、67页。。在这里,“实用主义”并无贬损之意,并不意味着邓小平背离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正是对邓小平强调务实精神的褒扬。
实用主义是美国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潮,比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早了整一个世纪。1998年,在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基辛格曾将其概括为“美国精神”。一方面,邓小平理论和实用主义都包含着突破教条主义束缚、大胆试验、大胆探索、大胆创新、求实务实、效率至上等精神,以及对规律和个人能动精神的重视。正因为这样,美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而中国则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迅速赶上欧亚强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邓小平理论又与实用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其一,在世界观上,实用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而是一个折中主义的大杂烩,有时甚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而邓小平理论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新哲学。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其二,在真理观上,实用主义过分强调真理的“效用”,忘记了真理要揭示客观规律的最终目的,而邓小平理论不仅强调真理的“效用”,更强调真理对客观规律的反映,坚持主观和客观、相对和绝对的统一。其三,在利益观上,实用主义反映了美国走向现代化的要求,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进行资本扩张、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主张,而邓小平理论则代表的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尽快发展生产力、迅速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三)狭隘民族主义还是胸怀世界的爱国主义
在国外邓小平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带有民族主义性质,而在邓小平时代则变得更加赤裸裸,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一起成为中共取得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近年来,这种观点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出现的频率有增无减。美国《新闻周刊》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指出:“随着经济的进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得更加强烈。拉住一位上海雅皮士,你会发现他——一名对台湾、日本和美国充满恶意的民族主义者。”③Fareed Zakaria,“Is China the World’s Next Superpower?”,Newsweek,May 9,2005.维尼·沃-蓝普·兰姆认为:“随着共产主义及其信条的死亡,共产党的权威迫切需要一种凝聚力以维护其巨大而复杂的国家统一。宣传爱国主义(在很多方面与民族主义或仇恨外国人的心理相重合)或许对于促进干部团结统一的目标是一种简易的途径,这也同时服务于党的合法性。此外,北京也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视为解除全球化毒害及失稳效应的解毒剂。”④Willy Wo-Lap Lam,Chinese Politics in the Hu Jintao Era:New Leaders,New Challenges,M.E.Sharpe,2006,p.213.彼得·海斯·格利思 (Peter Hays Gries)的《中国的新民族主义》(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和克里斯托夫·R.胡斯 (Christopher R.Hughes)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Routledge,2006),系统分析了中国民族主义自邓小平以来“不断强化”的过程、实质及其国内外影响。
尽管民族主义具有形形色色的外表,但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把本民族或本国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压倒一切价值的一种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主张将国际主义置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上,但并不反对民族独立和主权,认为“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62页。。邓小平本人在英国培格曼公司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序言”中曾满怀深情地说:“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①《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正是本着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邓小平一方面主张把国家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反对别国无理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主动承担国际义务,从世界发展中把握中国发展的制高点。 “民族主义论”知其一,不知其二,带有片面性和主观猜测性。
(四)“新权威主义”还是“中国特色民主主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冈部达味、毛理和子就提出,中国在毛泽东之后,走了一条“新权威主义”的治国路线。近年来,在探索中国成功经验的过程中,相当一些人强调“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例如,巴里·诺顿指出,中国经验的核心在于对传统威权主义体制的变革,可称为“威权主义升级模式”。其要点在于:第一,国家主权最为重要,它是国家实行国内经济改革而无需屈从于外部控制或者受到国际上不稳定形势影响的根本的前提条件;第二,维持对经济核心部门的控制,同时全面实现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第三,创建一种协商机制,同时限制公民社会和反对团体的自主性;第四,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发展,格外重视电信系统的建立,甚至允许一个适度的、非整体的“博客世界”存在;第五,增进国际经济和政治联系。②Barry Naughton,“Singularity and Replicability in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China Analysis,January,2009.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王正旭(Zhengxu Wang)提出了“混合型政权”(hybrid regime)的概念。 “混合型”的意思是“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严格的权威”,而是一种“半权威主义,竞争性权威主义,竞选型权威主义,自由化了的独裁政府,半民主,伪民主,部分民主,粗俗民主,竞选民主,以及没有民主的竞选。他们是‘带形容词的民主’或‘带形容词的权威主义’”③SuJian Guo,ed.,China’s“Peaceful Rise”in the 21st Century,Ashgate,2006,p.118.。
马克思主义无疑承认权威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页。但是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权威仅仅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新权威主义”传递的是西方人的政治价值观。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带有极权主义性质,邓小平以来的改革确实使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总体依然处于“半集权” “半专制”状态。这种判断以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为标准,要求中国实行像美国一样的民主。这不仅违背了人类社会组织方式和民主方式的多样性,而且是极其不现实的想法。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研究部主任李成指出的:“长期以来,很多美国人不仅将美国式民主制度看作是全球民主制度的典范,而且还相信,民主制度的实现并不会太费周折。例如,很多人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独裁政权,民主制度便会在这些地方自动生根发芽。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简单,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需要一些前提条件,但是却很少有美国人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些条件对于‘得天独厚’的美国来说从来都不成为问题。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不顺利,恰恰是因为缺乏这些前提条件。在这方面,美国人确实缺乏一定的敏感性。”⑤闫健:《对话李成:中国的政治改革,国际环境及未来》,《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