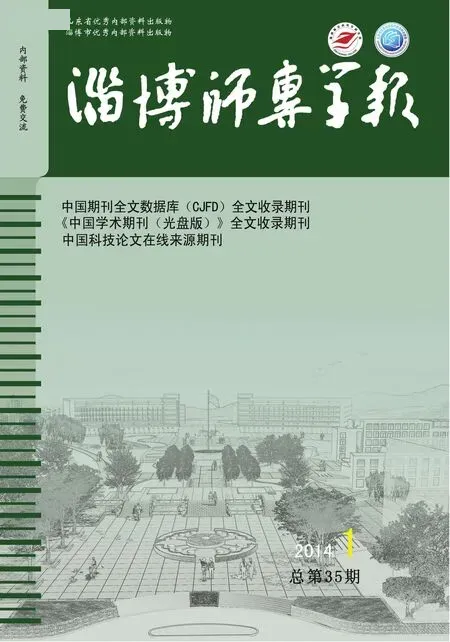从《白鹿洞书院揭示》看朱熹的学规理念
王 彬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朱熹的《白鹿洞书院书院揭示》在教育史上是一份重要文献,历来研究者都给予了很高的重视,踵其事而增其华,但对于《白鹿洞书院揭示》背后的内容,尚有众多阐微发隐之处。隐微之处,集中在朱熹为学规所作的“跋”。现将“跋”中相关部分征引如下:
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于上,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
据朱熹所言,在《白鹿洞书院书院揭示》之前,已经有了学规,但其待学者为“浅”,因而引发了朱熹的不满。那么,这里自然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一、待学者为“浅”的学规是什么样子的?二、“浅”的反义是“深”,《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不是“深”的体现?三、“深”与“浅”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朱熹的学规理念。
一、《丽泽书院学规》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年)知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时撰就的,以淳熙六年为“标点”,我们将观察的目光聚焦到之前的学规上。毫无疑问,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前早已产生了官学学规,如仁宗时期的《京兆府小学规》,但官学学规和书院学规属于不同的体系。我们暂且不将官学学规纳入考察的范围之内,我们要考察的是淳熙六年之前的是书院学规。朱熹说的“近世于学有规”之“规”,指的也应是书院学规,否则缺少比较的必要性。
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前,最有名的当是吕祖谦为丽泽书院撰写的《丽泽书院学规》(包括《乾道四年(1168)九月规约》《乾道五年(1169)规约》)。我们可以将《丽泽书院学规》视为“近世于学有规”之“规”的代表,察看其特点如何。由于原文较长,限于篇幅,我们将部分内容援引如下:
乾道四年(1168)九月规约
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饰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同志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
凡预此集者,闻善相告,闻过相警,患难相恤,游居必以齿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尔汝。
旧所从师,岁时往来,道路相遇,无废旧礼。
毋得品藻长上优劣,訾毁外人文字。
毋得干谒、投献、请托。
毋得互相品题,高自标置,妄分清浊。
语毋亵、毋谀、毋妄、毋杂。
毋狎非类。
毋亲鄙事。
乾道五年(1169)规约
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
肄业当有常,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一岁无过百日,过百日者同志共摈之。
怠惰苟且,虽漫应课程而全疏略无叙者,同志共摈之。
不修士检,乡论不齿者,同志共摈之。
通读《丽泽书院学规》,我们可以发现充斥其间的语气是非常强硬的,最明显的表现是“毋”字很多,这是郑重的“警告”,让学生不要犯错,否则结果很严重,是“除其籍”,是“同志共摈之”。
《丽泽书院学规》中强烈的禁令语气来源于哪里呢?此处,我们也许可以看一看官学学规了。官学的产生远远在书院之先,书院是自唐代才开始兴起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书院学规借鉴官学学规,这也是顺理成章的推测。官学学规旨在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很少涉及教育理想,只是一些冰冷的规范,如论者所言:“官学学规详订管理规条,惯用消极的禁令惩戒,具有权威和惩罚性质。”[1]我们谨举上文提到的《京兆府小学规》为例,部分援引,以佐证我们的论述:
一、应生徒入小学竝须先见教授,投家状并本家尊属保状。
一、教授每日讲说经书三两纸,授诸生所诵经书、文句、音义,题所学字样,出所课诗赋题目,撰所对诗句,择所记故事。
一、应生徒有过犯竝量事大小形罚。年十五以下,行扑挞之法;年十五以上,罚钱充学内公用,仍令学长上簿学官、教授通押。
行止踰违。盗博斗讼。不告出入。毁弃书籍。画书牕壁。损坏器物。互相往来。课试不了。戏玩喧哗。(按:此即“过犯”)
由上面征引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官学学规明显具有强迫性。其强迫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必须做什么”,如“应生徒”入学必须先见教授,投递保状,这是入学手续的规定;二是“不能做什么”,一旦违规,就会受到惩处,如“行止踰违”便要依据年龄的大小“行罚”。
毋庸讳言,官学学规的两种强迫性特点,《丽泽书院学规》皆具备,只是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偏重了“不能做什么”,即“毋”要如何如何。这种强烈的“禁惩”意味,应该便是“近世于学有规”之“规”的主要特点。我们如此推论,还有一点根据,试看《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另一句话:
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
朱熹的这句话就是针对“近世”学规而发的,“规矩禁防”正对应着《丽泽书院学规》中的“毋”要怎样怎样。
二、《白鹿洞书院揭示》
我们说朱熹对当时既有的书院学规不满意,才在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之时亲自起草了《白鹿洞书院揭示》,这种说法只是就本文的视域而言的。事实上,朱熹对当时的整个教育似乎都不甚满意,尤其是以功名利禄为导向的科举。如“跋”中所言:“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这是对当时科举的不满,但此种不满不在本文的视域之内,故而置之不论。我们仅从《白鹿洞书院揭示》与之前的学规对比中,考察朱熹的学规理念。现将《白鹿洞书院揭示》全文征引如下,以便比异: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通览上文,我们不难发现,《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绝无一点“禁惩”的语气,没有一个“毋”字,全是教人如何做,而不是警告学生不要做什么。至于所教的内容,则体现了朱熹的教育理念,包括教育内容、为学次序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全是“善”的方面。可以这样说,《白鹿洞书院揭示》像一个忠厚长者对后生学子的谆谆劝告,与威吓性的禁令迥异其趣。
顺便一提的是,《白鹿洞书院揭示》开启了后世书院“劝善”式学规的传统,一直备受重视,与之相比,《丽泽书院学规》则落寞了。
三、“深”“浅”之辨
上文中,我们以《丽泽书院学规》为“近世于学有规”之“规”的代表,经过分析,可见其主要特点是“禁惩”意味浓厚,体现在学规之文上,便是“毋”字较多。我们可以将这种特点再次提炼,概括为“警恶”,即对不良行为(恶)的警告,是对学生行为的最低要求。如果连这个最低要求也达不到,只能受到惩罚。《白鹿洞书院揭示》则与之相反,其主要内容是劝人为善,与“警恶”相对。我们可以概括为“劝善”,是对学生行为的高要求。
朱熹说“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警恶”是否便为“浅”,“劝善”是否便为“深”?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深”“浅”二字在另一处的用法。欧阳修《问进士策第三首》有语曰:
夫礼以治民而乐以和之,德义仁恩长养涵泽,此三代之所以深于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浅者尔。
欧阳修的话是论“治民”的,大致是说“治民”当以“德”“礼”为主要途径,如此才可谓“深于民者”;如果徒以“政”“刑”治理民众,“此其浅尔”。这种“治民”的观念其实是儒家的老传统,如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如果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治民”观念的原因,就应该与儒家对人性本善的认识有关了。此处姑不具论,且承上文。古人的用语毕竟与我们有膈膜,让我们换而言之,以便更为晓畅明白。“德”“礼”其实就是我们“以德治国”中的“德”,“政”“刑”则是我们“以法治国”中的“法”。“法”的规范,实则为人之行为的最低要求;而“德”之为德,其实是对人的行为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感召,它并不是强制性的。再联系欧阳修的话,我们便可以知道何者为“深”、何者为“浅”。在“治民”上,以道德的力量向民众发出感召,劝其为善,这是“深”的;仅仅凭借法律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警其恶念,这是“浅”的。
“治民”上的“深”与“浅”能否与学规上的“深”与“浅”相提并论,这是我们接着要讨论的问题。学规作为规范,作用的对象是学生。宋代与此前的魏晋南北朝及唐五代相比,一个重要的突破便是士族门阀的势力式微了。如果说唐代的文化属于贵族文化,宋代的文化则明显的具有“平民化”倾向。通过逐渐规范的科举制度,宋代的“四民”——士农工商——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出身于农、工、商人的子弟皆可以通过科举变身为“士大夫”。宋代入学的门槛也很低,在校的学生来源于各个阶层。如果对宋代的学生身份做一个界定,他们应该属于“士”,或者确切地说,属于准“士”。“士”为“四民”之首,其地位是可想而知的。按照儒家的观念(即上文欧阳修为代表的观念),“治民”尚且要以“德”为主,何况是对待准“士”呢!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记载,宋神宗熙宁六年,“置诸路学官,更新学制有司立为约束,过于繁密”。刘挚上疏曰:
学校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从出,非行法之所。虽群居众散,帅而齐之,不可无法,亦有礼义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长者之道,则下必以君子、长者之行而应乎上。若以小人、犬豕遇之,彼将以小人、犬豕自为,而况以此行与学校之间乎!
在这段引文中,刘挚将“治民”(“治天下”其实就是“治民”)与学校如何对待学生联系起来,并进行类比,这可以佐证我们将“治民”上的“深”与“浅”与学规上的“深”与“浅”相提并论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刘挚的话更道出了朱熹为什么提倡“劝善”式的学规。在儒者看来,以“法”治人,是视人为“小人”“犬豕”(这个用词当然有点偏激),是对人格的不尊重;在推行教化的学校里,更不能用“法”来对待学生。这其中内含的深意也便是孔子所说的“民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的区别。
由此可见,学规如何对待学生,可以说是“治民”思想的一种微观体现。将儒家的“治民”思想一以贯之到学规中去,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学规待学者,如果仅仅“警恶”,自然为“浅”;只有劝其为善,才是“深”的。
在以上的行文中,我们一直使用“深”“浅”二字,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这样贴合原意,也是因为这二字属于“文言”,在“白话”当中很难直接找到对应词。如果非得予以训释,我们可以这样解说:“深”与“浅”皆用来形容对待人或事的态度,“深”里面包含有尊重、礼貌的意思,近似于“厚待”;“浅”则与“深”相反,可谓“薄待”。
四、余论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对朱熹的学规理念应该有所理解了。朱熹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士,他不提倡待学者“浅”、以“警恶”为主的学规,因而草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圭臬。如果凭此而断言朱熹反对“警恶”式的学规,恐怕又犯了一个错误,而这一点,往往为人们忽视。事实上,朱熹并不否认“警恶”式学规的作用,根据还是《白鹿洞书院揭示》“跋”中的一句话,只不过这句话不太引人注目:
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为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
引文中的“此言”是指《白鹿洞书院揭示》,“彼”就是指“近世于学有规”的“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学生的行为太过出格,必要的惩罚也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以《丽泽书院学规》为代表的“警恶”式学规绝对不能省略。
乍一看来,朱熹对待“警恶”式学规的态度似乎是矛盾的,他明明不满意于待学者为“浅”的学规,为何又言其不可“弃”呢?仔细想来,这其实又是不矛盾的,朱熹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劝善”式学规缺乏、“警恶”式学规独存的状况而发的。明白这一点,我们方可以对朱熹的学规理念有一个完整的表述:学规当以“劝善”为主,“警恶”为辅;主辅不可倒置,但亦不能缺少其一。
在上文第三部分中,我们说朱熹的学规理念其实是和儒家的“治民”思想一以贯之的。关于“主”与“辅”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儒家“治民”思想中找到类似的表述,如王安石《策问·六》中有语曰:
述诗书传记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泽后世,必曰礼乐云,若政与刑,乃其助尔。
“助”即“辅”,再参之以上引欧阳修的话,我们可以想见朱熹在学规上对“主”与“辅”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为了进一步佐证论点,让我们再引魏了翁《跋朱吕学规》中的一段话:
白鹿之规五,温温乎先民之徽言;丽泽之规三,凛凛乎后学之大戒也,至矣备矣。(按:“丽泽之规三”即《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中的二“凡”加《乾道五年规约》中的一“凡”)
魏了翁是南宋理学家,他说《白鹿洞书院揭示》“温温乎”(即“劝善”)而《丽泽书院学规》“凛凛乎”(即“警恶”),但只有二学规相结合,才“至矣备矣”。由此可见,二者不可缺一,只是要分清以谁为主,以谁为辅。朱熹对此分得很清楚。
概而言之,《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前的学规是“警恶”式的,与儒家基本的“治民”思想相背离;朱熹对待学者为“浅”的学规产生不满,撰就了以“劝善”为主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但朱熹也不否认“浅”之为规的作用;“深”与“浅”之间,以“深”为主,以“浅”为辅。“深”与“浅”的结合,是朱熹学规理念的完整表述。
[1]吴小玮.中国古代学校的三种“学规传统”[J].大学教育科学,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