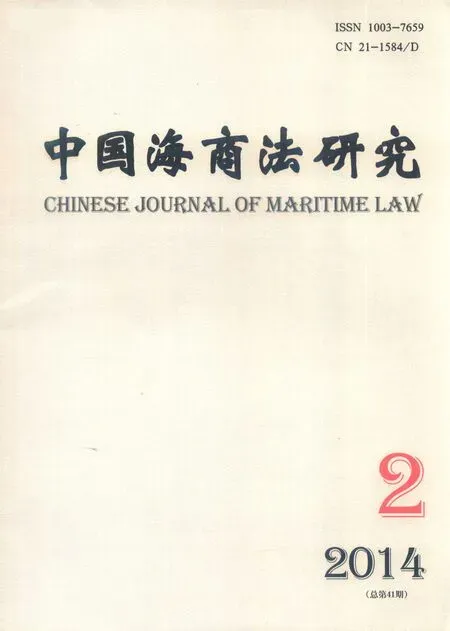时运渐具、时机未成:《海洋基本法》热的冷思考
周 江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重庆 401120)
近年来中国在岛礁归属、南海断续线性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划界争端、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巡航及远洋执法等海洋法律问题上与海洋相邻国家屡生龃龉。面对诸种逐权乱象、维权危局,有学者呼吁:中国《海洋基本法》的颁布应提上日程。[1]
然而,恰是在二百年前,萨维尼(Savigny)与蒂博(Thibaut)关于立法与法学使命的激烈论战便已警示了基于政治因素及对法律的独特的科学性存在盲目自信而立法的危害。可资为证的是,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因立法意识过于超前,立法内容过分简约,或对于法律运行环境了解不足而导致立法效果有限的例子确曾存在。因此,对于倡议中的《海洋基本法》这样一部效力位阶较高、涵盖范围极广的法典,立法的必要性是否成立,立法的时机是否成熟,是摆在中国学者及立法者面前不能回避的问题。
考察当前中国《海洋基本法》立法问题之研究成果,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论证立法的必要性时极富激情,规划其具体文本内容则语焉不详。就笔者目力所及,认为必须立法的各界人士大致基于以下理由:健全中国海洋立法、执法体系,确立海洋摩擦中的维权依据之必要;维护海洋和平与安全、发展海洋经济之必需;提高国民海洋意识、促进海洋法律研究之必备;顺应国际海洋法发展潮流之必然。
不可否认,上述理由确实揭示了中国在落实“海洋强国”战略中已经面临或者可能面临的诸多问题,但制定《海洋基本法》是否便为应对的必由之途?笔者拟就上述疑问展开探讨。
一、《海洋基本法》的立法内容未达共识
一如前述,目前有关《海洋基本法》的论著中,申明立法之必要性和可行性者较多,对于《海洋基本法》所应当涵盖的基本内容则缺少细致的探讨。其间虽有认为《海洋基本法》应当对中国海洋安全、海洋产业、管辖外海域及国际海洋事务作出具体规定者,[2]亦不乏主张《海洋基本法》内容重点是政策性的宣言者。[3]综观既有成果,除了对海洋事务进行综合管理此一条以外,有关《海洋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具体内容、与现有立法的衔接、应对国际事务的挑战等方面缺少充分讨论,达成共识更是无从谈起。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今世界海洋大国、强国非常重视以法律作为海洋管理与维权的依据,但就可以查证的资料而言,多数国家并没有类似于《海洋基本法》的综合型海洋立法,国内学界述及的相关立法例,亦不过英国、加拿大、日本、越南等寥寥数国。
英国作为从18世纪以来称雄海洋的传统海洋国家,于2009年开始施行《海洋及沿近海使用管理法》(Marine and Coastal Access Act,2009)。该法是一部典型的海洋世纪时期的海洋综合管理法,包括了325个条文,分为11个部分,基本内容包括:海洋管理组织、专属经济区、海洋规划、海洋许可证的审核发放、海洋生态保护、近海渔业管理、海洋执法、海岸利用等。[4]其在宏观层面对英国的海洋事务进行了周延性的总结,在微观层面也对海洋法的具体实施做出了详细规定。加拿大《海洋法》(Oceans Act,1996)共有109条,其内容主要包括:加拿大可管辖的各类海域、海洋管理战略以及海洋管理机构的权责与功能。[5]越南《海洋法》(luât Biên Viêt Nam,2013)含7章55条,分别就越南管辖海洋区的范围、海洋区内的活动、海洋经济、海洋巡逻和稽查以及违反该法的处理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6]日本的《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法,2007)由40条法律条文组成,主要内容包括立法目的、基本计划、基本政策的实施、海洋管理机构等内容。[7]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海洋基本法》和《海洋构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海洋構築物等に係る安全水域の設定等に関する法律,2007)同时生效。这两部法律确立了日本海洋的新战略,拓展了日本管辖海域的空间范围。可以说,日本的《海洋基本法》的基本内容,是对本国政府与邻国日渐尖锐的海洋摩擦与竞争中的立场、策略和实施路径的总结。
总的来说,英国、加拿大、日本、越南四国的海洋法虽然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内部结构、外部形式、语言表达及详略程度等立法技术层面有所不同,但都涉及国家海洋战略、海洋基本政策与制度、管辖范围与管辖权、海洋管理机构及其职权等内容。在摩擦海域的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海洋执法等问题上,尤以日本和越南为代表,其国内海洋法足以构成海洋管理机构日后行动的明确的法律依据。
因此,无论立法体例如何设计、立法程序如何设置,一国海洋法律关系当中的基本法理和至关重要的法律制度都是《海洋基本法》应当包括的不可或缺之内核。如果上述认识可以成立,对中国而言,《海洋基本法》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海洋战略与基本海洋规划、海洋管辖权的范围与实施机构、与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海洋问题的立场与应对、国际海洋事务等。
关于《海洋基本法》应当具备的上述核心内容,目前尚未有高层的政治决心与明确表态,亦难言已由立法机构、学界、媒体、民众广泛参与、充分讨论进而形成共识。因此,中国《海洋基本法》的文本起草还无从谈起。缺失了核心内容、仅将现有的宣言、纲要、规划中的一些宣示性内容拼凑成典,除了在本已庞杂的中国海洋法体系中增加一个新文本以外,再难有所作为。
二、《海洋基本法》立法非改进现行海洋法体系的必由路径
诉诸《海洋基本法》并非改进整个海洋法体系的不二法门。对此,笔者将结合中国涉海法律文本结构及现行海洋执法体系存在的问题略作分析。
(一)法律文本结构
根据既有研究成果的总结,中国现有海洋法文本结构当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法层级与内容不完整。纵向而言,中国宪法中缺少针对海洋的明文规定,在宪法和各单行法之间缺少一个统领海洋事业的基本法律。横向而论,各单行法内容不能覆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各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8]85其中海洋安全规划、海洋基本战略等国内海洋事务以及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海洋事务在国内立法中的空白尤为突出。
第二,部分法律规则陈旧、重叠甚或冲突。中国现行的海洋法律大多为针对某一领域或某一行业的专项立法。法律、法规和规章相互交织,立法层次和立法部门繁多,并且很多法律生效于20世纪80年代,规定的制度多有落后,与新近立法也多有冲突。[9]对于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出现的新问题、新政策、新方法,更是鲜有立法文件予以体现。
第三,法律体系过于庞杂。目前中国参加和签署的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领域的公约有五十多个。国内涉海立法在二十余年间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十余部法律、二十余个法规。另外,中国将大量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和实施细则规定在各种条例、办法之中。[10]如《关于进一步推进海域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海域使用测量管理办法》和《海洋生物质量监测技术规程》等。
但是,上述问题的客观存在并不必然得出需要制定《海洋基本法》的结论。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没有明确写明“海洋”二字的“缺憾”并不影响中国现有的整个海洋法律体系的合宪性。这种“缺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亦不会对海洋法律实践产生具体的影响。仅仅为了弥补形式上的“缺憾”就大动干戈地制定一部海洋法典,其合理性何在?
其次,制定一部新的法典以统帅原有的法律体系,确为应对部分立法内容陈旧、重复、冲突问题的可选之道。但是对于上文所言的庞杂的中国海洋法律体系而言,制定新法所要付出的各部门协调以及旧法清理成本不容小觑。而就法律的重复规定和法律规范的冲突而言,法律修正案的解决方式则因涉及主体较少、级别较低、时间较短而优势显明。可见,制定新法既非唯一验方亦非最佳选项。
最后,通过增加一部新法来解决法律体系庞杂的问题,其本身就是有违逻辑的,除非这部新法能够取代旧有的单行海洋法。然而,目前对于中国海洋基本法的讨论都是基于与旧有法律体系兼容而非取而代之的意义上进行的。因此,通过制定《海洋基本法》来解决中国现有海洋立法体系问题的理由同样难以立足。
(二)海洋执法体系
中国海洋执法体系被指至少存在三大缺陷。
第一,分散型执法体制导致重复建设、执法效率低下以及协调不畅。[9]过去的“诸龙治海”格局在人员和装备配备等方面,存在重复建设和执法资源的浪费。更突出的问题出现在协同执法方面。农业部、公安部、国土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的跨部门协调本属不易;基层边防所、沿海县乡政府和事业单位与上级主管单位的自下而上的协调更加困难;国务院搜救中心属于国务院相关部门和中央军委联席会议的办事机构,权威有余但稳定性不足。
第二,远洋执法能力建设力有不逮。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政府对于管辖海域的执法活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离岸较远的管辖海域遭到周边国家的觊觎、抢占和抢先开发,当中国主张国际法上的合法权利时必然与已经形成的各方利益集团产生矛盾,极端的表现方式就是摩擦和对峙。
第三,海军在海洋执法当中机制缺位、地位未明。“海军在执法层面上缺乏国内法的明确授权,遇有海上涉外侵权事件发生,只能站在具体涉海行政执法部门背后辅助执法。”[11]
面对上述海洋执法体系的种种不足,《海洋基本法》同样并非解决问题之唯一策略。
针对分散型执法主体的弊端,建设统一的综合性海洋执法体系的确是海洋大国普遍的做法。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国家都建立了类似美国的“海岸警备队”的综合海洋执法主体。但是综合型海洋执法体系的构建并不必然需要制定《海洋基本法》。其典型反例就是在海岸警备队建设最为成功的美国也没有这样一部法典。而且,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综合海洋执法体系改革亦是在没有《海洋基本法》的情况下进行的。
针对远洋执法能力建设的不足,主要依靠资金投入、人员配备等行政手段解决。立法并非与之直接相关。而海军在海洋执法当中的法律地位与执法机制问题,历来属于海洋执法当中需要谨慎考虑的内容。为避免加剧海洋摩擦与对峙、维护海洋和平与安全,中国海洋法律体系中对海军参与海洋执法的情形做严格限定——必须经其他海洋执法主体委托,不能主动参与。在这一问题上,现行立法并无不妥之处。因此,通过制定《海洋基本法》来弥补中国现有海洋执法体系不足的理由亦为不妥。
三、提高海洋法律意识及促进海洋法律研究与《海洋基本法》并无直接关系
(一)海洋法律意识
中国国民海洋意识的淡薄早已得诸多方面证据之昭明。一项针对中国国民海洋意识的调查显示,有46.9%的受访者认为海洋权益的威胁来自内部,特别是中国国民海洋意识的淡薄。[8]86近年来沿海地区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不断炸礁、填海连岛,导致人为因素灭失的岛礁达400多个。[12]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有学者指出“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很重视海洋立法,用海洋立法来提升国民的海洋意识,增强海防和海权的观念”,[1]因而推进海洋基本法的制定有利于提升国民的海洋意识。[13]
细究之下,上述论证当中存在着论证对象及逻辑关系的混淆。就论证对象而言,海洋立法固然能够提升国民的海洋意识,但是此处的“海洋立法”不能必然等同于《海洋基本法》的立法。就逻辑关系来说,推进海洋基本法的制定固然有利于提升国民的海洋意识,但海洋意识的提高确未必只能依靠制定《海洋基本法》这种方法。充分条件的成立,并不必然导致必要条件同样成立。
从海洋意识的内涵来说,符合当代世界发展潮流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海洋意识应当包括国家管辖海域以外资源开发的观念、资源宝库观念、全球通道观念、海洋健康观念、海上安全观念等内容。制定海洋基本法与这些观念的形成之间的关联实非直接、密切、非此不可。在没有制定《海洋基本法》的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国民仍然有着强烈的海洋意识。因此,提高国民海洋意识不能构成制定《海洋基本法》之必要性依据。
(二)海洋法律研究
也有学者主张通过《海洋基本法》的制定提升海洋问题的研究水平。[14]持此主张的学者指出:海洋基本法制定的调研、审议和立法的过程,可以吸引一大批人员参与海洋问题的研究工作,可以进一步培育和壮大中国研究和管理海洋问题的人才队伍。同时,也可利用此机会,增设海洋教育和海洋问题研究机构以及海洋问题研究基金会等组织机构,以全面提升海洋研究水平。
就逻辑关系而言,此种主张片面地强调立法对海洋法律研究的推动作用,而忽略了立法也应当建立在充分的海洋法律研究之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多数立法实践来看,一部新法的诞生的确可以推动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热潮。但是立法必须以相当程度的理论成熟为基础。况且中国海洋法律问题的热潮已然形成,全国多个海洋管理机构、科研院所、财团法人致力于海洋法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中国法学会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中海洋法领域的题目频获立项。在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当中,以“海洋法”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得到的相关法律文献达数千条。以英文撰写的中国海洋法的文章也在国外重要的期刊中发表。[15]可以说,海洋法研究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领域。问题的关键在于现有的研究成果是否足以支撑立法,即立法准备工作及可行性论证是否充分。
四、《海洋基本法》立法非世界海洋法发展潮流
所谓潮流,需喻社会发展变动之趋势,乃是洞见者登高一呼而应者云集。而对于《海洋基本法》或《海洋法》进行法典式立法活动,除三面环海的加拿大、海洋法历史悠久的不列颠、意图通过国内法固化侵占成果的越南和地处东北亚的野心家日本以外,海上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和俄罗斯、曾经有海上马车夫美誉的荷兰、殖民主义时期海上霸主西班牙与葡萄牙、众多欧洲临海国家以及中国周边的朝鲜、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等国都没有进行类似的立法活动。因此,制定《海洋基本法》本身并非在当下就已经是或一定是国际海洋法发展潮流。
维护海洋和平与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发展海洋经济方是国际海洋法发展的潮流。《联合国宪章》当中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宗旨及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当然地覆盖海洋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巴黎非战公约》以及《圣莫雷海战守则》也一再明确维护海洋和平与安全是首要原则,应当尽一切努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因此,有必要讨论的问题应当是:制定《海洋基本法》是否能够维护海洋和平与安全?海洋和平与安全是否必须要通过制定《海洋基本法》来维护?
显而易见的是,即使一国制定了《海洋基本法》,也未必能够维护海洋和平与安全。关于此,日本的实践可资为例。日本将海岸警备队建设、海岛及人工构筑物等敏感的法律问题写入法律条文中,并以执行国内法为由不断与周边国家发生摩擦和对峙。可以说,日本的《海洋基本法》恰与维护海洋和平与安全的潮流格格不入,其立法成果及执法措施几可谓逆国际海洋法发展的潮流而动。因此,不设前提、不限定具体内容的立法未是必顺应国际海洋法发展的潮流的。而海洋和平与安全也未必能够通过一个冲动而缺乏长远、细致思考的国内立法行为而得到保障。
此外,发展海洋经济、开发海洋资源应是国际海洋法又一核心命题。随着陆地资源日趋枯竭,海洋的经济价值越发为全世界所看重。在南海等许多海洋问题上,经济利益始终是事态发展的关键推手。以可预测和持续性的方式公平合理地分配海洋经济利益是国际海洋法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近年来也不断地在海洋经济方面进行改革和探索,“蓝色海洋经济圈”、“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等国家级战略先后试水,“滨海新区”、“横琴经济特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等海洋经济开发实践接踵而至。在没有《海洋基本法》这样一部统帅性的法律的前提下,中国的海洋经济建设仍然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发展海洋经济在不同的海洋区域、不同的沿海地方、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正处在探索阶段的中国海洋经济建设,不宜用效力位阶如此之高的法典去约束,应当以单行法律或法规、规章的形式进行摸索和试验。相对成熟的实践经验总结是在法典当中涵盖海洋经济行政管理制度的基础。而现行的海域使用权及海域使用管理制度以及其他海洋经济行政管理制度虽难免有不如意之处,却绝非病入膏肓、非大破大立不可。
五、《海洋基本法》立法时机难言成熟
目前,主张制定国家海洋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的学者认为,无论是从政治因素还是从立法技术上来说,中国都应当用开创性的思维和纵览东西方法律文明的智识制定《海洋基本法》。
一则,就立法的政治因素试作推敲。不难发现,高层虽然有海洋基本战略的讲话、规划,但是对钓鱼岛、南海断续线、大陆架划界等海洋敏感问题如何最终解决,缺乏明确表态。高层相关的表态仍然比较抽象,缺少可操作性制度衔接或者有意不操作、不实施。这样的政治表态体现在立法中只能是基本原则或者是序言,具体的规则内容很难说已经有了高层的政治共识和明确支持。反例仍然是美国,从发动全球海洋圈地运动的《杜鲁门公告》开始,美国的历任总统发表的讲话、公告及推动的法案都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有明确的授权和预算支持。然而美国至今也没有制定《海洋基本法》或者《海洋法》这样的法典。
二则,就立法基础尤其是民意基础再作揣摩。正如许多支持《海洋基本法》立法的学者所言,中国晚近立法多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式立法。在海洋法领域,考虑到海洋环境的复杂与特殊、海洋开发所必需的巨额投入,照搬此前已有的政府主导式立法,使立法超前于民意基础似乎无可厚非。然,此种论断只有在适当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笔者认为此种前提可以有两种:第一,国内海洋实践迫切需要立法且民意热切期盼之时,或者,第二,虽多数民众不甚了解,但本国整体海洋技术相对领先且沿海民众海洋开发实践相对成熟。中国目前的整体海洋技术难言领先,沿海民众在海洋开发与利用方面也鲜有独特而成熟的实践经验。此外,《海洋基本法》与中国相当比例的内陆民众的经济社会生活不发生密切的联系。除了朴素的国家民族感情以外,民众对《海洋基本法》缺少了解,也没有经济上的必要性去支持、推动。而前文所引证的众多海洋意识淡薄的证据,本身也证明了民意基础的缺乏。学界亦是如此。尽管有同仁热情高炽地倡议立法,却并没有带来相对成熟的立法内容及其合理性的讨论。建构主义哲学观认为今日之行为建构未来之世界。然而今日中国的智力成果尚难使高层下定决心。中国需要的是治海之策,而非治海之吁请。因此,在海洋技术、海洋实践、海洋民意、海洋立法技术均未具备的前提下,片面强调立法机构的能动性,片面强调海洋法独立于海洋实践的科学性,难免有过分乐观之虞。
综上所述,各种因素决定了中国践行“海洋强国”战略的当务之急,实非仓促地诉诸《海洋基本法》这一宏大立法来彰显对海洋的重视。笔者以为,在当下阶段更应关注的并且更具现实意义的工作可以映射至如下两个方面。
就学术研究而言,可以考虑将围绕海洋所发生的国家间关系、行政关系、刑事关系和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纳入一个作为整体的“海法”(law at sea),[16]并在这一体系之下,经由学界、媒体、民众广泛参与及充分讨论,形成有关《海洋基本法》立法内容的共识,再以此共识为基础,推动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
就立法实践而言,结合目前中国管辖海域摩擦与对峙频发的态势,探定当前亟须立法的基本内容:第一,为军事力量参与海上执法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规定启动军事力量参与海上执法的职权归属和程序,为军事力量参与海上执法的行为方式划定法律边界;第二,为整合资源和力量,构建综合性海上执法平台提供法律基础。
六、结语
回首再申:诚然,以现有的基础制定一部十几条的原则性、宣示性的文本并非难事,且先例比比皆是。若如此,则此类文本不应当冠以《海洋基本法》之名,因其并非中国几代海洋法人殚精竭虑所追求的那部法典。
[1]陈小菁.海洋基本法应尽快走上立法轨道[N].解放军报,2012-03-14(6).CHEN Xiao-jing.The legislation procedure of Ocean Basic Law should be in motion as early as possible[N].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aily,2012-03-14(6).(in Chinese)
[2]于宜法,马英杰,薛桂芳,郭院.制定《海洋基本法》初探[J].东岳论丛,2010(8).YU Yi-fa,MA Ying-jie,XUE Gui-fang,GUO Yuan.Preliminary study on enactment of Ocean Basic Law[J].Dongyue Tribune,2012(8).(in Chinese)
[3]金永明.黄岩岛事件呼唤中国海洋基本法[N].中国海洋报,2012-05-11(A4).JIN Yong-ming.Huangyan Island Incident calls for Chinese Ocean Basic Law[N].China Ocean News,2012-05-11(A4).(in Chinese)
[4]Marine and Coastal Access Act 2009[EB/OL].[2013-12-29].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9/23/contents.
[5]Oceans Act(S.C.1996,c.31)[EB/OL].[2013-12-29].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O-2.4/index.html.
[6]Quôc hôi thông qua luât Biên Viêt Nam[EB/OL].(2012-06-22)[2013-12-29].http://vietnamnet.vn/vn/chinh-tri/77375/quochoi-thong-qua-luat-bien-viet-nam.html.Congress passed Vietnamese Law of the Sea[EB/OL].(2012-06-22)[2013-12-29].http://vietnamnet.vn/vn/chinh-tri/77375/quoc-hoi-thong-qua-luat-bien-viet-nam.html.(in Vietnamese)
[7]日本《海洋基本法》(中译本)[J].庄玉友,译.金永明,校.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08(1):128-133.Japanese Ocean Basic Law(in Chinese)[J].translated by ZHUANG Yu-you.proofread by JIN Yong-ming.China Oceans Law Review,2008(1):128-133.(in Chinese)
[8]邢广梅,刘子玮,刘君然,陈雪松,刘晓博.试论制定我国《海洋基本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2(1).XING Guang-mei,LIU Zi-wei,LIU Jun-ran,CHEN Xue-song,LIU Xiao-bo.On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the legislation of Chinese Ocean Basic Law[J].Journal of Xi’an Politics Institute of PLA,2012(1).(in Chinese)
[9]高之国,辛崇阳.制定我国海洋基本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下)[N].中国海洋报,2010-11-09(A2).GAO Zhi-guo,XIN Chong-yang.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legislation of Chinese Ocean Basic Law(Ⅱ)[N].China Ocean News,2010-11-09(A2).(in Chinese)
[10]许维安.我国海洋法体系的缺陷与对策[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8(1):128-133.XU Wei-an.Defec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legal system of law of the sea[J].Ocea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2008(1):128-133.(in Chinese)
[11]刘斌.借助法律解决南海争端,军方专家力推中国《海洋基本法》[N].南方周末,2011-06-30(B11).LIU Bin.In order to settl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with resort to law,military experts put the enactment of Chinese Ocean Basic Law in the first place[N].Southern Weekly,2011-06-30(B11).(in Chinese)
[12]曹瑞林.海洋世纪呼唤海洋基本法[N].解放军报,2011-03-07(05).CAO Rui-lin.The century of ocean calls for Ocean Basic Law[N].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aily,2011-03-07(05).(in Chinese)
[13]陈丽平.代表建议制定海洋基本法[N].法制日报,2012-01-06(003).CHEN Li-ping.NPC deputies proposed the legislation of Ocean Basic Law[N].Legal Daily,2012-01-06(003).(in Chinese)
[14]金永明.中国制定海洋基本法的若干思考[J].探索与争鸣,2011(10):21-22.JIN Yong-ming.Reflections on the legislation of Chinese Ocean Basic Law[J].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2011(10):21-22.(in Chinese)
[15]GAO Zhi-guo,JIA Bing-bing.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history,status,and implications[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3(1):98-124.
[16]司玉琢.面向海洋世纪 确立海法研究体系[J].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2):1-2.SI Yu-zhuo.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search system of law at sea based on the century of ocean[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aw,2010(2):1-2.(in Chinese)